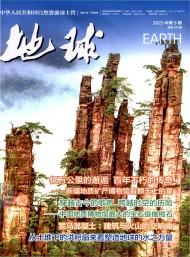地球科學論文范文
時間:2023-04-06 08:47:3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地球科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保護地蔬菜;病蟲害防治;科學用藥技術
溫室、暖棚、拱棚等保護設施內蔬菜產量高、品質好、生產時間長,但病蟲害亦多。現代科學技術為蔬菜病蟲害的防治提供了多種有效的農藥,但在實際生產中,用同樣的農藥治同樣的病蟲害,有些人反映效果好,有些人則說效果差,同樣的方法同樣的濃度,在這個棚效果十分理想,在另一個棚里施用后則出現藥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用藥方法的正確與否。
保護地內溫濕度可以人為控制。溫室封閉后便于高溫或煙霧滅菌滅蟲,對防治病蟲十分便利,效果亦佳。但如何依照蔬菜的生物學特性和當時的生態環境,靈活掌握用藥品種、時間、濃度和方法,達到既控制病蟲害,又不影響植株正常生長,使產量達到最高,關鍵是科學合理用藥。保護地蔬菜防治病蟲害在考慮采用農業措施如起壟、排濕和生物防治的前提下,再考慮綜合防治及化學農藥防治,化學防治要講究科學用藥。
1按植株生長發育規律用藥
蔬菜作物的生長發育要在一定的溫濕度條件下,才能順利完成。全天光合產物的70%是上午合成的,須配合較高溫度,下午光合作用速度下降,養分輸送運轉,溫度以低為宜,需比上午低5~20℃左右,夜間生理代謝也不是全停止,前半夜光合產物需配合適當的溫度(18℃左右),如果運輸不順利,光合產物停留在葉子上,葉子便會過于肥厚,果實產量下降。植物后半夜休息,生理活動是呼吸,這是一個消耗養分的過程,溫度宜低些,使養分消耗減少,以利于提高產量。如黃瓜為12℃即可。藥物對作物的勞作(光合作用及營養正常運轉)有抑制和破壞作用,所以在晴天中午光合作用旺盛期和前半夜營養運轉旺盛期盡可能少用藥或不用藥,特別對瓜果類作物尤其不要用藥。
種子均為植株衰老采收,多系菌源,下種時宜用熱水浸泡或拌藥消毒。幼苗期高濕低溫系染病環境,加之保護地設施內連年種菜,土壤雜菌多,播種前必須進行消毒。早春定植后多濕高溫低,以防細菌性病害為主;高桿蔓生作物中后期通風不良,高濕高溫,此時應以防治真菌性病害為主;立夏育苗或延秋栽培多高溫干旱,以防治病毒病為先。目前保護地生產上,黃瓜以防治霜霉病,西葫蘆、番茄以防治病毒病,茄子、辣椒以防治黃萎病、疫病(死秧),韭菜以防治灰霉病,芹菜以防治葉斑病為主[1]。
2按發病規律用藥
施藥前要正確診斷發生的病害或可能發生的病害,勿將非侵染性病害認定為侵染性病害。如溫室黃瓜、早春甘藍等蔬菜,因前半夜溫度低,在中下部光合作用旺盛的葉片上,因“倉庫”爆滿,營養不能運走,致使葉片增厚老化,出現生理障礙,葉片上出現圓形點,如同疥蛤蟆身上的點子。對這類生理病害,打藥無濟于事。再如黃瓜生長點萎縮、中部葉緣發黃是缺水引起的非侵染性生理病癥,與細菌、真菌、病毒無關,自然打藥也不起作用。治蟲時需先確定危害蔬菜的主要昆蟲,然后選擇專一性配廣譜性的殺蟲劑,進行有目的的綜合防治,切勿圖省事、省時,將不能混用的農藥胡亂配合防治病蟲害。勿用殺蟲劑治病,勿用殺菌劑滅蟲[2]。
細菌性病害發病的環境多系高濕低溫有病原菌;真菌性病蟲害發病環境是高溫中濕(15~22℃)有病原菌;病毒性病害是在高溫干旱環境、作物上有蟲傷或機械損傷傷口時才發病,人為地控制一兩個發病條件均可減輕和防止病蟲害發生,無發病條件作物有類似癥狀者,應考慮其他因素。所以,噴藥前必須辨清病蟲害的特征、發生活動特性和農藥的防治對象、性質,做到對癥下藥。
3按藥效適時用藥
防治農藥多是保護性藥劑,要提前施用,以防為主,要在病害發生前或剛發生時噴藥[3]。滅蟲農藥在扣棚后定植前或漚制糞肥期施用,消滅地下害蟲,蔬菜生長期用毒性較大的殺蟲劑易造成藥害,毒性小、用量少則效果差;地上部害蟲在羽化期或著果前施用,成齡害蟲抗藥性強,也有一定的回避能力,防效差。又如對番茄鉆心蟲施藥過晚,蟲已鉆入果實內,很難消滅。
配藥前先看準農藥有效期,新出廠的農藥,濃度以最大限度對水,臨近失效期的農藥以最低限度對水,濃度不要過大,如普力克、乙磷鋁,否則效果反而差,且浪費藥劑,易燒傷植株。另外,需認準農藥的有效成分,勿把含有效成分80%的農藥,按40%濃度配制噴灑,也不要把含量5%的農藥當做50%對水施用。農藥以單一品種施用較為適宜,也可將2種農藥混用,如作用對象相同則用量減半,如作用對象不相同則按最低濃度噴施,且以內吸收性和融殺性混用為好。
4按溫濕度大小適時適法噴藥
保護地內溫度高低懸殊大,濕度大,噴藥時掌握溫度在20℃左右、葉片無露水時進行,藥液易著葉面,水分迅速蒸騰后,藥液形成藥膜,防病效果好,維持時間長[4]。梅雨連陰天或剛澆水后勿在下午至傍晚噴藥,因此時作物葉子大量吐水,易沖洗藥液而失效(保護地內露水70%以上系葉片通過氣孔吐水所致),高溫季節(溫度超過30℃)不用藥,否則葉片易受害老化。溫高、干燥、苗弱,用藥要少。一般感病或發生蟲害應連噴2次,間隔5~7d,陰雨天只要溫度在20℃以上就可噴藥,以葉背面噴藥為重,鈣化老葉少噴,以保護中小新葉為主。噴霧量以葉面著藥為準,勿過量而使葉上流液,否則葉面著藥少,浪費藥劑,效果差。個別植株感病,以涂抹病處為宜;病害嚴重時,以噴、熏結合為適,防病管理中以降濕為主,盡量減少噴藥量和次數,既可達到控制病蟲害的發生與危害,又能節約藥劑,生產無公害蔬菜,創造蔬菜最佳的生長發育環境,獲得高產和高效。
5參考文獻
[1]毛榮姿,夏建平.無公害蔬菜生產病蟲害防治技術[J].現代農業科技,2009(20):178,181.
[2]張霞.溫室蔬菜病蟲為害的特點及綜合防治技術[J].內蒙古農業科技,2006(S1):27-28,31.
篇2
關鍵詞:澳大利亞 科技政策 政策研究 科技戰略 ARC
Abstract: As a Commonwealth R&D funding agency,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iving advice on national S&T policy and its coordination while it makes an effort to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amines policy research and strategic planning in ARC and their effects in-depth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n innov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learn lessons for R&D management of our government, especially during this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time of China.
Keywords: Australian S&T Policy; Policy Research; Strategic Planning; ARC
科技政策與戰略是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科技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同的國家或機構從不同時期國家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需求出發,制定與其總體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政策與戰略,構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體制的基石。20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新變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以及知識經濟的崛起,許多國家的科技政策與戰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各國的科技、經濟、社會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科技政策與戰略的重要性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其制定過程也逐步規范化與制度化。了解這些制度與方法,對于我國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特別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和“十一五”科技發展戰略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相比,澳大利亞的研究與發展(R&D)規模相對較小,但其研究領域又呈現出往往是科技大國才會具有的多樣性,更接近于如我國等發展中大國可能達到的狀況,因此,其R&D管理應當是我們關注的研究對象,而國內現有的研究多以美國、日本等科技大國為主,對澳大利亞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近年來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澳聯邦政府在推動科技為解決國家社會經濟重大問題服務以及在科技管理部門推行績效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我國轉型時期科技體制改革也有相似之處,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中的許多方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國內關于澳大利亞的研究多針對其政策戰略的具體內容,缺乏對其制定過程及方法的分析。本文試圖以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作為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的范例,把對ARC的分析置于澳國家科技政策與戰略演變的背景下,深入考察其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過程及其產生的作用與影響,提示對我國R&D管理的借鑒與啟示意義。
1 ARC的改革與發展
1.1 澳大利亞的科技政策與R&D管理體制
澳大利亞具有較強大的科學基礎,在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的世界舞臺上表現活躍。迄今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亞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SCI統計數據表明,1993-1997年澳研究人員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占世界論文總數的2.7%,平均每百萬人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高于美國、德國和法國等科研規模更大的國家。[ ]“澳大利亞的科學基礎比許多國家更具多樣性,……在地球和環境科學、生物學和醫藥研究方面特別具有優勢”[ ],這與澳大利亞獨特的自然資源狀況有關。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說明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間關系的指標——專利對科學論文的引證——顯示,在如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等知識密集的高技術行業,澳大利亞專利對化學、物理學、工程學和生物學等學科的高質量論文有很高的引用率,而且,這些專利所引用的澳大利亞論文中有95%產生于公共資金資助的研究。[ ]
澳大利亞政府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資助科學研究,但直到70年代初以前,聯邦政府沒有統一的R&D或科技預算,沒有全國性的科學咨詢機構,沒有一個負責制定科技政策或協調全國研究工作的政府部門。[ ]進入7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來,聯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認為創新對國家的繁榮至關重要,科技政策逐步從對科學研究的自由放任轉變為強調科技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大了R&D的投入和支出水平。澳大利亞的R&D支出從20世紀80年代起保持快速增長,到90年代中期R&D占GDP的比例已接近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1996-1997澳大利亞R&D的總支出為87億澳元,約占GDP的1.65%,其中公共部門的R&D支出占GDP的0.85%,在OECD國家中排第四位。[ ]近年來,隨著政府進一步鼓勵公共部門R&D成果的商業化和私人部門向R&D投資,產業界的R&D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續上升,政府及公共部門對R&D的支持也在加大,但公共資金支持的主要領域仍然是基礎研究。
澳大利亞的R&D管理體制呈現由聯邦政府起主導作用的多元化格局,政府通過投資和政策引導等方式,在推動科學發展的同時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繁榮,其活動范圍覆蓋了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實驗開發乃至商業化等R&D的各種類型。目前,澳聯邦政府資助R&D活動的主要部門和機構有聯邦教育、科學與培訓部(DEST)、國防科學技術組織(DSTO)、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理事會(NHMRC)、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澳大利亞核科學技術組織(ANSTO)等,其中只有ARC是以支持醫學研究之外的所有學科的科學研究和研究培訓為主的資助機構。
1.2 ARC的成立與發展
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亞研究撥款委員會(Australian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縮寫為ARGC),負責資助大學的高水平科研,澳全國范圍的同行評議系統就是自那時起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如前所述,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的科技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開始質疑使用公共資金的科學研究到底為納稅人貢獻了什么,要求研究人員走出“象牙塔”,參與更廣泛的競爭,為解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服務。[ ]ARC于1988年依據《就業、教育與培訓法(1988)》成立,取代ARGC,成為國家就業、教育與培訓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縮寫為NBEET)的組成部分,與原機構相比其職能也得到了拓展,負責資助與管理大學和大學以外的科學研究及其教育計劃及項目,完成NBEET和聯邦就業、教育與培訓部交付的任務,以及就國家優先研究領域或研究政策的協調等問題向NBEET提供咨詢。
然而,在ARC成立近10年后,對其整體運行狀況開展的評估發現,ARC在履行資助管理和政策咨詢這兩項職能時不能很好地協調——ARC本身更多地關注資助活動的管理,而負責聽取其政策建議的直接主管和決策部門NBEET又對高等教育部門之外的研究政策興趣不大。[ ]因此,為了使ARC更好地履行職責,同時也是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驗,聯邦國會于2001年3月通過了《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法案(2001)》(簡稱為ARC法案),決定同年7月起,ARC成為聯邦就業、教育與培訓部(2001年11月26日更名為教育、科學與培訓部)下一個法定的獨立機構,擁有自己獨立的決策部門——ARC委員會,在資助活動及其管理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在國家政策和戰略制定中也將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1.3 ARC法案及其影響
根據ARC法案,ARC的作用是對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和科學政策提出建議,并推動開展最高水平的、有益于澳大利亞全社會的科學研究與研究培訓。在研究資助方面,ARC繼續支持除了臨床醫學和牙醫研究以外所有學科領域內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科學研究和研究培訓;在政策與戰略方面,除了ARC原有的就國家優先研究領域和研究政策協調提出建議之外,政府于1999年12月的白皮書《知識與創新:研究與研究培訓的政策聲明》,向ARC提出的3項重點要求也仍然適用于作為獨立機構的ARC:幫助形成與保持學術界和產業界、政府組織和國際社會的有效聯系;促進公眾理解科學及其對社會的貢獻;比較澳大利亞與其他研究活躍的國家的科研績效,并評估國家對科研投資的回報。[ ]
新法案實施后,ARC最大的變化是在其組織結構、資助框架和管理模式等幾方面。在組織結構方面,作為獨立法定機構的ARC有著自己的決策部門ARC委員會,成員由14位來自有關政府部門、聯邦研究資助機構、學術界、產業界和相關社會各界代表組成,ARC的日常工作由具有卓越科研水平和突出研究管理能力的首席執行官(CEO)負責。ARC下設三個部門,即:學科與項目管理、政策與計劃協調以及合作部門。其中最大的是學科與項目管理部門,分為6個學科群(生物科學與生物技術;工程學與環境科學;人文學科與創造性藝術;數學、信息與通訊科學;物理學、化學與地球科學;社會、行為與經濟科學),每個學科與項目管理機構都有一個專家咨詢委員會,負責對研究申請進行同行評議。[ ]
在資助框架的變化方面,新的ARC將原有支持項目、人員、設備和機構的資助類型進行重新整合,避免資助活動中的分散與重復。新的資助框架稱為“國家競爭性資助計劃”(NCGP),分為兩種資助類型“發現”和“合作”——“發現”旨在發展和保持澳大利亞在廣泛的學科領域范圍內具有國際水準的高水平的科學基礎,而“合作”則是試圖通過加強澳大利亞國家創新系統內部以及澳大利亞與國外創新系統的聯系,鼓勵和拓展各種合作方式,以使科學研究更好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
在管理模式方面,《知識與創新》白皮書提出,新的ARC必須建立計劃透明、重在績效的管理體制。因此,ARC聲明每年將提交一份覆蓋未來三年的戰略計劃,設立擬達到的目標,并提出戰略實施行動的時間表以及結果形式,以實現真正的績效管理。[ ]事實上,從2000年到目前為止,ARC共制定兩份戰略計劃,即2000-2002年戰略計劃和2002-2004年戰略行動計劃,是ARC資助及管理工作的政策與戰略指南。
2 ARC的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
ARC不僅在國家科技政策與戰略的制定、協調和實施中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ARC也十分重視針對自身資助和管理工作而開展的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以下將分別進行分析。
2.1 國家科技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
由于ARC負有向聯邦政府提出有關科技活動及其資助政策建議的責任,從成立之日起,ARC就開始了一系列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工作,其中有些是由ARC主持的,有些是ARC參與的工作。
由ARC支持的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分析、政策評估和政策建議等多種形式,政策分析重在理論研究,為政策制定奠定理論基礎;政策評估重在對已有政策進行評估,為政策調整提供實際依據;而政策建議則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建議。其政策研究多是利用其與學術界(特別是科技政策研究專家)的廣泛聯系,以委托研究課題方式或由ARC人員牽頭、政策專家參與的方式進行,課題或研究任務完成后形成的專題研究報告、評估報告或政策建議由ARC提交有關部門,其內容涉及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產學研結合、科學研究的資助模式、學科交叉研究、科學研究的評估指標、科學研究及其教育活動的國際化等國際科技政策界也普遍關注的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關于科學研究的商業化問題、知識產權管理問題、科學研究的評估問題等在ARC的政策研究中占到相當的比重,如《將科學研究的效益最大化:ARC和高等教育理事會關于知識產權的聯合建議》(1995)、《評估大學的研究: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研究評估實踐之比較》(1997)、《學科交叉研究》(1999)、《向未來投資:澳大利亞專利與基礎研究的關系》(2000)、《為了國家利益的研究:澳大利亞大學研究的商業化》(2000)、《多樣性與集中性:澳大利亞大學的研究資助與研究活動模式》(2000)等。這些政策研究為國家科技政策制定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ARC主持的國家科技戰略制定主要圍繞資助戰略展開,如90年代制定若干前沿學科的國家資助戰略,2000年主辦基因組學與基因技術國家戰略研討會,2002年制定國家的優先研究領域等。而ARC參與制定的國家科技戰略議題廣泛,形式多樣。以1999-2000年度為例,1999年針對其參與起草的聯邦政府關于21世紀發展高等教育部門研究與研究培訓的政策性文件《新知識、新機遇》討論稿,ARC向學術界和產業界廣泛征詢意見,以完善這一國家科技發展戰略;1999年ARC還參與了國家科學技術普及戰略和產學合作戰略的討論和制定;2000年3月ARC主席參加了國家創新峰會,負責主持《向思想投資》主題的討論;同年3月,ARC主席赴歐洲參加歐盟政策研討會和出席澳大利亞與歐盟科學技術合作聯合委員會會議,推動雙方的科技合作;2000年6月ARC主席參與主持了在巴黎舉行的OECD全球科學論壇,代表澳大利亞政府提出建立全球創新平臺,促進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等等。[ ]可以說,這些戰略制定大多是以ARC開展的政策研究為基礎的。
轉貼于 2.2 ARC政策的評估與研究
在開展國家科技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的同時,ARC也十分重視自身決策與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評估是提高決策與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乃至前提條件之一,尤其是隨著近十多年來OECD國家科研評估之風興起和澳大利亞本國政府對績效評估的重視,因此ARC的政策研究常常伴隨有評估。ARC政策領域的研究和評估主要對象有其學科政策、資助政策和管理政策等。
第一類是學科評估與學科發展戰略研究。1990-1997年ARC對其在自然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幾大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24個學科的5年資助結果進行了評估,以說明其“分配資源的管理工作”是否有效。[ ]評估由3-4位專家(包括聘請的國外專家)組成的評估專家組獨立進行,內容涉及資助結果和資助過程及管理,如:資助項目的產出和影響如何?受資助方向和人員是否合適?資助強度是否足夠?項目遴選和評議工作如何?等等。專家組根據評估結果對ARC所資助的學科研究水平做出判斷,并就相關管理問題提出建議。ARC有義務回答評估專家的問題,針對接受的建議提出解決設想,對不接受的建議則需說明理由。因此,評估過程既是ARC了解其資助績效的過程,也是改進其政策和管理工作的過程。在開展學科評估的同時,ARC也結合評估結果開展學科資助政策研究工作,為制定學科發展戰略提供依據。
第二類可稱為資助類型的評估與研究。在1992-1998年間,ARC還針對其項目類型的運行情況進行了評估,包括研究項目類型、教育項目類型、研究設施資助計劃和研究中心資助計劃等。以小額項目類型評估和研究為例,其內容主要有:小額項目類型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合適?與大額項目的關系是否協調、在實現其近期和長期目標方面有效性怎樣?該項目類型的整體性(項目人員、規模和用途等)如何?經費分配的機制和準則是否需要改進以及其他與項目運行有關的問題。[ ]
第三類是管理政策的評估與研究,通常委托專業的政策研究專家進行,對象包括ARC的同行評議過程、對學科交叉研究的資助政策、任命學科評審組成員的程序、ARC的組織結構,等等。專家開展這類評估和研究,往往是基于較為深入的理論研究,并進行國際比較,分析ARC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以評估ARC的同行評議為例,評估報告分析了同行評議的定義和起源、開展有效的項目申請同行評議所需條件、同行評議的局限與受到的批評等,同時還介紹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等相關機構的同行評議,研究了ARC大額項目申請同行評議的情況,最后提出政策建議。[ ]
上述三類政策評估與研究工作在ARC的政策制定和改進管理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ARC的高度重視。而且,多數評估與研究報告都可從ARC網站獲得,從而使得ARC的工作與澳大利亞更多的政府部門、更廣泛的科學界和更廣大的社會各界公眾構成了公開、透明、活躍的互動關系,推動了科學的社會化,也提高了ARC自身的影響力。
2.3 ARC戰略的制定
ARC自身戰略可分為學科戰略和總體戰略兩個層次,關于學科戰略的制定前面已經提及,主要結合學科評估進行,而總體戰略的制定如前所述,在《知識與創新》白皮書對ARC提出績效管理的要求以來已成為ARC工作必不可少的內容。ARC的戰略制定從機構的使命出發,首先明確制定戰略的指導原則,然后設立主要發展目標,再將總體戰略分解為幾個主要領域,結合經費預算,形成戰略實施的行動時間表,并提出衡量其結果的績效指標。
以ARC的2002-2004年戰略行動計劃為例。[ ]其制定戰略計劃的指導原則為卓越性、集中性、靈活性、戰略性、伙伴關系、橋梁作用和績效管理,與7個主要發展目標相對應的7個戰略行動領域是:發現、合作、研究培訓與職業發展、研究設施、優先領域制定、公眾理解科學和績效管理。限于篇幅,不可能對這些領域的戰略逐一介紹,僅以“發現”領域為例。“發現”的戰略目標是“發展和保持澳大利亞在廣泛的學科領域范圍內具有很高國際水準的科學基礎”,這一目標又可分為3個子目標:卓越性、靈活性和創造性,在每個子目標下制定不同的投資戰略,采取不同的實施措施。(1)在“卓越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通過同行評議遴選具有高國際水準的研究,確保澳大利亞擁有實現研究卓越性的廣泛基礎。正在采取的行動包括:繼續改進ARC的同行評議,并在保證研究質量的基礎上,對學科間的資助經費進行調整;通過提供研究的直接成本,確保ARC的資助達到可與國際競爭的水平。(2)在“靈活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保持與加強反應迅速的靈活資助機制,以滿足不同研究的需求,抓住新出現的研究機會。正在采取的行動是在NCGP框架下保持“發現”領域的資助靈活性,并在廣泛的研究領域內保證都有資助活動;從2003年開始的行動是在不同的計劃間實現靈活資助,以滿足不同學科群的需求;2004年開始的行動是縮短項目申請處理周期,每年實行多輪受理與批準。(3)在“創造性”目標下的投資戰略是支持多學科研究和早期研究人員提出的創新性方法,正在采取的行動是,向最優秀和最具創造力的研究人員提供長期項目支持,保留對早期研究人員的資助計劃,向創新性研究提供約100萬澳元的種子資金資助。
在制定發展目標、投資戰略和具體行動的同時,ARC還提出了“發現”領域的預期結果——即促進知識進步以推動新發現與創新產生——以及衡量結果是否成功的指標:(1)“卓越性”的績效指標有兩項:通過國際同行和終端用戶的評估顯示,并輔以投入-產出定量分析的支持,表明“發現”在廣泛的學科范圍內產生了國內外具有競爭力的產出與結果;澳大利亞具有競爭優勢的研究領域其實力得到加強。(2)“靈活性”的績效指標也有兩項:對ARC受資助者所來自的國別進行調查和分析顯示,“發現”吸引國際水平的研究人員來到并留在澳大利亞;對“發現”領域ARC資助計劃的靈活性和敏捷性進行調查,人們表示滿意。(3)“創造性”的績效指標為一項:評議報告和國際同行的評估顯示,ARC通過申請書評議和項目遴選過程而支持的研究具有新穎性特征,采用了創新方法。
從上述指標的具體化程度可以看出,ARC的戰略絕非“大而無當”或“空洞無物”,每個戰略目標都有可測度的績效指標,真正能夠發揮“宏觀指導、微觀操作”之功效。需要強調的是,ARC從2000-2001年度報告起,每年在年度報告中根據戰略計劃提出的績效指標,列出本年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進展,以檢驗其實現戰略目標的績效情況,使得戰略計劃最終能夠落到實處。
3 結論與借鑒
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是政府R&D管理部門和機構的主要職責之一,其公開性、科學性、合理性、可行性是國家R&D管理水平的重要體現。從ARC的政策研究和戰略制定可以看到,作為一個政府機構不僅要積極參與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而且要重視自身的政策研究與戰略制定,以此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并提升自身的影響力;科學合理的評估是制定政策與戰略的重要依據,也是檢驗政策與戰略實施結果及效果的手段之一;政策和戰略制定的過程可看作是實施的基礎,因為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中的公開討論與磋商能夠使相關各方的思想進行充分的交流與協調,以求達成必要的共識,并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而這正是政策與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比我國的科技政策與戰略制定工作,我國存在重制定、輕實施的現象,在戰略制定中又存在重設想、輕論證的問題,在公開性、科學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也有許多可改進之處。考察ARC的狀況,有以下幾方面的經驗可以借鑒。
3.1 戰略制定是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行績效管理是近年來發達國家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一大趨勢。美國于1993年頒布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PRA),率先通過法律在聯邦政府部門和機構實行績效管理,要求各部門和機構制定5年戰略規劃(且每3年修訂一次),并每年提交年度績效規劃和績效報告,年度經費預算的批準與績效報告的審議直接相關。[ ]澳大利亞也于1997年通過了《財政管理和績效法案(1997)》,1999年通過了《公共服務法案(1999)》,規定了要對政府的工作實行績效管理。ARC法案的第6章對“規劃和報告”制度作了詳細規定,明確指出制定戰略計劃在其整個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年度報告中必須包括根據戰略計劃中設立的目標對ARC當年的實施情況進行績效評估的內容。因此,對于ARC來說,戰略制定不是一種姿態的展示,更不是爭取經費的手段,而是法律所要求的實行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制度將其工作置于政府和社會的公開監督之下,結果恰恰是增強了政府和公眾對ARC工作的信心,政府對ARC的投資在2001-2005年間將增加一倍!
我國近幾年也在公共管理中引入了績效管理的概念,但實施中只是在局部有所試點,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制度安排。在戰略制定中往往仍然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偏愛制定宏大的中長期規劃,缺乏包括具體績效指標的實施方案、特別是年度績效規劃,而且,在規劃或計劃覆蓋的時期結束時也不要求開展評估,易造成“虎頭蛇尾”的現象。
3.2 評估是制定科技政策與戰略的重要依據
ARC凡有重大的政策變動或戰略出臺,必評估先行,評估已成為政策與戰略制定的重要依據乃至必要前提。ARC在2001年轉變為獨立機構前,對其組織結構、資助計劃、評議過程等開展了一系列評估,包括對國外職能類似的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在專門針對機構改革而開展的評估中,政策研究專家從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出發,就ARC的組織機構、運行機制和管理成本等與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等國的類似機構進行比較,充分討論現有體制的利弊,探討組建新機構的可能性,并提出具體建議。無獨有偶,日本國會于2002年秋通過法案,決定從2003年10起將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轉變為一個獨立機構。此前,JSPS也委托包括國外專家在內的外部評估委員會,于2002年2月開始對JSPS的組織結構及運行狀況等進行評估,充分考慮將來作為獨立機構的JSPS的地位、組織、功能與作用等方方面面,以此為依據提出政策建議。通過這樣的嚴格評估過程制定出來的政策與戰略,自然很有針對性,而缺乏評估的政策與戰略制定則如同“盲人摸象”。近年來我國科技界也開展了廣泛的評估活動,但評估對象還多限于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和研究項目等,以科技政策為對象的評估還不多見。隨著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評估活動也將逐步成為政策與戰略制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3.3 公開的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是實施的重要保障
現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公開性,從問題的提出到公眾參與的各方討論,再到政策制定與實施,都要求公開進行。ARC的經驗表明,公開的政策與戰略制定過程不僅是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也是政策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制定優先資助領域戰略以及在不同的學科間分配經費一直是政府科研資助機構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因為每個學科都有其要求增加資助的理由。ARC的策略是,讓本機構以外的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澳大利亞科學界以外的國外科學家、科學界以外的產業界以及更廣泛的公眾參與這一過程,通過對其他機構資助活動及重點的了解,對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關鍵技術和科學問題的把握,以及聽取國外科學家的咨詢意見,制定的優先領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可行性,不僅得到科學界的理解,也得到公眾的支持,保證了優先領域資助戰略的順利實施。而我國以往在科技政策與戰略實施中多有不到位的情況,除了政策與戰略目標不夠明確、內容不夠具體等原因,也和制定過程缺乏公開性和相關各方的廣泛參與有一定的關系,這也應是今后改革的一個重點。顯然,ARC的策略值得借鑒。
參考文獻
[ ]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Austral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a Glance 2000,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2000
[ ] P.J.Sheehan等著,柳卸林等譯,《澳大利亞與知識經濟》[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7年,p64
[ ] F. Narin等, Investing Our Future:the link between Australian patenting and basic research[R],Canberra:ARC and CSIRO,2000,arc.gov.au/pdf/00_02.pdf
[ ] J Ronayne,Science in Government[M],London: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84
[ ] 同1
[ ] Don Aitkin, Research policy in Australia, 1989-1999: a retrospective[J], Research Evaluation, Vol.8, No.2, August 2000, pp151-154
[ ] Professor David Penington, Review of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R], ARC, July 1998, arc.gov.au/pdf/98_11.pdf
[ ]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1999-2000[R],2000, arc.gov.au/pdf/00_05.pdf
[ ]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nnual Report2001-2002[R], 2002,arc.gov.au/pdf/ar_2001-02_chap2.pdf
[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 Statement on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R], 1999, detya.gov.au/archive/highered/whitepaper
[ ] 同10
[ ] 同8
[ ] 同7
[ ] Peter Laver, Advice on the Small Grants Scheme, 1992, arc.gov.au/pdf/92_14.pdf
[ ] Fiona Q. Wood, The Peer Review Process[R], 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