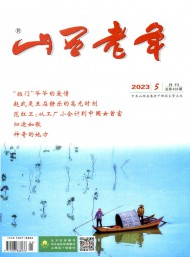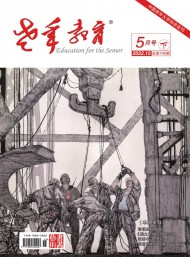老作家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2 09:39:47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老作家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老作家慶祝國慶征文
走進那條小巷,遠遠地就聞見了焦面的芬芳。那熟悉的麥香,讓我的思緒回到了兒時的故鄉。那里沒有現在的山珍海味,但是有焦面那誘人的芬芳。
不怕讀者笑話,我寫下焦面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心中惴惴不安。因為我不知道我記憶中的焦面,是不是就是我筆下焦面的寫法。但是,我揣測半天,還是寫下了焦面這兩個字。因為我清楚,焦面是炒出來的。應該是這個焦,而不應該是辣椒的椒或攪拌的攪。但是,焦面卻不能炒焦了。我奶奶是炒焦面的好手。印象中,奶奶站在廚房的鍋臺前,在飄搖的油燈下,一鍋鏟一鍋鏟地炒著鍋里的焦面,心平氣和,不急不躁。我們兄弟兩個則圍在鍋臺前,看著越炒越香的焦面,饞得直流口水。母親雖然不掌勺炒面,但是也緊密配合。因為她知道,這炒面要用文火。火大了,面就糊了;火小了,面又不熟。那噴香的熱氣從翻炒的焦面中升騰起來,升騰到奶奶笑瞇瞇的臉上。連奶奶腦后扁巴巴的發髻上的銀簪子,也沐浴著焦面的芬芳。被焦面充盈著的廚房是溫馨的。在這樣溫馨的廚房里,等待也涂上了幸福的色彩。七十年代末,是個并不富裕的時期。老百姓還在為吃飽飯,而勞碌甚至愁苦。這芬芳的焦面就成了寶貝。既然是寶貝,那就不是輕易能享用的了。眼見著,奶奶將炒熟的焦面就著鍋,一鏟一鏟地裝進大口的瓶罐里。我們失望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不是奶奶不心疼你們,而是這東西要留著待客和應急!”奶奶嘴上這樣說著,手上還是將最后半鏟子的焦面倒進了早已放在鍋臺上的一個空碗里。此刻,我們兄弟像餓極了的豬崽一樣,不約而同地撲向那只碗,爭搶那僅有的一點美味。“別搶,別搶,每人都有一份!”母親說著拿過那只碗,倒上一兩滴香油,再用勺子從糖壺里挖點白糖,撒在碗里的焦面上,最后倒上合適的白開水,使勁地攪拌,那焦面就調好了,可以享用了。母親公平地將焦面分成兩份,我們兄弟一人一份。弟弟非要原先盛焦面的那個碗,因為那個碗的內一側還多些焦面分攤時的殘留。看著我們倆狼吞虎咽的樣子,在一旁干看著的奶奶和母親都開心地笑了。“慢點慢點,沒有人跟你們搶!千萬別噎著!”奶奶還不忘了提醒我們。可我們已經被焦面的芬芳,陶醉得忘乎所以了。更加可笑的是,第二天,母親還笑著告訴我說:“娃,你夜里還說夢話呢!”我問母親我說了什么夢話。母親笑得合不攏嘴,過了半晌才說:“你在夢里還問我,憑什么把那個碗給弟弟?說我偏心!”公務員之家:
往事如煙,光陰似箭。一晃,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如今又迎來了建國六十年大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吃穿不愁的老百姓們,又開始考慮如何才能吃出健康吃出長壽來了。于是,玉米、山芋、飯瓜等粗糧又成了大小酒店和城市人飯桌上的新寵。兒時的焦面堂而皇之地在城市里登堂入室,兒時那熟悉的麥香在城市的天空下到處留芳。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講究科學飲食的城里人,知道了看起來并這不起眼的焦面,原來還有除熱、補虛、通便的作用,對降低膽固醇,預防動脈硬化、心臟病大有好處。如此說來,還有可能出現焦面有供不應求的狀況。想到這里,我徑直奔向賣焦面的鋪子,準備多買幾袋在家放著。不是待貴客,也不是防不時之需,而是為了身體健康。
老作家新中國60周年征文
惟茲清季失柄,宇內沸騰。外戈擾攘,內患頻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奪明。風飄飄而木落,天慘慘而云凝。生民煎迫,萬姓悸驚。兇歲辛丑,受辱異邦;哀年庚子,見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國步;水深火熱,待拯民生。積貧積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萬畝,西北失蔽翰,東南喪藩屏,可不謂危乎?遂令懷寶國士,奮拳攘臂;蘊奇書生,畫策陳情。乃有,辛亥革命,廢千年之皇權,希一朝之和平。無奈挽頹柱而心瘁,救覆瀾而力罄。哀離黍,喟空城,痛郢都,傷新亭。力豈惡乎出于己?術未得也功難成。于是嘉興舟泛,上海會開,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昌旗揚,長沙義舉,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農,聚群眾,建部伍,申號令,井岡山頭點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驅日寇,反圍剿,大渡河邊高懸熠熠赤旌。紅旗展,白日熒,兵馬壯,槍彈精;士氣足,軍心齊,組織密,紀律明。處軍民若魚水,驅敵虜似鹯鷹。犯寒冒暑,斬棘披荊。妙絕帷幄,張良謀運萬里;勇冠甲胄,樊噲功震千營。更賴壺漿遍薦,具瞻道路;兜鍪齊戴,踴躍擊鐺。善俘虜不忍京觀,縛蒼龍早備長纓。四渡赤水,三大戰役,廿載攻討,萬里長征。尚記否?南昌城上旌旗獵獵,寶塔山下戰鼓彭彭,平型關旁坦克隆隆,瀘定橋邊炮彈聲聲。未敢忘,錦州城中烈風颯颯,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莊外圍困重重,江陰渡口沖鋒陣陣。壯宇宙而長記,感山河而同銘。乃至廓滅霧氛,澄清區宇,羈長蛇,翦巨鯨,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復歸于靜。遂建國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劃州省。農桑再秉鋤耒,士子復持書經。斯功至偉,甌裂而璧合于唐;厥業豈細,瓜分而玉成于秦。
方今建國六十歲矣,正漢武揚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嘆老耄;國逢五紀,猶稱弱冠。踔厲奮發,昂藏偉建。切磋兮琮璧,華彩漸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積云,蔭翳天衢;剽疾兮怒風,沖騰霄漢。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矯兮翠松,挺秀出澗。猛捷兮乳虎,乍嘯出谷;回舞兮飛龍,正躍自淵。念茲明時,何慚子云之賦詠?躬此盛世,當效太白之書劍。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實賴改革開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來,突破枷鎖,擺脫束縛,滌除計劃舊制,開啟市場新篇。勸農興商,去陋納善,力行改革開放路,樹立科學發展觀。乃至庶物豐盈,貿易活躍,經濟增長,人民乂安。
若夫民為國本,農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義斯在,今亦為然。衣食之重,國家憑賴;改革之功,農村肇端。破除集體主義大鍋飯,實行家庭聯產大包干。遂界畎畝,畫畛甽,興壟畦,刳溝洫,濬漕渠,引溉灌,藝禾黍,墾良田。水庫往往而有,河道歷歷可觀。東北黑壤,頗宜種稻;新疆沃野,盡使植棉。更有推行機械化,愈增工效;倡導科技化,倍增畝產。實行產業化,鞏固市場;促進國際化,突破籬藩。傳統農業,力樹桑麻,自給自足,自封自閉,當年曾見飽腹少;現代科技,雜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種自產,從此不謂吃飯難。嘗謂以微薄之耕地,活烝眾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麥稷粱豆,瓜茄菇筍,桃李杏柿之屬,隨處皆見,不可盡記焉。香椰芒果,荔枝龍眼,豐殖兩廣;松茸紫薯,竹蓀椪柑,富產四川。青鯽鯉鯧之魚,犬豕牛羊之肉,陳城鄉之店鋪,走往來之商販。自羲農稷契以來,稼穡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創新思維,改變觀念,活躍市場,鼓勵工商。有無貿遷,供銷兩旺。西陲珍貨,順康衢而東進;南域奇寶,浮舟楫而北上。麗都名會,不乏瑰異;閭閻鄉廛,時見琳瑯。輻輳所及,轂輪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廣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陽,西有成都重慶,東有南京蘇杭,并人煙阜密,街道縱橫,高樓林立,店鋪櫛比,遠軼漢之宛洛,絕勝唐之蜀揚。更兼合肥武漢、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呼和浩特,堪稱繁華者,則星羅棋布,車載斗量。漁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蕪城上海,陡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頻驚新變;開放以來,不復舊樣。設特區,引資本,建城市,辦工廠,小企業若雨后春筍,大公司似陽來草長。加工車間,綿綿流水線;制造企業,轟轟機車床。稅出名區,財開多道,寶泉流轉不息,銀行出納無妨。古謂食貨為先,食有余而貨乃足,以今日觀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贍貨富,國家乃思經始,造道梁,興土功。建國伊始,有周臺之謀,懼秦宮之力;改革之后,修漢道之遠,筑唐殿之雄。斯非窮竭人力,乃因百業興隆。地有貧富,豐殷于此而疏于彼;國如棋局,運籌乎外而總乎中。是以五縱七橫,連都邑而有達;二灘三峽,蓄能源以無窮。西氣東輸,酌油烷而損益;南水北調,溝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眾,無嗟缺水之苦;東省家庭,不虞乏氣之用。九州一家,正當如此,四海無外,理應攸同。更有火箭絕霄,盡人皆知長征號;衛星繞地,舉世猶稱東方紅。神九飛天,遠揖織女邈漢;嫦娥探月,近窺玉兔桂宮。珠峰測繪,度量穹柱;南極科考,舟乘雪龍。偉功今造,攬歷史而絕無,視世界亦僅有,可不為頌?
至夫建國未幾,庠序之謹一度沉淪,幸賴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憶茲三中全會,復開高考;千萬學子,再試經綸。于是禮樂備,學校密,文化興,教育敦。處窮困之士,豈遇窮困之時?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長沙之墮馬,賦相如之凌云。青山綠水,勿為嚴子;朱門紫闥,正待終軍。堂集俊彥,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一定華夏五千載;清朝史重修盛舉,再論滄桑十二君。奪首金于洛城,洗雪體壇屈辱;邀百國于北京,弘揚奧運精神。如斯種種禮節復興者,非倉廩豐實,孰能致之哉?
老作家建國60周年感賦征文
惟茲清季失柄,宇內沸騰。外戈擾攘,內患頻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奪明。風飄飄而木落,天慘慘而云凝。生民煎迫,萬姓悸驚。兇歲辛丑,受辱異邦;哀年庚子,見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國步;水深火熱,待拯民生。積貧積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萬畝,西北失蔽翰,東南喪藩屏,可不謂危乎?遂令懷寶國士,奮拳攘臂;蘊奇書生,畫策陳情。乃有,辛亥革命,廢千年之皇權,希一朝之和平。無奈挽頹柱而心瘁,救覆瀾而力罄。哀離黍,喟空城,痛郢都,傷新亭。力豈惡乎出于己?術未得也功難成。于是嘉興舟泛,上海會開,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昌旗揚,長沙義舉,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農,聚群眾,建部伍,申號令,井岡山頭點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驅日寇,反圍剿,大渡河邊高懸熠熠赤旌。紅旗展,白日熒,兵馬壯,槍彈精;士氣足,軍心齊,組織密,紀律明。處軍民若魚水,驅敵虜似鹯鷹。犯寒冒暑,斬棘披荊。妙絕帷幄,張良謀運萬里;勇冠甲胄,樊噲功震千營。更賴壺漿遍薦,具瞻道路;兜鍪齊戴,踴躍擊鐺。善俘虜不忍京觀,縛蒼龍早備長纓。四渡赤水,三大戰役,廿載攻討,萬里長征。尚記否?南昌城上旌旗獵獵,寶塔山下戰鼓彭彭,平型關旁坦克隆隆,瀘定橋邊炮彈聲聲。未敢忘,錦州城中烈風颯颯,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莊外圍困重重,江陰渡口沖鋒陣陣。壯宇宙而長記,感山河而同銘。乃至廓滅霧氛,澄清區宇,羈長蛇,翦巨鯨,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復歸于靜。遂建國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劃州省。農桑再秉鋤耒,士子復持書經。斯功至偉,甌裂而璧合于唐;厥業豈細,瓜分而玉成于秦。方今建國六十歲矣,正漢武揚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嘆老耄;國逢五紀,猶稱弱冠。踔厲奮發,昂藏偉建。切磋兮琮璧,華彩漸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積云,蔭翳天衢;剽疾兮怒風,沖騰霄漢。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矯兮翠松,挺秀出澗。猛捷兮乳虎,乍嘯出谷;回舞兮飛龍,正躍自淵。念茲明時,何慚子云之賦詠?躬此盛世,當效太白之書劍。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實賴改革開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來,突破枷鎖,擺脫束縛,滌除計劃舊制,開啟市場新篇。勸農興商,去陋納善,力行改革開放路,樹立科學發展觀。乃至庶物豐盈,貿易活躍,經濟增長,人民乂安。
若夫民為國本,農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義斯在,今亦為然。衣食之重,國家憑賴;改革之功,農村肇端。破除集體主義大鍋飯,實行家庭聯產大包干。遂界畎畝,畫畛甽,興壟畦,刳溝洫,濬漕渠,引溉灌,藝禾黍,墾良田。水庫往往而有,河道歷歷可觀。東北黑壤,頗宜種稻;新疆沃野,盡使植棉。更有推行機械化,愈增工效;倡導科技化,倍增畝產。實行產業化,鞏固市場;促進國際化,突破籬藩。傳統農業,力樹桑麻,自給自足,自封自閉,當年曾見飽腹少;現代科技,雜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種自產,從此不謂吃飯難。嘗謂以微薄之耕地,活烝眾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麥稷粱豆,瓜茄菇筍,桃李杏柿之屬,隨處皆見,不可盡記焉。香椰芒果,荔枝龍眼,豐殖兩廣;松茸紫薯,竹蓀椪柑,富產四川。青鯽鯉鯧之魚,犬豕牛羊之肉,陳城鄉之店鋪,走往來之商販。自羲農稷契以來,稼穡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創新思維,改變觀念,活躍市場,鼓勵工商。有無貿遷,供銷兩旺。西陲珍貨,順康衢而東進;南域奇寶,浮舟楫而北上。麗都名會,不乏瑰異;閭閻鄉廛,時見琳瑯。輻輳所及,轂輪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廣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陽,西有成都重慶,東有南京蘇杭,并人煙阜密,街道縱橫,高樓林立,店鋪櫛比,遠軼漢之宛洛,絕勝唐之蜀揚。更兼合肥武漢、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呼和浩特,堪稱繁華者,則星羅棋布,車載斗量。漁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蕪城上海,陡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頻驚新變;開放以來,不復舊樣。設特區,引資本,建城市,辦工廠,小企業若雨后春筍,大公司似陽來草長。加工車間,綿綿流水線;制造企業,轟轟機車床。稅出名區,財開多道,寶泉流轉不息,銀行出納無妨。古謂食貨為先,食有余而貨乃足,以今日觀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贍貨富,國家乃思經始,造道梁,興土功。建國伊始,有周臺之謀,懼秦宮之力;改革之后,修漢道之遠,筑唐殿之雄。斯非窮竭人力,乃因百業興隆。地有貧富,豐殷于此而疏于彼;國如棋局,運籌乎外而總乎中。是以五縱七橫,連都邑而有達;二灘三峽,蓄能源以無窮。西氣東輸,酌油烷而損益;南水北調,溝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眾,無嗟缺水之苦;東省家庭,不虞乏氣之用。九州一家,正當如此,四海無外,理應攸同。更有火箭絕霄,盡人皆知長征號;衛星繞地,舉世猶稱東方紅。神九飛天,遠揖織女邈漢;嫦娥探月,近窺玉兔桂宮。珠峰測繪,度量穹柱;南極科考,舟乘雪龍。偉功今造,攬歷史而絕無,視世界亦僅有,可不為頌?
至夫建國未幾,庠序之謹一度沉淪,幸賴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憶茲三中全會,復開高考;千萬學子,再試經綸。于是禮樂備,學校密,文化興,教育敦。處窮困之士,豈遇窮困之時?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長沙之墮馬,賦相如之凌云。青山綠水,勿為嚴子;朱門紫闥,正待終軍。堂集俊彥,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一定華夏五千載;清朝史重修盛舉,再論滄桑十二君。奪首金于洛城,洗雪體壇屈辱;邀百國于北京,弘揚奧運精神。如斯種種禮節復興者,非倉廩豐實,孰能致之哉?
至乃文教敷宣,武備不櫜。衛江山以永固,繕甲兵而勿韜。英雄浴血,青簡不滅;國家遭辱,丹心常表。矻矻于民主獨立,反帝反寇;孜孜于和平自由,援越援朝。國有利器,方能長保。導彈裝,機槍配,潛艇深,艦船巡,坦克沖,飛機嘯。震邇懾遠,兩彈爆炸;游天窺地,一星環繞。同根同祖,兩岸孤峽,怎限臺灣?順天順人,一國兩制,回歸港澳。兵不可玩,然不可不威,釁不可生,然不可不防。當今和平之世,尤非忘危之時也。
老作家紀念新中國60周年演講稿
惟茲清季失柄,宇內沸騰。外戈擾攘,內患頻仍。九州倏乎造昧,四海忽焉奪明。風飄飄而木落,天慘慘而云凝。生民煎迫,萬姓悸驚。兇歲辛丑,受辱異邦;哀年庚子,見覆神京。土崩瓦解,堪虞國步;水深火熱,待拯民生。積貧積弱殆百年,割土割地近萬畝,西北失蔽翰,東南喪藩屏,可不謂危乎?遂令懷寶國士,奮拳攘臂;蘊奇書生,畫策陳情。乃有,辛亥革命,廢千年之皇權,希一朝之和平。無奈挽頹柱而心瘁,救覆瀾而力罄。哀離黍,喟空城,痛郢都,傷新亭。力豈惡乎出于己?術未得也功難成。于是嘉興舟泛,上海會開,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昌旗揚,長沙義舉,組建人民子弟兵。合工農,聚群眾,建部伍,申號令,井岡山頭點燃星星野火;打土豪,分田地,驅日寇,反圍剿,大渡河邊高懸熠熠赤旌。紅旗展,白日熒,兵馬壯,槍彈精;士氣足,軍心齊,組織密,紀律明。處軍民若魚水,驅敵虜似鹯鷹。犯寒冒暑,斬棘披荊。妙絕帷幄,張良謀運萬里;勇冠甲胄,樊噲功震千營。更賴壺漿遍薦,具瞻道路;兜鍪齊戴,踴躍擊鐺。善俘虜不忍京觀,縛蒼龍早備長纓。四渡赤水,三大戰役,廿載攻討,萬里長征。尚記否?南昌城上旌旗獵獵,寶塔山下戰鼓彭彭,平型關旁坦克隆隆,瀘定橋邊炮彈聲聲。未敢忘,錦州城中烈風颯颯,孟良崮里霰雪霏霏,小李莊外圍困重重,江陰渡口沖鋒陣陣。壯宇宙而長記,感山河而同銘。乃至廓滅霧氛,澄清區宇,羈長蛇,翦巨鯨,天下分裂三十八年,而一朝復歸于靜。遂建國共和,定都北京,重理疆界,更劃州省。農桑再秉鋤耒,士子復持書經。斯功至偉,甌裂而璧合于唐;厥業豈細,瓜分而玉成于秦。
方今建國六十歲矣,正漢武揚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嘆老耄;國逢五紀,猶稱弱冠。踔厲奮發,昂藏偉建。切磋兮琮璧,華彩漸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積云,蔭翳天衢;剽疾兮怒風,沖騰霄漢。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矯兮翠松,挺秀出澗。猛捷兮乳虎,乍嘯出谷;回舞兮飛龍,正躍自淵。念茲明時,何慚子云之賦詠?躬此盛世,當效太白之書劍。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實賴改革開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來,突破枷鎖,擺脫束縛,滌除計劃舊制,開啟市場新篇。勸農興商,去陋納善,力行改革開放路,樹立科學發展觀。乃至庶物豐盈,貿易活躍,經濟增長,人民乂安。
若夫民為國本,農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義斯在,今亦為然。衣食之重,國家憑賴;改革之功,農村肇端。破除集體主義大鍋飯,實行家庭聯產大包干。遂界畎畝,畫畛甽,興壟畦,刳溝洫,濬漕渠,引溉灌,藝禾黍,墾良田。水庫往往而有,河道歷歷可觀。東北黑壤,頗宜種稻;新疆沃野,盡使植棉。更有推行機械化,愈增工效;倡導科技化,倍增畝產。實行產業化,鞏固市場;促進國際化,突破籬藩。傳統農業,力樹桑麻,自給自足,自封自閉,當年曾見飽腹少;現代科技,雜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種自產,從此不謂吃飯難。嘗謂以微薄之耕地,活烝眾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麥稷粱豆,瓜茄菇筍,桃李杏柿之屬,隨處皆見,不可盡記焉。香椰芒果,荔枝龍眼,豐殖兩廣;松茸紫薯,竹蓀椪柑,富產四川。青鯽鯉鯧之魚,犬豕牛羊之肉,陳城鄉之店鋪,走往來之商販。自羲農稷契以來,稼穡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創新思維,改變觀念,活躍市場,鼓勵工商。有無貿遷,供銷兩旺。西陲珍貨,順康衢而東進;南域奇寶,浮舟楫而北上。麗都名會,不乏瑰異;閭閻鄉廛,時見琳瑯。輻輳所及,轂輪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廣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陽,西有成都重慶,東有南京蘇杭,并人煙阜密,街道縱橫,高樓林立,店鋪櫛比,遠軼漢之宛洛,絕勝唐之蜀揚。更兼合肥武漢、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呼和浩特,堪稱繁華者,則星羅棋布,車載斗量。漁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蕪城上海,陡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頻驚新變;開放以來,不復舊樣。設特區,引資本,建城市,辦工廠,小企業若雨后春筍,大公司似陽來草長。加工車間,綿綿流水線;制造企業,轟轟機車床。稅出名區,財開多道,寶泉流轉不息,銀行出納無妨。古謂食貨為先,食有余而貨乃足,以今日觀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贍貨富,國家乃思經始,造道梁,興土功。建國伊始,有周臺之謀,懼秦宮之力;改革之后,修漢道之遠,筑唐殿之雄。斯非窮竭人力,乃因百業興隆。地有貧富,豐殷于此而疏于彼;國如棋局,運籌乎外而總乎中。是以五縱七橫,連都邑而有達;二灘三峽,蓄能源以無窮。西氣東輸,酌油烷而損益;南水北調,溝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眾,無嗟缺水之苦;東省家庭,不虞乏氣之用。九州一家,正當如此,四海無外,理應攸同。更有火箭絕霄,盡人皆知長征號;衛星繞地,舉世猶稱東方紅。神九飛天,遠揖織女邈漢;嫦娥探月,近窺玉兔桂宮。珠峰測繪,度量穹柱;南極科考,舟乘雪龍。偉功今造,攬歷史而絕無,視世界亦僅有,可不為頌?
至夫建國未幾,庠序之謹一度沉淪,幸賴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憶茲三中全會,復開高考;千萬學子,再試經綸。于是禮樂備,學校密,文化興,教育敦。處窮困之士,豈遇窮困之時?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長沙之墮馬,賦相如之凌云。青山綠水,勿為嚴子;朱門紫闥,正待終軍。堂集俊彥,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一定華夏五千載;清朝史重修盛舉,再論滄桑十二君。奪首金于洛城,洗雪體壇屈辱;邀百國于北京,弘揚奧運精神。如斯種種禮節復興者,非倉廩豐實,孰能致之哉?
企業晚會小品--抄襲風波
企業晚會小品--抄襲風波
人物:
胡超男,某企業職工,三十歲左右。
胡妻女,胡超妻子,三十歲左右。
老馬男,某企業內部刊物主編,五十多歲,高度近視。
老作家男,近八十左右,(可由扮演馬老師者改扮)。
花城與新時期文學發端
如果把“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定于1979年,那么《花城》的創刊可謂適逢其時。當時的文化現狀和社會語境,決定了文學期刊仍然是政治表達、情緒釋放與文化消費的重要載體,于是除了“十七年”時期的刊物先后復刊外,眾多文學期刊也相繼創刊,《花城》便是其中之一。《花城》創刊之初即發表大量“傷痕”與“反思”性質的作品,先鋒探索姿態也初露崢嶸,比如大力推介西方文化思想與現代派,大批發表港臺文學。這些,對“新時期”文學的發端與推進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79年4月至1980年底,《花城》(以書代刊的“文藝叢刊”)先后出版七期,直至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開始定期出版《花城》文藝雙月刊止。按照原主編范漢生先生的口述,這是《花城》的創刊階段。在這個階段,《花城》走在了沖破禁錮的前面,她不僅滿足了大量讀者的閱讀需求,而且參與建構且見證了“新時期”文學的行蹤。①本文的考察對象即是《花城》創刊時期的七期叢刊,以期窺斑“新時期”文學的發端。
一、《花城》與“新時期”作家的構成
《花城》前七期雖然順利打開了局面(創刊號印數即達25萬冊),兩年內就已經站在了很高的文學平臺上,但直到80年代其作者群才算基本上全面代表了“新時期”文學的作家構成。不過,《花城》在創刊階段就建起了一個水準很高的老中青作家梯隊,這已十分不易。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時,出席會議的作家代表可謂“五世同堂”(五四時期的“文壇老將”、五四以后的作家、新中國培養的作家、“右派”作家、文壇新秀)。《花城》前七期的作者,恰能展現這一構成的概貌。老作家有:巴金、沈從文、葉圣陶、夏衍、卞之琳、蕭軍、蕭乾、端木蕻良、臧克家、姚雪垠、艾蕪、徐遲、楊沫、聶紺弩、陳登科、歐陽山、秦牧、王西彥、黃藥眠、黃裳、葉君健、嚴辰、鄒荻帆、蔡其矯、吳有恒、李克異、曾敏之,等等;中青年作家有:張潔、林斤瀾、從維熙、彭燕郊、李瑛、沙鷗、黃永玉、柯藍、李晴、雁翼、范若丁、梁信、祖慰、王先霈、陳伯堅、程賢章、謝竟成、、彭拜、韋丘,等等;青年作家有:劉心武、史鐵生、高行健、孔捷生、鄭義、陳建功、洪三泰、楊干華、林賢治、段劍秋、畢必成、王梓夫、翟禹鐘、林雨純、李鋼,等等。從以上作家隊伍的構成來看,其影響已是非同一般。1981年,《花城》與《收獲》《當代》《十月》一道被譽為“新時期”文學期刊的“四大名旦”,后又與《收獲》《鐘山》形成所謂“三足鼎立”,《大家》創刊后,又有了“四分天下”之說。正是由于《花城》的高水準作家隊伍的建構,以及其先鋒探索姿態,才使它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當代文學史一般認為,80年代作家的“主體”由“復出作家”(或“歸來作家”)和知青作家兩部分組成。然而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始,作家的“主體”實際上由老作家和“復出作家”構成,《花城》前七期可以證實這點。只是,作家隊伍在當時已開始出現分化與重組,最明顯的莫過于,老作家與“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已在加速失去文壇的中心地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老作家已難維持曾經旺盛的創作活力,他們已處于人生的回憶與整理階段,更容易被作為“財富”或“資源”來對待;二,“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已難合拍于改革開放的時代語境,由于歷史與政治的原因,他們不再受到重視;三,思想解放運動與西方文藝思潮的涌入,對很多老作家和“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往往持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文壇熱點集中于對外來文化思想的轉化吸收與自我創新上。不過,這并非意味著老作家在“新時期”無所作為。事實上,諸如巴金、楊沫在內的很多老作家及其曾經的中心作家,在當時及之后的八十年代,都激起過很大的反響。《花城》前七期的作家作品,就很能說明問題。“復出作家”和知青作家后來成為“主體”,這是一種必然。前者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歸文壇,社會心理優勢明顯;另外,他們的創作觀念與“新時期”的潮流并無隔膜,復出之時即能融入;再者,“復出作家”正處中青年精力旺盛期,生活儲備充足,他們一度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中堅,委實不足為怪。與此同時,知青作家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經歷了特殊年代,飽含傾訴的欲望,更希望能夠體現自身的價值,這些都會促使他們迅速作出反應,迎時代潮流而上。其中,不少知青作家“”時期已開始創作,只是還未定型尚處探索階段,“新時期”的到來,正給他們一展身手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知青與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始,即已顯示非凡的實力。《花城》前七期不僅發現了一批青年作家,而且努力發掘他們的潛力。《花城》在“新時期”文學發端時期所作的巨大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當時劉心武37歲,高行健39歲,史鐵生28歲,鄭義32歲,陳建功30歲,孔捷生27歲,林賢治31歲,李鋼31歲,等等。洪子誠在《花城》上發表文章,當時也只有39歲。其中劉心武、高行健、史鐵生等人,在當代文學史上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總之,《花城》自創刊之后的七期,我們從中不僅能夠看到“新時期”作家構成的概貌,而且《花城》也為青年作家的發現、培養與整體文壇格局的重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花城》與“傷痕文學”
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發表后,“”之后的文學就在“傷痛”中開始復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正是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后出現與交叉匯流中開始的。“傷痕文學”最早出現,但是在渴望光明與未來的時代潮流之下,以上三者很快變得模糊不清,融合難辨。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在控訴“”給人造成“內傷”的同時,進而將“”發生的歷史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十七年”時期,痛定思痛后,最終把眼光放到對未來的希冀上。《花城》創刊期與“傷痕”敘事密不可分。“傷痕文學”本指小說,但從《花城》前七期來看,“傷痕”在每種文體中都是集束式出現,可謂“遍體鱗傷”。除海外港臺小說外,前七期共發表完整小說38篇,其中包含“傷痕”內容的竟達30篇。其他文體,包括詩歌、散文、電影文學、訪問記,甚至是“花城論壇”的批評文章,涉及“傷痕”的內容竟也占六成以上。以現在眼光看,這類敘事似乎過于泛濫,可“新時期”文學恰恰是在“傷痛”之下揭開序幕的。所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與諒解的一股文學思潮,《花城》也可謂扣緊了時代的脈搏,充分見證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盛產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幾近于無。《花城》雖有長篇小說連載,比如創刊號上有歐陽山的《柳暗花明》,但作品并非寫于“新時期”;第二期有李克異的《歷史的回聲》,但其不僅寫于“”期間,內容也是關于抗戰的,著實沒有“傷痕“的影子。研究者閻綱在當時就指出:詩歌、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話劇、散文報告文學,在“新時期”之初都已復興,唯有長篇小說落后了。“長篇,制作困難;三年,時間太短”,“現代迷信和非現實主義侵蝕嚴重,包袱太重,積重難返,恐怕也是原因之一”②。其實不需做深刻的原因分析,“”剛過,文學大門洞開,“春風”吹拂之下,病樹吐芽,鮮花含苞,大多數作家急切表現創傷性的記憶與進行短平快的控訴,實在來不及進行大架構的思考,這確乎合乎常理。結合當時實際情況,《花城》創刊號即創20多萬冊的發行紀錄,確實得益于“傷痕文學”。創刊號之所以暢銷,極可能是因為頭條發表了華夏的中篇小說《被囚的普羅米修斯》。小說講述了“四•五”中的一個英雄人物,被當作反革命入獄又最終平反的故事。據說,當時多家雜志不敢發表,《花城》編輯部主任李士非堅信,平反是眾望所歸的、也是必然的,于是大膽采用了這篇稿子。小說發表后迅即引起轟動。就在小說發表后不久,也得到了平反。《花城》用稿之慧之銳之大膽,由此可窺一斑,也算是引領了“新時期”文學風氣之先。同期還發表“傷痕文學”開創者劉心武的短篇小說《干杯之后》。從文末標注的寫作時間來看,大概是《班主任》發表一年后的作品。這個短篇與《班主任》一樣,都存在藝術上的粗糙與嚴重的“”文學的痕跡。比如小說一開始就說:“經歷了一場‘’造成的洗劫以后,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便春風重降,溫暖和煦,萬物蘇生”;類似政策說教的也不在少數,如:“新時期對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不是可以降低而是必須更高。黨委需要立即更深入地學習領會、更堅決積極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所制定的新時期的總路線,以及由這總路線所決定的各項方針和政策”。這些語言顯得干枯與牽強,極大影響了小說的文學性表達。本來是寫新老兩代科學家在“經典理論”與“新理論”之間的爭鋒與所造成的心靈創傷的,結果讓黨委書記賀真架在當中,讀來不倫不類,使得小說的主人公被喧賓奪主了。這類情形與“”遺風,以及不經意之間就冒現出來的“毛語體”,在前七期《花城》“傷痕”類作品中可謂俯拾即是,確實留下了“新時期“文學弊端的證據。然而,我們卻可以反過來思考這個缺陷。這些帶有“傷痕”的“傷痕文學”恰恰是最真實的文學史痕跡,重讀《花城》創刊階段的文學,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這種歷史原貌與“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及其發展的歷程。其實也并非沒有異質性的“傷痕”作品。創刊號上林斤瀾的短篇《一字師》讀來就頗含深意,饒有趣味。《一字師》以第一人稱述說了中學語文教師吳白亭對錯別字十分敏感,出于職業習慣,看見錯別字如不糾正就坐立不安,為了改正造反派小將大字報里的某個錯字,曾幾次被當場揪住批斗。這種近乎迂腐的固執行為或奇異之舉,卻飽含了一顆忠于教育事業,又頑強地同愚昧抗爭的偉大心靈。第五期頭條發表從維熙的中篇《泥濘》,這部小說已從純粹的“傷痕”中掙脫出來,飽蘊反思與改革的意味,而且頗具歷史感,讓人耳目一新。小說以作者“我”和一個回北京途中的旅伴共同失眠而攀談,來展開“我”與旅伴對往昔的追憶。小說的“傷痕”意味濃厚,被迫害者在反右派斗爭和中先后遭遇悲慘迫害,從中看到在罪惡的年代中各種人物的傷痛與悲哀。盡管傷痛永遠無法彌合,但作者卻寄予了對光明的向往,最終以一種美好的理想來結束小說。傷痛中帶著樂觀,而不是停留在悲哀中無法自拔,從而催人反思、勵人奮發成為小說的主旨。除了純粹的“傷痕”敘事之外,有些作品以愛情為背景來寫“傷痕”。畢必成的電影文學《廬山戀》(四期),李晴的短篇《茉莉啊,茉莉》(七期),兩者中的戀人都因“”被拆開,也都因新時期的到來而再次重逢與結合,情節感人,且令人充滿期待。此類作品在“新時期”同屬“解凍”之列,是很有影響且非常受歡迎的。楊沫的報告文學《不是日記的日記》(七期),則從另一角度來抒寫科學家的“傷痕”,同時也融入了自身的創傷性記憶。楊沫是放下正在創作的《東方欲曉》來寫這個報告文學的,她的寫作姿態深深體現了一個老作家的責任感與良心。說《花城》在創刊階段一“傷”到底,未免有失察之嫌。《花城》似乎在遍地“傷痕”中尋求某種平衡,海外與港臺文學的引入恰如起到一種中和的功效。更何況,我們從第四期發表的小說來看,又似乎能感受到《花城》的某種努力與傾向。在本期的四個短篇與一個中篇中,我們實難捕捉到“傷痕”的影子,歷史題材與民間傳說成為敘事的內容。
三、《花城》與巴金、高行健
沈從文小說中鄉情賞析論文
內容摘要:
“情愫”,也作“情素”;愫:真實的情意,誠意;“情愫”本意,就是真情實意。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通過記寫“湘西世界”自然優美、健康人生形式等方面的“美”來展現本意。本文將從“人情美”、“風俗美”和“寫作動因”三個部分作闡釋,分析作家從作品到理論構建的如詩如畫、恬靜淡遠、風格獨具的“湘西世界”,和獨特的功利原則與美學觀的顯現,以及構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動因,進而展現作者對湘西人民命運的關注,對故鄉發展的關切,體現作家創作的理性精神與文化情懷,反映作家對湘西故土的深深情愫。
關鍵詞:《邊城》故鄉情愫人情美風俗美
前言
《邊城》是沈從文最具影響的代表作,創作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最初在天津《國聞周報》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六期上連載,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書店出版了單行本,在作者本人的《選集》和《文集》中都曾被編選過。這部作品先后被翻譯為多種外文流傳世界,曾有“震動中外文壇”之譽。《邊城》的故事梗概是:在湘西山城茶峒,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兄弟同時愛上了老船夫的外孫女翠翠,翠翠雖然對二人都有好感,內心卻深愛著儺送。天保因為自己的愛得不到理會,在痛苦煩悶中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難。哀傷悲痛的儺送一時無心耽戀愛情,又與家里為婚事發生摩擦,隨后也隨船出走下桃源,不知歸期。在一個暴風雨之夜,經不起打擊的老船夫溘然長逝,留下孤獨的翠翠,懷著對祖父傷悼和對情人思念的雙重感情繼續守著渡口,而儺送卻不知何時歸來,也許明天,也許永遠都不回來。
縱觀《邊城》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我們不難看出人性作為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在沈從文筆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也是他創作的起點和歸宿。小說《邊城》無論從獨特的藝術風格,還是它所表現的故鄉美景,即人情美和風俗美,這無疑是沈從文謳歌與贊美故鄉的代表作。同時,他用柔美的筆墨、深沉的感情描繪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縛的原始古樸的湘西,謳歌自由、自得的人生,表現出一種倫理的善與道德的美,與都市紳士階層的道德淪喪形成鮮明對照,除了帶有30年代民主主義作家的共同傾向外,還以“鄉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謬。《邊城》中所描寫的“美”,即是故鄉的“人情美”和“風俗美”,作家不僅著筆于神秘綺麗的自然風光,更蘊含于人身上,是作者對故鄉揮之不去的深深依戀的集中表現。
工農兵文學藝術奉獻
由倡導的工農兵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受到的贊揚和貶否都最為激烈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樣式。贊揚它的人,從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從政治著眼的,如1947年8月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特地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把趙樹理樹為邊區的“方向性”作家,邊區的文聯副主席陳荒煤還寫過《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文[1]。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則是在政治的語境中,給某些作品以藝術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對工農兵文學的代表作品《紅旗譜》評價說:“在‘紅色經典’作品里,我個人認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藝術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畫的豐滿度上,《紅旗譜》達到的水準確實堪稱杰作,而且它在階級敘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貶否它的人,則從“”開始至今21世紀,尚且拋開“”時期不說,即就上世紀80年代而言,不但從政治上而且從藝術上對它進行徹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上世紀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文學(指以趙樹理小說為代表的工農兵文學)便被視為政治的‘傳聲筒’和‘吹鼓手’”。[3]當今,因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這樣一來,似乎工農兵文學只有特定時代的政治價值(當然,這是指文學不應追求的政治宣傳“價值”),而缺失藝術價值。因此,一個問題便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誕生于上世紀40年代綿延至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長達30余年的工農兵文學,究竟有沒有藝術上的成就和貢獻?站在21世紀今天的時間點上,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幾十年前產生于戰爭年代的工農兵文學的整體,準確地評價它的藝術價值,進而確定它的文學地位,這無論是對于歷史還是對于未來,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這是擺在我國學術界面前的迫切任務。在探討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之前,必須弄清工農兵文學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工農兵文學,應該包括兩種:一種是“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趙樹理的小說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而且要表達工農兵群眾的思想感情,還要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另一種是“非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4]筆者在談論工農兵文學時,又曾經指出它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建國前階段、中期的建國后至“”前階段和后期的“”階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謂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主要就是指這一時期。下面,我們具體來論述一下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
工農兵文學的貢獻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嶄新、獨特的典型形象,豐富了我國乃至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前,獨特的典型形象和獨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學作品藝術成就最重要的標尺;而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后,對社會、人生的獨特思想感悟被視作最為重要的成功標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許多讀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夠長久留在人們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為重要的原因。誠然,中國文學有重視典型人物塑造的傳統,古代戲劇和古代小說都塑造出了許多獨特的典型,如崔鶯鶯、杜麗娘、李逵、林沖、賈寶玉、林黛玉、曹操、孫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農兵文學顯然也是在努力繼承這一傳統。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農兵文學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堅的《地覆天翻記》等等,都在盡力地描寫人物性格。但是應當承認,它們都還沒有塑造出一個真正夠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們所寫的人物,雖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為典型形象應有的獨特性和概括力,那種具有深厚文化意蘊的厚重感,都還明顯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楊白勞,依然顯得單薄,且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有某種相似之處。而后期的工農兵文學,即“”期間的工農兵文學,其許許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符號,談不上什么藝術典型。當然,那些至今還留在許多人記憶之中的樣板戲,其中的阿慶嫂,有獨特的個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蘊,可惜描寫得不夠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離。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國后至前的工農兵文學,對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們可以點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漢、林道靜、江姐、楊子榮。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論,典型形象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類型性典型形象。《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和《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屬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紅巖》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則屬于類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稱道的是,無論哪一種、哪一個,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豐滿、獨特的,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地域特點和歷史積淀,因而充滿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和評論文章,在評論這些人物的時候,都只從政治的角度著眼,只注意他們無產階級的階級特征,或者只注意其個性,這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人物身上遠遠突破了階級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蘊。具體說來,他們的性格體現出以下的特點:
1.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說:“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6]74因此,階級性當然是工農兵文學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對于封建地主的仇視和憎恨,無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馮蘭池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系,而是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馮蘭池為了霸占黃河堤下農民們的大片土地,受到農民們的阻撓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領頭抗拒的朱老忠的父親朱老鞏,同時還要對朱老忠斬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為地主的一般的貪婪與兇惡,而且還是屬于非正義的滅絕人性的邪惡,這卻不但是農民而且是全人類都要憎恨和仇視的,因而也就讓朱老忠對他的憎恨變成了對邪惡的憎恨,而朱老忠的報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階級性,而具有了社會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惡、追求正義的社會、文化意義。梁三老漢作為農民,他的階級性表現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這表現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問題上長久猶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長期統治的中國,這種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卻又不是農民所獨有,而是老一代工人、農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猶豫也就有了社會性。而作為類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靜,她是在革命中成長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長進步,并不只是表現為由一個不滿封建軍閥統治的青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戰士,而且是由一個向往公平正義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愿為人民謀幸福的人,她既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又是具有社會正義感的社會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會性。楊子榮當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偵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體描寫了座山雕等匪徒對夾皮溝普通民眾的作惡多端,所以,楊子榮對他們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現出他是清剿國民黨殘匪的英雄,而是一個為民除害的英雄,這同樣也給他的思想性格賦予了社會性。同樣,江姐并不只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的獄中英雄,她面對的是與人民為敵的兇狠無比、喪失人性的國民黨特工,因而,江姐與反對人民的勢力斗爭到底的大無畏精神也有了社會的意義。
2.時代性與歷史性的融合工農兵文學是在大變革的時代格局中審察、認識人物的,因此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但同時工農兵文學又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時代性和歷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時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當時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浪潮的影響和裹挾,具有革命的覺悟和要求,所以他才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識又是歷史上農民造反意識的延續,在他身上,既有水滸英雄的粗豪氣息,也有風起云涌的大革命時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漢既有上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歷史大變動時代的心理波動,又有歷史所造成的下層人民的膽怯和固執。林道靜既有大革命運動時期的革命沖動,又有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先鋒意識。楊子榮既有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時一往無前的氣概,又有歷史上革命志士堅忍不拔的英氣。江姐既有革命勝利前夕的堅韌,也有歷史上革命者舍生取義的文化積淀。
3.地域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成中國地緣廣闊,各地的生活風俗、精神氣質有不少的差異。工農兵文學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這一問題,努力表現人物的地域特點。但是中國又長期形成了大一統的傳統文化。工農兵文學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堅持的“出水才看兩腿泥”的堅韌中,顯現出“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穩的燕趙風骨,而這又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蒼涼之風;梁三老漢身上的保守,既體現出終南山的封閉,又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靜身上既有北方學生的率直和執著,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君子骨氣。楊子榮既有東北軍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武俠氣。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堅韌和沉敏,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韌性。總起來說,朱老忠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有仇必報、勇于反抗的,尋求翻身解放、追尋公平正義的,豪爽、堅韌、凄清的、時代大動蕩中理性的農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著廣大底層民眾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漢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舊的,在社會變革面前猶豫、徘徊的普通農民;林道靜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執著、率性,充滿遠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楊子榮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英勇機智而又豪情滿懷、為民除害的革命偵察英雄;而江姐則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從容、沉敏,為了最廣大人民利益甘灑熱血的無產階級的獄中英雄。
這些典型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獨特的。同是農民的典型,朱老忠明顯的不同于《水滸傳》中的李逵,雖然兩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滿了蒙昧、魯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黨的教育之前,前者也顯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漢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雖然兩者都是種地的農民,但后者懶惰、奸狡,前者勤勞、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靜當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比如吳用,吳用參加起義是以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個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靜則是以追求遠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來感受革命浪潮的洶涌。她也不同于魯迅筆下的狂人和夏瑜,后兩者雖然覺醒,但脫離人民大眾,而前者卻是和人民共同斗爭,她身上體現出一種親民性。江姐更不同于歷史上的造反者,她的從容堅定是由遠大的理想所支撐的,而歷史上的造反者當然沒有這種思想和胸懷。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學史上別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數是王孫貴族,或者資產階級人物,只有少數平民百姓,同時因為“歐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區”在中古“以后漫長歲月里,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征逐漸消失”,“中古歐洲發生了工商業革命,導致了一個工業社會的興起”[7]34,原本樣式的農村和農民已基本不復存在,所以以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不多,真正的農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漢大相徑庭,如19世紀初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小說《艾凡赫》中的羅賓漢,他雖然反抗封建壓迫,但又充綠林好漢,有百步穿楊的絕技,是個傳奇式的人物,“表現出他狹義的性格”[8];巴爾扎克小說《農民》中的尼雪龍是“熱誠地信仰者共和主義理想,嚴格說,不過是小生產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堅硬如鐵,純凈似水”,不謀私利,“忠肝義膽”的、“尋常中的優秀人物”,這一形象“不免顯得有些蒼白”,只能作為“一個道德象征”[9];《堂吉訶德》中的桑丘則是一個樸實善良、機靈樂觀、目光短淺、自私狹隘的普通農民形象;前蘇聯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青年農民潘苔萊是“勤勞作,愛家園,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卻又被虛榮弄得錯頭錯腦,其靈魂卑鄙惡劣”[10]的小人;還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說《戈丹》中的農民何利,是一個雖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無反抗意識的農民。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種追求人民群眾徹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國文學中所有的農民形象絕對沒有的。而梁三老漢那種在新事物面前表現出來的中國式農民的守舊和猶豫,特別是由個人發家致富到集體富裕的歷史性向往,更是外國文學中的農民形象所不具備的。作為知識分子的林道靜和法國作家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于連,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斷追求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則是只圖個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楊子榮一身正義,他是為民除害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化身,而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則是維護正義的個人英雄。江姐是“為天下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奮斗的獄中英雄,而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筆下的牛虻則只是同情下層人民的志士。總的說來,工農兵文學同以往中國文學以及外國文學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別,在于胸懷和理想上面,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是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體,這是他們思想意識的分水嶺。正是在這一點上,充分顯示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獨特性,確立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無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從而豐富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彰顯了工農兵文學的藝術成就和藝術貢獻。否定這些形象的人往往認定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傳的虛假人物,其實從這一時代過來的人都可作證:這樣的人物形象是真實的,因為那一時代就是那樣。
構建革命文學想象
“革命文學”倡導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有比較長的過程,學界一般將其源頭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文學主張。雖然田仲濟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學研究會”已經在“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但當時并未引起學界注意。近年來,有學者揭示了長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漢政權時期出現的“革命文化”、“無產階級文化”[2](P418)言論,另有學者再次把革命文學的源頭明確追溯到“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研究會才是初期革命文學的最先倡導者。”[3]這些不同觀點的出現,其意義不在確認誰是革命文學的首倡者,它的重要價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學研究中的某種思維定勢,為革命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其實,如果把“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適度區別開來,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種關于革命文學的想象,即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創造社“元老”們分別倡導的革命文學。
一、文學研究會倡導的“革命文學”
1921年前后,文學研究會的核心成員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李之常等人在《文學旬刊》、《文學》周報上展開過一次關于“文學與革命”問題的討論,討論者曾積極倡導“革命文學”。一般文學史著作往往從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出發,對這次討論要么避而不談,要么只看作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一種過渡,零星地談到其中的某些觀點,作為文學研究會的“先進性”或“局限性”的注腳。其實,這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關于“革命文學”的討論,更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和意義的文學現象,它展示了文學研究會作家對“革命文學”的獨特想象。其特點主要有:
(一)既強調文學的功利性,也強調其獨立價值
文學研究會以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觀聞名,但它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談文學的使命的。它倡導“革命文學”,也是立足于“文學”。無論是要求揭示現實社會的黑暗,還是要求展示未來社會的光明;無論是強調反映底層民眾生存的悲慘,還是強調要擔當喚醒民眾的重大責任,都是以“文學”為軸心,在強調“文學”具有相對獨立的價值,文學家具有重要的主體性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強烈的文學功利性目的與相對的文學獨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統一。鄭振鐸的《新文學觀的建設》一文,就是從“文學是人生的自然的呼聲”,“文學以真摯的情緒為他的生命”出發,強調“文學之高尚使命與文學之天真”共存,認為:“文學就是文學;不是為娛樂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也不是為宣傳,為教訓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會底文學論》一文中,以與鄭振鐸同樣的思路來說明:在鼓動民眾起來革命的過程中,文學和文學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論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認為:“今日底文學是人類活動底結晶”,是“新時代底指導者,鞭策者”,斷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國舍文學又有什么呢?”[5](P82、81)鄭振鐸、李之常的觀點合乎文學研究會的主流意見。文學研究會在提倡“為人生”的功利性文學觀時,就強調“文學”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應該成為“治文學的人”的“終身的事業”[6](P72)。文學研究會之所以會由最初的著重批判傳統的“文以載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掃除“游戲消遣”的文學,當然有與鴛鴦蝴蝶派爭奪文學陣地和讀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們認為“游戲消遣”的文學既像“載道”文學一樣具有宣揚“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戲”的態度純粹把文學當作“工具”而不是“終身的事業”,因而對“文藝”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現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也宣揚“愛”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