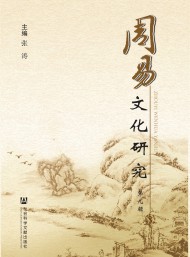明代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7 16:34:31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明代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明代史館研究論文
明代修纂史書的機構——史館,是一個尚未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明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職官志·翰林院》、《明會典·職官·翰林院》等都沒有提到過明代史館,《春明夢余錄·翰林院》雖然在輯錄史臣們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館,但同樣未作具體說明。只有黃佐的《翰林記·史館》(廖道南的《殿閣詞林記·史館》實取自此)對此有50余字的簡單介紹。當代學者對明代纂修活動留意甚多,而對作為纂修機構的史館則較少探討(注:吳晗:《記明實錄》(《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2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討明代修纂活動的論著,以及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等探討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館的論著,均未暇論及明代史館問題。),本文擬就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館基本面貌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凡記注起居,編纂六曹章奏,謄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詩》,《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
深究明代史學轉型的原因
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明代自然災害論文
摘要:“田地陷阱”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迫使廣大農民背井離鄉,甚至棄農經商的重要原因,而“田地陷阱”現象的形成與頻繁的自然災害、定額田賦制度缺陷以及災害應對制度的缺失有著直接的關系。自然災害意味著傳統農業生產所面臨的巨大風險,而定額的田賦征收制度并沒有風險因素的考慮,而在災害發生之時,封建官府非但沒有有效的災害應對措施,而且試圖維護定額田賦制度,力求轉嫁災害風險與損失的舉措迫使廣大災民逃離故鄉,不愿繼續承種土地,“田地陷阱”問題也由此愈演愈烈,其影響與后果均不可低估。
關鍵詞:明代自然災害;明代人口;制度缺失;“田地陷阱”;重賦論;災害風險
土地向來被視為民生之本,農業之基礎,然而,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發展進程中,卻一直存在著一種與珍視土地相悖背的、厭棄與逃避承種土地的離奇現象,筆者稱之為“田地陷阱”。“田地陷阱”問題突出地表現為大量農民畏懼擁有土地,不愿租種土地,甚至離土離鄉,四處流亡。古今許多研究者往往將這種農民逃亡問題歸咎于嚴重的自然災害,不合理的封建田賦制度等諸多因素,特別是賦稅過于繁重的因素尤為討論者所關注。然而,面對“田賦陷阱”現象背后復雜的社會與自然背景,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分析與評價上述某一種因素,都難以給出較為完滿而妥帖的解釋。在本文中,筆者試圖選取中國傳統經濟時代的一個典型時期與一個典型區域——明代山西為研究切入點,在全面分析自然災害與人口變動狀況的基礎上,結合自然災害與定額田賦制度的交互作用,對“田地陷阱”問題的形成進行較深入的探討,進而展現傳統賦稅制度與災害應對制度的致命缺失以及“田地陷阱”對社會心理及價值取向造成的深刻影響,拋磚引玉,以就教于高明。
一、“田地陷阱”問題及其成因解析——質疑“重賦論”
據筆者所見資料,“田地陷阱”之語出自明代大臣周詩的奏疏。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丙戌,周詩在其所上奏疏中明確提出了“田地陷阱”現象,他指出:
方今天下最苦,民貧不樂其生。臣嘗吏于南北,稍知病源。大約豪宦連田阡陌,其勢力足為奸欺,而齊民困于征求,顧視田地為陷阱,是以富者縮資而趨末,貧者貸產而僦庸,又其甚者則弱者逃,強者盜矣……臣又聞淮之南北,逃亡特甚,有經行數千里絕無人煙。
明代流刑探究論文
【內容提要】在傳統的五刑制中,流刑處于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以有效懲治降死一等的重罪作為預定目標。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從隋唐以來,流刑懲治力度不足的問題一直很突出,在降死一等重刑的層面,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調整措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本文對明代的流刑進行了通貫的考察。文章認為,早在明初洪武一朝,傳統流刑已經基本廢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條目基本以“寬”、“減”的形式,以徒役或以贖免的方式得到落實。而流刑所承擔的司法任務則由五刑之外的口外為民與充軍,主要是充軍來完成的。
【關鍵詞】明代流刑口外為民充軍
--------------------------------------------------------------------------------
一
隋唐之際,以徒流刑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確立。在五刑制的確立中,流刑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流刑的來源雖早,然秦漢以來,這種以鄉土觀念為前提的懲治方式并未得到經常的實施,這意味著其懲治力度如何已經很久沒有得到司法實踐的檢驗,這明顯與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漢以來零星出現的“流”,多將犯人流至邊方,其實施的重心仍在勞役,而非流遠本身,這與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后期進入五刑體制,占據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并改變自己以勞役刑為重心的特征,而以把犯人流至遠方作為主要的懲治內容,其中恐怕與魏晉之際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關系。《唐律疏議》注解“流刑三”一條,稱,“《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2]這可能是對這一歷史事實最好的注解。
正是因為流刑進入五刑制有這樣較為特殊的背景,盡管五刑制的確立在中國古代刑罰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五刑制本身從一開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懲治力度不足,與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五刑制剛剛確立的唐代就已經十分明顯。
明代史館研究論文
明代修纂史書的機構——史館,是一個尚未受到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明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職官志·翰林院》、《明會典·職官·翰林院》等都沒有提到過明代史館,《春明夢余錄·翰林院》雖然在輯錄史臣們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館,但同樣未作具體說明。只有黃佐的《翰林記·史館》(廖道南的《殿閣詞林記·史館》實取自此)對此有50余字的簡單介紹。當代學者對明代纂修活動留意甚多,而對作為纂修機構的史館則較少探討(注:吳晗:《記明實錄》(《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2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討明代修纂活動的論著,以及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等探討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館的論著,均未暇論及明代史館問題。),本文擬就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館基本面貌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凡記注起居,編纂六曹章奏,謄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詩》,《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
明代史學研究論文
摘要: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明代宋玉批評
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評,在風起云涌的文學論辯之中,并沒有出現唐代那種儒學復古思潮與新文學思想對于宋玉非褒即貶的兩極走勢,也沒有出現宋代那種文學宋玉批評與理學宋玉批評的涇渭分明的兩極標準,而是表現出與元代宋玉批評的共同走向,即張揚唐宋以來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評主流意識,而優勝于元代宋玉批評的特點則在于對宋玉的文學史地位、文學成就、文學風格等各個方面作出了進一步的時代審美定位。
一、對屈宋文學史地位的新評估: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
關于屈宋的文學史地位,在以復古為尚的有明一代,無論是師范古之文體,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相號召的前后七子,還是體悟古之文心,以“獨抒性靈”為旨歸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這兩者思想傾向的文人學士,他們都在“古”的范疇中討論屈宋的文學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雖以宋代朱學為官學,但又表現出文化界對朱學的疏離,文人學士的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討論又著意淡化朱學而突出屈宋與傳統儒學的關系,在“經”的范疇中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統》說:“《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法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夸,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語中強調屈宋雖非經傳正統,但“文猶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諤軒詩集序》又說:“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后,體裁屢變,而道揚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喭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揚馬多才,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而言蕩,而去古遠矣。”則進一步申明屈宋志“貞”、言“懇”,“道揚諷規猶有三代遺意”。朱右之論盡管以經論文,但對于屈宋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楊士奇,臺閣體代表人物。史稱“歷相四朝,文章德業為一時輔臣之冠”[1]。其《東里集續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說:“律詩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之意,顏、謝以后,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楊士奇評古詩“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評屈宋則“尚有古詩之意”,與“古意雖衰”者大有區別,這也是強調屈宋與古詩三百篇最為接近。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說:“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詠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認為《詩經》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詩言志”之根本。李夢陽,前七子之首。其評屈宋文字見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貞的同年進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錄》(何景明《大復集》附)。汪道昆記述說:“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表明了李夢陽對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師以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與李夢陽齊名。其評論屈宋言論,見于同里樊鵬《何大復先生行狀》(何景明《大復集》附)。據樊鵬所言:“初,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馬,詩許曹、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又見于后賢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復集》附):“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亡于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于其言論之中,“賦賞屈宋”,與李夢陽同調,睥睨千古愿與屈宋等前賢同游,則流露出大復先生對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關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對山集序》稱:“夫文至弘正間盛矣,于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2]其《對山集》卷九《夢游太白山賦序》說:“余歷覽載籍所志,古人之辭,由屈原、宋玉以來不可勝數,而浮靡侈放之辭,蓋托諷寄興者之所共趨,《上林》之后,益蕪益漫,亡能爾雅,志士之所賤也。”評論屈宋“蓋托諷寄興者”,雖有“浮靡侈放之辭”,但與“《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爾雅”,話語中對屈宋表現出充分的肯定。陸深,與前七子中徐禎卿為學友,有文名,史稱“博雅為詞臣冠”[3]。其《儼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隨筆上》說:“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難過,豈氣運然耶!故左氏、莊、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極稱屈宋騷賦獨領風騷,后之為騷為賦者皆追隨之學習之,而皆望塵莫及。
王世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龍后主盟文壇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張助甫》說:“自六經而下,于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于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于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其對屈宋的激賞,繼踵前七子,與李夢陽、何景明完全一致。陸粲,嘉靖丙戍進士,師從當時名儒經學家王鏊,史稱其“嗜學,博通古今”[4]。其《陸子余集》卷一《靜芳亭稿后序》說:“昔者,楚在春秋時為大國,號多人才,若申叔、時聲子、子革薳、啟疆、王子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于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后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辭賦著稱,沨沨乎亦風雅之流亞也。”陸粲以經術論文,以為屈宋“亦風雅之流亞”,褒獎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5]文學思想與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鈔?論列》說:“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將屈宋視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說:“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仆獨謂孔氏之言者圣學也,今人未能學圣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后代,然競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認為屈宋雖“力不足”兼擅詩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賦”,則“絕藝后代”。其對屈宋的評價絕不亞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應麟,曾與王世貞交游,被王世貞稱為末五子之一,文學主張全從王世貞之說。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說:“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榖、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認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師百代”的文學前賢。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中又說:“至先秦盛漢黃初開元大家遺言,若孟莊,若屈宋,若左丘、兩司馬、陳思、李杜十數公,輒廢書太息曰:‘偉哉!六經而后,文不在茲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數公其人,終吾身執鞭其側,何憾哉!’”足見其推崇屈宋等先賢竟到了五體投地的境地。從以上明代關于屈宋文學史地位的評述中不難看出,自明初至胡應麟所處的嘉靖時期,無論是經學人物,還是活躍在文壇上的臺閣體、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學家,這些學術名流對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們一方面從復古的視角出發認為屈宋“文猶近古”,其人是時人文學復古的師范楷模,其作品是時人學習古文的臨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則又從“宗經”的視角出發肯定屈宋為“風雅之流亞”,以經學儒教的標準認同了屈宋對于先圣儒學的精神繼承與文學傳播。盡管“文猶近古”、“風雅之流亞”的評定,在唐代新文學思潮和宋代文學宋玉批評中都有過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對這兩種評定的重申與強調有著與唐宋不同的意義,即認定屈宋的文學作品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語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學精神是明人復古的學習古代文學宗經明道的創作精神。
二、對宋玉辭賦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亞
關于宋玉在辭賦史上的地位問題,在明代學者的認識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騷賦莫及”是為共識,幾乎沒有什么異義,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屈原與宋玉是并列齊名,還是宋玉不及屈原。對于這一問題,元代一些學者曾經有過討論,提出過“騷人稱屈宋,宋豈敵子平”的看法[6],但并沒有將問題引向深入,僅是以漢揚雄對宋玉“詩人之賦”與“詞人之賦”的批評和屈宋的師承關系為依據,而沒有就辭賦文學自身的特點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對于這一問題,明代的學者則逐漸將問題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進一步的新的認知。從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壇時期的宋玉批評來看,基本的特點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觀點,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著重申說宋玉追隨屈原、紹明騷賦的文學貢獻而已。何喬新,景泰五年進士,為“一時名臣”,晚年“杜門著書”,有《周禮集注》《儀禮敘錄》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辭序》說:“蓋《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他以宋玉為屈原后學,是踵武屈原的辭賦作家。皇甫汸,嘉靖進士,以六經為“天地之文肇”,論文偏重義理。馮時可《雨航雜錄》說:“其詩名與王元美相齊。”[7]其《皇甫司勛集》卷三十五《夢澤集序》說:“夫楚多才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于上官,宋玉蒙詬于登徒,禰衡被害于曹瞞,然其志則爭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對古楚先賢之遭際寄與同情,而言“宋玉蒙詬”實在是肯定了宋玉的為人。謝榛,后七子之一,本為七子詩社社長,后因與李攀龍不睦,被排擠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學思想“實自榛發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轉海南方伯詩以寄懷》以宋玉喻友,詩曰:“君才今宋玉,絕代有清標。”比喻中不難看出謝榛對宋玉情有獨鐘的贊賞。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辭序》說:“孔子曾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頒白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鴃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淸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他認為宋玉是最能夠承繼屈原的辭賦家,是屈原的真正傳人。王世貞對于宋玉類似的評論還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說:“楚于春秋為大國,而其辭見絕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國之廢,而屈氏始以騷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輩相與推明基盛。蓋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簡、子美之為之祖。”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續稿》卷五十五《王夢澤集序》說:“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紹明之,及秦漢而后,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京之彥埒,至唐而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差為宏博,與屈氏分途,而皆不朽。”這些言論雖然旨在借屈宋評價唐代詩人,但指認宋玉是屈原的繼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顯的。在明代,將屈原與宋玉并列與否的問題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間及其以后的《楚辭》注釋家和研究者。陳第,嘉靖間人,“學從禪門,證入率由心得,與諸家異”。他曾與學問大家焦竑“相與辨析,竑嘆服,自謂弗如”[9]。
明代流刑探究論文
【內容提要】在傳統的五刑制中,流刑處于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以有效懲治降死一等的重罪作為預定目標。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從隋唐以來,流刑懲治力度不足的問題一直很突出,在降死一等重刑的層面,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調整措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本文對明代的流刑進行了通貫的考察。文章認為,早在明初洪武一朝,傳統流刑已經基本廢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條目基本以“寬”、“減”的形式,以徒役或以贖免的方式得到落實。而流刑所承擔的司法任務則由五刑之外的口外為民與充軍,主要是充軍來完成的。
【關鍵詞】明代流刑口外為民充軍
一
隋唐之際,以徒流刑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確立。在五刑制的確立中,流刑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流刑的來源雖早,然秦漢以來,這種以鄉土觀念為前提的懲治方式并未得到經常的實施,這意味著其懲治力度如何已經很久沒有得到司法實踐的檢驗,這明顯與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漢以來零星出現的“流”,多將犯人流至邊方,其實施的重心仍在勞役,而非流遠本身,這與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后期進入五刑體制,占據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并改變自己以勞役刑為重心的特征,而以把犯人流至遠方作為主要的懲治內容,其中恐怕與魏晉之際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關系。《唐律疏議》注解“流刑三”一條,稱,“《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2]這可能是對這一歷史事實最好的注解。
正是因為流刑進入五刑制有這樣較為特殊的背景,盡管五刑制的確立在中國古代刑罰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五刑制本身從一開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懲治力度不足,與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五刑制剛剛確立的唐代就已經十分明顯。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員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當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滿,“有官者得復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當地,流限一般為六年,不應流而特流者為三年。期滿,即可返回原籍。對于這種流刑的懲治力度,北宋熙寧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說:“---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5]可謂一語中的。還可以再與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然“著鉗若校”,在官吏監督下進行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徒刑實際懲治的強度,與流刑相去不遠,甚至輕重有所倒置。
明代京營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明代制度條文具在,但明前期之制,自明中后期人以下即缺乏精準認識。本文利用《實錄》、原始文件,辨《會典》、《明史》和各種筆記之誤,重新認識京營的成立時間、淵源、職能。永樂、洪熙、宣德之際,北征軍隊不及遣返,常駐京師,遂突破“戰時出征,事畢還衛”原則,漸成常備軍駐京之制;三大營體制來源于靖難戰爭中的北軍體制和永樂歷次北征中的親征軍體制;至正統時期,三大營由戰時體制演化為訓練體制,突破衛所編制,但不合戰爭需要,故明代中期三大營改為兵將相習、隨時臨戰的團營。以上三點結論為以往研究所未涉及,與明代中后期人的系統記載也多有不同。
【關鍵詞】明代前期,京營,三大營,親征。
[Abstract]ThemilitarysystemoftheearlyMingDynastyhadnotbeenexactlyinterpretedsincethelateMing.Thedateofbirth,theoriginandthefunctionoftheCapitalArmy(Jingying)isre-researchedbyMingShilu(MingAnnals)andsomeoriginaldocumentsinsteadofMingHuidian(MingSystem),MingShi(MingHistory)andsomeBiji’s(HistoricNotes).ThethreeconclusionsontheCapitalArmyintheearlyMingaredifferentfromnotonlythoseofotherresearchers,butalsothesystematicrecordsinthelateMing.
[KeyWord]earlyMingDynasty,CapitalArmy,ThreeGiantDivisions,Emperor-headedExpedition
明朝在京師常駐重兵,稱京營,是明軍的核心成分。在正統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變中,不堪一擊的京營遭到毀滅性打擊,明朝隨后在京營的三大營之上設立了兵將相識、練戰一體的十團營。關于此后的京營,史籍中有詳盡而系統的記載,但對此前京營的形成與體制演變,史料記載卻充滿了混亂和矛盾。京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形成標志或者成立時間?京營的三大營體制是由何而來的?三大營的主要職能是作戰還是訓練?澄清以上問題,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時勢雙重作用下的變遷歷程和獨特形態。
一、京營的成立:永樂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代朝貢貿易研究論文
一、互惠模式的朝貢貿易
互惠是朝貢貿易得以長期維系和繁榮發展的基礎。在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雙邊關系中,明朝皇帝深深感受到“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11]可知,明朝想通過這種“厚往薄來”“重義輕利”的貿易來實現對帖木兒王朝的“懷柔”和“羈縻”,進而塑造一種“遠方萬國無不臣服”的盛世景象。實際上,朝貢貿易對明帖雙方都是有利的,一方面,明朝通過豐厚的回賜,使得帖木兒王朝獲利頗豐,進而得到了其尊重,如沙哈魯對明朝“恭敬的態度”正說明了明朝確實在雙邊關系中樹立了自己的威望;此外,明朝通過朝貢貿易獲得了不少稀缺資源,如大批西域良馬通過朝貢貿易輸入中原,緩解了明朝戰馬緊缺的問題,為抵御北方蒙古勢力的不斷侵襲提供了保障。同時,一些異國風味的奢侈品輸入宮廷,也進一步滿足了皇室顯貴的奢侈享受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帖木兒王朝從朝貢貿易中可謂“獲利百倍”,他們向明朝進貢物品的同時,獲得了遠比所貢物品實際價值更大的回賜品,包括鈔、彩幣、絹布、茶葉、鐵器等中原產物,既滿足了他們日常生活所需,又成為他們不畏艱難險阻前來朝貢的動力。同時,正是由于中原地區大量的物品流入撒馬爾罕,也為帖木兒不斷地征服四域提供了物質保障。正因為此,在明代中國則出現了“貢使絡繹乎道,駝馬迭貢于廷”[12]的繁盛陸上絲綢之路。
二、再分配模式的朝貢貿易
對于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朝貢貿易而言,帖木兒王朝在政治上是以“明朝”為其想象中的中心,他通過朝貢的方式把自己國內的土特產品進貢到明朝,然后明朝再根據進貢的具體情況賞賜,其賞賜物品中既有中原地區的特產,如茶葉、絲綢、瓷器等,也有從別的國家進貢過來的各種生活用品等。顯然,明朝在不知不覺中就充當了物品“中轉站”的角色,使得整個朝貢圈中的物品得到了流通,解決了某些物品在一定國家的稀缺情況,如明朝戰馬的緊缺、西域各國茶葉、絲綢、鐵器的緊缺等等。李金明進一步明確指出:“朝貢貿易中的附進物貿易本身就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長途販運貿易,它具有不等價交換、賤買貴賣的特點,朝貢國既可把海外奇珍當作奢侈品運到中國來,又把中國的一般商品運回本國而轉化為奢侈品。[13]可見,在朝貢貿易過程中,雙方都獲得了高額利潤,而這種收益正是朝貢貿易得以長期維系和持續發展的根源所在。此外,朝貢貿易不僅豐富了朝貢圈中大多數國家的物質文化生活,而且在整個亞洲地區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經濟作用。
三、市場交換下的朝貢貿易
帖木兒王朝的朝貢使團從嘉峪關入關后,由甘肅鎮的主管官員按照朝廷的規定將其分為“起送”和“存留”兩類。“起送”指的是從使團當中選取一小部分經過河西走廊前往北京覲見皇帝的成員。非起送者,便是存留,存留使臣分別留居在甘州、肅州二城。[14]“起送”使團到達北京朝貢完畢后,明朝允許貢使可以將帶來的物品在京師會同館開市三天或五天進行自由貿易。同時,明朝規定“凡遠夷之人,或有長行頭匹,及諸般物貨,不系貢獻之數,附帶到京,愿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關給鈔錠,酬其價值”。[15]在交易時,各種行鋪和官吏都可以來會同館公平交易,如果有拖欠貢使金錢而延誤貢使歸期者,也會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存留使臣也會在甘州、肅州兩地的市場上把所攜帶物品銷售出去。葡萄牙旅行家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說道:陜西行省西境的兩個城市甘州和肅州如同廣州省南端的澳門一樣,“全國各地成千的商旅,從那里到來”,“使團大多在上述兩個城市駐留進行商品交易”。[16]實際上,甘州、肅州等地由于受到朝貢貿易的影響,商業十分繁榮,出現了從事各種商品銷售的專門店鋪。由此可知,在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朝貢貿易中,的確存在著以明朝國內市場為基礎的比較發達的價格形成體系,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動因促使帖木兒王朝比較積極地參與到具有市場交換性質的朝貢貿易中,進一步促進了明代朝貢貿易的鼎盛和地域經濟的繁榮。總體而言,互惠、再分配和市場交換三種模式的社會交換理論原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協調,共生于朝貢貿易的整個過程。事實上,在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朝貢貿易中,這三種模式的交換形式都是真實存在的,并且與政治、外交、禮儀等因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毋庸置疑,朝貢貿易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商業貿易,在古代中國周邊各族與內地中原的交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滿足了周邊游各族游牧經濟自身的內在需求,而且中原王朝也通過朝貢在內的各種民族貿易的形式,從周邊地區輸入了大量的畜產品和其他土特產品。這既有力地促進了周邊地區和中原王朝之間資源的優化配置,豐富了內地人民的物質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社會經濟的交流乃至互補。當然,朝貢貿易也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僅僅是周邊民族中上層統治者與他們有密切聯系的少數富商大賈的一種經濟特權,真正受益的也是他們,很難惠及平民。特別注意的是,朝貢貿易是以周邊各族政權與中原統一王朝的進貢與賞賜的為主要貿易形式,而對于沿途經過地區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過境性貿易活動的性質,雖然朝貢貿易也對沿途地區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但其對沿途地區社會經濟的帶動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朝貢使團在返回途中的貿易活動,是相當活躍的,不僅規模大,而且有一定中原王朝命令禁止的商品也在購買之中,這實際上有一定的走私貿易的性質。但毋庸置疑,朝貢貿易正是依賴這種經濟上的互惠而得以長期維系和繁榮發展,這對我們當今重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