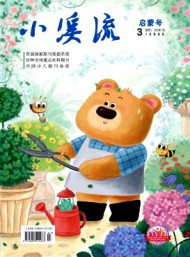啟蒙運動范文10篇
時間:2024-03-05 02:35:39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啟蒙運動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啟蒙運動研究論文
卡爾·波普爾(1902-1994)可稱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的哲學家之一,終其一生都在與“本質主義”及其變形“歷史主義”(又譯為“歷史決定論”),與“整體論”作不懈的斗爭。令人高興的是,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經典著作”的二卷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終于在世紀末擺上了大陸書店的書架。也許總有一天,卡爾·波普爾的名字會像牛頓和達爾文的一樣,出現在我們中學課本和黑板上。
我知道波普爾是從他的一本講演集《通過知識獲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譯,中國美術學院版)開始的。在一個“知識”及“理性”都受盡西方及本土后現代主義奚落的時代,波普爾在這本書中自始自終堅持自己是“啟蒙運動最后一名追隨者”,堅持自己是一名“理性主義者”,“信仰真理與人類的理智”。當然,這不意味著波普爾“信仰人類理智的全能”,并不意味著他希望自己和別人都成為“純粹理性的存在物”。(《西方信仰什么》,《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中國美院版第238頁)更重要的是,波普爾自始至終堅持“批判理性主義”立場:“你可能是正確的,我可能是錯誤的;即使我們的批評性討論不能使我們明確決定誰是正確的,我們仍會希望在討論后對事物看得更清楚。我們都可以互相學習,只要我們不忘記真正重要的不是誰正確,而是我們更接近真理。”(同上第239頁)
波普爾作為啟蒙運動追隨者和批判理性主義者,堅持從康德“人為自然立法”的科學理性立場出發,進而認為是人賦予生活、賦予歷史以意義,從而同黑格爾之流的歷史理性主義者劃清了界線,后者往往為“預言家”和“救世主”們提供了合法性論證。(《通過知識獲得解放》同上第181頁)另一方面他堅持,個人的尊嚴只有在自由批評的氛圍中才能得到體現,具有真理意味的見解只有在公共批評空間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從而同專以“知識即權力”論(尤其在漢語語境中)攪局的后現代主義者劃清了界線,后者把人們對“真理”的探索偷偷換成對各自“動機”的探索。(《框架的神話》,同上第84頁)
在人類的各種權利中,思想自由可說是唯一真正的天賦人權。我們有理由像斯賓諾莎一樣驕傲:能對國家主席生殺予奪的卻無法剝奪顧準的思想自由。然而,波普爾指出:思想自由“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壓制。我們需要別人,以便使我們的思想受到檢驗,弄清我們的哪些觀念是正確的。批評性討論是個人思想自由的基礎。但是這意味著,沒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為每個充分運用他的理智的條件。”(《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頁)盡管誰也無法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但萬馬齊喑的時代究竟是悲哀的,沒有一個公共批評空間,沒有思想者之間的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必然是殘缺的不充分的。
處身于西方語境里的波普爾認為,“批判理性主義”因其內在邏輯注定要與一切傳統相沖突相決裂,但歸根究底,“理性主義是建立在傳統之上的:批評性思考的傳統、自由討論的傳統、簡單清晰的語言的傳統、和政治自由的傳統。”(《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頁)在波普爾看來,自由主義是一種傳統,并非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產物,更非灑熱血拋頭顱的產物。于是文化相對論者底氣十足:既然本土缺乏自由主義傳統(但從不缺少莊子式的“自由”),那么,國人命中注定只能談“紀律”,不能談“自由”了。我以為漢語語境中的自由主義傳統雖然“稀薄”了點,卻并非全無血脈。且不說自孔子倡“有教無類”以來綿延幾千年的私學傳統,單是明清之際遍及江南的文人社黨運動,晚清維新變法以降的結社辦報熱潮,多種詮釋版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毀譽交加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新啟蒙洪流,九十年代至今的學院派自由主義思潮(我先前在一首小詩里譏之為“罐裝自由主義”實在有失厚道),無一不在為本土自由主義傳統培本固元。我們雖然無法預測本土自由主義傳統何時才能長成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卻能斷言:自由主義作為人類普遍倫理之一決非任何風刀霜劍所能戕害的。
波普爾信奉“批判理性主義”,卻從不認為它是唯一的普世宗教或普世真理,從未主張把它載入憲法條款。前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問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麥克米倫: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后者回答是信仰基督教。波普爾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回答,西方社會“不是基督教社會,和它不是理性主義社會一樣。”“基督教要求我們達到只有圣徒才能達到的行為和思想的純潔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會的大量嘗試歸于失敗,其原因即在于此。它們總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不容異說,導致狂熱。不僅羅馬和西班牙可以講述這樣的故事,而且日內瓦、蘇黎世和許多美國基督教的實驗也如此。這些實驗教導我們,敢于實現人間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會到達地獄。不待說,不是基督教的觀念導致了恐怖和殘忍,而是關于唯一的統一觀念的觀念,對一種統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導致了殘忍和恐怖。由于我自稱為理性主義者,我認為,指出理性主義的、羅伯斯庇爾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義,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或猶太人的狂熱的恐怖主義更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6頁)波普爾的告誡不僅對因小安或大富而有意無意地忘卻者,對因無知和憤激而莫名其妙地憧憬者,是一劑不可或缺的良藥,而且對一切奉“市場”為唯一宗教,奉“發展”為唯一真理的偽自由主義者,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清醒劑。針對柏拉圖提出的“誰應當統治”這個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波普爾指出:無論是“哲學家為王”的柏拉圖式答案,還是“人民為王”的盧梭式答案都是錯誤的,因為問題本身是錯誤的。正確的提問應該是“應當授予政府多大權力?”或“我們如何才能這樣發展我們的政治制度,即甚至無能的和陰險的統治者也不能造成過多的危害?”換言之,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約束與平衡的問題,政治權力的獨斷專行如何用制度控制的問題。(《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頁)
反啟蒙運動研究論文
對法國啟蒙運動及其在歐洲各國的盟軍和弟子的核心觀念的抵抗,與這場運動本身一樣古老。宣揚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觀察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是惟一可靠的求知方式,從而否定宗教啟示的權威,否定神學經典及其公認的解釋者,否定傳統、各種清規戒律和一切來自非理性的、先驗的知識形式的權威,自然會受到教會和眾多派別中的宗教思想家的反對。不過,主要是由于他們和啟蒙運動哲學家沒有共同的基礎,所以這種反對并無多大進展,只是激起了對那些被視為威脅教會和國家權威的觀念的傳播所采取的鎮壓措施。更可怕的反對來自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傳統。持進步主義信條的法國思想家,不管其內部有何分歧,他們都是基于一種以古代自然法學說為根源的信念:無論何時何地,人性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地域或歷史中的多樣性,與恒久不變的內核相比是不重要的,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也正是因為這個內核,這與定義動物、植物或礦物的道理相同;存在著普遍適用的人類目標;可以制定出一個合乎邏輯的、易于檢驗和證實的法律和通用規則的結構,以此取代無知、精神惰怠、臆斷、迷信、偏見、教條和幻覺所造成的混亂,尤其是人類統治者所堅持的"同利益有關的錯誤",它們應對人類的挫折、罪惡和不幸負主要責任。
牛頓物理學在無生命的自然王國里連連獲勝,人們相信,和它相似的方法,也可同樣成功地用于幾乎沒有多少進步可言的倫理學、政治學以及一般人類關系的領域。一旦這種方法生效,不合理的、壓迫人的法律制度及經濟政策就會被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理性統治將把人們從政治和道德的不公正及苦難中解救出來,使他們踏上通往智慧、幸福和美德的大道。始終存在著一種反對這種觀點的學說,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智者學派的普羅泰哥拉、安提豐和克里蒂亞斯,認為包含著價值判斷的信念和以此為基礎的各種制度,并不取決于對客觀不變的自然事實的發現,而是取決于人類的意見,后者是可變的,會隨著社會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道德和政治價值,尤其是正義和一般社會安排,都是建立在變動不定的人類信仰上。亞里士多德引用過的一位智者對此做了總結,他宣稱,此地和波斯都有火在燃燒,但人類的制度就在我們眼前發生著變化。因此似乎可以說,在人類事務方面,原則上不可能用科學方法確定普遍真理,即無論處在什么時代。什么地方的任何人,都能使用正確的方法加以證實的真理。
這種傳統在十六世紀的懷疑論者科爾內里烏斯·阿格里帕。蒙田和沙朗的作品中得到了有力的重申,他們的影響又可在伊麗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時代的思想家和詩人的感情中找到。這種懷疑主義也幫助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否定自然科學或其他普遍理性方案的主張,宣揚維護純潔的信仰,例如那些偉大的新教改革家和他們的追隨者,以及羅馬教會的冉森派。存在著一個單一的、通過邏輯演繹得出的結論的嚴密體系,它是運用普遍正確的思維原則的結果,并且是建立在小心篩選出的觀察或實驗數據上--這種理性主義的信念,被從博丹到蒙田等有社會學頭腦的思想家進一步動搖。這些作家既利用歷史的證據,也利用在亞洲和美洲等新大陸的旅行和探索所提供的新文獻,強調人類風俗的多樣性,特別是不同的自然因素,具體而言是地理因素,對不同的人類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它們導致了制度和世界觀的不同,而這又造成了信仰和行為的巨大差別。大衛·休漠的革命性學說,尤其是他證明了事實真理同邏輯或數學中的先驗真理之間不存在邏輯關系,也大大強化了這種觀點。休漠的這些思想有可能使某些人的希望破滅,他們在笛卡爾及其追隨者的影響下,認為能夠根據任何經驗都無法駁倒或改變的普遍正確的公式,通過一系列嚴密的邏輯論證步驟,建立起一個包羅萬象、能夠解答一切問題的單一知識體系。
然而,人類價值或對包括歷史事實在內的社會事實的解釋的相對性,不管多么深地進人了這些社會思想家的頭腦,他們仍保留著一種共同的核心信念,即所有時代的所有人的終極目標,其實是一樣的:人人都追求基本的物質和生理需要的滿足,譬如食物、住所、安全,以及和平、幸福、正義、個人天賦的和諧發展,真理,甚至包括更含糊不清的美德、道德完善以及羅馬人所謂的高貴人格。氣候冷暖,山地國家和平原國家的差別,可能會使手段有異,只要不是強求一致,適合所有情況的普遍公式就不存在,然而終極目標本質上卻是一樣的。這一類有影響的作家,如伏爾泰、達朗貝爾和孔多塞,都相信藝術和科學的發展是人類達到這些目標最強大的武器,也是反對無知、迷信。空想、壓迫和野蠻制度--它們束縛人類的努力,阻撓人們追求真理和理性的自我定向--最銳利的武器。相反,盧梭和馬布利相信,文明的制度本身就是使人類腐敗,脫離自然和內心單純,脫離符合自然正義、社會平等以及自發人類感情的生活的一個主因;矯揉造作的人囚禁、奴役和敗壞了自然人。但是,盡管有這些深刻的觀點分歧,在某些重要的問題上卻存在著廣泛的一致:自然法(不再是以正統的天主教或新教教義的語言加以闡述)和永恒原理的真實性,只有遵守它們,人們才能夠變得聰明、幸福和自由。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著世界,有神論者、自然神論者和無神論者,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清教徒和原始主義者,相信進步以及科學和文化最豐碩成果的人,莫不如此認為。這些規律既支配著無生命的自然,也支配著有生命的自然,支配著事實和事件、手段和目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支配著所有的社會、時代和文明;只要一背離它們,人類就會陷人犯罪、邪惡和悲慘的境地。思想家們對這些規律是什么、如何發現它們或誰有資格闡述它們也許會有分歧;但是,這些規律是真實的,是可以獲知的(或者是十分確定,或者只是極有可能)--這仍然是整個啟蒙運動的基本信條。而對它的攻擊,則是對這種主導信仰體系最可怕的反對。
在這場反對運動中可能發揮過決定性作用的一位思想家,是拿波里的哲學家吉安巴蒂斯塔·維柯。他以不同尋常的原創精神,特別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科學》中堅信,笛卡爾主義者認為數學有著科學之科學的地位,是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數學具有確定性,僅僅是因為它乃人類的發明。它并不像他們設想的那樣,與實在的客觀結構相~致;它只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個真理體系;借助于它,我們能夠探明規律--外部世界現象的發生--但并不能發現它們為何那樣發生或為什么目的而發生。這是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的事情,因為只有事物的制造者,才真正了解它們是什么以及它們是為什么目的而被制造。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并不了解外部世界--自然--因為它不是我們制造的;只有創造了它的上帝才了解它。不過,由于人直接擁有人類的動機、意圖、希望和恐懼,這是他們自己的東西,因此他們能夠認識人類的事務,正如他們不能認識自然一樣。
按維柯的觀點,我們的生活和活動,不管是集體的還是個人的,反映著我們為求生存、為滿足我們的各種欲望、為相互理解并理解我們自己的過去所做的努力。對最基本的人類活動的功利主義解釋是錯誤的。首先,它們是純粹表現性的;唱歌跳舞,祭拜神抵,言談和戰斗,以及使這些活動得以實現的各種制度,構成了一種世界觀。語言、宗教儀式、神話、法律、各種社會、宗教和司法制度,都是自我表達、希望表明人是什么以及追求什么的不同形式;它們遵循著可以理解的模式,因此,再現另一些社會的生活,甚至在時空上相距遙遠的社會的生活,是可能的,只要我們問一下自己,什么樣的觀念、感情和行動架構能夠產生詩歌、紀念物和神話。人們的成長包括個性和社會性兩個方面;產生了荷馬史詩的社會,與上帝通過他們的圣典向他們說話的希伯來人的社會,或羅馬共和國的社會、中世紀的基督教社會、波旁家族統治下的那不勒斯城,顯然是大不相同的。成長的模式有跡可尋。
新啟蒙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我國化論文
20世紀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啟蒙運動史上的重要環節。它以“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為口號,宣揚愛國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倡導新文化建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啟蒙的歷史局限,實現了啟蒙目標的現實化、啟蒙武器的民族化、啟蒙態度的理性化、啟蒙主體的大眾化和啟蒙哲學的科學化。在國難當頭的艱難形勢下,它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一、新啟蒙運動提倡“中國化”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開始于,而形成大規模和廣泛深刻的影響則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從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提出,雖然經歷了長期的認識過程,但有其邏輯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啟蒙運動的歷史功績不可忽視。這是因為,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闡釋和探討。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張申府從文化建設的角度提出學習西方的文化必須走“中國為主”的“中國化”道路。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信奉者,張申府認為文化建設不能離開本國的國情,不能沒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統一體,“一般”必須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體表現。因此,“許多外來的東西,我們以為,用在中國就應該中國化。而且如其發生效力,也必然地會中國化。”(張申府:《論中國化》,《戰時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則是這一運動中“中國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學是推動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學脫離實際而變成空洞的理論,那是相當有害的。為此,他在批評哲學界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的同時,殷切地希望中國的哲學界盡快“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他提出,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所發表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的科學規律,承認它有一般的指導的作用,而同時卻一刻也不能忘記,這些規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中間,因為客觀條件的差異,而有各種各樣特殊的表現形式。因此,當我們在中國的社會里來應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也必須要具體地了解中國社會。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馬克思主義,真正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中國化”的內涵上,新啟蒙運動者指出,“中國化”決不是要求大家“抱殘守缺”,也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中國本位論”的再版,“它的內容是豐富的、歷史的、民族的,同時是國際的”,“它是綜合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它是我們一切優良珍貴的傳統以及國際的一切優良的傳統的一種交流,是代表人類最進步的立場,創造世界新文化一環的中國新文化”。
在關于“中國化”途徑的探討中,新啟蒙者認為,應該“有條件地吸收國際文化,批判接受中國歷史的傳統,融合貫通”(《柳湜文集》,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815頁),要依靠傳統的民族形式,創造真正中國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則從研究“中國的特殊性”出發,提出,“當我們在中國的社會里來應用來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必須要具體地來了解中國的社會。”
啟蒙運動中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啟蒙運動基督宗教人文主義美國國父法國革命
論文提要中國學界一般以“理性主義”來概括啟蒙思想,并據此得出啟蒙運動中的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相對立的結論。本文先分析啟蒙思想在英國的代表洛克的“經驗主義”、在法國的代表盧梭的“情感主義”、在德國的代表康德對理性的批判,揭示這三大思想家對基督宗教的正面態度;再分析伏爾泰等抨擊教會的法國思想家對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態度;最后對比了啟蒙思想的實踐者即美國國父們與法國革命領導人對基督宗教的態度之不同,及其對兩國革命與后果的影響之不同。文章反駁了上述流行結論,指出基督宗教不但為人文主義提供了神圣的核準,而且提供了必須的補充。
1.對于啟蒙運動這么一個偉大的歷史運動,由于其中包含無數燦若明星的思想巨匠,紛紜萬千的思想杰作,而其復雜多變的思想潮流更如滾滾滔滔的長江大河,包含著數不清的支流和NC027流、漩渦和瀑布、淺灘和急流,絕不可能在這短短的篇幅中給出一幅完整的圖景。我們在此所能做的,只是就其與我們的主題有關的方面,即從十七至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中人文精神與基督宗教的關系方面,作一點與流行觀點不同的思考與評論。
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中國人對于啟蒙運動的一般看法中的某些缺失。這種缺失最突出的表現,是用“理性至上”來代表啟蒙運動的一般特點。與此相關,中國作者關于啟蒙運動的描述,多半都強調啟蒙學者們將所有的東西都“置于理性的審判臺前”,尤其是將理性與宗教對立起來,將二者說成“理性啟蒙”與“宗教愚昧”的關系,甚至還說成進步與保守、革命與反動的關系。這些說法里包含的諸多片面或曲解,都同對啟蒙時期歷史事實的片面描述有關,其中也涉及對當時思想家們與基督宗教的關系和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的片面描述。
一般而言,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整體的思想傾向,都符合廣義的人文主義。但是這種傾向,卻未必都符合我們所說的人文精神——例如,某些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關于“人是機器”的說法,很難說有利于提高人的地位和強調人的價值。另一方面,這種傾向也未必是與基督教精神相違的——恰恰相反,那些并不脫離基督教精神的啟蒙思想家,都對人的自由的高度張揚,對人的地位的實際提高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這里最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強調經驗甚于理性的洛克,強調情感甚于理性的盧梭,以及強調實踐理性甚于純粹理性(也可以說是強調廣義的道德甚于狹義的理性)的康德。
現代啟蒙批判合理性管理論文
摘要:啟蒙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因此在現代性的風潮中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啟蒙自身的痼疾,又摻雜著包括浪漫主義在內的現代批判者的盲目與過火。現代啟蒙批判在挖掘出了一些真問題同時,以其自身的行動確證了啟蒙的永恒價值。現代啟蒙批判總體上就是一種啟蒙。
關鍵詞:啟蒙;批判;浪漫主義;問題意識
Areflectionon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
Abstract:AlthoughEnlightenmenthadgainedagreatachievement,italsohasbroughtlotsofproblems,henceitconfrontedadestructivecritiqueinthemoderntimes.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canbeinquiredfrommanyaspects,duringwhicharetwomainpoints,firstfromtheEnlightenmentitself,secondfromtheblindnessandoverreachednessinmoderncritique.ThemoderncritiqueofEnlightenmentitselfisacertainkindofenlightenmentessentially。
Keywords:Enlightenment;critique;romanticism;problematicconsciousness
一
論現代啟蒙批判的合理性
摘要:啟蒙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因此在現代性的風潮中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啟蒙自身的痼疾,又摻雜著包括浪漫主義在內的現代批判者的盲目與過火。現代啟蒙批判在挖掘出了一些真問題同時,以其自身的行動確證了啟蒙的永恒價值。現代啟蒙批判總體上就是一種啟蒙。
關鍵詞:啟蒙;批判;浪漫主義;問題意識
一
作為“理性的勇氣和思想的激進主義”(卡西爾語)之象征,啟蒙運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毫無疑問,通過把科學的方法運用于人類的普遍事務和人類永恒幸福的追求,啟蒙運動已經作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減輕了人類的苦難,避免或者阻止了不公正,揭示了無知;教條得到了反駁,偏見和迷信成功地受到了公眾的嘲笑。啟蒙時代的人們相信,求助于主義、無知和權威以證明專斷行為的合理性是行不通的,那只不過是自私、懶惰、愚昧或我無聊的托辭。事實表明,如果拿這段倍受詰難的啟蒙運動的歷史來與19世紀更為混亂的理論表征和20世紀傷痕累累的歷史記憶相比較的話,我們肯定會意識到啟蒙運動的思想更少引人誤入歧途。由此看來,“18世紀天才的思想家們的理智力量、誠實、明晰、勇敢和對真理的無私的熱愛直到今天還是無人可與之媲美的。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人類生活中最美妙、最富有希望的樂章。”[1](P25)無論從哪個方面說,極具天才特性的啟蒙運動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在這期間,啟蒙運動不僅提高了人類生活在物質方面的舒適水平,而且緩解了人類的饑餓、疾病和恐懼的痛苦。在啟蒙的旗幟下,個人的天才力量和理智無畏的探險共同構筑了一個“英雄化”的時代,這使得我們今天視為進步的許多成果相形之下變得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合理的現實存在都不是最終的,都必將面對歷史的烈焰和事實的考驗。曾經是啟蒙運動一面大旗和時代精神標志的那個巨大的疑問詞Quid(為什么)如今又懸在了后啟蒙運動時代的上空,成為人們心靈中一個新的興奮點(其實這種疑問和驚異乃是人類的基本本性)。后來的浪漫主義、存在主義、解構主義甚至幾乎所有的現代哲學都以“啟蒙”的Quid來質疑啟蒙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所有的光榮夢想徹底幻滅后,康德的誠實之思就變成了數學上的費馬大定理。康德欣喜地看到:“人類走向改善的轉折點即將到來,它現在是已經在望了。”[2](P163)歷經滄桑巨變的我們卻不禁要問,這位誠實可靠而又嚴肅認真的哲人是憑借什么來認為“人類是在不斷朝著改善前進嗎”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除去被人們抨擊過的理性樂觀主義之外,康德似乎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因而對該答案的求證就成了后康德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或者說,證實或證偽這個思想史上的“費馬大定理”就成了左派、右派以及中間派的共同目標。由此福柯才會認為,“現代哲學沒能解答而又無法擺脫的這個問題(按指“何為啟蒙”)隨著此文(按指康德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而悄然進入思想史中。”[3](P528)也許啟蒙是一個永恒的,即所謂“不能解答而又無法擺脫的”問題。雖然人們沒能解決該問題,但該問題卻不斷地滋養著后世的思想。同樣地,康德的啟蒙之思終究成了現代問題意識的源泉。
現代學術思想由于缺乏統一的嚴密的研究綱領,因此在較為零碎的發散性研究中,學者們往往以標新立異、另辟蹊徑或者不落窠臼、不落俗套為美學境界。加之近現代歷史的巨變導致人們心態失衡,怨心濃烈,在激蕩的歷史境遇中往往以“證偽”的方式來求得思想的發展。對啟蒙而言,后世的思想家大多從否定的方面來看待先輩的學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必須的,所謂相反者相成,同時也是持不同意見者的正當權利。但無論如何,單向度(one-dimensional)以及過火(overreached)的批判都有陷入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洪流中去的危險。而如果要超越時下對傳統的“解構”或“酷評”(套用坊間的世說新語)的混亂和偏激,同時又能挖掘出一些真問題,我們必須小心在意。的確,我們是在泥沼上尋找著前進的道路。
啟蒙主義發展途徑與新時代愛情小說略論
啟蒙主義自五四時期傳入中國文學以來,以極強的生命力在中國文學的沃土上瘋長,20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新啟蒙主義”,既爾九十年代末又有了“后啟蒙主義”的旗幟。在其成長的歷程中,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新時期愛情小說僅是文學大豹之一斑,借此談點自己的陋見和淺識。
一、啟蒙運動的發展脈絡
在論述啟蒙的概念時,我們很容易想到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的論述:“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我國文化界接納康德的啟蒙主義,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發展。
1936年底,以還原五四啟蒙精神、承傳五四民主傳統的新啟蒙運動在艾思奇、陳伯達、張申府、胡繩等進取的知識分子中間展開。張申府在《什么是新啟蒙運動》中說:“就字面說,啟蒙就是開明的意思。再分別說,啟蒙就是打破欺蒙,掃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啟蒙運動都必要三個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2]艾思奇在同題文章中解釋說:“為什么叫做新啟蒙運動呢?因為中國過去的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高峰)是一種啟蒙運動,而現在的這一個文化運動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啟蒙運動。”至于為什么還需要來一個新啟蒙運動,作者的回答是:“因為舊的啟蒙運動沒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3]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王元化為龍頭的“新啟蒙”就是在這個時期順應潮流,并被推到浪尖上的。[4]
進入1990年代以后,學者們在經過熱情的實踐和冷靜的反思后發現,新啟蒙主義也并不是完美的,所以開始了對新啟蒙主義的“反思和批判”,這就是被稱之為“后啟蒙”時代。
文藝復興歷史作用研究論文
自七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關于歐洲文藝復興,發表了一些文章和著作,主要論述了文藝復興在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成就,但是關于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觀點多有分歧,談得不夠。本文試圖就文藝復興的思想解放作用及與啟蒙運動的關系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
一
“文藝復興”一詞,原意系指“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是,當時西歐各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包括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對經院哲學和僧侶主義的否定;藝術風格的更新;方言文學的產生;空想社會主義的出現;近代自然科學的開始發展;印刷術的應用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等等。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與其說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說是“近代文化的開端”;與其說是“復興”,不如說是“創新”。“文藝復興”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標志著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是新文化,是當時社會的新政治、新經濟的反映,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思想和文化領域里的反封建斗爭。
恩格斯曾高度評價“文藝復興”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他寫道:“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45頁。)
如果說地理大發現是人類向未知的物質世界進軍的話,那么文藝復興則是人類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進軍,是在精神世界中進行的探索。這個探索在文學、藝術、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學領域內創造了豐碩的成果。文藝復興的重大歷史意義在于它促使歐洲人從以神為中心過渡到以人為中心,在于人的覺醒,在于人們把重點從來世轉移到現世。它喚醒了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創造精神以及科學實驗的精神,從而在精神方面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和確立開辟了道路。文藝復興在歐洲歷史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人的發現。與中世紀對比,文藝復興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帶來了一系列巨大的變化。最突出的變化是關于人價值觀念的轉變。在中世紀,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不足稱道。文藝復興發現了人和人的偉大,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創造力,提出人要獲得解放,個性應該自由。重視人的價值,要求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反對消極的無所作為的人生態度,提倡積極冒險精神。重視現世生活,藐視關于來世或天堂的虛無飄渺的神話,因而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在文學藝術上要求表達人的感情,反對虛偽和矯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談》。重視科學實驗,反對先驗論;強調運用人的理智,反對盲從;要求發展個性,反對禁錮人性;在道德觀念上要求放縱,反對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認為事業成功及發家致富就是道德行為。提倡樂觀主義的人生態度。這種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對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個究竟,決不滿足于一知半解的精神,為創造現世的幸福而奮斗的樂觀進取精神,把人們從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資產階級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創造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發現,就是這種人文主義精神的外在表現。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而“地理大發現”的主角哥倫布和卡波特都是意大利人。他們都是在人文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參加地理探險事業的。哥倫布不顧艱難險阻,投身于充滿危險,艱苦的探險事業,就說明他富于樂觀進取和積極冒險的精神。趨使他遠渡重洋,翻水越浪的動力,是尋找黃金的強烈欲望,也是為了追求現世幸福的渴望。向西尋找去東方的航路,是建立在地球是圓形的科學信念上的,也說明他堅信科學實驗的精神及探求精神。可以說“地理大發現”是文藝復興運動的副產品。當然促成地理大發現還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及條件,但是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的時代精神相吻合,是毫無疑義的。
啟蒙時代歷史觀探析論文
一、18世紀理性開啟歷史新方向
通常人們把18世紀的西方史學界定為“理性主義史學”,因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特征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是一股彌漫整個歐洲的社會思潮,因而歷史學領域也不例外。(注: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頁。)然而何謂“理性”?則大多不予追究。正如德國文化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所說:“18世紀的精神通常被描述為一種‘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義意指一種超然冷漠和抽象玄奧的態度,并與實踐的、社會的、和政治生活實際相脫離的話,那么,沒有任何描述會比這更不恰當,更易為人誤解的了。”(注: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頁。)可以說“理性”是一個極易引起分歧而又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18世紀理性不是狹隘意義上的理性,而是一種比較樸素意義上的、古典意義上的理性。
18世紀理性是與基督教信仰相對立的。當時的啟蒙學者把理性看作是與宗教信仰相對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狄德羅在《百科全書》的“理性”一條中指出,理性是“人類認識真理的能力”,“人類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幫助而能夠自然達到一系列真理”。在他們看來,理性是一種“自然的光亮”。康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總結和頌揚了啟蒙運動,康德發表于1784年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中指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注: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2頁。)因此,理性是自然而然的智慧,理性是通向真理的直接向導。
不過,18世紀理性也是與形而上學體系相對立的。與17世紀唯理論理性相比,18世紀理性更富有古典哲學的意味。英國歷史學家阿倫·布洛克專門考察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分析了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的相似性,指出: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一樣,18世紀的哲學家也崇拜經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義者一樣,他們對抽象哲學體系沒有耐心,不僅攻擊天主教經院哲學,而且也攻擊笛卡兒的唯理論。他們在說理性的時候,心中想的是對智力的批判性、破壞性的運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邏輯體系的能力。他們是經驗論者,是經驗和常識的哲學家,不是17世紀笛卡兒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論者。他們……對形而上學沒有興趣,關心此時此地的人生中的實際問題——道德的、心理的、社會的問題。(注: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7頁。)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揭示了“近代頭腦”更關懷事實和現實的思想特征,“近代輿論氣候的性質乃是事實性的更多甚于是合理的。支撐我們思想的那種氣氛是如此飽和著現實性的東西,以至于我們只消有最低限度的理論性的東西,就很容易過得去了。”(注:卡爾·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3頁。)
18世紀理性與笛卡兒唯理論有著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識必須形成體系,而是它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注:哈多克:《歷史思想導論》,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一斷語:“啟蒙運動的靈感部分來自笛卡兒、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論,但是這個運動的真正創始人是艾薩克·牛頓和約翰·洛克”。(注:伯恩斯、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301頁。)可以說,“敢于認識”是啟蒙運動的座右銘,而“實踐成了啟蒙運動的口號”(注:哈多克:《歷史思想導論》,第94頁。)。
如果說17世紀的唯理論理性具有一種“體系癖”,那么18世紀理性則是沖破唯理論體系的“獨創力量”。對于18世紀啟蒙理性,卡西爾有著更冷靜的分析和更富建設性的思想體系。卡西爾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精辟地闡明了18世紀理性的內涵與特征,指出18世紀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還原與理智重建的雙重功用。理性的性質和力量只有根據它的功用才能看清。(注:卡西爾:《啟蒙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頁。)正是這種功能上的理性而非純邏輯演繹的理性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是其出發點也是結果,是旗幟也是前進的動力,是它特殊的魅力也是真正的體系價值所在。卡西爾說:“或許沒有哪個時期會像18世紀那樣,在理論和實踐、思想和生活之間,存在一種較為完全的和諧。一切思想都立刻轉化為行動;一切行動都從屬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論標準而下的判斷。正是這種特征給予了18世紀的文化以力量和內在的統一。”(注:卡西爾:《國家的神話》,第219頁。)
啟蒙時代歷史觀分析論文
一般把18世紀初到1789年法國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稱為啟蒙時代。這一時期,是啟蒙運動“真正重要的階段”(注:伯恩斯、拉爾夫:《世界文明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301頁。)。作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啟蒙理性主義沖擊了幾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領域,包括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開創了啟蒙時代的文化新氣象。其中,歷史學作為一個新興而重要的思想領域,其知識地位得到首次確認,形成了獨特的印記并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力量。
一、18世紀理性開啟歷史新方向
通常人們把18世紀的西方史學界定為“理性主義史學”,因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特征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是一股彌漫整個歐洲的社會思潮,因而歷史學領域也不例外。(注: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頁。)然而何謂“理性”?則大多不予追究。正如德國文化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所說:“18世紀的精神通常被描述為一種‘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義意指一種超然冷漠和抽象玄奧的態度,并與實踐的、社會的、和政治生活實際相脫離的話,那么,沒有任何描述會比這更不恰當,更易為人誤解的了。”(注: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頁。)可以說“理性”是一個極易引起分歧而又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18世紀理性不是狹隘意義上的理性,而是一種比較樸素意義上的、古典意義上的理性。
18世紀理性是與基督教信仰相對立的。當時的啟蒙學者把理性看作是與宗教信仰相對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狄德羅在《百科全書》的“理性”一條中指出,理性是“人類認識真理的能力”,“人類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幫助而能夠自然達到一系列真理”。在他們看來,理性是一種“自然的光亮”。康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總結和頌揚了啟蒙運動,康德發表于1784年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中指出:“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注: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2頁。)因此,理性是自然而然的智慧,理性是通向真理的直接向導。
不過,18世紀理性也是與形而上學體系相對立的。與17世紀唯理論理性相比,18世紀理性更富有古典哲學的意味。英國歷史學家阿倫·布洛克專門考察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分析了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的相似性,指出: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一樣,18世紀的哲學家也崇拜經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義者一樣,他們對抽象哲學體系沒有耐心,不僅攻擊天主教經院哲學,而且也攻擊笛卡兒的唯理論。他們在說理性的時候,心中想的是對智力的批判性、破壞性的運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邏輯體系的能力。他們是經驗論者,是經驗和常識的哲學家,不是17世紀笛卡兒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論者。他們……對形而上學沒有興趣,關心此時此地的人生中的實際問題——道德的、心理的、社會的問題。(注: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7頁。)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揭示了“近代頭腦”更關懷事實和現實的思想特征,“近代輿論氣候的性質乃是事實性的更多甚于是合理的。支撐我們思想的那種氣氛是如此飽和著現實性的東西,以至于我們只消有最低限度的理論性的東西,就很容易過得去了。”(注:卡爾·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3頁。)
18世紀理性與笛卡兒唯理論有著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識必須形成體系,而是它必須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注:哈多克:《歷史思想導論》,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一斷語:“啟蒙運動的靈感部分來自笛卡兒、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論,但是這個運動的真正創始人是艾薩克·牛頓和約翰·洛克”。(注:伯恩斯、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301頁。)可以說,“敢于認識”是啟蒙運動的座右銘,而“實踐成了啟蒙運動的口號”(注:哈多克:《歷史思想導論》,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