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財產法團體主義特征論文
時間:2022-10-27 08:17:00
導語:外國財產法團體主義特征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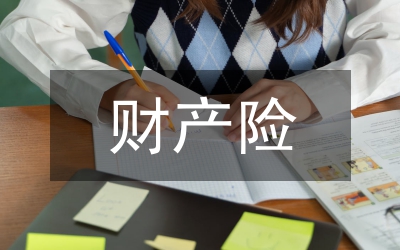
內容提要:本文論述了日耳曼財產法團體主義的特征、成因及意義。文章分四部分:首先,指出了日耳曼財產法中的團體主義在法律上主要表現為雙重所有權,并著重介紹了“支配權”(Gewere)制度,由此導出與團體主義相關聯的財產轉讓的地域性和形式主義;其次,將這種帶有團體主義色彩的日耳曼財產法與羅馬法進行了比較,揭示其在財產觀念和財產權利體系上具有不同特點;再次,文章認為導致日耳曼財產法團體主義的成因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財產觀念、社會經濟形態和王權的作用,其中著重探討了王權的作用;最后,對日耳曼財產法的這種團體主義特征進行了評價。
正如歷史學家們所說,“就在基督教從內部征服羅馬帝國的同時,日耳曼蠻族部落正從外部威脅著羅馬帝國。”[1]公元5世紀中葉,在西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東哥特、西哥特、法蘭克、汪達爾和勃艮第等日耳曼王國,大多數是直接從原始社會轉向封建制國家,仍然保留著大量的習慣法,并在日耳曼人中廣泛適用;而同時,日耳曼征服者讓羅馬自由人“仍保持其自由,相互間仍得自由生活在其羅馬法之下”[2]。不過,隨著羅馬人和日耳曼人的交往頻繁,“爾后條頓因素之吸收入羅馬因素之中,以及日耳曼征服者之接受被征服人民之語言文字,究不過一時間問題耳。”[3]但是,這一融合的時間進程卻是緩慢的,它幾乎經歷了幾個世紀:從公元5世紀到9世紀,各種社會成分、組織之間相互爭吵、斗爭,呈現一種混沌狀態,這實質上是中世紀封建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日耳曼習慣法經羅馬法學家和基督教僧侶的改造,歐洲大陸出現了眾多“蠻族法典”,如《尤列克法典》、《耿多伯德法典》、《薩克森法典》、《巴伐利亞法典》和《薩利克法典》[4]等;在不列顛也有盎格魯•薩克森人頒布的《埃塞伯特法典》、《伊尼法典》和《阿爾弗特列法典》等。這些法律對財產的規定,大都帶有日耳曼法的特征:團體主義。這種特征對整個歐陸封建時代都有重大影響,并通過羅馬法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的生活。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日耳曼財產法中的團體主義
在法律關系方面,日耳曼財產法中的團體主義集中地表現在“雙重所有權”(differenttitle)制度之中。有些羅馬法學家也喜歡把日耳曼法中的這種較為復雜的“所有權”解釋為“分割所有權”,以此來適應羅馬法理論。所謂“雙重所有權”,是指將同一土地的所有分為“上級所有權”(拉丁文為“dominiumdirectun”)和“下級所有權”(或“利用所有權”,拉丁文為“dominiumutile”)兩種,它們分別代表領主(或地主)對土地的管領權、處分權和耕作人對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這就不同于羅馬法的“一物一權原則”,有較大特色。[5]有位日本學者描繪這種景象時說,“狩獵權與漁業權以及在中世紀存在的無數種特權,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重要的財產。物在一方面服從某一個人支配;同時也可以在另一方面服從于他人的支配。例如,土地的管理、處分等方面服從團體或領主的支配,在使用、收益等方面服從團體成員或臣下的支配。”[6]法律史學家亨利•梅因認為,這一特色幾乎成了中世紀歐洲土地所有權的主要特點:“封建時代概念的主要特點,是它承認一個雙重所有權,即封建地主所有的高級所有權以及同時存在的佃農的低級財產權或地權。”[7]
而事實上,文獻記載的狀況比我們這種簡單分類和梳理要復雜得多,它涉及到日耳曼法中的一個較為復雜的“支配權”(Gewere)[8]制度。今天的人們經常將德文中的“Gewere”(英文為Seisin;法文為Saisin)與羅馬法上的占有(Possession)相提并論,認為它是一種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制度。這樣,適用羅馬法理論,我們便可以將所謂的支配權分為兩種:即受法律上保護的事實支配的占有(possessiocivilis)和不受法律保護的事實上支配的握有(possessionaturalis);但德語中更多的是指是后一種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然而,事實上卻存在著與羅馬法意義上的占有或握有完全沒有關系的Gewere的例外的事例,例如與被繼承人死亡同時產生的尚未獲得占有但立即發生的繼承人的支配權。[9]德國學者艾希霍恩(Eichhorn)在1823年將這種Gewere的例外事例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擁有暫時利用權利的人(從仆、管理人、臣下)的支配權并存的“自主支配權”(Eingengewere),以及與宮廷法(Hofrecht)上的下級所有者的支配權并存的一般法(Landrecht)上的上級所有者的支配權。[10]第二類為未取得對于財產的事實上的支配,依據法院的程序接受財產讓渡的人的支配權。[11]1826年德國學者福爾格拉夫(Vollgraff)指出存在依據法院的確認而未經交付設定的支配權[12];1827年德國學者米特邁爾(Mittermaier)又指出被物理力量放逐出土地的人的支配權還繼續存在[13]。
這些大量存在的所謂“例外的”事例說明,我們將Gewere與possessio等同對待的看法是不周延和存在問題的;換句話說,要理解Gewere,必須從羅馬法上事實上的支配的概念和既有的思維習慣中解放出來。按照邏輯的分類,我們實際上可以將Gewere進行協調,大致進行三種分類:(1)作為單純的事實上支配的支配權(例如侵奪者的Gewere);(2)進行事實上的支配的同時,又擁有該實力進行支配的權利的支配權(例如行使占有的所有者的Gewere);(3)沒有事實上支配的支配權(例如前述所謂“例外的”事例中的Gewere)。[14]當然,將這三種日耳曼法律生活中的事實加以歸納并使支配權制度成為整個物權法建構基礎的學者是德國學者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他將Gewere與對物的權利等同起來,強調事實上的Gewere與法律上的Gewere這樣兩個范疇;并在這樣兩個范疇之上和整體的Gewere的概念之上,構建整個物權法。[15]而這些財產領域的規則,旨在將“心素”(animus)和“體素”(corpus)相互結合起來,在權利安定和交易安定之間建立起統一和協調的關系。[16]
日耳曼法的這種財產制度是與中世紀歐洲的莊園制經濟制度和領主分封制政治制度分不開的。莊園首先在加洛林時代清楚地出現,在大約13世紀以前一直是歐洲西北部地區的主導性農村社會經濟組織。莊園土地一般數百到數千英畝,一部分屬于領主,一部分屬于農奴。[17]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定社會單位(如莊園、氏族和公社)里的個人“所有”的土地要進行轉讓的話,“只能在同一公社內部進行,所有權不允許落到外公社去。”[18]與此相適應,甚至遷徙,也往往要注意村落團體的利益,如《撒利克法典》規定,“如果有人要遷入別個村莊,而那個村莊中有一個或幾個居民愿意接受他,但有人,即使是一個人,出來反對,那么,他不得遷入該村。”[19]由此而來,這種雙重所有權或支配權便帶有較強的地域性。
日耳曼財產法的這種地域性,旨在于強調社會秩序穩定和注重交易安全;這種價值目標的訴求中,財產的轉讓自然也就會注重形式主義。土地轉讓自不待言,即使動產所有權人對財產享有完全所有權,并有追及力,但其轉移也必須遵守一套嚴格的程式,否則便不發生法律效力。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所有權人的追及權,根據是否履行了“一定的程式”而具有不同的效力。如果基于所有權人的意志按一定程式轉移了對財產的占有(如委托保管、借用和出租等),而占有人又將財產經過一定的程式轉讓給了第三人,那么所有權人則喪失了對財產的追及權,只能對占有人請求賠償。這樣,通過這種程式,就割裂了原所有權人對其財產的絕對權利。這種“以手易手”的程式[20],就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公示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繼羅馬法以來認為“所有權絕對”的觀念,開始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和社會交易安全。德國法中創造的法外觀說(dieRechtsscheintheorie),就是這一理論的現代翻版。[21]
但事實上,Gewere不僅僅是占有,而且代表了對財產的一種總的擁有之事實狀態。本來,Gewere相當于拉丁語的“vestitura”或“investitura”(著裝),意指占有移轉(通過占有而著裝)的行為。后來轉義為該行為招致的狀態即占有(指物的事實支配)狀態本身。而這種事實上的支配,在動產的情況下是持有,在不動產的情況下在于用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Gewere”制度是日耳曼物權法的基礎。在日耳曼法中,物權只有通過Gewere才能把握,物權全部都通過Gewere的外觀(持有或用益)來展現;而只有采取Gewere形式所體現的才被視為物權,并作為物權受到保護(稱Gewere為物權的外衣乃至表現形式也是此意)。因此,雖然說Gewere是占有,但是不是從本權分離出來獨立的、與本權對立的占有,而是在其背后設定了本權、表現本權的占有。而且,如果把Gewere視為本權的話,那也不是從本權中分離出來的赤裸的本權,而是帶有對物進行事實上的支配的外衣的本權。因為日耳曼法上的Gewere中存在的占有與本權的這種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Gewere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即說它是占有它就是占有,而說它是本權的話,它也是本權。這也正是我們將它理解為“支配權”的原因所在。
同時,支配權制度發揮著以下三種效力:(1)防御的效力。擁有支配權的人被推定為合法具有物權的人,推翻這種推定需要裁判上的攻擊即訴訟(也就是說,對于裁判外的攻擊,擁有Gewere的人可以依靠自力救濟進行排除)。訴訟中擁有支配權的人占據證據上的有利地位,享有舉證優先權。另外,訴訟中的爭點就是支配權的正當權源(本權)在當事人中的何人那里,關于支配權的訴訟不是與本權關系獨立的占有之訴(在Gewere之訴以外不存在本權訴訟),并且它不但通過Gewere調整裁決占有,還調整裁決本權關系。(2)攻擊的效力。較強支配權推翻較弱支配權。例如,物被侵奪者具有的支配權(觀念的Gewere)推翻侵奪者現有的支配權。而所有人的支配權推翻租賃期間屆滿后的承租人的支配權。在兩種情況下,前者都可以通過自力救濟或訴訟從后者那里收回標的物。(3)移轉的效力。因為物權都通過支配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物權的移轉也只有通過支配權移轉的方式完成。在不動產轉讓的情況下,最早是需要進行支配權的現實轉移的;后來,在要式合意讓渡方式下不通過現實的,而是象征性的移轉即可(觀念的Gewere);再后來,就由登記取代了。而動產的轉讓一直以來都堅持要求進行現實的支配權的移轉。[22]
二、與羅馬財產法的比較
當然,日耳曼財產法中的這種團體主義特征,是與羅馬財產法進行比較而存在的。這里,本人擬從財產觀念、財產權利分類(主要是對“占有”和“所有”的認識上)兩個方面,來探討它們之間的區別。
日耳曼法中沒有“物”的抽象概念,更不象羅馬法將物區分為“有體物”和“無體物”[23],它只有關于“財產”的籠統概念。按照財產的目的來劃分,日耳曼法中的財產一般可以分為幾類:(1)一般財產,即指人們為一般生活目的(包括法定人權范圍內的為完成義務而結合的權利或法律關系)而存在的財產總稱;(2)結合財產,即繼承人自己的財產與繼承的財產的結合體;(3)部分財產,即一般目的之外,依特別目的而結合的財產,如破產財團清算財產、世襲財產;(4)獨立財產,即以獨立的目的結合的,從一般財產中獨立出來的財產(獨立財產一般適用特別法規);(5)集合財產,即為特殊目的,歸屬于眾多主體的財產的一部分結合而為一財產,如合伙財產、共同繼承財產。
事實上,人們進行種種活動的法的手段就是財產,而財產作為一種手段就是權利和義務的總和。因此,“財產”一詞,在日耳曼法中就有幾種涵義:(1)財產是由過去、現在和將來存在的眾多的權利和法律關系構成的單一體;(2)構成財產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必須具有金錢的價值,如商人的客戶關系、勞動者的勞動力,雖然可以用金錢來估價,卻不是權利或法律關系,而無法構成法律上的財產;(3)財產也包括債務,這是一種消極的財產;(4)財產結合的契機在于人,財產具有單一的存在性和同一性。[24]這樣,日耳曼法實際上承認了財產的客觀存在,使之具有單獨的價值和意義。這一點與羅馬法將財產融入權利之中不同:在羅馬法上,財產僅僅是由人所支配的對象或客體,其本身不具有獨立的價值。
在財產權利分類方面,羅馬法上占有與所有的概念是嚴格區分的;換句話說,在羅馬法上的possession和近代法上的占有,是與本權對立的一種權利。而如前所述,在日耳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區分,只有唯一的支配權制度。這種制度是由古代日耳曼法的土地總有制發展而來的。在當時的土地總有制中,只有圍墻內的宅基地屬于村落的成員所有,耕地、牧場、森林等共有地的利用都從屬于宅基地。在村落中有宅基地的人才是村落的成員,村落的成員對自己的宅基地有“Gewere”。那時,以宅基地為核心區分了兩種家長支配關系,即對農民財產的物的支配關系和對住宅內居住的家族奴婢的人的支配關系。后來,對人的支配關系發展為“地方行政長官”(Vogtey);對物的支配關系則為“Gewere”。對物的支配關系以后又發展為物對物的從物關系與人對物的所有關系的分離,從而使村民對分割的土地享有“Gewere”。可見,日耳曼法中對物的支配關系最初出現的概念就是“Gewere”,它是日耳曼法對物支配權的基礎,同時其發展的脈絡又是所有權發展的脈絡。[25]
因而,在種類方面,支配權可分為觀念的支配權(ideelleGewere;saisinededroit)和重疊的支配權(mehrfacheGewere)。雖然支配權應該是與對物的事實支配相伴的,但是在下列情況下即使不伴隨有這種支配也認為是具有支配權的。這被稱為觀念上的支配權。——即:在對物進行非法占有侵奪的情況下,被侵奪人對侵奪人的關系中;繼承開始時繼承人雖然沒有現實地取得對于繼承財產的占有也暫稱繼承人而相對于繼承財產的其他現存占有人的關系中;判決確定了土地的歸屬時勝訴者在判決后對于敗訴者的關系中;通過要式合意(Auflassung)方式進行不動產轉讓的情況下,還沒有現實轉讓占有的受讓人對出讓人的關系中,都視為具有支配權。
在重疊的支配權中,作為不動產支配權要件的事實上的支配即用益是不論是否為間接或者直接的,所以在土地的出借關系中,不僅直接用益土地的租地人,而且征收地租的地主和領主也對土地具有支配權。這樣,同一不動產上就成立了幾重支配權,這種重疊的支配權無非是中世紀日耳曼封建土地階層組織在物權法上的反映。另外,支配權因表現的權利不同而劃分為所有支配權(Eingengewere);封地支配權(Lehnsgewere);用益租賃支配權(Pachtsgewere);質的支配權(Pfandgewere)等類別。可見,這種支配權的劃分,又有些近似于近代法上對于物權(本權)所做的分類了。[26]
與此不同,羅馬法中則存在完整的財產權權利體系,如所有權、他物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和準物權(或類物權)等;而在日耳曼法中,所有權和他物權都稱為“Gewere”,只有完全自由的所有權與不完全自由(即附有負擔)的所有權的區別。擁有完全所有權的人享有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全部權能,而不完全所有權的擁有者則僅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權能。這就不像羅馬法區分自己之物和他人之物,而只不過是在所有權的權能范圍內存在著區別。從權利的功能來看,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等他物權不是與所有權性質相異的物權,而是所有權的一部分,是所有權權能的一個表現形式。羅馬法原則上不承認獨立的財產概念,作為財產在法律上進行特別處理的只是例外情況。在羅馬法語源上,財產作為有獨立意義的只是服從于家長權的家族和被允許持有財產的奴隸的特有財產、妻子的自持財產和繼承財產。所有的財產都是家長的權利,熔入家長權的支配領域,而財產只不過是家長的人格屬性。所以說,“羅馬法以人為中心,所有的權利歸結為人;而日耳曼法以財產為中心,所有的權利歸結為財產,而人只不過是作為財產管理人而行為的。”[27]
由此可見,日耳曼團體主義的財產法中,更確切地說是將土地的所有權利歸屬于宅基地,而非利己的個人。在日耳曼法中的繼承,也是對被繼承人財產的繼承而非是被繼承人人格的繼承,——土地繼承的結果是使領主權發生繼承。封建制度的產生,使對土地的擁有轉向對土地的支配,而對土地的支配則意味著對在其土地上居住的人進行支配。領主的支配權實際上附著于土地、產生于土地、并與土地一起移轉與消滅。因此,與其說日耳曼治下的農民隸屬于領主,毋寧說是隸屬于土地而臣事于宮廷。
中世紀與上古時代不同的是,對土地的利用不僅是收取果實,還有收取利息和課賦的利用形式。因此,“土地的事實上的利用者不論有無利用的權利,都取得‘Gewere’。因此,直接的利用者與間接的利用者、法律上的支配者與事實上的支配者,他們都享有‘Gewere’。”[28]也就是說,“在古代日耳曼法中,即使沒有土地所有的事實,更確切地說是只要存在對土地的事實上的利用,也就表現為某種形式的物權。”[29]不過,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博士認為,近代的所有權的一個更為重要的特點是“近代所有權嚴格區別于占有,而成為完全的觀念性存在,它在社會心理側面上表現為特殊或近代的所有權意識”;而在“Gewere式規范體系”之中,人們只是在某人具有這種事實上現實占有(這是為一種“外來力量”所支配的)時,才會尊重這種所有或占有。據此而認為,從對“所有權”之事實狀態到“所有權的觀念化”,這是一種主觀自發性的近代法觀念上的進步。[30]但是,忽視事實或現實狀態(秩序)是否就是近代化的進步呢?而且,近代法上的取得時效并不是作者所認為的完全是從“無權利突然轉變為完全權利”;而相反,近代法中的占有制度同時繼承了羅馬法上的possession和日耳曼法上的Gewere。而如有關基于占有進行的權利推定、重疊占有(自主占有和他主占有;直接占有和間接占有)、即時取得等制度,都是屬于Gewere系譜的;并且,登記制度也與Gewere密切相關(——Gewere是自然公示方法,而登記是人工的公示方法)。當然,與此相對,占有之訴是屬于羅馬法上的占有制度系譜的。
三、團體主義的成因
我們有理由相信,早期日耳曼人苦寒的游牧生活所產生的財產觀念,也影響了這種財產法中團體和交易安全思想。因為游牧環境下土地是一種“當然的”財富,以致于人們在觀念上根本不用去考慮。這種人類思維的慣性讓我們很是費解:有些東西對我們極為重要,重要得連我們都忘記了、或忽視了它的存在。“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這乃是他們所重愛的唯一財富。”[31]其實,塔西佗忘了告戒那些日耳曼人:畜群是以牧場或土地的存在為基礎的!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商業不發達,只有帝國的邊境才有通商,比較重視金銀;而“至于住在內部的那些部落則仍然保持著淳樸的以物易物的古風。”[32]這種被塔西佗稱道的淳樸古風刮到“曾經文明”的羅馬大地上,不免使人們仍然去回溯“物物交換”下的交易安全性。
當然,導致日耳曼財產法這種特征的更為本質的原因,也許是“日耳曼法的重心在于家庭婚姻,以及尚未廣泛買賣的土地”[33]。因為注重身份的社會控制往往缺乏對財產流動的興趣;而封建時代的主要財產——土地,也往往與人的身份聯系在一起。那時的封建領主擁有一個很大的專供自用的農場,而這就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W.坎寧安博士考察了英國中世紀的經濟制度后認為,“在經歷了一個封建時代各地具有很多相似特點的過程之后,原有賴于隸農人身承擔的義務終于與他們所享有的財產連結起來了。因此,我們也就把隸農所享有的那威爾格土地叫作領地勞役制土地,而在領地服勞役的義務最好還是看作是一塊領地勞役制土地的使用權所附帶的。……他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佃農,他領有一定面積的種著莊稼的土地,而地租則以勞役的形式繳納。”[34]這樣,在領地附著的勞動力就成為土地價值體現的關鍵。在此情形下,為配合領主的農地管理,出現了許多對隸農的限制,如不讓隸農子女上學、不讓他們任圣職或進城作學徒等。因此,中世紀日耳曼法的團體主義實質上是身份制社會的一種后果。當然,這種勞役制土地所具有的身份關系較之奴隸社會中的人身依附關系來說,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為它通過土地作為媒介,已經部分地擺脫了人身隸屬關系,為日后人身與財產的分離創造了條件。
莊園領主制度的目標只是在于實現自給自足。“這一原則,在查理曼大帝的《教士會法規》中寫得清清楚楚,在格羅泰斯特的《條例》中說得明明白白,可以看作是明智的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則;鑒于鄉間的商業活動多半也就是在一年一度的交易會上進行,這在交通閉塞、交易機會很少的時代是可以理解的。”[35]這種自然經濟側重于對財產的生產管理,而并不在意較少出現的流通規則的建立。這不同于商業繁榮時期,財產規則的產生——即對財產及其契約的保護,“都不是傳統社會所提供的,主要是商人自己提供的。”[36]而維持這種自然經濟管理的經驗則來自傳統習俗或國王的特權。因此,“實際上,在許多世紀中,所有有關土地權的訴訟或有關土地收益的訴訟都是以法定占有為依據,而從來不是以所有權為依據,也就是說,土地占有的合法性受傳統習慣保護。”[37]但這種習慣是一種傳統社會的壓力或統治,它不同于今天國家法和自治法之外的習慣法的適用。這種財產規則中的團體或社會思想就有違私法自治的本質特征。不過,考慮到日耳曼部落經濟方式和封建等級制度,財產法的這些團體主義色彩和社會化管理模式還是可以理解的。
這種注重生產管理的財產制度所隱含的政治因素是:注重穩定和加強封建王權的中央集權作用。這就引出了本文試圖重點揭示的問題,即王權在日耳曼財產法團體主義特征形成中的作用。
封建時代的歐洲經常處于一個不穩定和混亂狀態,王權政體、貴族政體和自由政體并存;而且前面已經談到,不動產的核心土地同樣也分為保有地和封地。[38]在這種狀態下,國王的特權不僅具有經濟(特別是財政)和政權上的作用,而且還發揮著秩序形成功能,具有團體主義意義。而這種在社會生活中較為強大的王權似乎并未導致東方社會財產權利不發達的后果,它只是導致對財產管理的重視。
漢斯•泰米(HansThieme)1942年寫了一篇有關中世紀財產權的論文,分析了中世紀國王特權(Regalien)的機能。國王特權是中世紀本來屬于法蘭克國王和德意志國王的諸項權能,或者說是由國王權力導出的諸項權能、而后又由諸侯或世俗的權力者通過明示的授予或長期的權利行使的結果而獲得的權能的總稱。主要內容包括開設市場許可權、貨幣鑄造權、關稅征收權、礦業漁業狩獵產物的權利以及對道路橋港口等的權利。他認為,過去的學說在分析國王特權的時候一方面強調其對國王以及領主的財政意義,[39]另一方面將其理解為所有權的種種分裂形態以及限制形態。但是,他認為,這種將其視為所有權的分裂形態或限制形態的態度,與中世紀的法律觀念不一致;這在無意識中把近代的觀念,即所有權是對物的自由支配和完全的物權的理解作為前提。實際上,中世紀的所有只不過是擁有物的一種形態,因此沒有必要將國王特權視為對所有權的限制。國王特權所擁有的,不是使所有秩序解體的功能,而相反是使其形成的功能。他認為中世紀的所有權人的權利是一種義務性的權利(Pflichtrecht);同時,他批判了在公法方面將其視為國王以及領主們財政上之必要的傳統考慮方式,重視國王特權的秩序形成功能。也就是說,傳統的觀點認為,國王特權是為財政所逼而不得不實行的,其結果造成了中世紀國家的逐漸沒落。而他認為,這種看法是對財政上的效果的過分評價。實際上,在中世紀,由于國王沒有可能通過立法來設定規范,而恰恰是通過國王特許權和諸項權能的授予,以此作為法律新秩序形成的重要手段而具有重大意義。被授予者,實際上是被授予了義務性權利,義務的內容幾乎完全能夠覆蓋權利的范圍。例如中世紀關于森林和鳥獸區的國王特許權的例子。被授予國王特許權的人對森林進行總體經營,而直接經營森林的義務則由在森林中分散定居的管理人承擔。他們宣誓忠實地維持、守護和管理森林,但必須滿足自己和有權利的居民建筑用材和薪木的采伐要求;同時也必須防止過度砍伐或不當采伐,并保證森林不受狩獵和放火的侵害。[40]
同時,還有學者認為,不僅國王特許權具有秩序形成功能,中世紀的授與、借貸(Leihe)也具有此種功能。如威爾黑姆•埃伯爾(WilhelmEbel)認為,授與不僅是國王特許權的授予,以此為語源的所有的授與都具有秩序形成的功能。為此,他對物的授與(Sachleihe),即土地的授與和權利的授與(Rechtsleihe,即官職及其它權限的授與)進行了研究。傳統觀點認為二者是有區別的。但這是以近代法對所有權(Eigentum)和占有(Besitz)進行區別為前提的。在這種前提下,近代學者雖然沒有明示,卻將出借人定義為所有人,而將被出借者定義為占有人。當然,雖然近代學者注意到了中世紀的“Gewere”與近代的占有相比是一種較強的權利,然而卻還是基本上把出借者作為所有人來理解了。而且近代學者將所有權作為對物的實體處分權,即實體所有權來處理。而接受出借者的權利也是對出借者的實體所有權的實質性干預或限制。這來源于羅馬法的所有權與債權和他物權的對立關系。他認為,在日耳曼財產法和德國的物權法中,所有權并不是其它物權的上位概念,而是在性質上和所有權相同的其它物權并列的東西。國王通過財產的授與對封臣進行的給養,不是一個擴散的過程,而是一個集中的過程;當然,這種歷史使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可能或已經實現,則又另當別論。對于財產的分配和官職的冊封,不是使國王的權利弱化,而是使原來從王權中導出的自由的自主支配權在盡可能廣的范圍內存在,從而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因此,他認為,中世紀的授與具有構建以王權為頂點的本來自主獨立的諸項權利的功能。[41]
在這種王權之下,無論是領主還是自耕農或隸農,人們都較為注重對財產的管理,——因為從某種角度說,終極意義的“所有權”是國王的。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站在財產幕后的這個國王終于消失,但王權的作用在團體主義的財產制度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英美普通法的形成,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權的作用在歐洲大陸和不列顛是不一樣的。在英國,王權力量強大,“全部土地所有權都直接或間接源于王權的觀點在英格蘭很早就被接受。”[42]而法國和德國,由于大采邑的領主的地位,國王的力量從來沒有如此強大。
四、結語
中世紀歐洲封建財產權,除了教會財產這一變異形式以外,都源于村落共同體的集體財產,這是與日耳曼統治者治下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的;而這種團體主義財產法,較之羅馬法中的財產觀念和財產制度,總的來說,是落后的、低級的。雖然它在法律構造中為后世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論指導,如前文所提到的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與交易安全的重視問題;但它在本質上,卻是為了契合封建制度下義務本位的社會觀念的。正如學者們所說,“封建財產及其相應的社會機構,充當了從家庭、確切地說是血親集體主義到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過渡的橋梁。在封建制度下,擁有土地的地主負有義務,遠不如資本家對所有權的自由利用或濫用的權利;土地不能自由交易而附有條件,并必須通過所有權人不敢違背的傳統習慣進行移轉,而且還需對其上級階層和下級階層負有預定的義務。這種制度的精髓是一種互惠服務的復合體。從奴隸到國王,所有的封建階層中的成員都被一定的互惠義務所束縛。義務感是封建社會的精神。”[43]
不過,這種團體主義的財產觀念在認識論上是較為有趣的:因為它承認了財產所具有的獨立品格;而羅馬法則主要將財產熔入人的權利和義務之中,不承認財產的客觀存在。例如,在一座房前的農民的財產,將會被作為莊園世襲的財產、繼承的財產、夫婦共同財產、妻子特有財產等客觀的單一體而區別對待;而且,這樣的財產不僅是權利的客體,還會作為權利的主體來處理,如日耳曼村落的各居民擁有的宅基地,它不僅是公法和私法上所有法律關系的中心,還是權利和義務的主體。“宅基地的所有者有時毋寧說是權利和義務的執行人、管理人或人。只有擁有獨立的宅基地的居民才可以出席村落會議而行使公法的權利,也只有他們才可以使用和收益村里的土地。所有的權利和義務都是以宅基地為中心的,而且依據宅基地的大小不同,權利義務的范圍也不相同。”[44]換句話說,就是指人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附于財產。而從本質上看,正如黑格爾所認識到的,在人與物的關系中,物只是人的意志的“定在”,只能是人的意志的客體:“人有權把他的意志體現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該物成為我的東西”;而“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這種目的,而是從我的意志中獲得它的規定和靈魂的。這就是人對于一切物據為己有的絕對權利。”[45]可見,較之羅馬法來說,日耳曼法中的這種財產觀是較為落后和低級的。當然,這種財產觀也是與日耳曼落后的文化與生產方式相一致的。
而這種落后的財產觀也并非一無是處,它為近代財產法的某些理論構造提供了一條路徑。例如日本民法第263條所規定的“入會權”,就是這種財產觀的近代法的再構造。所謂“入會權”,是指“一定區域的居民對特定的山林、原野、例外情況下對水面進行共同收益的習慣法上的權利”[46]。這種權利雖然規定在所有權“共有”一節中,但其實質上是一種帶有人身和財產雙重性質的財產權利。它最初分為“部落所有”和“非部落所有”兩種,后被概括為三種形態:私有土地入會的情況、公有土地入會的情況和固有土地入會的情況。正是在這種財產觀念指導下,日本成功地完成了對落后農業社會的法律改造,從而走上了現代化的軌道。也許,這種財產觀對目前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法律重構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它一方面可以實現土地的價值;另一方面也可以穩定和維持龐大的農業人口。當然,這是一個應該更深入研究以后才能下結論的課題。總之,歐洲中世紀日耳曼法也存在一個發展的過程。在日耳曼財產法后期的發展中,這種團體主義和羅馬法中的個人主義逐漸融合。同時,在法制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教會法的影響和11世紀諾曼人入侵不列顛以后導致普通法系的不同道路。不過,教會法在財產領域主要表現為教會特權的擴張和強調教會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47];而公元1066年諾曼底登陸在法律方面的影響卻極為深遠,它導致了西方法律制度中兩大法系的分野。[48]日耳曼財產法的團體思想也影響了教會倫理,而諾曼底公爵則將這一思想帶到了不列顛島,并最終成為其傳統之一。當然,促使這一思想成為傳統的因素就是:王權的作用在英國得到加強,而在歐洲大陸則被削弱;因為缺乏一個穩定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團體主義很容易分崩離析。所以,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日耳曼法雖然未得到很好地保存,但卻在英國普通法傳統中得到了發揚光大。甚至有人直接說“英美法屬于日耳曼法”,是“相對地比較最純的日耳曼法現代版”。[49]也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本人認為,將歐洲各國中世紀以來的共同淵源僅僅歸結于“希臘哲學、羅馬法和羅馬天主教教會的社會倫理”[50]的看法,是認識不夠全面的;更何況,日耳曼法的很多規則和理念也都融入了羅馬法,并通過羅馬法傳遞給了大陸法國家。
除此之外,日耳曼財產法中的團體主義趨向在這幾個方面的具體影響是值得重視的:(一)它在一種權利之上建立了幾個權利的規則,特別是其土地占有和訴訟制度[51];(二)在“分割”權利的基礎上對交易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強調;(三)在財產權利中對經營管理的重視及其經驗。這些影響對于社會化進程加快的今天,意義尤為重大。不過,團體主義的財產觀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即容易忽視人的個性與自由,也即忽視了人的本質或財產對人生目的的終極意義。這一點,是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的。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多蒙學友李紅海博士進行校對并查找資料,在此深表感謝。)
[1][美]菲利普•李•拉而夫、羅伯特•E.勒納、斯坦迪什•米查姆、愛得華•伯恩斯:《世界文明史》(上卷),趙豐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5月第1版,第387頁。
[2][美]孟羅•斯密:《歐陸法律發達史》,姚梅鎮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86頁。
[3][美]孟羅•斯密:《歐陸法律發達史》,姚梅鎮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89頁。
[4]《薩利克法典》編纂完成于公元486-496年,是法蘭克王國的習慣法和國王法令的匯編,也是流傳至今、影響最大的“蠻族法典”的典型代表。
[5]參見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論》,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版,第49-51頁。
[6][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15頁。
[7][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67頁。
[8]正如本文下面要論述到的,將德文“Gewere”翻譯為“占有”,在含義上是不全面、也不準確的,而羅馬法傳統中又缺乏一個較為精確的對應詞。日文中往往采用音譯的方法。這里,本人接受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米健先生的建議,譯為“支配權”,似較為妥當。另外,也特別感謝米健教授對文章修改所作的指導。
[9]參見[日]喜多了佑:《外觀優越的法理》,千倉書房1976年5月20日版,第102-103頁。
[10]參見[德]艾希霍恩:《德國私法導論》(Eichhorn,EinleitungindasdeutschePrivatrecht)(1823),S.395ff.
[11]參見同上,S.450ff.
[12]參見[德]福爾格拉夫(Vollgraff):AcPBd.9(1826),S.51.
[13]參見[德]米特邁爾(Mittermaier):Grands?tzedesgemeinendeutschenPrivatrechts,3.Ausg.(1827),S.264,vorA.9.
[14]這一分類經過了幾位學者的理論建構。首先為將這三種支配權作出理論上綜括而進行最初準備工作的是德國學者艾希霍恩。他將Gewere分為狹義和廣義的兩種:廣義的支配權是具有處分物的事實上的能力的文中第一種支配權;其他兩種支配權是他所說的狹義的支配權。艾希霍恩的見解在1826年被德國學者克羅普(Cropp)接受和利用,實際上又對其進行了加工。克羅普認為,艾希霍恩所說的“Gewere”的語源意義是Were,即被圍起的護欄保護內部和平的房基地(HausundHofraum)。
而德國學者阿爾布雷希特則不是從Were作為圍起護欄之地的語源來探究Gewere的概念的。而是力圖說明Gewere的語源意義在于保護,在他的著作中他開門見山指出“名詞的Gewere(Gewehre,Were)及動詞的geweren雖然具有多種含義,但是他們共同的基本意義是保護(Schutz)、防御(Verteidigung)和保證(Sicherung)”。這就由此證明了Gewere的基本含義是保護。這樣,阿爾布雷希特就將Gewere的基礎置于物的保護這一點上找到了解決點,這也就逼近了將文中三種Gewere加以綜括的命題。而且對他來說,物的保護與物的擁護是同一的。當然,艾希霍恩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艾希霍恩所說的擁護或保護物的權利的概念只是針對第二種或第三種狹義的Gewere統一起來的意義,而阿爾布雷希特則尋求在廣義的Gewere中進行擴充。他得出了Gewere的新的分類法,即有事實上支配的支配權、無事實上支配的支配權和事實并法律上的支配權三種;也就是事實上的支配權(diefakischeGewere)和法律上的支配權(diejuristischeGewere)組合。以上論述,請參見前引艾希霍恩書,S.395ff;又參見CroppimHudtwalckerundTrummersKriminalistischenBeitr?gen,Bd.2(1826),S.16ff;又參見[德]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DieGewerealsGrundlagedes?lterendeutschenSachenrechts(1828),1ff.
[15]見前注中對分類理論的介紹。又參見[日]喜多了佑:《外觀優越的法理》,千倉書房1976年5月20日版,第110頁。
[16][德]佐姆(Sohm):“ZurGeschichtederAuflassung”,FestgabefürTh?l(1879),S.111,S.90f.
[17]莊園的前身可以追溯至羅馬大地產,但與之不同的是,莊園是由農奴而不是奴隸耕種的;而農奴一般有屬于自己的土地,而對領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也較奴隸要弱一些。參見[美]菲利普•李•拉而夫、羅伯特•E.勒納、斯坦迪什•米查姆、愛得華•伯恩斯:《世界文明史》(上卷),趙豐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5月第1版,第545-547頁。
[18]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92頁。
[19]《薩利克法典》第45章“關于遷移”第1條;該章往下規定了具體規則。參見《薩利克法典》,何平校對,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8-29頁。
[20]如在土地轉讓中,往往移交一只手套或一只矛作為合法所有權的標志。參見《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5版),第8卷,第31頁。
[21]日本學者喜多了佑先生認為,“十九世紀初,在德國私法學將構建外觀優越的理論作為課題的時候,已經將日耳曼法,特別是中世紀德國法中與外觀優越類似的法現象Gewere制度納入視野中了。Gewere制度是將事實上的占有狀態觀念化為法律上的所有狀態的德國固有的法律制度,人們想到了外觀優越的法理就是以此為發展論基礎的。”參見[日]喜多了佑:《外觀優越的法理》,千倉書房1976年5月20日版,第101頁。
[22]參見[日]末川博主編:《民事法學辭典》,有斐閣昭和35年(1960年)版,第462-463頁。久保正幡所撰寫“Gewere”辭條;參考文獻[日]石井良助《日本不動產占有論》和[日]川島武宜《近代社會與法》等。
[23]查士丁尼在《法學階梯》中說,“有些物是有形體的,有些是沒有形體的”。他的這種劃分,是按照其性質是否能夠被“觸覺到”而加以區分的。參見J.2,2;中譯本為[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12月第1版,第59頁。
[24]參見[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40-42頁。
[25]德國學者呂克特(Rückert)認為,法律保護是以應受保護的權利存在為前提的,它不僅僅指對單純的事實上的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說,呂克特學說的核心命題是“Gewere是物權整體”。參見[德]呂克特(Rückert):UntersuchungenüberdasSachenrechtderRechtsbücher(1860),SS.101ff.176,178,158f.,7.
[26]參見[日]末川博主編:《民事法學辭典》,有斐閣昭和35年(1960年)版,第463頁。在英美法中,“Seisin”是指自由保有不動產權下對于不動產的占有。通過許可土地承租人進入封地、行使臣從和忠誠的權利而完成的封建授予。這種占有之下,占有者可主張自由保有不動產利益。依據不動產的性質而立即占有的權利。這種對不動產的占有就是根據日耳曼法中“Gewere”而來的,但是,它已經經過了普通法的改造。在英美法上,這種占有可以分為幾種狀態。(1)Actualseisin(事實或實際占有),通過本人或其承租人、人進住而公示(pedispositio);或者通過法律擬制,如依據用益法或(很可能是)轉讓、遺贈等沒有事實上的反對占有時,在政府授權或權利讓渡情況下對于自由保有不動產的占有。它意指事實上的占有,而與擬制占有(constructiveseisIn)或法律上的占有(possessioninlaw)相區別。(2)Constructiveseisin(擬制占有),法律上的seisin而事實上沒有占有;正如在政府授予某人以專有權,但是他從未對授予的土地進行任何形式的占有,他就對授予給他的所有土地具有擬制的占有,而另一人同時具有事實占有。(3)Covenantofseisin(占有保證協議)(參見Covenant辭條)。不動產轉讓人對于買方就其確實擁有他意圖轉讓的數量和質量的不動產進行的保證。(4)Equitableseisin(衡平占有),是法律上的占有(legalseisin)的同義語。即土地上衡平利益的占有。因此,設定抵押的人因收取地租而擁有土地的衡平占有。(5)Liveryofseisin(讓渡自由保有地),占有移轉,通過封建授予。(6)Quasiseisin(準占有),依據官冊享有不動產產權者對于其有權的土地享有的占有。該不動產土地的自由保有權屬于領主,依據官冊享有不動產權者不享有seisin本義上的權利,但是他享有與自由保有不動產權者相類似的占有的準占有或習慣占有。(7)Seisinindeed,自由保有不動產的事實占有;與actualseisin,seisininfact相同。(8)Seisininfact(事實上的占有),可主張不動產自由保有利益的人的占有;與事實上的占有相同。(9)Seisininlaw(法律上的占有),因不動產的性質而立即占有的權利。因古老的有形授予原則不再有強制力,一項契據的交付則產生法律上的占有。參見《布萊克法律辭典》第5版(Black’sLawDictionary5thedition),WestPublishingCompany1979,pp1218-1219.
[27][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31-32頁。
[28][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114頁。
[29][英]保羅•拉法格爾:《財產的演進:從野蠻到文明》(PaulLafargue,TheEvolutionofProperty:FromSavagerytoCivilization),London:GeogeAllenUnwinLTD.1921,7thEd.
[30]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申政武、王志安、渠濤、李旺譯,王晨校訂,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79-81頁。同時可以參見川島武宜博士所著《所有權法的理論》和《近代社會與法》。
[31][古羅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馬雍、傅正元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新1版,第57頁。
[32][古羅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馬雍、傅正元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新1版,第57-58頁。
[33]蘇彥新:《羅馬法在中世紀西歐大陸的影響》,載《外國法譯評》1997年第4期。
[34][英]伊•拉蒙德、W.坎寧安:《亨萊的田莊管理》,高小斯譯,王翼龍校,商務印書館1995年10月第1版,第5頁。
[35][英]伊•拉蒙德、W.坎寧安:《亨萊的田莊管理》,高小斯譯,王翼龍校,商務印書館1995年10月第1版,第8頁。
[36][英]約翰•希克斯:《經濟史理論》,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7月第1版,第35頁。
[37][法]馬克•布洛赫:《法國農村史》,余中先、張朋浩、車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9月第1版,第148頁。
[38]參見[法]基佐:《歐洲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起到法國革命》,程洪逵、沅芷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第1版,第47-48頁。
[39]傳統觀點認為,“中央皇家管理機構對民法和刑法事務日益進行干預,也由于財政方面的原因。”[英]霍爾茲沃思:《英國法的一些創制者》(第2卷),第173頁以下;轉引自[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潘漢典校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337頁。
[40]參見[日]村上淳一:《近代所有權概念的成立》,載《私法學的新展開》,有斐閣1983年10月10日版,第211-212頁。
[41]參見[日]村上淳一:《近代所有權概念的成立》,載《私法學的新展開》,有斐閣1983年10月10日版,第213-216頁。
[42][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潘漢典校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335頁。
[43][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78-79頁。
[44][日]石田文次郎:《財產法中動的理論》,嚴松堂書店1942年7月20日第8版,第17頁。
[45]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6月第1版,第52頁。
[46][日]中川善之助、遠藤浩、泉久雄:《民法事典》,青林書院新社1982年12月10日第3版,第214頁。
[47]如凡是侵占教會財產的,均應受到“棄絕罰”的處分,即不得參加圣禮領受圣物;不得執行教會的法定行為;不得接受尊位、恩俸和神品;不得接受教會職務;不得行使選舉權;不得與親友往來等。這在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時代是一種很嚴厲的懲罰。關于教會法對近世的影響,參見[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洪鈞、張志銘、夏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48]誠然,也用不著夸大這種區別。從實質上看,兩大法系沒有多少區別;重要區別在于法律或法學的方法上。普通法除了少量運用立法、如1290年《買地法》(QuiaEmptores)和1285年《附條件贈與法》(DeDonisConditionalibus)對習慣法進行改造以外,主要是圍繞訴訟,通過擬制、規避和衡平等方法來實現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平衡。這里,還有一個問題要說明。有人認為諾曼人征服之前的盎格魯•薩克森法為古代條頓人的習慣法,對英國法沒有什么影響(參見沈宗靈:《比較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198頁)。這種觀點缺乏歷史感。實際上,諾曼征服者甚至只是繼續盎格魯•薩克森人的法律統一運動,通過比歐洲大陸更為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形式推行于該國。參見《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5版),第8卷,第33頁。
[49]參見[日]早川武夫、村上淳一、稻本洋之助、稻子恒夫:《外國法》,張光博、金峰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6頁。
[50][瑞典]K.A.莫戴爾:《當代歐洲的法律傳統文化》,聶秀時譯,載《外國法譯評》1999年第1期。
[51]關于早期普通法中的權利訴訟,請參見李紅海博士所著文章《早期普通法中的權利訴訟》(載《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這里不再展開論述。
- 上一篇:紀檢委實踐科學發展觀心得體會
- 下一篇:經貿委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