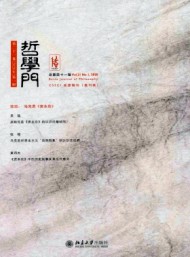哲學史范文10篇
時間:2024-04-15 19:59:0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哲學史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巴門尼德哲學與古希臘哲學史
內容提要:巴門尼德哲學不只是對過去唯心主義哲學的繼承,更是對此前整個古希臘原始樸素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他所提出的“存在”范疇與此前原始樸素哲學家們提出的“始基”范疇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他的“存在論”哲學對古希臘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乃至對整個西方哲學史均有著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始基;存在;思維;哲學進展
巴門尼德哲學的出現是古希臘哲學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和質的飛躍,然而有的人由于不理解巴門尼德哲學,對哲學進展秘密的無知以及囿于自己所形成的評價標準和概念框架,卻把它說成是“人類認識前進運動中包含著的后退。”[1]。由于巴門尼德哲學不能解釋一般人的常識,所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就與它有緣了。但是,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去貼標簽有什么用呢?以是否“唯物”、“唯心”、是否“辯證”為標準來評判一種哲學的進步與落后,這合理嗎?本文并不想指出巴門尼德哲學是否“唯物”、是否“辯證”,而只是想指出:這個所謂“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后退”的哲學正是它自己的母親——它之前的希臘哲學史所孕育和產生出來的,并且產生出來的這個哲學自身也子孫滿堂。
一、古希臘原始樸素哲學對智慧的追求——巴門尼德哲學的來源
對于巴門尼德哲學的來源,人們一般只提及畢達哥拉斯和塞諾芬尼,而很少提及泰勒士等其他自然哲學家,因而忽視了巴門尼德哲學同其他原始樸素哲學之間的批判繼承關系。由于片面“劃線”,巴門尼德哲學被理解為唯心主義繼承唯心主義的結果。所以,這里有必要從思想理論內涵上考察一下它同其他原始樸素哲學之間的關系。
巴門尼德哲學主要是指他的存在論哲學。“存在”是巴門尼德哲學的基本范疇。他把“存在”規定為具有“不生不滅”、“永恒不變”、“獨一無二”、“完整不可分”等特性。也就是說,在巴門尼德看來,存在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動的[2]。他這樣的“存在”,在一般人的眼中,在現實世界中,是找不到的。所以,缺乏一定思維訓練的人、缺乏一定哲學史背景的人是難以理解的,似乎只是哲學的胡說。這里要問:巴門尼德哲學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巴門尼德自己頭腦里突發奇想而編造的奇談怪論嗎?都不是,而是希臘哲學史自身發展的結果。
康德哲學是西方哲學史的轉折
摘要:康德把“人是什么”這樣一個大問題細分為三個小問題,他的這三問所對應的三本書也是康德留給我們的答案。康德因《純粹理性批判》而名聲鵲起,這是他劃時代的作品,也是康德哲學的基石。文章將會從康德哲學起源的時代背景和康德批判純粹理性的重要意義來證明為何說康德哲學是西方哲學史上的轉折。
關鍵詞:康德哲學;西方哲學史上的轉折;《純粹理性批判》;起源背景;重要意義
一、康德哲學起源的時代背景
(一)政治社會背景。《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個版本,是在1781年發表的。法國大革命的高潮是在1793年,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7至18世紀遍及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所帶來的對專制貴族的憤恨,對人性自由的渴望,康德的哲學思想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有人說,康德的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我認為這個論斷是正確的。因為法國專制王朝的革命在德國引起了一場思想的風暴。在《純粹理性批評》的序言中,康德說道:“我們的時代是真正批判的時代,一切都需要經過批判。”這也就是說,法國革命動搖了真實世界的統治,開辟了歷史的新紀元,而康德哲學就如同理論界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洗心革面”式的理論革命。他對法國革命的法則和原則大體是秉承贊揚的態度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保留的,他認為他們(法國革命者)太血腥了,但是他們的原則應該加以弘揚,這就是在康德自己的哲學架構里進行弘揚。首先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弘揚了法國革命的那種批判精神:一切都需要經過批判。(二)科學背景。科學可以劃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牛頓的物理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從《純粹理性批判》中可以看出康德深受牛頓的機械論的影響。當然,他并不局限于牛頓的機械論,他盡量地想擺脫牛頓的影響,但是很多方面又自然而然地受牛頓影響,比如分析論,經驗分析的方法,通過分析經驗把它分解成一個個部分來加以考察。在人文科學方面,盧梭相當于第二個牛頓。盧梭的關于人的學說和知識也是非常受到康德的推崇的。在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曾經提到,康德曾經讀盧梭的《愛彌兒》,打破了自己鐵定的作息時間。他通宵讀《愛彌兒》,如癡如醉,以至于第二天下午不能出來散步了。他每天下午三點都要出來散步,鄰居們都拿它來對表:康德出來散步了,那么現在就是三點了。康德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未提及關于人的問題,但他后來提及了這一點:所有的問題到最后都是關于人的問題。(三)哲學思潮背景。康德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理性的危機。當時的哲學就是唯理論和經驗論兩個派別在爭論,卻沒有任何結論。唯理論和經驗論并不簡單等同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因為唯理論里面有唯物主義者也有唯心主義者,經驗論中也是如此。在當時,特別是到了斯賓諾莎以后,獨斷論是唯理論走到了盡頭時候被提出的;萊布尼茨想把唯理論和經驗論調和,但是依舊沒有改變獨斷論的現狀。經驗論到了休謨的時候,也走到了盡頭,他提出了懷疑論,這種思想幾乎要使得一切科學被取締了,一切自然科學都要被動搖了。以笛卡爾為首的唯理論者與以洛克帶領的經驗論者浩浩蕩蕩地在各自的理性之路上行進,卻不約而同地在路的盡頭看到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就在這時,康德只身一人,披荊斬棘地開辟了另一條路——批判哲學。
二、康德批判純粹理性的重要意義
(一)化解懷疑論所帶來的哲學危機。有些東西是先天就懂得的知識,但是休謨從懷疑論的角度,對那些先天知識一個個的加以推翻,這使得當時的哲學和科學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康德對休謨的懷疑論作出有力的回應。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即“先驗”——人能夠認識能力范圍內的知識,這在當時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認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這種判斷是如何成立的,由此引出了“物自體”的概念——超出純粹理性范圍的知識是不可以被認識的。這奠定了康德哲學中二元論的基調。二元論的思想在康德的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科學與宗教、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現象界”與“物自體”等,均可證實這一點。(二)重塑形而上學的使命。在康德之前,理性成為了最高權力,理性也是法國大革命解決一切現實問題的最核心武器。康德所要做的是對理性進行批判,因為他認為這種過度的理性會導致人們忽視了自然和人類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形而上學有兩大使命,第一是為自然界立法,把科學的規律、科學的法規建立起來;第二是為自由立法,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道德律令。前者是人與自然的服務關系,后者指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只有把科學的基石打牢,形而上學才不會輕而易舉的被挑戰。的馬克思也從康德這里汲取了一定的思想,從人的物質資料生產和實踐的角度來全新的闡釋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三)其提出的問題具有永恒的思辨性。康德哲學具有一個非常偉大的意義,就是他提出的問題具有永恒的討論性,讓后續的哲學家不斷的進行思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我能夠知道什么?這是認識論的問題。第二,我應當做什么?這就是在引出“物自體”概念后康德發現自己陷入了泥潭中,而后他便將意圖在倫理學的“此岸”上來完成認識論的“彼岸”尚未完成的理想。他提出了“道德律令”,要求在遵循“人是目的”的條件下來服從道德約束。第三,我可以得到什么?這是康德對于現世間的不公平的德福之間的解決辦法,他將享受幸福寄托到了上帝身上,這歸根到了宗教的問題上。后世的人有的覺得康德是矛盾的,我覺得從康德行文看,康德并不矛盾,他的邏輯非常嚴密,但是表達方式非常繁瑣,因此顯得很矛盾。
我國哲學史研究論文
[提要]史的撰寫從1開始就對中國哲學的有導向性作用,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是與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問題聯系在1起的。現有中國哲學史論述的種種不足直接導致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因此,必須重寫中國哲學史。重寫中國哲學史必須從哲學的1般意義和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積極開發中國哲學特有的問題域,闡明它與的互動關系,特別要突出中國哲學的根本特征——實踐哲學的意義。就中國傳統哲學特征而言,實踐哲學遠比心性之學更具解釋力和現實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觸使得原教旨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利用西方哲學的某些資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在使用西方哲學觀念解釋中國哲學時仍要謹慎,概念不是純粹的形式。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哲學自己的概念體系是未來中國哲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內在批判和釋義學闡發則是新的中國哲學史的基本論原則。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內在批判自主性
1
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不滿的加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成了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話題,甚至被某些刊物評為2003年10大熱門學術話題。對研究現狀的不滿導致對其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哲學學科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于,與文學、史學等學科不同,中國人是在接觸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學”的。
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本沒有“哲學”1詞。漢語“哲學”1詞是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發明,他在他的《百1新論》(1874)中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1詞,但同時特別聲明:他用它來與東方的儒學相區別。直到1902年中國人才在《新民叢報》的1篇文章中第1次將“哲學”用于中國傳統思想。用是用了,卻并未解決1個真正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可稱為“哲學”的東西嗎?
在有些西方人看來,答案是否定的。胡塞爾在他的維也納演講中就否認中國有哲學。伽達默爾也認為遠東文化中那謎1樣的沉思與智慧與西方哲學不是1回事。理由是哲學是希臘人創造的1種非常特殊的東西,有其特殊的形態、內容、概念和問題。中國人自己1開始也這么看。王國維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之1,也是那個時代西方哲學造詣最深的中國人之1。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文中,根據自己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檢討中國傳統,發現在中國“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之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1]雖然王國維在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國傳統有哲學,但從整篇文章的上下文來細細玩味,不難發現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國并無嚴格意義(即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哲學史教育現況與革新策略
中國哲學史課程是中國高等院校本科哲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是一門“成智”且“成人”的極具傳統意蘊的學科。目前就國內而言,有哲學專業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里開設。但在以實用性、功利性和針對性為特點的市場法則下,中國哲學史課程的“命運”歷經坎坷、屢遭冷落,其發展前景令人擔憂。所以不論是在教師教學理念、教學方法,還是在課程內容設置、考核評價方式等方面都必須進行較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基本現狀
目前,中國哲學史課程在非哲學專業的本科教學形勢不容樂觀,雖然很多高等院校都開設有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但其教學成果遠遠沒有達到老師的期望值和學科建設本身應該達到的高度。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所遇到的這種困窘與處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作為非哲學專業的本科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選修課的形式開設,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一些辦學資歷不是很深,同時又相對缺乏哲學社會科學傳統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現按照自己的師資力量及現有教師專業特點隨意調整教學計劃,任意安排哲學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就哲學課程的開設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設課的情況。其他專業要么只開設西方哲學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學等同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包括儒道禪等中國的智慧[1]。這導致了人們將哲學看做為政治,有時甚至是時事政治。所以哲學在很多大學只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著,教師的教學是為了維持這個學科延續而不至于衰亡、絕種而為之,或者是為了保持學科體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罷了。
2.學生學習興趣不濃。中國大學的哲學專業設置過少,并非每個大學都設有哲學系,就是在僅有的幾個哲學系里,幾乎沒有多少學生將哲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也沒有人將哲學作為第二專業選修[1]。大多數學生基本上都認為,哲學史的學習不但抽象乏味,晦澀難懂,而且都是幾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難免與現實社會脫節。從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的選課現實中不難發現,選修中國哲學史的學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學生,但總體上課的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背外語的較多,很難展開教學互動,收效較微。通過調查問卷顯示,對中國哲學史學習興趣不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了無用,二是上課聽不懂,主要是為了修夠學校指定學分才不得已選之。
3.課程自身建設不足。由于課程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哲學史課程建設相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哲學師資隊伍建設不足。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師資是立教之基、興教之本、強教之源。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是推動課程教育改革發展、提高課程教育質量水平的關鍵。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國哲學課程的師資嚴重不足,在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專業中,也是一個人同時上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多門課程,或者直接讓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同時教授中國哲學史,這樣往往造成課程教學與課程建設之間的惡性循環。其次,相關配套課程開設不足。如果單是開設一門中國哲學史或單是一門西方哲學史課程,很難形成學生學習的哲學氛圍,也容易造成同學對哲學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選修課時限制下,大多數專業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很難系統地讓同學窺其全貌,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只能有選擇性地講解,容易造成知識鏈條的脫節。
哲學史綜合創新研究管理論文
張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所主張的具有開放性、主體性、辯證性和創新性的“綜合創新”文化觀,從文化繼承的目的、對象、方法以及繼承和創新的關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則。張岱年先生針對古今中外的文化問題所提出的“綜合創新”的文化觀,不僅是一種文化理論,而且也是一種方法論。它從文化系統的可解析性與可重構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離性與可相容性出發,通過批判與會通、分析與綜合、解構與建構,實現文化的綜合創新。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言,貫徹“綜合創新”的方法論原則,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學史高度,體會“一本萬殊”之理,承認相反之論,從雜多中求統一,從矛盾中求會通,努力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和西方哲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在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解構與重構中,會通古今中西,以求達到綜合與創造、繼承與創新的統一。這正是通過“綜合創新”方法所要實現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標。20世紀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說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馮友蘭先生,在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經開啟了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綜合創新之路。這具體表現在:一是明確地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和中國哲學的直覺主義相結合,建構了一套哲學方法論與哲學史方法論———“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學包括實用主義和新實在主義的觀念和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層次上,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科學主義的方法、人文主義的方法相結合;而這一結合是在他力圖把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打通并適當地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實現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種綜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
歷史地看,在跟馮友蘭先生同時或稍后的一些中國哲學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層面上、不同的范圍內,探索并嘗試融貫、綜合各種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以求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如三四十年代的張氏兩兄弟張申府先生、張岱年先生就嘗試“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倡導和運用邏輯解析方法,并將解析法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結合,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既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又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奠定了張岱年先生一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基礎。張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一書,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出發,主張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并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正確方法,就是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原理來分析研究中國歷史上每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闡明哲學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第一,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意義,注意考察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斗爭與相互轉化;第二,重視唯物主義的理論價值及其在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對于階級社會中的哲學思想進行切合實際的階級分析;第四,堅持發揚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學風,對于哲學史的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于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哲學思想的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精密的分析和論述,基本上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為主導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可以看出,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貫、整合,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統帥下達到了“綜合創新”。
事實上,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已呈現多元化趨勢。他主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如中國舊有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西方現有的解釋學方法、發生認識方法、結構主義和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等,以便在各種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補中,揭示中國哲學史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又如劉文英先生強調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采用的各種方法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主張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以及語義分析方法、結構分析方法、解釋學方法與比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綜合,以實現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價值。這可以說是一種理性、開放、公正、平實的態度,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顯然,他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已不是以往那種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過重新理解和詮釋并加以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綜合古今中外各種研究方法論的探索,體現的正是“綜合創新”的路向。
海外華人學者傅偉勛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討老子之“道”所蘊涵的哲理而觸發詮釋學構想,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基本上建構起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創造的詮釋學”。從傅偉勛先生所建構的“創造的詮釋學”方法論看,它實際是中西哲學方法論的融會貫通。誠如傅先生自己所說,“創造的詮釋學”的“建構與形成有賴乎現象學、辯證法、實存分析、日常語言分析、新派詮釋學理路等等現代西方哲學中較為重要的特殊方法論之一般化過濾,以及其與我國傳統以來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乃至大乘佛學涉及方法論的種種教理之間的‘融會貫通’”。所以,他的“創造的詮釋學”便具有一種辯證開放的性格。顯然,傅偉勛先生在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時,仍然走的是綜合古今中西以求創新的道路。
中國哲學史研究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中國哲學史的撰寫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有導向性作用,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是與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現有中國哲學史論述的種種不足直接導致了目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因此,必須重寫中國哲學史。重寫中國哲學史必須從哲學的一般意義和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積極開發中國哲學特有的問題域,闡明它與時代的互動關系,特別要突出中國哲學的根本特征——實踐哲學的意義。就中國傳統哲學特征而言,實踐哲學遠比心性之學更具解釋力和現實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觸使得原教旨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利用西方哲學的某些資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在使用西方哲學觀念解釋中國哲學時仍要謹慎,概念不是純粹的形式。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哲學自己的概念體系是未來中國哲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內在批判和釋義學闡發則是新的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方法論原則。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內在批判自主性
一
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不滿的加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成了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話題,甚至被某些刊物評為2003年十大熱門學術話題。對研究現狀的不滿導致對其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哲學學科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于,與文學、史學等學科不同,中國人是在接觸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學”的。
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本沒有“哲學”一詞。漢語“哲學”一詞是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發明,他在他的《百一新論》(1874)中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一詞,但同時特別聲明:他用它來與東方的儒學相區別。直到1902年中國人才在《新民叢報》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將“哲學”用于中國傳統思想。用是用了,卻并未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可稱為“哲學”的東西嗎?
在有些西方人看來,答案是否定的。胡塞爾在他的維也納演講中就否認中國有哲學。伽達默爾也認為遠東文化中那謎一樣的沉思與智慧與西方哲學不是一回事。理由是哲學是希臘人創造的一種非常特殊的東西,有其特殊的形態、內容、概念和問題。中國人自己一開始也這么看。王國維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之一,也是那個時代西方哲學造詣最深的中國人之一。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根據自己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檢討中國傳統,發現在中國“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之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1]雖然王國維在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國傳統有哲學,但從整篇文章的上下文來細細玩味,不難發現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國并無嚴格意義(即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哲學史前提性反思研究論文
近年來,“重寫”之風席卷整個學術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領域自然也不能免俗。問題是,“重寫”(rewrite)這個詞的含義究竟是什么?顯然,“重寫”不同于“重復”(repeat),也許每一個打算“重寫”中國哲學史的人主觀上都不會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低水平的重復。這樣看來,“重寫”的意圖是拿出與前人有重大差別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來。然而,這里說的“重大差別”的含義又是什么呢?究竟是單純術語上的翻新,還是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不用說,人們一般都傾向于把“重寫”理解為“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
這樣一來,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就轉化為如下的問題,即如何實現中國哲學史“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毋庸諱言,我們這里說的“總體思路”涉及到哲學觀。換言之,對于任何一個有志于重寫中國哲學史的人來說,如果他還沒有確立起新的哲學觀,那么,“重寫”就只是一個修辭學意義上的口號。要言之,沒有新的哲學觀,就不可能有新的中國哲學史。然而,任何一個研究者要確立起新的哲學觀,就必須對傳統哲學觀的弊端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不了解哪些哲學觀是舊的,又如何知道另一些哲學觀是新的呢?眾所周知,哲學作為學科是唯一的,但哲學觀卻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不能說:“張三有張三的哲學,李四有李四的哲學”,而只能說:“張三有張三的哲學觀,李四有李四的哲學觀”。既然哲學觀是多元的,那么從不同的哲學觀出發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就會在總體思路上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當然,所有對中國哲學史的有效的“重寫”都蘊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對傳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所蘊含的哲學觀的批判性反思。事實上,沒有這樣的前提,“重寫”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傳統的哲學觀中,哪些哲學觀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響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種哲學觀:一是把哲學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二是把哲學理解為對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思維知識的概括與總結;三是把哲學理解為關于世界觀的學問。下面,我們逐一批判這三種傳統的、影響深遠的哲學觀。
哲學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嗎?
把哲學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把哲學史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史,進而簡單地把唯物主義與進步、唯心主義與反動等同起來,構成了一種簡單化的、但又極有影響力的哲學觀。不少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深受這一哲學觀的影響。比如,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1957)中就這樣寫道:“中國哲學的歷史和別的國家的哲學一樣,是唯物主義的發生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①在這樣的表述方式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幾乎成了哲學的代名詞。
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未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作為正價值與負價值簡單地對立起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中,馬克思指責那種撇開社會歷史、奢談抽象物質概念的唯物主義是“抽象的唯物主義”,它與同樣撇開社會歷史、奢談心靈作用的“抽象的唯靈論”實際上是同一個東西:“抽象的唯靈論是抽象的唯物主義;抽象的唯物主義是物質的抽象的唯靈論。”②在《神圣家族》(1844)中,馬克思進一步深化了對“抽象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他在批評霍布斯把幾何學家的抽象感性取代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時,氣憤地寫道:“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了。”③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中,馬克思在批評舊唯物主義的被動性時指出:“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④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并沒有把唯物主義的一切形式都作為正價值而與唯心主義對立起來。事實上,在唯物主義的所有形式中,他肯定的只是“實踐唯物主義”,而對其他形式所具有的共性———抽象性進行了不懈的批判,同時也對唯心主義的能動性作了高度的評價。眾所周知,列寧也在《哲學筆記》(1895-1911)中寫道:“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于聰明的唯物主義。”⑤這段重要的論述實際上消解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那種被夸張的、簡單化的、絕對的對立.
中華哲學史研究情況及其難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哲學作為思想中的現實,當代中國哲學史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史,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重大現實問題和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總結、概括和反思,展開了一系列具有時代內涵的哲學論爭,取得了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科技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和宗教學在內的哲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成果和哲學教育的重要成果。系統地研究1949年至今的當代中國哲學史,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當代中國哲學史》,既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和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迫切要求,也是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一、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1.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當代中國哲學史
中華民族是富有哲學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體現中華文明的中國哲學精神。20世紀以來,中國學者撰寫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國哲學史,其中,胡適、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等撰寫的中國哲學史產生了歷史性和世界性影響。近60年來,特別是近30年來,中國學者又陸續地撰寫了多部近代中國哲學史、現代中國哲學史和當代中國哲學史。但是,較之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國哲學史和近現代中國哲學史,1949至2009的當代中國哲學史尚缺乏全面、系統、深入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靈魂、主線和基本內容,并以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敘述方式撰寫當代中國哲學史,是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的重大的歷史任務。
2.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經驗總結
當代中國哲學史從根本上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在當代中國60余年的哲學歷程中,哲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在探索和回答時代性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深入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中,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宗教學、科技哲學以及文化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價值哲學等部門哲學的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寫“當代中國哲學史”的方式總結這一歷程和經驗,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哲學史研究范例管理論文
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哲學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哲學史教育現況與革新對策
中國哲學史課程是中國高等院校本科哲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是一門“成智”且“成人”的極具傳統意蘊的學科。目前就國內而言,有哲學專業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里開設。但在以實用性、功利性和針對性為特點的市場法則下,中國哲學史課程的“命運”歷經坎坷、屢遭冷落,其發展前景令人擔憂。所以不論是在教師教學理念、教學方法,還是在課程內容設置、考核評價方式等方面都必須進行較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國哲學史教學基本現狀
目前,中國哲學史課程在非哲學專業的本科教學形勢不容樂觀,雖然很多高等院校都開設有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但其教學成果遠遠沒有達到老師的期望值和學科建設本身應該達到的高度。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所遇到的這種困窘與處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作為非哲學專業的本科院校,中國哲學史課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選修課的形式開設,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一些辦學資歷不是很深,同時又相對缺乏哲學社會科學傳統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現按照自己的師資力量及現有教師專業特點隨意調整教學計劃,任意安排哲學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就哲學課程的開設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設課的情況。其他專業要么只開設西方哲學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學等同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包括儒道禪等中國的智慧[1]。這導致了人們將哲學看做為政治,有時甚至是時事政治。所以哲學在很多大學只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著,教師的教學是為了維持這個學科延續而不至于衰亡、絕種而為之,或者是為了保持學科體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罷了。
2.學生學習興趣不濃。中國大學的哲學專業設置過少,并非每個大學都設有哲學系,就是在僅有的幾個哲學系里,幾乎沒有多少學生將哲學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也沒有人將哲學作為第二專業選修[1]。大多數學生基本上都認為,哲學史的學習不但抽象乏味,晦澀難懂,而且都是幾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難免與現實社會脫節。從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的選課現實中不難發現,選修中國哲學史的學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學生,但總體上課的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背外語的較多,很難展開教學互動,收效較微。通過調查問卷顯示,對中國哲學史學習興趣不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了無用,二是上課聽不懂,主要是為了修夠學校指定學分才不得已選之。
3.課程自身建設不足。由于課程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中國哲學史課程建設相應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哲學師資隊伍建設不足。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師資是立教之基、興教之本、強教之源。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是推動課程教育改革發展、提高課程教育質量水平的關鍵。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國哲學課程的師資嚴重不足,在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專業中,也是一個人同時上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多門課程,或者直接讓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同時教授中國哲學史,這樣往往造成課程教學與課程建設之間的惡性循環。其次,相關配套課程開設不足。如果單是開設一門中國哲學史或單是一門西方哲學史課程,很難形成學生學習的哲學氛圍,也容易造成同學對哲學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選修課時限制下,大多數專業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很難系統地讓同學窺其全貌,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只能有選擇性地講解,容易造成知識鏈條的脫節。
相關期刊
精品范文
10哲學與科學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