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人格權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3 09:23:00
導語:商事人格權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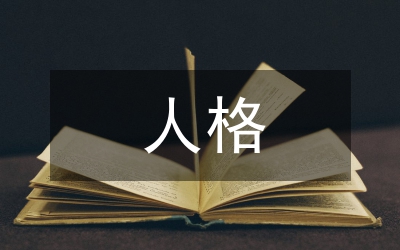
摘要:商主體作為法律主體也享有各種人格權,然而這種人格權卻明顯超出了傳統民法人格權理論,處于一種理論體系上無從歸屬的尷尬境地。于是,有了從各種角度與立場出發的形形色色的判斷。但是,如果從人格權與民商事主體間關系的一般理論出發,我們就會發現,商主體的人格權實際上只能借助于商事人格權理論獲得解釋。并且,獨立于民法之人格權,兼具人格權屬性與財產權屬性的商事人格權理論的提出,恰恰解決了民法人格權理論的矛盾與商主體賴以依存的人格權理論缺失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關鍵字:商事人格權,一般商事人格權,具體商事人格權,法律屬性,制度
一、引言:問題的提出
在當今社會,商品經濟的烙印越來越深地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以至于學界普遍地認為所有民事主體都成為“經濟人”了。此即近年來學界所熱衷討論的“人的普遍商化”現象。[1]這種現象反映在財產法上至為明顯,即使在人格權法上,也反映出人格利益的財產屬性的加強。譬如,自然人可以將其姓名授權他人作為商號或商標使用,從而獲取高額收益;自然人的肖像可以通過商業化使用而創造大筆財富;甚至個人隱私也可以轉化為財產。企業法人的名稱、商譽、商業秘密等更是可以作為直接的物質財富,而對企業的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然而,這種基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自然產生的現象,卻給理論界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這些權利究竟該如何定性?傳統民法認為,人格權是非財產性權利,并不以一定的財產利益為內容。人格權的客體即人格利益不能直接表現為商品,其價值也不能用金錢衡量。人格權又具有專屬性,只能為權利主體所享有,不能轉讓和繼承。[2]顯然,上述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現象與企業法人人格利益的直接財產屬性,并不能為傳統民法人格權理論所解釋。
對此,理論界提出了不同解釋。有人提出“商品化權”或“公開權”以解釋,并認為其含義為“真實人物將其姓名、肖像或其他表明其身份的個體特征授權他人用于商業使用,并禁止他人未經授權進行商業使用的權利。”[3]與此相似的提法,還有“形象權”。[4]并認為所謂形象權就是指一個人對與其人身有密切關系的各種形象因素的商業價值所享有的權利。此種權利如同作者對其作品所享有的使用權一樣,從性質上講非屬于人身權,而屬于財產權,且為獨立于物權、債權與知識產權的獨立財產權類型。[5]盡管這些提法對于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現象能夠較好地解釋,使得為傳統民法人格權理論所不能包含的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權有了法律上的歸屬,但也只能解釋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現象,對于企業法人人格利益的直接財產屬性則無能為力。
另有人就企業法人名稱、商譽等具體人格權性質提出各種不同學說:有人認為商號權是一種既有人身權性質,又有財產權性質的權利;[6]有人認為商號權就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依法對其注冊商號所享有的專用權,其內容具有人身權和財產權雙重屬性,在權利類型上屬于知識產權;[7]有人認為商譽屬于法人名譽內容的一部分,法人的名譽與法人的商譽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差異,商譽權即屬于法人名譽權的重要組成部分;[8]有人認為商譽權雖然具有無形財產權性質,但財產性只是其非本質屬性,人格權才是其本質屬性,故屬于一種有別于相關權利的特殊人格權。[9]應該說,這些學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問題在于其立論均基于傳統的人格權理論,堅守著傳統民法的人格權特征,從而根據是否符合該特征而得出商主體人格權法律屬性的結論。面對完全不同于民事主體的商主體,卻堅持用傳統民法的人格權理論解釋商主體的人格權法律屬性,當然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還有人提出“商事人格權”概念,并認為所謂商事人格權,是指公民、法人為維護其人格在商事活動中所體現出的包含金錢價值在內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種民(商)事權利。它是人格權的商事化,反映的是自然人和法人在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會現實,反映了人格權在商品社會中的發展變化。[10]應當說,這是一種頗有創見的觀點。從表面上看,該說在發現傳統人格權理論對于所謂“商事人格利益”的無能后,提出了以營利性為首要特征的“商事人格權”概念,從而解決了這種包含著明顯營利色彩的衍生于人格權的權利屬性問題。然而,從本質上說,這種商事人格權的提法只是使問題回歸于人格權內部而已,如果說,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問題尚能依此解釋的話,關于商主體對于其具有明顯而直接的財產屬性的人格權,何以包容于否定財產屬性的人格權中,則難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這種建立在民事主體所享有的傳統人格權框架內的商事人格權理論仍然具有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商法的視角出發,就會發現,正如一般民事主體必然要具備維系其生命的人格權,商主體要作為獨立的法律人格而存在,也必然要以維系其法律人格的人格權為前提。基于概念上的嚴謹性考慮,我們認為可以將商主體所專有的人格權稱為商事人格權。至于上文所述“商事人格權”的提法,則因其具有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并混淆了一般民事主體人格權與商主體人格權的本質區別,我們認為并不可取。限定于商主體專有意義上的商事人格權理論的提出,則不僅賦予了商主體以作為私法主體所不可或缺的獨立的人格權,還使得商主體所享有的具有直接財產屬性的人格權的法律屬性問題得以解決:不屬于財產權,不屬于知識產權,也不屬于兼具人格權與財產權屬性的復合性權利,而是作為商主體存在基礎的獨立的人格權。應該說,這種理論具有極高的理論與實踐價值。但由于大陸法系各國都未對此作出立法與司法上的認定,在理論上也沒能予以必要的關注,使其缺少了立法例、司法判例與學術研究成果的支撐。為使商主體所享有的人格權的法律屬性得以明朗,更為使作為商法核心的商主體理論體系得以完善,我們愿在此就商事人格權問題做一些初步探討。
二、商事人格權界說
(一)商事人格權內涵界定
“人格是法律上一個最為抽象的概念”。[11]關于人格的含義理論上有多種理解,在法律上亦具多重意義:[12]第一種含義是指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的權利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與主體、權利主體、法律主體、民商事主體等概念相同;第二種含義是指作為民商事主體法律資格的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權利能力、權利能力概念相同;第三種含義是指一種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又稱人格利益,是指人格權的標的。據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分別在商事法律人格與商事人格權中使用的“人格”概念,其含義并不一致:前者系就商主體而言,后者則系從商主體所享有的人格權之客體-人格利益而言。
“人格權與吾人生存有不可分離之關系”,[13]可見人格權既為民事主體所必需,也以民事主體為其存在前提。因此,對于作為特殊形態的民事主體的商主體來說,商事人格權既為其所不可缺少者,同時,商事人格權又必須以商事法律人格為其存在前提。據此,并非所有人都能享有商事人格權,只有商事法律人格者,即商主體才能享有。基于此,自然人人格利益商品化利用所產生的商品化權,因其主體的純粹自然人屬性,也就是說未能通過履行相關手續成為商主體,不能歸入商事人格權范疇。有人認為,受民法商事化的影響,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嚴格的身份界限的消失,民事權利開始具有更多的營利色彩這一商事權利屬性,體現在人格權上就是普通的人格權向商事人格權的發展,可以稱之為人格權的商事化。并進一步將這種商事化了的人格權稱為商事人格權。[14]很明顯,這種觀點未能正確理解商主體的內涵,并以權利的營利性作為商事權利的判斷標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權利必然歸屬于一定主體,一定性質的權利也必然歸屬于一定性質的主體。商主體作為特殊形態的民事主體,可以享有一般民事主體的許多權利,但一般民事主體則不能享有專屬于商主體的權利。因此,有必要對商主體與一般民事主體的關系做一個簡單界定。提出“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嚴格的身份界限的消失”命題的學者的原本觀點應是,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參加市場交易活動,隨時都可能從事營利性活動,因而都發展成“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從而民事主體與商主體的界限趨于模糊甚至“消失”了。應該說,這純屬誤解。毫無疑問,商主體是以實施營利性行為為目的的“人”,但并非凡實施了營利性行為的人就是法律上的商人。《法國商法典》第1條規定:“從事商活動并以其作為經常性職業者,為商人。”[15]《日本商法典》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商人,指以自己名義,以實施商行為為業者。”[16]顯然,要想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商人,并非偶爾甚至經常從事一些市場交易行為即可滿足條件,其行為必須滿足特定條件,一般來說須以其財產為基礎而具備連續性。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將所有具有營利色彩的人格權都稱為商事人格權,是對商法的嚴重誤讀。
關于商主體的判別標準問題殊為復雜,且各國立法例各異,但一般來說,商主體的成立須以商事登記為必要條件。具體來說,采商事登記成立要件主義立法例者為絕大多數國家,乃20世紀下半葉后各國商事登記立法的主流,而采商事登記非成立要件主義立法例者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且其形成乃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貿易時代的產物。[17]在我國,歷來對商事登記高度重視,一貫將其視為商主體的成立要件。[18]因此,商事人格權的主體必須為經依法登記取得主體資格的商主體,其具體形態雖然各不相同,但都以企業的形式表現出來。據此,對于那些不具有商主體資格的自然人、國家機關、一般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經營、國家不再核撥經費的事業單位除外)、民辦非企業單位等通過人格利益的商業化利用而享有的“商品化權”,并不能稱為商事人格權。
盡管商事人格權概念既無立法上的規定,又乏學理上的研究,但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借鑒民法上關于人格權尤其是法人人格權的界定方法,對商事人格權作如下界定:所謂商事人格權,指的是商主體所特有的經法律確認而以商事人格利益為客體的商主體之商事法律人格所必備的基本權利。
(二)商事人格權外延考辨
至于商事人格權究竟包含哪些類型,同樣由于缺乏法律的規定,我們只能根據人格權的一般理論作出初步的判斷。鑒于商法對商事人格權問題尚欠研究,我們只能根據傳統民法關于法人人格權理論展開分析。王利明教授等在其《人格權法》中提出法人亦有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之分。其中一般人格權的內容具體體現在法人的人格獨立與人格平等兩個方面,具體人格權則包含了名稱權、名譽權這兩種類型。[19]在其他代表性民法教材中,也大抵持相似觀點。但認為法人具有一般人格權或者說對法人一般人格權加以研究者則屬個別。[20]在法人得享有的具體人格權的范圍上,除名稱權與名譽權外,另有人認為還應包括秘密權(在企業法人即為商業秘密權),[21]還有人認為應包括榮譽權與信用權。[22]顯然,在法人人格權具體構成上,學者們也是莫衷一是,難以從其論述中歸納出共同的結論。
在立法例上,由于各國大多未對人格權作單獨的規定,只是在侵權之債中對自然人的姓名權、名譽權等具體人格權予以債法上的調整,對于法人等組織的人格權則未見規定,關于商事人格權更是僅有商號的規定。具體來說,《法國民法典》中除在1994年修正案中規定了身體權外,即使在“非經約定而發生的債”中也無關于人格權的規定。[23]《德國民法典》盡管在第12、823、824、825條分別規定了姓名權、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自由權、信用權、貞操權、名譽權,但并無法人人格權的規定。[24]《瑞士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被有些學者譽為“標志著現代人格權立法已經進入了完善的程度”。[25]雖然該法第一次對“人格的保護”作了專門規定,但僅規定了姓名權,對于法人人格權則未見規定。[26]盡管在題為“侵權之債”的《瑞士債法典》第1章第2節,對人格權的法律保護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乃基于自然人人格權之保護而設置。[27]《日本民法典》只是在債權之侵權行為中規定了“名譽毀損”的救濟。[28]采民商合一立法例的《意大利民法典》只是在“自然人”一章中規定了身體權、姓名權與肖像權,在多達2969條的法典中比別無其他人格權規定。[29]同樣采民商合一立法例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在第19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在1084條規定了對生命權和健康權的救濟,在1100條則規定了對于“傳播詆毀名域、侵害人格尊嚴和商譽信息而造成的損害”應予以精神損害賠償。[30]在商法典中,雖然《德國商法典》、《日本商法典》、《韓國商法典》等均對商號作了專門規定,[31]但也僅僅對商號作了規定。
由此可以看出,大陸法系主要國家,不管采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立法例,民法典對于人格權的規定都極為有限,對于法人人格權更是只有采民商合一立法例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對商譽侵權的精神損害作了規定。然而,在這些國家,關于人格權的保護力度卻并不像其法規那樣缺乏。創建于德國的一般人格權理論多年來一直為各國司法實踐所采納,從而使具體人格權立法上的缺憾得以彌補。應當說明的是,盡管大陸法系國家不將判例視為法律淵源,但20世紀以后隨著兩大法系的融合以及成文法局限性越來越多的暴露,司法判例正逐漸成為各國事實上的法律淵源,正所謂“立法周全固然重要,判例更不容忽視”。[32]因此,盡管法律缺乏對人格權的明文規定,但人格權并無無從保護之虞。對于商事人格權來說,商法典中盡管也只有關于商號的規定,另外《俄羅斯聯邦民法典》規定了商譽的精神損害賠償,但對于商譽權與商業秘密權的侵害,各國也同樣要予以救濟,只不過是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而已。[33]
就我國而言,《民法通則》創造性地對人身權作了專章規定,明確規定了為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婚姻自主權等具體人格權,為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權則規定了名譽權、榮譽權,此外,還規定了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享有名稱權。[34]顯然,可能屬于商事人格權的有名稱權、名譽權與榮譽權。除此之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還對侵害商業秘密的行為作了專門規定,從而確立起了商業秘密權。
那么,在我國,上述為我國法律所確認的權利中,究竟哪些應劃入商事人格權的范疇?是否還存在沒有為現行法律所確認的其他商事人格權?對此,我們應根據法律主體與人格權的一般關系,尤其是商事法律人格(商主體)與商事人格權的一般關系予以回答。
我們從商主體一般人格權問題開始展開論述。眾所周知,一般人格權乃由德國司法實踐首創,因此,為明確其內涵中是否包含了商事人格權,我們先對德國一般人格權理論作一個簡單回顧。據德國學者考證,《德國民法典》制訂者有意識地未將一般人格權納入法典第823條第1款保護的法益范圍。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案件中承認了一般人格權。而這一判例很快傳播開來,其效力為各級法院所肯定,并且在法律后果方面得到了實質性擴大。在述及一般人格權的內容時,作者說到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觀察問題(或者以損害企業營業為由),法院對于“寶馬汽車案”也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決。[35]由此可知,德國學者是將商主體包含在一般人格權主體中的。事實上,一般人格權之所以產生,乃在于傳統民法典在缺失人格權的一般規定的情況下,許多人格利益受到侵害,只能尋求刑法與行政法的保護而不能得到民法的充分保護。因此,二戰后,在人格獨立、人格尊嚴、人格自由亟需保護的情況下,在缺乏人格權制度因而欠完備的民法制度中,承認一般人格權就極為必要。[36]由于大陸法系國家只對商號權作出了規定,因而商主體的人格權即商事人格權需要通過民法中的人格權制度予以保護;而并不完善的人格權制度又有賴于一般人格權的補充,因此,商事人格權必然也要包括商事一般人格權。就我國法律實踐來說,盡管一般人格權尚未成為立法上的概念,但在司法實踐中則受到普遍承認,在學界更是毫無爭議地被視為人格權制度的基本內容。具體到商事一般人格權來說,盡管學界尚未明確提出這一概念,但早已承認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權。而法人一般人格權的內容,具體體現在法人的人格獨立和人格平等兩個方面。顯然,人格獨立與人格平等實質上正是商主體的本質要求。(具體論證將在本文第四部分展開)因此,商事一般人格權之存在當無疑義。
關于具體商事人格權的范圍,同樣缺乏法律規定與學理研究。即使就法人人格權而言,也不無疑義。如上所述,我國能夠為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權規定了名譽權、榮譽權,此外,還規定了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享有名稱權,《反不正當競爭法》則確立了商業秘密權。但這些權利哪些能夠成為法人人格權,不僅缺乏法律規定,在對此展開研究的法學文獻中也是觀點不一。在各種觀點中,對于名稱權、名譽權作為法人人格權并無爭議,尚難確定者在于榮譽權、信用權、商業形象權與商業秘密權。鑒于辨析這一問題絕非三言兩語所能完成,故將其作為本文的第三大部分予以詳細論述。
三、具體商事人格權述評
關于具體商事人格權,所涉內容繁多,絕非一篇論文所能完成者,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考察具體商事人格權的概念與法律屬性,通過比較研究得出一個盡可能科學的結論,希望對于確立商事人格權制度有所裨益。
(一)關于名稱權
確切地說,商主體的名稱權應稱為商號權,一則各國立法均如此規定,二則只有商號權才能準確地反映出商主體的特殊屬性。商號的概念在不同國家的法律中有著不完全一致的解釋。一般來說,商號又可稱為商事名稱、商業名稱,指的是商主體在從事商行為時所使用的名稱,即商主體在商事交易中為法律行為時,用以署名或讓其人以之與他人進行商事交往的名稱。[37]在我國,商號的法律淵源主要有《民法通則》、《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以及其他單行法規與部門規章。但是在這些法律文件中,關于商號的界定很不清晰。《民法通則》在規定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享有名稱權的同時,又將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的名稱稱為“字號”;[38]《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第7條則規定:“企業名稱應當由以下部分依次組成:字號(或者商號,下同)、行業或者經營特點、組織形式。”顯然,我國法律是將字號等同于商號,根據《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商號乃企業名稱的核心組成部分,而《民法通則》又將字號混同于企業名稱,導致了商號使用上的混亂。基于此,應當嚴格界定商號的含義。多數學者從傳統習慣以及理論體系性出發,主張將商主體的名稱統稱為商號,即從廣義上理解其含義。[39]也有人認為在現代企業法律制度中,多使用“商業名稱”或“企業名稱”,而不單獨使用“商號”。并將我國臺灣地區修改《商業登記法》時改“商號”為“商業名稱”作為明證。[40]但在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商法典中則以商號指稱之。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例的,其作法有所不同,乃將商號權概括在姓名權中,一并加以保護。[41]事實上,問題不在于有多少立法例使用商號或其他名稱,而在于這種名稱是否合適,是否符合我們的交易習慣,哪一種名稱本身都是無所謂好壞的。鑒于我國長期以來都以商號或字號指稱商主體,因此,商主體的名稱權稱為商號權即可。
任何法律主體都必然要以一定的名義標識,并憑借該名義參與社會活動。在自然人,用以標識的名義為姓名,在公法人,其名義為相應機關名稱,在商主體則為商號。毫無疑問,這種用以標識法律主體的名稱應屬于人格權的客體,基于該名稱而享有的名稱權則應屬于人格權的范疇。因此,商號權是一種名稱權,性質上似乎應歸屬于人格權。不過,與民法一般名稱不同的是,商號是商品生產經營者即商主體出于營利目的而創設使用的一種有別于一般民事名稱的特殊名稱。基于此,由于作為商主體的資信狀況、營業風格、特色的象征,商號的使用能為其所有者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因此,“為保護商號所有人對其商號中蘊含的財產利益的享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及一些國家的國內法將商號納入知識產權之列”。[42]我國也有不少學者持相同或者類似觀點。有人認為“商號權就是商品生產經營者依法對其注冊商號所享有的專用權,其內容具有人身權和財產權雙重屬性,在權利類型上屬于知識產權。”[43]另有人認為,商號權應作為知識產權規定于有關知識產權法中,而不應作為人身權規定于民法人身權部分。[44]還有人認為,商號是一種無形財產,商號權作為無形財產權,應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45]除了知識產權或財產權說外,還有人格權說。該說認為,商號是商主體在營業中表彰自己的名稱,實質上與姓名無異;而姓名權屬于人格權,因此商號也應屬于人格權。[46]略有不同的是,有人認為商號權本質上屬于人格權,不過,盡管不是無體財產權,但具有某些無體財產權的性質。[47]更多的學者還是認為,商號權是兼人身權與財產權于一體的混合權利。[48]我們認為,商號是商主體在社會活動中用以確定和代表自身,并區別于他人的文字符號和標記,它依附于商主體,是商主體相互區別的重要外在標志。商號作為一種文字符號和標記,不是圖形,也不是形象,這一點是與姓名相同的。因此,有人將其歸入人格權范疇。然而,姓名權作為人格權,必然具有人格權的一般屬性:其一,專有性,即它與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離,也不得由權利人拋棄;其二,非財產性,即它本身不具有直接的財產內容,也無法體現為確定的財產價值,作為姓名權客體的姓名不能像財產權客體一樣可以轉讓或繼承。顯然,商號權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其一,商號權具有可轉讓性。商號權讓與,歷來有兩種學說。[49]一是絕對轉讓主義,認為商號轉讓應當連同營業同時轉讓,或者在營業終止時轉讓,商號轉讓以后轉讓人不再享有商號權,受讓人獨占該商號權。各國商法典一般采此學說。[50]二是相對轉讓主義,又稱自由轉讓主義,即商號轉讓可以與營業分離而單獨轉讓,并可以由多個營業同時使用同一商號,商號轉讓以后,轉讓人仍享有商號權,受讓人亦取得商號權。[51]顯然,不管哪一種主張,都是同意商號權可以轉讓的。這一點使其與具有專屬性的姓名權區別開來。其二,商號權具有直接財產內容,或者說,以財產權為其主要權利內容。實際上,既然商號權可以轉讓,當然具有財產性,或者說具有直接財產內容。商號作為企業經營能力、資信狀況等的象征,是企業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作為合伙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的合伙人與企業主,對其商號當然擁有所有權(合伙企業為共有權)。當合伙企業合伙人或個人獨資企業主死亡時,其所擁有的商號權作為死者財產,自然可以由其繼承人繼承。這也是商號權與一般民事名稱權與姓名權的根本區別所在。其三,商號權具有公開性。商號必須登記注冊,除了出于國家藉此予以審查控制的目的之外,另一目的便在于使商號公示,一則使其為人所知,二則便于國家監管。對于姓名權來說,盡管每個人都有登記于戶口簿上的正式姓名,但除此之外,自然人還對其筆名、藝名、化名等享有姓名權。
商號權與知識產權也具有明顯的區別。其一,沒有時間性。商號權與企業共存亡,而企業的存續在各國立法及實踐中多無時間限制,所以商號權依附于企業無限期地受法律保護。知識產權則具有嚴格的時間性。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財產權,與商號權的存在必須以其所依附的商主體的存在為前提相比,實際上才真正可謂能夠“永恒存在”,但各國法律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斷然將其限定為只在一定時間內有效。[52]其二,商號權具有更加嚴格的地域性。各國法律普遍規定,商號登記的效力受一定區域范圍內使用之限制。除全國馳名的大企業的商號可以在全國范圍內享有專用權外,其他商主體的商號只能在其登記的某一地區范圍內享有專用權。[53]對于知識產權來說,盡管也只能在其依法產生的地域內有效,但其地域范圍則以國家或者法域為限,在歐共體等對知識產權實行一體化保護的地區,其地域范圍更是擴大到所有成員國內。即使就相對接近于知識產權特性的無形性與專有性而言,也非如人們所想象。實際上,無形財產為數眾多,不可能所有無形財產都劃入知識產權范疇。專有性則為所有絕對權的共同屬性。因此,將商號權劃入知識產權殊為不當。事實上,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乃在于這些學者認為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商號權的,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又被許多國家國內法與國際條約視為知識產權法的組成部分。應當說,這是不夠嚴謹的。畢竟,這只是由于歷史上的某種誤會所造成的一種法律保護模式而已,并不能因此判斷其法律屬性。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商號權不同于姓名權,因其具有可以轉讓與繼承的直接財產內容,并以依法公開為必要;也不同于財產權或知識產權,因其具有嚴格的“人身”依附性,不可脫離商主體而獨立存在。因此,與姓名權為民事主體所必需相同,商號權作為商主體的人格權,亦為商主體所必需。
(二)關于商主體的名譽權
實際上,商主體的名譽權并非法定概念,除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了法人名譽權外,只有少數國家關于名譽權的規定中隱含了對商主體名譽的保護。對此,在立法與學理上,普遍使用的概念則是商譽權與信用權。但一般而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鮮有對商譽權保護的明確規定。就我們所能查閱的立法資料來看,在民商分立國家,民法典與商法典中均未見關于商譽權的規定,在民商合一國家,也僅見《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100條規定,“傳播詆毀名譽、侵害人格尊嚴和商譽信息而造成的損害”,“無論致害人有無過錯,均應補償精神損害”。這一條可算作關于商譽權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則以“信用損害”為題對信用作了專門規定。有人認為,“綜觀大陸諸國,除德國民法典外均未對信用權在法典中作出規定,概認為適用名譽權。”[54]實際上,這種理解只適用于一般民事主體,因為絕大多數國家都未將信用權視為一般民事主體獨立的人格權。事實上,大陸法系多數國家是采用競爭法來保護商譽權或信用權的。例如,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題為“商業誹謗”的第15條第1款規定:“對他人的營利業務、企業主或領導人本人、他人的商品或工業給付惡意主張或傳播構成損害商事企業的違背真實的事實者,應被科以最高為1年之徒刑或罰款”。[55]依此,似應采用商譽權概念為宜。但是,在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第1條第6項的規定中,卻明確采用了“營業上的信用”概念。[56]而在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題為“毀謗”的第14條的規定中,也使用了“商業企業和商業企業主信用”的概念。并且,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第1條第5項的規定實際上是關于商譽權的規定。如此看來,商譽權與信用權又似乎是并不相同的權利類型。不過,日本學者小島庸和強調該類權利是一種反不正當競爭權,僅具有禁止權效力,并不能構成獨立的權利類型。[57]
因此,在究竟應使用哪一個概念,或者說如何使用這些概念問題上,確實頗費思量。在學術界,關于這個問題也并無定論。有人認為,關于信用和商譽,臺灣有些學者將其相提并論;其實,商譽并非一個法律術語,而是一個經濟學術語,其含義與信用無甚區別,只須以信用代替即可。[58]顯然,該觀點持的是等同論。另有人認為,商譽權與信用權系不同類型的權利。譬如,有人認為,傳播流言、宣稱某工廠因遭受火災而停產的行為并不構成對其名譽權的侵害,但構成對其信用權的侵害;[59]甚至有人就信用權與商譽權分別撰文作長篇論述。[60]就我國而言,我們認為,盡管不宜否定信用權的獨立價值,但在商主體上,采用商譽權概念較為妥當,而不宜將信用權確立為與商譽權相并列的權利類型。究其原因有三:其一,盡管各國在競爭法中多數將關于商譽與信用的侵害同時規定,但并未將其確立為獨立的實體權利,而商譽權則已見于立法規定,或通過擴大對名譽權的解釋而得到適用;其二,我國立法從未確立過信用權概念,而商譽權(部分主體)則已為《民法通則》規定的法人名譽權所包含,《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也對侵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行為作了明確規定,并無將信用權獨立規定之意;其三,實際上,至少對商主體來說,信用乃商譽中的組成部分,包含了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的商譽已將信用包含于其中。至于有人認為商譽并非一個法律術語,而是一個經濟學術語,則純屬誤解。實際上,商譽與信用都是經濟學術語,相比較而言,在法律術語中,倒是商譽更多地被使用。
關于商譽權的法律屬性,同樣是觀點各異。在經濟、管理學界,一直將商譽作為財產看待。譬如,有人認為,商譽是一種未入帳的無形資產,不能離開企業整體而單獨存在,其未來收益與成本無直接關系,是一種不可確指的無形資產。[61]與此同時,有關法律文件還從資產或產權的角度肯定了商譽的無形財產的性質。1992年財政部與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聯合頒發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第37條確認:“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專有技術、土地使用權、商譽等。”同年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通則》兩個規范性文件都規定:“無形資產是指企業長期使用,但是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商譽等”。顯然,這是將商譽權視為財產權。
在法學界,關于商譽權的法律屬性,大體上有三種學說。其一,人格權說。在多數民法教材中,都有法人名譽權的內容,或稱名譽權主體除自然人外,還有法人與其他組織。同時明確認定,名譽權乃人格權之一種,并且,對于自然人與法人、其他組織的名譽權并未區分。[62]顯然,這是將法人、其他組織的名譽權作為人格權看待。在這些著作中,盡管未明確提出商譽權概念,但所謂法人、其他組織的名譽權則指的是或者說主要指的是商譽權。需要說明的是,在人格權說中,有人認為,法人名譽權與自然人名譽權一樣純粹屬于精神性權利,只具有間接的財產內容;[63]也有人認為,“法人的名譽權與公民的名譽權相比,與財產權的聯系更為密切,權利本身的財產性更為明顯。”[64]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說商譽權與名譽權尚有所區別的話,也僅僅因為加害人及侵害方式的不同而由不同的法律予以調整而已。“當一個企業的名譽被一般人(即非競爭對手)侵害時,其所侵害的是名譽權;當一個企業的名譽被其競爭對手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等規范的手段侵害時,其所侵害的是商譽權”。[65]其二,人格權與財產權混合權利說。一般來說,持該說者皆主張商譽權兼具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屬性,但若嚴格區分,則又可劃分為不同類型。有人認為,商譽權雖然存在無形財產權性質,但財產性只是其非本質屬性,只有人格權才是它的本質屬性。[66]實際上,這種觀點從本質上講仍屬于人格權說,只不過認為商譽權具有明顯的財產權屬性。另有人認為,“商譽權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知識產權,而是兼具財產權和人身權雙重屬性的新型權利。”[67]該說在肯定了商譽權兼具財產權和人身權雙重屬性的同時,否定了商譽權的知識產權屬性,提出商譽權應屬于一種新型權利,但未能確定究竟屬于何種權利。還有人認為,商譽權應歸類于知識產權,因為它具有人身性和財產性的雙重屬性,而這恰恰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征所在。此外,作為商譽權客體的商譽是人的腦力、智力的創造物,與各種各樣的信息有關,而且這些信息與各種有形物質相結合,因此符合知識產權的固有的無體性特征。[68]其三,財產權說。該說主張“商譽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特殊財產,由此所生之權利當為財產權。”[69]為證明其觀點,該說主張者以國際國內相關會計規則將商譽視為無形財產作為其立法上的依據。應當說,這種觀點看到了商譽權中非常重要的性質,沒有將其混同于一般民事主體的人格權或知識產權,但遺憾的是,未能明確提出商譽權究竟屬于何種性質的權利。
關于商譽權的法律屬性,在各執一詞的眾多觀點面前,確實令人難以判斷。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些觀點所持的理由予以剖析,將商譽權與各相關權利予以比較,最終得出商譽權確切屬性的結論。“人格權說”的理論缺陷在于強調了商譽權的精神利益而忽視甚至否認商譽權的財產屬性。事實上,商譽作為對商主體經濟能力的社會評價,不同于對一般民事主體側重于道德方面的社會評價,已演化為直接的財產利益,因而應從屬于一般人格利益的名譽中分離出來,并受到法律的特別調整。此外,商主體作為由法律創設的自然人之外的法律人格,本無得以享受精神利益的具有情感的肉體,根本談不上享有精神性權利。[70]可見,這種新型的民事權利顯然有別于人格權范疇的名譽權。
“人格權與財產權混合權利說”承認商譽權具有財產權與人格權的雙重內容,正確地說明了商譽權所具有的本質屬性,但其具體結論卻存在或多或少的明顯缺陷。商譽權固然具有人格權的某些屬性,如為主體所必需并與主體不可分離,但這并不是該項權利的本質屬性。如上所述,在國際國內的許多會計規則中都是將商譽作為無形資產考核的。在國際多邊投資協議中,商譽則與版權、專利、商標都是可以用于投資的資產形式。[71]肯定商譽權兼具財產權和人身權雙重屬性,否定商譽權的知識產權屬性,并提出商譽權應屬于一種新型權利,確屬正確的思路。但問題在于,商譽權中財產權與人身權究竟孰輕孰重,兩者關系如何,人身權屬性具體表現為哪些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型權利究竟屬于什么權利,該說都無法回答。至于將商譽權歸入知識產權的觀點,應當說,同樣只是看到了商譽權的表面現象。盡管在兼具人身權性與財產權性,并具有無形性與專有性方面,商譽權與知識產權極為相似,但很明顯,商譽權并不具備知識產權所具有的時間性、地域性與可復制性的特征。
關于“財產權說”,我們認為,商譽權固然具有非常明顯的財產權屬性,甚至可以說這就是其本質屬性,但商譽權畢竟是為商主體所專有并與其不可分離者,因此,不能忽略這種嚴格的人身依附性。事實上,正如名譽權對于一般民事主體乃必不可少者,商譽權對于商主體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這就顯示出其“人格權”的屬性。但很明顯,這種基于商主體特殊身份的“人格權”完全不同于一般民事主體的人格權,而是以財產權為其最主要內容的權利。因此,我們將其歸入商事人格權范疇。
(三)關于商主體的榮譽權
商主體的榮譽權概念既未見任何法律的規定,在學理上也是極少有人使用的概念。遍查大陸法系各主要國家的民法典與商法典,均未見關于榮譽權的明確規定,更不用說對商主體的榮譽權的規定了。所能見者,唯我國《民法通則》第102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榮譽權,禁止非法剝奪公民、法人的榮譽稱號。”學理上則認為:“榮譽權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獲得、保持、利用榮譽并享有其所生利益的權利。”[72]但關于榮譽權的法律歸屬,則有不同認識。根據《民法通則》第102條前半句的規定,榮譽權應為人格權,根據后半句的規定則似乎應歸入身份權的范疇。因此,我國學界這兩種觀點都有。[73]事實上,盡管榮譽權主體因其榮譽而擁有特定的“身份”,但這種“身份”與身份權法意義上的身份含義并不一致。今天私法中所謂“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屬于“家族”所有的權力和特權。[74]有學者則明確提出:“民法上身份云者,謂基于親屬法上之相對關系之身份,有一定身份然后得享有之權利也。”并認為身份權即親屬權。[75]據此,我們認為還是將榮譽權歸入人格權為宜。綜觀各國立法與司法實踐,并未對榮譽權作出獨立規定,乃將其作為名譽權的一部分予以保護。盡管,我們認為,由于榮譽與一般名譽相比有其特殊性,因而我國《民法通則》將榮譽權獨立于名譽權予以特別保護,確有其必要;但是,其差異主要在于榮譽的獲得與內容不同于一般名譽而已,并不至于在權利屬性上作出截然不同的歸類。
就商主體的榮譽權來說,應不存在理論障礙。任何形態的商主體都有可能獲得榮譽稱號,如“質量信得過企業”、“守合同重信用企業”等。問題在于,榮譽權能否成為商事人格權?也就是說,榮譽權是否為商主體作為法律人格所必需者?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很簡單。既然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作為獨立的人格權或者作為名譽權的一部分并無爭議,那么商主體的榮譽權作為商主體的人格權當無疑義。但商主體的榮譽權究竟是因為其歸屬于商主體而成為商事人格權,還是因為不同于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而歸屬于商事人格權,則不無疑問。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性質上屬于精神性權利,并無財產內容,作為人格權當然還具有不可轉讓性。商主體的榮譽權也不能轉讓,此與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相同,但商主體的榮譽權往往能夠為商主體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從而具有財產權屬性。從實際操作來看,則往往將商主體的榮譽權作為商譽權的一部分看待。但不管怎樣,商主體的榮譽權具有財產權屬性都是不容否認的。這一點使其與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區別開來。同時,商主體的榮譽權與商譽權一樣,也具有嚴格的人身依附性,從而與財產權區別開來。因此,將其歸入獨立類型的商事人格權較為適宜。
(四)關于商業形象權
商主體作為法律的擬制物,并無自然人的肖像,自然無肖像權可言。[76]但商主體在經營過程中,往往會為其設計企業形象,這種企業形象也往往會成為企業的標志,從而使其具有了相當于自然人肖像對于自然人的標識作用的人格標識功能。由此形成的虛擬的企業商業形象利益也需要得到法律保護,因此在歐、美、日即出現了日益發達的“商業形象權”保護方式。[77]與此相近的概念還有公開權、商品化權、形象權等。如上所述,這些概念實際上含義相同,其英語表達都為“rightofpublicity”。形象權作為將形象(包括真人的形象、虛構人的形象、創作出的人及動物的形象、人體形象等等)付諸商業性使用(或稱營利性使用)的權利,與本文所提出的商主體對其企業形象所擁有的商業形象權明顯不同。
提出形象權概念的學者認為“此種權利如同作者對其作品所享有的使用權一樣,屬于財產權,而不是人身權。”[78]提出“商業形象權”概念的學者則認為該權利屬于知識產權。應當說,基于人格權以及作品的商品化利用而形成的形象權確實具有明顯的財產權屬性,但其同樣明顯的人格權屬性也不容忽視,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其法律歸屬實難判定,但將其斷定為財產權則顯然失之武斷。商業形象權的客體-企業形象,由于要以作品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屬于版權范疇。但是,很明顯,企業形象的本質,不在于企業得以擁有對于其所設計的企業形象的版權利益(包括精神性與物質性利益),而在于借助該企業形象擴大企業的影響,從而為其創造巨額經濟利益。因此,事實上乃作為企業法律人格標識而存在的企業形象,并不能將其等同于僅僅作為受版權法保護的作品。不過,與肖像權相比,商業形象權又具有明顯的為肖像權所不具有的財產權屬性,良好的企業形象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往往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能為其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另外,肖像權除去新型的形象權因素外,只能為權利人所專有,并不能轉讓、拋棄和繼承。而商業形象權則不然,商主體可以自由地將其處分,如可以通過廢棄企業形象而拋棄對其享有的權利,可以通過轉讓企業形象而獲取高額回報,此外,商主體終止之后,其繼受者可以繼續擁有其商業形象權。基于此,我們認為,商業形象權應當劃入商事人格權的范疇。
(五)關于商業秘密權
關于商業秘密權,據查證,各國民、商法典中均無規定。對此,各國大多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79]此外,也有不少國家通過合同法、侵權法予以保護。[80]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中,盡管沒有使用“商業秘密”概念,但其“未披露過的信息”實際上就指的是商業秘密。[81]在學術界,則基本上是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加以研究。
至于商業秘密權的法律屬性,多數學者都將其歸入知識產權或財產權的范疇。[82]另有學者將其作為法人人格權的重要內容。[83]還有人將其歸入“商事人格權”的范疇。[84]盡管,如上所述,該“商事人格權”概念乃為我們認為并不確切者,但反映出該說主張者認為商業秘密權具有人格權的屬性。誠然,商業秘密對一個企業來說,尤其是對于諸如“可口可樂”公司等企業來說,具有著決定其興衰成敗的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是,這種對企業運營具有至關重要的生產因素,從本質屬性上說,并非決定商主體法律人格的因素。易言之,商業秘密對企業固然非常重要甚至能對其“生死存亡”起決定性作用,但既不依附于商主體,也并非商主體維持其法律人格所必不可少者。這一點,與隱私權不一樣。盡管隱私權乃為保護自然人的個人信息,使該個人信息得有自然人本人支配,似乎與商業秘密權相似。然而,法律之所以確立隱私權保護制度,乃在于隱私對于自然人的人格尊嚴與人格自由極其重要,對自然人維持其正常生活可謂不可或缺。顯然隱私權具有明顯的人身依附性。因此,我們認為不宜將商業秘密權歸入商事人格權范疇。
四、商事人格權法律屬性與制度價值
(一)商事人格權的法律屬性
通過對具體商事人格權的逐項分析,可以看出,除了一般商事人格權外,還存在著商號權、商譽權、商事榮譽權、商業形象權等具體商事人格權。通過具體商事人格權性質的界定,我們同樣能夠得出結論:商事人格權既非傳統民法意義上的人格權,也非知識產權,更不能籠統地稱之為財產權,而是一種兼具了傳統人格權與財產權特征的新型權利,唯有“商事人格權”概念才能準確地指稱之。
商事人格權作為商主體特有的人格權,乃商主體維持其法律人格所不可或缺者。但商事人格權畢竟為商主體所專有的人格權,不可能具有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權中的物質性人格權-生命權、身體權與健康權,也不可能具有所謂“精神性人格權”,因為商主體既無精神的載體-肉體,自無精神可言,精神性人格權也就無從談起了。如此一來,似乎陷入了矛盾:既無物質性權利又無精神性權利,豈不是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了么?事實上,這正是商事人格權的特殊性所在。我們說商事人格權無物質性權利與精神性權利,乃以傳統人格權理論為參照得出的結論。傳統人格權理論人格權不具有財產內容或者說不具有直接的財產內容,因此,除為維持自然人的物質存在所不可缺少者,故稱之為物質性權利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外,其余諸如姓名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則只能歸入精神性權利范疇。對于商事人格權來說,則不能依此判斷。商主體固然無自然人的物質形體,但依“法人實在說”理論,則商主體也同樣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只不過這種實體不同于自然人的物質實體-肉體,乃系為法律所創設的組織體。[85]要維持該組織體的存在,或者說,要使其得以正常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除了企業資本、設施等條件外,商號、商譽等商事人格權的客體也是必不可少的。盡管,有人認為法人也有精神,基于法人實在說,其機關成員的精神即屬法人的精神,[86]但是,如上所述,這種理解顯然是一種誤解。從這個意義上說,商事人格權似應歸入物質性人格權范疇。然而,如此界定又極可能與自然人的物質性人格權相混淆。因此,我們認為,商事人格權實乃一種為傳統人格權理論或者說適用于民事主體的人格權理論所解釋,只能在商法的體系內獲得解釋。也就是說,商事人格權作為商主體所專有的權利,只能解釋成一種獨立的商事權利。
需要說明的是,切不可將商事人格權與同樣作為組織體形態的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的人格權混為一談。就其性質而言,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的法律人格要素也同樣不同于自然人,故其人格權也與自然人殊為不同。在具體表現上,不唯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不能享有自然人之物質性人格權,即便在被學界認為屬于法人人格權范疇的名譽權方面也與自然人之名譽權具有顯著差異。事實上,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的人格權與商事人格權也具有明顯差異,并不能歸入同一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所享有的名稱權,不僅不具有財產權屬性或者說不具有直接的財產權屬性,而且在侵權救濟上也頗為不同。一般認為名稱權包括名稱決定權、名稱使用權、名稱變更權與名稱轉讓權等內容。顯然,對公法人來說,并不可能行使這些權利,更談不上通過行使這些權利獲取經濟利益了。非營利組織雖可行使這些權利,但因其非營利的性質,同樣不能通過其名稱的使用與轉讓獲取經濟利益。對公法人來說,實際上談不上私法上的侵權救濟。他人(包括組織)既不可能干涉公法人的名稱權,也不可能以民事侵權的方式假冒或者盜用公法人的名稱。若有人假冒或者盜用公法人的名稱,其直接侵害的乃國家利益,因而構成行政違法或者刑事犯罪。就各國立法例而言,自然人之外的組織體人格權多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保護,顯然,公法人的名稱權不能依此獲得保護。從性質上講,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經營性競爭已經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似應可以適用侵權法或競爭法,從而依此獲得保護。然而各國事實上并未將其納入侵權法與競爭法的范圍,因而也不能獲得私法方式的救濟。因此,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所享有的名稱權與商主體的商號權具有極為明顯的內容與性質上的差異。其二,在名譽權方面,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也明顯不同于商主體。基于名譽權的一般屬性,我們認為,公法人實際上并不應獲得名譽權的保護,或者說公法人就根本不具有名譽權。由于公法人作為公共服務機構的特殊法律屬性,其理當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即便社會輿論對其評價有不妥之處,除非惡意攻擊政府而因此應追究行政與刑事責任,均不應提起侵權之訴。非營利組織應擁有名譽權,但其名譽權也明顯不同于商譽權。應該說,非營利組織并非不能獲得營利,只不過,其盈利不能分配于其投資者,而只能用于社會公益事業。因此,非營利組織的名譽權既有人格標識意義,也具有一定財產權屬性,只是該項財產權只能歸屬于非營利組織這個抽象的法律人格,而不能最終歸屬于其投資者。并且,由于非營利組織特有的非營利屬性,即使發生非營利組織間的合并,也不能藉此獲利;因而,非營利組織的名譽權只能在正常經營過程中通過使用而體現出其財產屬性,而不能通過轉讓獲得經濟利益。其三,在榮譽權方面,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同樣區別于商主體。公法人固然也能獲得榮譽稱號,但除去獲得的各種獎金外,這種稱號并不能為其帶來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經濟利益。非營利組織的榮譽權除了獎金外,可能會為其創造較高的經濟利益,從而具有間接的財產權屬性。但由于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可轉讓性,該榮譽權難以在整體轉讓中作為“商譽”的一部分獲得財產上的體現。因此,非營利組織的榮譽權也不同于商主體的榮譽權。其四,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盡管也具有一定的標識(如政府機關、學校的徽章),但該標識不同于商主體的商業形象。應該說,公法人的標識也具有人格標識意義,但除此之外,并不能像商業形象那樣通過宣傳創造經濟利益,也不能通過轉讓獲得經濟利益。至于非營利組織,雖然可以通過宣傳創造經濟利益,但卻不能為其投資者帶來最終的經濟利益。基于此,公法人與非營利組織對其標識所擁有的權利,也明顯不同于商業形象權。
有鑒于此,應當將商事人格權作為一種獨立的商事實體權利,在商法典或類似商事立法中予以明確規定。在大陸法系國家,無論采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立法例,都將商法視為民法的特別法,認為民法是抽象化的法律表現,商法是具體化的法律表現。如民事所有權制度是商事交易財產的一般規定,商事物權制度是商事交易財產的特別規定;民事主體制度是商主體制度的一般規定,商主體制度則是民事主體制度的特別規定。[87]顯然,對于民法中規定的能夠適用于一切民商事法律關系的制度,商法當然無須重復規定,但是,對于商法中的不能為民法一般規定所包含的特殊制度,則只能也應該由商法單獨規定。但遺憾的是,傳統商法卻大多未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使得商事人格權這樣重要的制度竟然在各國商法中都未能占據一席之地。我們認為,應當改變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對商事人格權予以保護的現行作法,恢復商事人格權在商法中原本應當擁有的地位。
(二)商事人格權的制度價值
如上所述,商事人格權既不能為傳統人格權所解釋,也不能為知識產權與財產權所解釋,只能作為一種獨立的商事權利而存在。事實上,也恰恰只有獨立存在的商事人格權才能使商主體制度得以健全起來。我們很難想象,商主體作為商事法律人格者卻沒有相應的人格權,同時,“寄居”于傳統人格權名下的各具體商事人格權,卻“處境尷尬”,無從獲得恰當的解釋。因此,提出商事人格權概念并在商法典或相關商事立法中予以明確規定,對于完善商主體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對此,我們必須解放思想,不能因為傳統商法中商事人格權制度的缺失,就斷定商法中不應存在原本為完善的商法所不可缺少的商事人格權制度。事實上,法律源生于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同時又要對經濟生活的實踐起到現實的指導作用,而不應自我局限于一種先驗的或繼受于外國立法例的模式。對于產生于商事交易實踐的商法而言,這種制度特性或者說規范要求更加明顯。并且,眾所周知,正因為商法只是對商人習慣法的簡單承認-盡管是用立法形式,而缺乏像民法那樣的深厚理論積累,在將商法作為民法特別法理念的指導下,從一開始就缺失了許多本應特別規定的基本制度,因而,可謂先天不足。如果說在近代商法產生之時的19世紀,由于商事關系的相對簡單,這種矛盾尚不突出的話,那么,在經濟生活早已發生了急劇變化的今天,這種法律的不妥當性就顯得尤其明顯。此外,屬于簡單商品經濟完善法性質的民法,其理論體系實際上早已在發生了并還在發生著的經濟生活異變面前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了。就民事權利體系而言,傳統民法將民事權利劃分為財產權與人身權,其中財產權又分為物權、債權,人身權則又可分為人格權與身份權,除此之外,還有被認為兼具人身權與財產權屬性的知識產權。顯然,這種劃分已經顯示出不完全性了。譬如,長期以來一直作為學界爭議焦點的股權及法人財產權性質問題,人格權商業化利用所形成的權利性質問題,就不能在傳統民法的理論框架內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對于商事人格權來說,同樣如此。實際上,商法中許多問題都已經超出了傳統民法的界限,或者說不能在民法理論體系中獲得解釋。盡管許多民法學家都堅信民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與擴張性,并且在所謂民法商事化的發展趨勢下,民法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最終會解決一切理論難題。但是,很明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不能為民法體系所包容的商事法律問題日益增多,許多問題依民法理論解釋都難免理論不周延性的尷尬局面。相反,如果我們能夠確立根源于民法又獨立于民法的諸如商事人格權等特殊制度,則既解決了民法理論試圖解釋而事實上又不能解釋的理論困境,又使商法制度具備了獨立發展的堅實的理論基礎。至于說這樣做將導致創設一些新概念或改變傳統概念的含義,如果因此而不敢創新,則顯然是將本應作為思維工具的概念變成了思維的束縛了。畢竟,在法律概念的構成上“必須”考慮到擬借助該法律概念來達到的目的或實現的價值。亦即必須考慮所構成之法律概念是否具備實現所期望之目的或價值的“功能”。[88]并且,任何規定都只對特定的時空具有妥當性。易言之,對特定時空妥當的規范從來都必須依賴生活在該時空的人,因此,應盡力使其得到演進、完善,而不能過于依賴先人或“外國的和尚”。因為對于先人,而且對于外國人所肯定的價值,當代人皆需經歷重新認識、承認與溝通的過程,才能使該價值取得當代之社會、文化上的存在基礎。[89]既然如此,我們自然不應在理論上自我“囚禁”,而應從經濟生活的實踐出發,立足于商法理論的完備,大膽創新,為我國商法同時也為世界商法理論體系的完善作出積極貢獻。尤其在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前夕,科學地確立商法的體系結構,對于科學地架構民法典,從而制定出一部為我國民法學界所企盼的具有國際影響的世紀性民法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前已述及,商事人格權可分為一般商事人格權與具體商事人格權。如果說具體商事人格權除了能夠在商法典或相關商事立法中得到規定之外,還能夠通過民法人格權制度、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中予以規制的話,一般商事人格權的制度價值則難以通過其他法律得以實現。如上所述,一般商事人格權以人格獨立與人格平等為內容,而這兩項內容既是具體商事人格權的抽象,又是對具體商事人格權的補充,因此確保這兩項內容的實現,對于維護商主體的獨立法律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商主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必然需要獨立形成其意志,并獨立實踐其意志,否則將使其喪失在市場競爭中作為“理性主體”正確判斷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能力。此外,作為商主體法律人格要素的財產獨立必須獲得法律保障。具體來說,公司應能夠對其“法人財產權”客體-公司全部財產擁有完全的支配與處分權,合伙企業也應當確保合伙財產獨立于合伙人個人財產,個人獨資企業則應當確保通過商業帳簿將其個人與家庭財產嚴格區分開來。由此可見,盡管不同形態的商主體對財產獨立的要求并不相同,但都有此要求,否則,商主體便無從獲得其法律人格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因此,必須努力排除各種因素對商主體的不當干擾,就我國而言,尤其要注意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受到事實上大量存在的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干預與控制,使其作為商主體所必不可少的獨立人格受到不良影響甚至趨于扭曲。同時,商主體若喪失其人格平等的法律地位,將使其難以作為正常的市場的競爭者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其結果,使得該商主體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之外,還將嚴重損害市場秩序,從而使市場經濟制度的功能難以得到正常發揮,最終必然要嚴重損害整個國家的競爭力。基于此,當商主體的人格獨立或人格平等的利益受到損害,又不能根據商號權、商譽權、榮譽權、商業形象權等具體商事人格權得到有效救濟之時,就應當依據一般商事人格權予以保護。這就需要以包含了一般商事人格權制度的商事人格權制度來調整了。
五、結語
商法的理論架構問題歷來是各國商事立法與商法理論中的難點,在我國尚顯年輕的商法學理論中,對此問題的精深理論研究也是極為匱乏。關于商主體與商行為的研究應該說也不乏力作,但往往停留在依照某個國家的商法體系結構加以描述,或者將各種體例予以一一介紹,最后匆匆得出一個難以令人信服的結論。面對各國差異極大的商法體系結構,尤其是各國商法在實踐中的尷尬處境,要提出一個能夠適應經濟生活發展要求并能夠協調各種法律部門之間關系的商法體系結構的設計方案,確實令人倍感躊躇。然而,商法理論的問題越多就越需要我們去努力解決,只有如此,才能指望我國商法從理論到立法全方位的繁榮。這就特別需要我們能夠潛心對一系列商法基礎理論問題作出精心的研究。就商事人格權而言,實際上只是一個小小的問題,但該問題的解決,對于商主體理論的完善極為重要。而商主體問題無疑乃我國將來制定《商法典》或《商法通則》,所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論問題。此外,商法理論中同樣極為重要的商行為問題,亦系商法理論研究中不容回避的根本性問題,需要學界共同關注并投入較大的力量予以深入研討。
注釋:
[1]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提法本身并不嚴謹,只是反映了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后,絕大多數人都被卷入了市場,參與商品交換,但這并非意味著人人都是商人。
[2]參見王利明等著:《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3]參見杜穎:《論商品化權》,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4]參見鄭成思著:《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頁;董炳和:《論形象權》,《法律科學》,1998年,第4期。
[5]參見董炳和:《論形象權》,《法律科學》,1998年,第4期。
[6]參見阮贊林:《商號權的幾個問題探討》,《商業經濟與管理》,2001年第5期。
[7]參見張麗霞:《試論我國商號立法中的問題》,《國際經貿研究》,1997年第1期。
[8]參見張新寶著:《名譽權的法律保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9]參見王娜加:《論侵害商譽權及其法律救濟》,載《內蒙古師大學報》1999年第1期。
[10]程合紅:《商事人格權芻議》,《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11]梁慧星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12]梁慧星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13]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14]參見程合紅:《商事人格權芻議》,《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15]金邦貴譯:《法國商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16]王書江、殷建平譯:《日本商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7]參見范健主編:《商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18]我國《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商事組織法以及《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個人獨資企業登記管理辦法》、《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均將登記作為相應企業的成立要件。
[19]參見王利明等著:《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5、113頁。
[20]魏振瀛主編的《民法》中(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8頁)也將法人作為一般人格權的主體,德國學者迪特爾。梅迪庫斯所著《德國民法總論》中(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9頁)也似乎認為法人得享有一般人格權。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梁彗星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等絕大多數著作中則均未規定法人一般人格權。
[21]參見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22]參見吳鋒、杜曉智:《法人人格權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23]參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0頁。
[24]參見鄭沖、賈紅梅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6頁。
[25]楊立新著:《人身權法論》(修訂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26]參見殷生根、王燕譯:《瑞士民法典》,1999年版,第12頁。
[27]參見吳兆祥等譯:《瑞士債法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2頁。
[28]參見王書江譯:《日本商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頁。
[29]參見費安玲、丁枚譯:《意大利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頁。
[30]參見黃道秀等譯:《俄羅斯聯邦民法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48、455頁。
[31]參見范健等譯:《德國商法典》,載《中德經濟法研究所年刊》(第6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頁;王書江、殷建平譯:《日本商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吳日煥譯:《韓國商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32][臺]王澤鑒著:《人格權、慰撫金與法官造法》,載臺灣《法令月刊》第44卷,第12期。
[33]參見吳漢東:《論商譽權》,《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34]參見《民法通則》第98—103條。
[35]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809頁。
[36]參見王利明等著:《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
[37]參見范健著:《德國商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頁。
[38]參見《民法通則》第26、33條。
[39]參見范健主編:《商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40]參見任先行、周林彬著:《比較商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頁。
[41]參見[臺]黃宗樂監修《六法全書。民法》,保成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6頁。
[42]參見張禮洪:《論商號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1995年第5期。
[43]張麗霞:《試論我國商號立法中的問題》,《國際經貿研究》,1997年第1期。
[44]參見于新循:《關于完善我國商號法律制度的幾點建議》,《重慶商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
[45]參見徐學鹿著:《商法總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頁。
[46]參見趙中孚主編:《商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頁。
[47]參見楊立新、吳兆祥:《論名稱權及其民法保護》,《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48]參見范健主編:《商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頁。
[49]參見楊立新、吳兆祥:《論名稱權及其民法保護》,《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50]德國、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國的商事立法奉行這一原則。
[51]法國商事立法奉行這一原則。
[52]參見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
[53]參見《日本商法典》第19、20條,《韓國商法典》第22條。
[54]參見蘇號朋、蔣篤恒:《論信用權》,《法律科學》,1995年第2期。
[55]參見《各國反壟斷發匯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頁。
[56]參見《各國反壟斷發匯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頁。
[57]參見[日]小島庸和:《無形財產權》,日本創成社1998年版,第43頁。
[58]參見蘇號朋、蔣篤恒:《論信用權》,《法律科學》,1995年第2期。
[59]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頁。
[60]參見吳漢東:《論商譽權》,《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參見吳漢東:《論信用權》,《法學》,2001年第1期。
[61]何俊德:《經濟性貶值狀況下企業商譽評估之初探》,《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62]參見江平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頁;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頁;王利明等著:《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頁;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頁。
[63]參見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64]參見王利明等著:《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頁。
[65]參見張新寶:《名譽權的法律保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66]參見王娜加:《論侵害商譽權及其法律救濟》,載《內蒙古師大學報》1999年第1期。
[67]趙萬一著:《商法基本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頁。
[68]參見梁上上:《論商譽與商譽權》,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5期。
[69]參見吳漢東:《論商譽權》,《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70]對于商法人來說,不管采關于法人本質的何種學說,無疑都無所謂精神可言。對于商合伙而言,作為具有獨立于合伙人人格的法律人格者,也無精神利益可言。即使是在法律人格上公認為依附于企業主個人人格的商個人,對于其企業商譽的侵害,也不能等同于對于其本人的侵害。
[71]參見鄭新建:《試論商譽權的法律屬性》,載《河北法學》2000年第1期。
[72]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2頁。
[73]江平主編《民法學》采人格權說,魏振瀛主編《民法》、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上)則采身份權說。
[74]參見楊立新著:《人身權法論》,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75]史尚寬著:《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76]即使對于商個人來說,盡管其法律人格依附于企業主個人人格,也應當將企業主與企業本身嚴格區別開來,企業主個人的肖像并不能成為企業的肖像。
[77]參見鄭成思:《知識產權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頁。
[78]參見董炳和:《論形象權》,《法律科學》,1998年,第4期。
[79]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7條、法國《公平交易法》第23、24條等均系對商業秘密的專門規定。
[80]參見齊樹潔、賀紹奇:《論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1期。
[81]參見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頁。
[82]參見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頁;寇占奎著:《論商業秘密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83]參見馬俊駒、余延滿著:《民法原論》(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頁。
[84]參見程合紅:《商事人格權芻議》,《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85]公司、合伙企業作為組織體當無疑義,個人獨資企業以及特殊形態的公司-國有獨資公司、一人公司,除了在僅將物質資本出資者視為成員意義上難謂組織體外,若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審視,還是可謂廣義的組織體。
[86]參見任勝君:《法人精神損害亦應賠償》,《律師世界》,1999年第7期。
[87]參見范健主編:《商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88]參見[臺]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
[89]參見[臺]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頁
- 上一篇:管理層收購立法完善研究論文
- 下一篇:縣委中心組在縣域經濟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