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傳播論文
時間:2022-07-19 05:57:00
導語:鄭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傳播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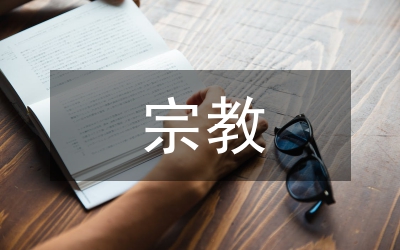
摘要:在下西洋中,鄭和使團作為中國對外傳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進行了多種文化傳播活動。無論在鄭和使團內部還是在鄭和使團與海外人民之間,都進行了宗教文化傳播,且大多通過宗教活動進行傳播,從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及傳播效果上,都體現了規范性傳播的特點。
關鍵詞:鄭和下西洋;鄭和使團;宗教活動;規范性傳播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歷時二十八年,前后到達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無論出發前在國內還是下西洋在海外,都進行了許多宗教活動,這些宗教活動的開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順利進行。從傳播學角度來說,每次宗教活動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傳播活動,從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看,都體現了規范性傳播的特點。
一、使團內部的規范性傳播
傳播學理論指出,在一個組織群體中,群體意識的強弱對組織內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響,群體意識強,組織內部的凝聚力就強,反之則凝聚力弱。而群體意識又包括群體目標、群體規范、群體感情和群體歸屬意識,這幾個要素越具備,群體意識就越強,越欠缺則群體意識越薄弱。鄭和使團作為中國對外傳播文化的組織,怎樣才能形成很強的群體意識以建立一個凝聚力強、有中國特色的形象組織?怎樣才能形成一套自覺遵守的行為規則和價值取向呢?“群體意識無疑是在群體信息傳播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鄭和使團內部需要進行規范性傳播,有意識地營造一種傳播情境,有目的地傳播有效信息,促成群體意識的形成。
鄭和使團下西洋,目的明確,紀律嚴明。也就是說,鄭和使團群體目標具備了,還要有統一的群體規范、強烈的群體感情和濃厚的群體歸屬意識,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終保持高度統一,嚴格遵守規則,保持組織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統一的群體規范,除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和措施外,還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體成員對組織在精神上形成一體化的感情,產生濃厚的群體歸屬意識,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也離不開宗教文化。因為自古以來,宗教在中國一直有較強的影響力,人們能夠憑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傳播關系,加深感情。從鄭和使團內部的宗教文化傳播來看,在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圍繞規范性傳播進行的。
(一)傳播目的的規范性
鄭和下西洋次數多,歷時長,每次下西洋需要近兩年時間,航海路途艱險遙遠,鄭和使團隊伍龐大,人員眾多,思想復雜,思想情緒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波動,行為難免有所松弛。從下西洋的實際過程看,鄭和使團舉行了多次宗教活動,單單瞻禮天妃海神在國內就進行了多次,如每次下西洋前沿途祭祀天妃,平安歸來后酬謝天妃等。從傳播學方面分析,這些宗教活動都體現了規范性傳播的特點,傳播了一種“神”的思想,在這些宗教活動中營造了一種特殊的傳播氣氛,不斷強化刺激成員的感官,以致每個成員都能接受內部所傳播的宗教思想,逐漸形成統一的認識和群體規范,堅定他們下西洋的意志,最后表現在行動上,全心全意為下西洋效力。
(二)傳播內容的一致性
鄭和使團所進行的宗教活動,有的活動有碑文記載,如泉州靈山圣墓行香時的立碑刻石記載“望靈圣庇佑”閉,鄭和印造的《大藏尊經》奉施全國各著名佛寺流通供養,以報答“率領官軍寶船,經由海洋,托賴佛天護持”阿之恩。第四次下西洋回國后興建天妃宮,立有《御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碑文描述了天妃顯靈搭救眾人、化險為夷的情景。第七次下西洋在劉家港興建天妃宮,宮內所刻碑文首推天妃說:“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之神,威靈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等等,從這些文字分析,鄭和使團在每次宗教活動中都傳播了一種“神”的思想。如神靈庇護、神靈相助、神能勝天等宗教思想,在傳播內容上體現了一致性。雖然使團成員中大多數對下西洋的目的明確,態度堅定,行為統一,但也有一些成員心存顧慮,尤其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許多成員對遠航路途遙遠、艱險等方面產生了畏難情緒,對航海能否生還憂心忡忡。如隨船醫生陳常,“臨終但日:‘今不葬身魚腹矣。’”這是當時使團成員中畏懼心理的典型表現。針對成員中存在的畏難心理,從當時的文化、心理、技術等方面需要出發,鄭和在使團內部傳播了宗教文化中“神”的思想,借助“神”的力量統一思想,規范言行,使無顧慮者意志更加堅定,有顧慮者解除憂患,對下西洋達成共識。
(三)傳播媒介的多樣性
鄭和使團每次進行宗教活動,都是按照一定的規范進行宗教文化傳播,從宗教活動的記錄分析,除了依靠當時使用得最頻繁的有聲語言外,還借助了多種傳播媒介,如體態語言、物質符號、碑文、書籍等多種媒介,在當時的傳播技術條件下,體現了傳播媒介的多樣性。如在永樂五年到宣德五年(1407-1430年)間,鄭和八次捐錢印造《大藏尊經》,在全國各著名佛寺流通供養,這里用的是文字傳播。鄭和使團第七次下西洋前重修天妃廟、新建夭妃官、拜祭天妃神、立碑、刻碑文等,則用了物質符號、有聲語言、體態語言、文字等多種媒介。
(四)傳播效果的顯著性
作為使團帶頭人的鄭和,他是中國當時流行的三大宗教的虔誠信徒,對伊斯蘭教、佛教都有信仰,且對天妃海神格外尊崇,他能成為使團內部宗教文化傳播的意見領袖,在使團中具有絕對權威性,他所傳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團成員中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因此他所傳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團成員中接受程度高。而且使團中的很多成員也有宗教信仰,如翻譯馬歡、哈三、蒲和日等也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隨從王景弘、侯顯、王貴通等人都信仰佛教,幾乎所有的成員都信仰天妃海神。因此,在宗教活動中,鄭和與宗教信仰者之間傳播機遇多,互動頻率高,傳播效果好,感情越來越深厚,關系越來越牢固,群體意識也越來越強,組織凝聚力也越來越強。另外,鄭和使團中那些虔誠的宗教徒在宗教活動中積極參與,傳播中所產生的共鳴強烈,形成的宗教文化傳播氣氛相當濃厚,對使團中那些有偏離性意見或思想觀念動搖者造成了一定的信息壓力,那些成員受到一種群體感染,也逐漸消除了偏離性意見,轉變了思想觀念,統一了思想,協調了活動,全體成員維持了群體的自我同一性,規范性傳播效果實現了,“眾愿如斯,咸樂趨事”。
二、在海外的規范性傳播
鄭和使團下西洋以前,東南亞、南亞、西洋一帶因宗教不一,經常發生爭端,海道不寧,因此郟和使團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規范海外各國友好相處,“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讓沿海各國人們自覺遵守這一規范?當然需要在使團與沿海國家人民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傳播關系,傳播必要的文化信息,促成和諧。傳播學理論指出,當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由于某些共同感興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進行有效傳播,而且任何傳播活動總是在一定時間、空間、場合與背景中發生的,超時空的傳播活動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下西洋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民之間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感興趣的宗教文化作為傳播紐帶,開展一些宗教活動,在活動中相互交流和溝通,從而達到規范性傳播目的。鄭和使團在海外宗教文化的規范性傳播主要體現如下:(一)傳播對象的差異性
鄭和使團與沿海各國各地區人民之間雖然因為宗教文化而形成了傳播關系,但是沿海地域復雜,各地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宗教等各方面差異性很大,因此鄭和使團面對的傳播對象千差萬別,在接受態度、行為、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從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資料分析,當時的南洋、西洋一帶有許多國家也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對鄭和使團來說,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建立傳播關系,較容易憑借共同的宗教文化找到合適的傳播對象。而東南亞、南亞各國,尤其是南洋群島一帶的小國家還沒有信仰伊斯蘭教、佛教,鄭和使團面對的傳播對象對所傳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他們對鄭和使團所傳播的宗教文化可能采取迷惑或抵制態度。沿海國家有些人民還信仰“鬼教”,此類傳播對象對鄭和使團所傳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抵制或排斥的。可見,鄭和使團面對的傳播對象在宗教文化現狀、接受態度和行為等方面都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
(二)傳播內容的靈活性
針對傳播對象的差異性,鄭和使團只有適當調整傳播內容,以求達到規范性傳播目的。對宗教信仰歷史悠久的國家,那里的人民宗教信仰穩定,鄭和使團就依照當地的風俗開展宗教活動,傳播當地人們樂于接受的宗教文化,使他們在原有的基礎上接受鄭和使團所傳播的宗教文化。而對沒有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國家,則選擇佛教或伊斯蘭教中讓他們較容易接受的內容進行傳播,傳播內容由淺人深,由少到多。對沿海地區原有的較好的宗教文化,鄭和使團則尊重他們,遵從他們的宗教文化,甚至在傳播佛教或伊斯蘭教的同時不同程度地接受當地的宗教文化。
如錫蘭山崇信佛教歷史悠久,鄭和使團每次到錫蘭山,必須到佛寺進行佛事活動,尤其是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向佛寺布施禮品外,還立石刻碑文,碑文分別用漢、泰米爾、波斯三種文字傳播佛教文化。在爪哇,發現土民崇信鬼教,鄭和使團曾極力勸服當地居民信仰伊斯蘭教。而在古里國時,發現當地人民“俗淳厚,尚信義”,既信仰佛教、伊斯蘭教,又敬重象牛,鄭和則命令部下切實尊重并接受當地風俗,且用文字記載此事,既傳播當地的風俗,也傳播佛教和伊斯蘭教。由此可知,鄭和使團在沿海地區傳播宗教文化,能夠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適時調整傳播內容,注意了傳播內容的靈活性。
(三)傳播方式的技巧性
鄭和使團面對不同的傳播對象,在傳播過程中必須講究傳播方法,注意傳播的技巧性。當時南洋、西洋一帶的許多國家和鄭和使團一樣,也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那么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很容易建立起有效傳播關系,在規范性傳播上技巧性要求不高。而對沒有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國家,則要講究傳播技巧,要在了解他們的信仰或特點的基礎上,采取感情訴諸或說服教育的方式傳播宗教文化,甚至采取恐懼訴求的方式傳播,強制受傳者接受規范性傳播內容,達到規范性傳播目的。
據《外國史略》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到爪哇時,爪哇土民崇信鬼教,鄭和使團曾勸服當地居民信仰伊斯蘭教。據印度尼西亞歷史學家斯拉默穆利亞納在《印度——爪哇王朝的覆滅和努山打拉伊斯蘭國家的興起》一書寫到:“鄭和先是在巨港,后來在山巴斯(西加力曼丹)建立穆斯林華人社區,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馬來半島和菲律賓等地建立類似的社區。他們遵照哈納菲教派的教義和義務用華語傳播伊斯蘭教。”面對宗教信仰不同的傳播對象,鄭和使團采取的傳播方式既有說服傳播,也有集中傳播。而對完全排斥佛教或伊斯蘭教的人們,在進行規范性傳播時,鄭和使團則采取多種傳播方式相結合。如對錫蘭山國王阿烈苦奈爾,第一次到錫蘭山,鄭和發現國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曾勸其“敬崇佛教,遠離外道”,改邪歸正,但未成功;第三次下西洋鄭和再次要求他改邪歸正,而他反而“欲圖害使者”,于是鄭和使團捉拿了他,并帶回中國交與明成祖,且在其親屬中選擇了較賢能且能尊佛教的人為錫蘭山國王,同時他也被遣送回國。可見,對抵制心很強的傳播對象,鄭和則采取了說服、強制、感化等多種方式傳播宗教文化。
(四)傳播效果的有效性
鄭和使團在海外進行規范性宗教文化傳播,對于統一沿海各國的宗教文化、聯絡各國各地區人民的感情、加強各國之間的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實現了規范性傳播效果,“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至今在南洋、西洋一帶還保留有三寶廟、三寶壟、三寶洞、三寶寺等古跡,有些寺廟中還擺有鄭和雕像,海外人民把鄭和當作神靈敬仰,足以說明鄭和使團在文化傳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當時,鄭和使團所訪問的亞非國家中,許多國家有信仰伊斯蘭教或佛教的傳統,鄭和使團中凡信仰伊斯蘭教或佛教又懂得當地語言的成員,紛紛以語言為媒介,以伊斯蘭教或佛教為信息紐帶,和當地老百姓交流,融入到當地的人民生活中,廣泛地傳播宗教文化,信息量大,既增進了與當地人民之間的感情,又能達到規范性傳播效果。而且在沿海一些地區相繼建立了穆斯林社區和清真寺,集中傳播伊斯蘭教,這樣,傳播范圍越來越廣,傳播渠道越來越多,有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等,傳播方式由說服傳播到感染傳播、教育傳播,程度越來越深,使得伊斯蘭教在南洋各地迅速、廣泛傳播開來。據資料顯示,當時的華僑穆斯林在各地區傳播伊斯蘭教十分積極,一個世紀之后,爪哇終于由華裔穆斯林創建的伊斯蘭王國所管轄了。可謂是“伊斯蘭教從群島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這也許是在宗教史上沒有先例的。”至今印尼日惹華文聯誼會會長鄧國光都說,印尼全國約有90%的人信仰伊斯蘭教,這是鄭和在印尼傳播伊斯蘭教的功勞。可見鄭和使團傳播伊斯蘭教的影響之大,效果之明顯。
除了向海外人民傳播佛教和伊斯蘭教外,也傳播了天妃海神的神力,使得海外人民紛紛來華朝貢或貿易,“洪濤巨浪帖不驚,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題卉服皆天氓,梯航萬國悉來庭”。
總之,從鄭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傳播來看,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信息的傳遞呈現接受與反饋的雙流向,充分利用當時的傳播媒介,運用一定的傳播技巧。傳播了宗教文化,實現了規范性傳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