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基本問(wèn)題探究論文
時(shí)間:2022-11-02 10:21:00
導(dǎo)語(yǔ):人文教育基本問(wèn)題探究論文一文來(lái)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xún)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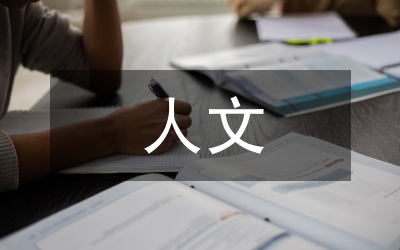
[論文關(guān)鍵詞]人文教育;人文精神;問(wèn)題
[論文摘要]“人文教育”給出了一個(gè)問(wèn)題域,在這個(gè)問(wèn)題域中,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著做一些根本性的追問(wèn)。通過(guò)對(duì)人文教育與人文學(xué)科的教育,人文教育與非理性主義教育的關(guān)系,以及人文教育的意義等三個(gè)問(wèn)題的追問(wèn),人文教育的實(shí)質(zhì)以及整個(gè)現(xiàn)代性狀況將會(huì)更清晰地向我們呈現(xiàn)出來(lái)。
上個(gè)世紀(jì)后十年,國(guó)內(nèi)學(xué)界頻頻出現(xiàn)“人文精神”、“人文教育”、“素質(zhì)教育”等提法,這表明我們對(duì)于現(xiàn)代性問(wèn)題和現(xiàn)代教育狀況的認(rèn)識(shí)邁出了新的一步。同時(shí),也說(shuō)明了現(xiàn)代社會(huì),尤其是現(xiàn)代教育中出現(xiàn)了普遍性問(wèn)題,而這些問(wèn)題已經(jīng)達(dá)到了令我們十分關(guān)切的地步。人文精神的“失落”或者“遮蔽”,以及現(xiàn)代教育中暴露出的種種弊病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世界性問(wèn)題。重建或復(fù)興人文精神,發(fā)展人文教育的呼聲得到了普遍響應(yīng)。但,至于什么是人文教育,為何要發(fā)展人文教育,以及如何發(fā)展人文教育,至今仍是值得追問(wèn)的。可以說(shuō),“人文教育”給出了一個(gè)問(wèn)題域,在這個(gè)問(wèn)題域中,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著做一些根本性的追問(wèn)。不澄清一些基本問(wèn)題,我們就難以在現(xiàn)代性批判中站穩(wěn)腳跟,難以走出非此即彼的邏輯怪圈,從而也就難以開(kāi)辟一條真正的人文教育之路來(lái)。
一、人文教育等于人文學(xué)科的教育嗎?
何謂人文教育?這個(gè)問(wèn)題并不那么容易回答。我們很難用一個(gè)簡(jiǎn)單的、抽象的邏輯概念來(lái)下定義。或許我們只能通過(guò)不斷地追問(wèn)來(lái)為回答此問(wèn)題做一些準(zhǔn)備。一談及人文教育,一些人就將之等同于某些人文社會(huì)學(xué)科的教育,以為只要開(kāi)設(shè)文史哲的課程,傳授人文學(xué)科的知識(shí)就算是人文教育了。一些學(xué)校把素質(zhì)教育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規(guī)定為:開(kāi)設(shè)幾門(mén)人文學(xué)科課程,學(xué)生修得多少學(xué)分,掌握了多少人文知識(shí),是否學(xué)會(huì)唱歌、跳舞、書(shū)法、閱讀等。在科學(xué)主義的影響下,教育成了知識(shí)的傳授與接受的問(wèn)題,教育效果是通過(guò)知識(shí)的回顧能力和重復(fù)的操作能力來(lái)判斷的。歷史上的人文教育的傳統(tǒng)在這個(gè)知識(shí)系統(tǒng)化的時(shí)代就演變成某些學(xué)科。實(shí)證主義先驅(qū)們甚至要把這些學(xué)科也科學(xué)化,變成“社會(huì)物理學(xué)”。雖然,今天有人已經(jīng)看出這樣做的不妥當(dāng),并對(duì)“社會(huì)物理學(xué)”報(bào)之以嘲諷,但是把文科與理科截然對(duì)立起來(lái)、劃清二者的界線的做法不但沒(méi)有走出現(xiàn)代形而上學(xué)的簡(jiǎn)單邏輯,而且似乎只會(huì)給問(wèn)題的解決設(shè)置更大的障礙。我們不得不在文科和理科之間做一個(gè)決斷。似乎二者就是兩個(gè)毫不相干、互不貫通甚至相互鄙視的彼此獨(dú)立的領(lǐng)域。
然而,實(shí)際上“人文教育并不等于只向?qū)W生傳授某些人文知識(shí),使其掌握某方面的技能”。在英文中,人文教育多用“l(fā)iberaleducation”這個(gè)詞組。國(guó)內(nèi)也翻譯成“通識(shí)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從這個(gè)詞中我們似乎看不到某種學(xué)科的偏向,相反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通”、“博”和“自由”。因此,我們就很難說(shuō),人文教育就等于人文學(xué)科的教育,因?yàn)槿宋慕逃娜蝿?wù)正是要改變這種把人文學(xué)科與自然學(xué)科對(duì)立起來(lái)的現(xiàn)代教育模式,走出片面性知識(shí)教育的怪圈。那么,毋寧說(shuō),人文教育是一種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這種理念、模式與單純的知識(shí)教育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人文教育所代表的教育變革是一種整體性變革,而不是簡(jiǎn)單地在以前學(xué)科教育當(dāng)中增補(bǔ)一些課程,或提高某些學(xué)科的名聲就能做到的。因此,其實(shí)質(zhì)在于人文精神,這種精神應(yīng)該貫穿教育的始終。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的內(nèi)容、方法、環(huán)境在內(nèi)的整個(gè)教育活動(dòng)都應(yīng)該是人文精神的體現(xiàn)。人文精神不是抽象的知識(shí),而是具體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特質(zhì)。這種精神特質(zhì)能夠在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找到其根基,也能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找到其原型。因此,如果我們把歷史做成了知識(shí),把文化變成了工具,把教師打造為教書(shū)匠,教育也就失去了它應(yīng)有的意義。
當(dāng)然,如果從具體的教育改革實(shí)踐的角度來(lái)看,我們不能立即推倒整個(gè)教育系統(tǒng),一切重新來(lái)過(guò),因?yàn)榇嬖诘臍v史并不像一段可以隨意開(kāi)啟和終止的人工程序那樣簡(jiǎn)單。因此,今天我們大力倡導(dǎo)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發(fā)展文史哲等學(xué)科,這是人文教育在現(xiàn)實(shí)性狀況下的一種可行的手段和途徑。但是,我們要對(duì)此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手段和途徑畢竟不是最終的目標(biāo)和本質(zhì)。只有真正把握了人文教育的實(shí)質(zhì),我們才不會(huì)使得改革的理念教條化,才不至于使得人文教育走人另一個(gè)死胡同。我們不能把對(duì)人文教育的思考封閉在一個(gè)狹小的范圍內(nèi),設(shè)置各種各樣的禁區(qū),以致窒息了思想,阻礙了實(shí)踐。缺乏不斷地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人文精神,那又何來(lái)人文教育呢?
二、人文教育是非理性主義教育嗎?
理性與非理性的分離隔絕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實(shí)際情形和問(wèn)題。在思想史上,它又是現(xiàn)代形而上學(xué)的一個(gè)命題。這種形而上學(xué)從“意識(shí)的內(nèi)在性”出發(fā),以“明確、可靠的”形式邏輯的方式將世界區(qū)分為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肉體、意識(shí)與物質(zhì)、理性與非理性等等。因此,我們就只能在抽象對(duì)立的二者之間抉擇,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而且理論上作這樣的區(qū)分并不是無(wú)目的性的,而恰恰是要在二者之間劃分出優(yōu)劣。啟蒙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現(xiàn)性主義逐步獲得了至高無(wú)上的權(quán)威。這種“理性的專(zhuān)制主義”,“或者體現(xiàn)為理智的邏輯,或者體現(xiàn)為思辨的邏輯;而無(wú)論它作為哪一種邏輯,卻都堅(jiān)稱(chēng)理性邏輯作為‘本質(zhì)’之君臨一切的先在性和普遍性。正像前者的發(fā)展導(dǎo)致了所謂‘工具理性’或‘分析理性’的全面統(tǒng)治一樣,后者完成自身為一種‘理性的絕對(duì)者”。于是,非理性就被判決為行為怪異、思維混亂、不講邏輯、不講道理,精神不正常。理性主義一開(kāi)始作為人類(lèi)解放的口號(hào),并且伴隨著科學(xué)和物質(zhì)文明的發(fā)展,而令人歡欣鼓舞。但是隨著工具理性的權(quán)威化,理性自身與理性的持有者日趨對(duì)立。因而在西方思想界就發(fā)起了非理性對(duì)理性的反動(dòng),叔本華、基爾凱郭爾、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等是這一流派的先驅(qū),當(dāng)代的后現(xiàn)代主義是其繼承和發(fā)展。非理性主義試圖恢復(fù)直覺(jué)、感覺(jué)、本能、情感、意志、欲望、需求、信仰、審美等的尊嚴(yán)和地位,將人的本質(zhì)從理性中拯救出來(lái),以非理性取而代之。
在這樣的背景下所倡導(dǎo)的人文教育也就被賦予了非理性主義的色彩。一些人以科學(xué)教育是理性主義教育為由,而推之人文教育就是非理性主義教育。因而當(dāng)代教育的主要論題就是在科學(xué)教育與人文教育、理性主義教育與非理性主義教育之間的抉擇或者調(diào)和,但其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作為某種“主義”,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都是通過(guò)否定對(duì)方來(lái)維護(hù)或提高自己的地位,誰(shuí)也不會(huì)滿(mǎn)足于平分秋色或擔(dān)當(dāng)小角色;其次,把人文教育與科學(xué)教育作為兩大類(lèi)學(xué)科的不同教育方法,這種做法非但不能化解矛盾,相反只會(huì)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互不理解的專(zhuān)業(yè)偏見(jiàn)。再次,把人文教育等同于非理性主義教育是理性主義的邏輯怪圈。似乎批判就是與之唱反調(diào),它往東我偏要往西,它堅(jiān)持理性主義、絕對(duì)主義,我們就要高唱非理性主義、相對(duì)主義、懷疑主義、虛無(wú)主義。實(shí)際上,對(duì)理性與非理性的抽象對(duì)立本身是現(xiàn)代形而上學(xué)的理論預(yù)設(shè),因此也就是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共同前提。因此,其正如海德格爾所說(shuō),單純的反動(dòng)仍然拘泥于它所反的東西的本質(zhì)之中;對(duì)形而上學(xué)命題的顛倒仍然是形而上學(xué)的命題。先秦教育沒(méi)有某某“主義”,然而卻堪稱(chēng)人文教育的典范;古希臘時(shí)期也沒(méi)有理性與非理性的抽象對(duì)立,卻被尊為輝煌的人文精神時(shí)代。今天,我們要解決像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這樣的現(xiàn)代性困境,為人文教育開(kāi)辟新的道理,的確需要更根本的思考,而存在論就為我們打開(kāi)了一個(gè)非常值得關(guān)。注的新境域。世界是意義的世界,是實(shí)踐的世界,就像沒(méi)有純粹的聲音一樣,我們很難說(shuō)有純粹的理性與純粹的非理性。那么,人文教育就不是抽象地談?wù)摾硇曰蚍抢硇裕瑥母旧险f(shuō)它是一個(gè)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塑造人文精神的實(shí)踐過(guò)程。我們或許可以說(shuō)這是一個(gè)各種感性、理性、情感等因素的復(fù)雜的交織過(guò)程,人文教育也并非要把人的生活分離成支離破碎的片斷,而恰恰是要將其還原為整體。如果不“博”,不“通”,又何謂“通識(shí)教育”呢?
三、人文教育的意義究竟何在?
現(xiàn)代教育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wèn)題讓所有關(guān)切教育事業(yè)的人們倍感憂(yōu)慮。今天,幾乎很少有人完全否認(rèn)人文教育的價(jià)值和意義。但是,至于人文教育的意義究竟何在,其回答就莫衷一是了。有人把人文教育提到了關(guān)系事業(yè)成敗、言行文野、思維智愚、人格高低甚至社會(huì)進(jìn)退和國(guó)家興衰的高度,以為這樣就能充分證明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實(shí)際上,其論證本身始終并未脫離實(shí)證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窠臼。因而與人文教育的實(shí)質(zhì)背道而馳。同時(shí),由于并未達(dá)到洞悉現(xiàn)代性本身的原則性高度,它也就難以論證有力。或許只有從人類(lèi)的現(xiàn)代性命運(yùn)的高度來(lái)看待此問(wèn)題,我們才更能明白人文教育的意義何在。
現(xiàn)代化首先在西方拉開(kāi)帷幕,并且迅速在全球擴(kuò)張,進(jìn)而成為人類(lèi)的歷史性命運(yùn)。現(xiàn)代性發(fā)端于對(duì)中世紀(jì)等級(jí)森嚴(yán)的權(quán)威的反叛,試圖把幾近窒息的人從天國(guó)和世俗的權(quán)威那里拯救出來(lái)。這樣一種偉大的信念和歷史使命感給了像哥白尼、布魯諾這樣的先驅(qū)們以超常的勇氣。然而讓那些為了自由、平等、民主、博愛(ài)殫精竭慮的人們始料未及的是他們?cè)谕频怪惺兰o(jì)神像的同時(shí)又不知不覺(jué)地塑造了另一尊神像。正如霍克海默所說(shuō),“啟蒙的根本目標(biāo)就是要使人們擺脫恐懼,樹(shù)立自主。但是,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勝利而招致的災(zāi)難之中”。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圖景,馬爾庫(kù)塞所說(shuō)的“單面人”已經(jīng)深切地被當(dāng)代人感受到了。尼采所預(yù)言的“虛無(wú)主義”也在步步逼近。技術(shù)權(quán)威和“人類(lèi)中心主義”非但沒(méi)有給我們帶來(lái)設(shè)想中的盡善盡美的自由,反而讓我們陷入了無(wú)法自拔的“進(jìn)步強(qiáng)制”中。現(xiàn)代文明無(wú)法回避的環(huán)境問(wèn)題、核武器問(wèn)題、恐怖主義、極權(quán)主義和各種沖突在二戰(zhàn)后進(jìn)一步被人們所關(guān)注。
現(xiàn)代形而上學(xué)已經(jīng)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世界被數(shù)學(xué)模式化了,“幾何式均質(zhì)化”的時(shí)空代替了生活中的“處所”,“可計(jì)算性本身被設(shè)定為統(tǒng)治自然的原理”。“從此以后,‘哲學(xué)’便處于一種窘境之中,不得不在‘諸科學(xué)’面前為自己的存在辯護(hù)”,因?yàn)椋叭绻皇且婚T(mén)科學(xué)的話(huà)就會(huì)失去聲望和效用”。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尚不明確的學(xué)科劃分在今天已經(jīng)涇渭分明,并且彼此隔絕。知識(shí)的爆炸使得任何想打通學(xué)科界限的人望而卻步。似乎我們離馬克思所說(shuō)的自然科學(xué)與關(guān)于人的科學(xué)成為“一門(mén)科學(xué)”的未來(lái)不是越來(lái)越近,而是越來(lái)越遠(yuǎn)。“在今天,各種學(xué)科的分崩離析的多樣性還只通過(guò)大學(xué)和系科的技術(shù)組織結(jié)合在一起,并且通過(guò)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的使用目的而保持著某種意義。”“大學(xué)成了培養(yǎng)工程師、醫(yī)生和程序員的場(chǎng)所,以使他們能夠在高科技公司找到報(bào)酬豐厚的工作。”哈耶克所說(shuō)的“綜合工科學(xué)院”(Ecolepolytechnique)則成為現(xiàn)代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培養(yǎng)工程師和專(zhuān)家,提供技術(shù)知識(shí),以市場(chǎng)需求為導(dǎo)向成為現(xiàn)代大學(xué)的口號(hào)。文化工業(yè)化、思想科學(xué)化,使得日趨專(zhuān)業(yè)化的學(xué)科當(dāng)中,社會(huì)應(yīng)用學(xué)科重于人文學(xué)科,理科重于文科,工科重于理科。
面對(duì)這樣的現(xiàn)代性困境,針對(duì)現(xiàn)代教育中出現(xiàn)的突出問(wèn)題,我們提出了人文教育。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彌補(bǔ)幾個(gè)教育漏洞、培養(yǎng)幾個(gè)天才兒童、挽救幾個(gè)不良少年這么簡(jiǎn)單。從根本上說(shuō),人文教育的發(fā)展關(guān)系到人類(lèi)的未來(lái)。人類(lèi)的現(xiàn)代性命運(yùn)是歷史造就的,而非源于我們主觀上的過(guò)失或無(wú)能,因此我們不可能簡(jiǎn)單地要求某一代人通過(guò)拋棄某種生活方式來(lái)一勞永逸地解決問(wèn)題。那種奢望通過(guò)某個(gè)人或某些人所設(shè)計(jì)的理想模式來(lái)改變世界的想法只是一個(gè)啟蒙時(shí)代的神話(huà)。如果人類(lèi)的未來(lái)還有希望,那么希望就在教育上,在未來(lái)的人身上。今天我們提出人文教育就是要為走出現(xiàn)代性困境而努力。雖然我們不能力挽狂瀾似地改變教育現(xiàn)狀,也不能立刻擺脫現(xiàn)代性困境,但是這種努力絕非白費(fèi)。未來(lái)的發(fā)展與今天的思想和實(shí)踐息息相關(guān)。我們把人文教育作為窺探現(xiàn)代性狀況的門(mén)戶(hù),希冀為人類(lèi)的未來(lái)開(kāi)辟道路,或者說(shuō)提供某種可能性。
熱門(mén)標(biāo)簽
人文關(guān)懷 人文科學(xué)概論 人文教育論文 人文護(hù)理論文 人文地理論文 人文關(guān)懷論文 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 人文精神論文 人文精神 人文地理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