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文化探討論文
時間:2022-12-01 02:24:00
導語: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文化探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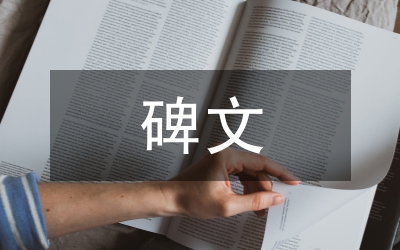
論文關鍵詞:善化金碑佛寺樓閣文化信息
論文摘要:遼金西京之大普恩寺,即位于今大同市城區西南隅之善化寺,該寺現存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一通。碑文撰寫者是南宋著明理學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卉。此碑記事、述史、寫人,真切感人,對遼末保大二年金遼大戰給佛寺帶來的巨大災禍,對圓滿大師忍辱精進重建大寺的經過,以及對金代重建的大普恩寺的建筑一一作了記述。此外,朱卉對自己被金人扣留西京十七年的生活記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一段歷史的真實情狀,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
一、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內涵
遼金時西京之大普恩寺,亦即今名之善化寺者,有金代撰文金代刻立的石碑。此碑撰文之人乃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叔祖父朱棄,且因其名節高尚、學優當時,故后人皆因人而稱此碑為“朱棄碑”,亦稱其為“善化寺金碑”。
“朱棄碑”現存于善化寺三圣殿內的西次間南側,刻立時間為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碑體總高4.58m,寬1.28m,厚0.24m,碑額雕刻著玲瓏剔透的璃首,額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記”,碑文名“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由時任魯縣開國子孔固書,濟陽郡開國伯丁障仁篆額,雁門郡雕刻藝人解遵一所刻。碑座為玄武石龜跌。“朱棄碑”共19行,每行52字,總計925字,為金代石碑之精品。茲錄此碑全文如下:
額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記
碑文: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擾哲王之抹弊,或忠,或質,或文,雖制治不同,其趨一也。世人構達磨對蕭梁氏之言,遂疑有為功德不可復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迎遺訓,具存貝典,則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將誘接眾生,同歸于善二其為功德,拒可測量哉!彼達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親提教外別傳之印,則于有為功德不無抑揚,是亦因時抹弊耳,非實貶也。具愿力必當,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為功德尚何警耶?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為大蘭若。遼末以來,再根鋒燼,樓閣飛為埃紛,堂殿聚為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為列屯,而喧寂頓殊;掠藏俘獲紛然錯處,而垢凈俄變;殘僧去之而飲泣,遺黎過之而增秋。閱歷滋久,散亡稍還。于是寺之上首、通玄文慧大師圓滿者,思童戲于畫沙,感宿因于移礎,發勇猛心,得不退轉,舍衣孟凡二十萬,與其徒合謀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盧舍之教,以慈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為門,咸懷后至之恥。于斯時也,人以須達期,家用給孤相勉,咸蘊至愿,爭舍所愛。彼髓腦支體尚無所吝,況百骸外物哉!于是舉幣委珠金,脫袍澎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于天會之戊申,落成于皇統之癸亥。凡為大殿暨東西朵殿、羅漢洞,文珠、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抖廊,合八十余楹。領璧變于涎值,丹鑊供其繪畫,攘椽梁柱飾而不侈,階序確闊廣而有容。為諸佛薩睡,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于名筆;為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于善工。膝容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二同聲二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為饒益,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圖于干戈未載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視己財貨,猶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衰檀信。經營終始,淹貫時序,皆予所目睹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時比哉?始予筑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茲寺,因得與寺眾往來,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眾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為請記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既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于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鐘,其上款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后,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后之作者,見其闊文,倘得其本末,為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眾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棄記。少中大夫、同知西京留守、大同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上輕車都尉、濟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丁嶂仁篆額。中憲大夫、西京路都轉運副使、上騎都尉、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固書。通玄文慧師、賜紫沙門圓滿提點。大定十六年丙申八月丁酉初一日癸酉,三綱:寺主沙門惠鐲,尚座行完,都維那棲演立石雁門解遵一刊。
二、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分析
1、佛教之信息善化寺是大同城內的一座古寺,在歷史的歲月中屢跪屢起,深蘊著昔時佛教因果義理弘揚與傳承的盛貌,記錄與儲存著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據寺內現存碑記記載,善化寺創建于唐朝開元年間(713741年),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明皇李隆基頒敦詔書,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并按年號稱寺名,統稱“開元寺”,而善化寺的舊寺舊址就是唐代的一處開元寺。至五代后晉時(936946年),開元古寺改名為大普恩寺,遼金時亦稱此名,迄明英宗始賜名善化寺。在明萬歷年間的《重修善化寺記》和《重修善化寺碑記》中,善化寺已經成為這座古老寺院的正宗名稱,當地百姓則一直以其位居城南而以“南寺”俗稱。
善化寺在明大同城之南門的西側,其東側也有佛寺稱“七佛寺”。善化寺地勢低凹,座北朝南,寺內的主要建筑一如唐代布局,皆分布在中軸線上,三重大殿,由下而上,由小漸大,在體積和量的變化中,體現出一種宏大、莊嚴、肅穆和高貴的盛唐古風。在三重大殿的東西兩側,還有兩座唐代遺風的閣樓,西閣為普賢閣,東閣文殊閣于民國初年在火災中塌毀。另外還有東西配殿,構成了“伽藍七堂”的古制。在善化寺三圣殿內保存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碑,以真實的記傳文字,儲存和傳達出那個時代這座古寺豐富的佛教文化信息。
在佛家看來,興建寺宇、崇飾塔廟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善化寺“金碑”中即以簡潔的語言表達為:佛、菩薩是以有所關懷的“應世”姿態,展現“誘接眾生,同歸于善”的崇高言教境界,善化寺“金碑”稱之為“佛菩薩境界”。在世俗看來,釋迎牟尼棄世出家專心求法,就是放棄人世的一切欲念與利益。在佛教傳人中國后的西晉時代,大和尚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稱佛教是“方外之賓”。佛教僧徒披裂裝,斷蓄發,托缽念佛,顯然與世俗之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然而,到了唐代百丈懷海和尚的時代,佛教僧徒則以一種積極應世的姿態,參與人世間所有善事和公益活動,以此作為修煉佛法的重要內容,修路架橋,販濟災民,做善于世,益事于人,積極引導眾生“同歸于善”。所以,本著這種思想認識,佛教寺廟和佛教形象正是以這種方式參與世俗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使人人心存善念,這即是佛菩薩的一種期待,也是佛菩薩的一種境界。在善化寺“金碑”的開題段落中,撰者朱棄以南朝時的印度僧人達摩蘆葦渡江,與南朝梁武帝蕭衍進言救世以為“功德”,四次闡述佛教“應世”的觀點,這種功德就如同現世哲王的救弊補世一樣,以此之為功德,大矣廣矣。
與上述相結合,佛教表明了一種觀點和態度,那就是興建寺宇崇飾塔廟,不僅僅是信仰行為,也不僅僅是建筑藝術行為,而是佛教積極“應世”,參與世俗社會思想文化建設的一種姿態和境界。這種努力的結果和收益,就如同英明睿哲的世俗社會管理者一樣,有著明顯的利益眾生的功德,而且其為功亦大矣。鑒此,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論述和闡釋,正是朱棄所撰這篇碑文的出發點,也是建寺修廟的目的。
2,史之信息碑記之文,在于記事,在于述史。在善化寺“金碑”中,朱棄用了很大一部分文筆來記事述史。要點有三:一是從“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為大蘭若”寫起,追溯普恩寺的佛緣久遠。然后一筆過去,具體陳述遼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遼大戰給佛寺帶來的巨大災禍,原本莊嚴宏偉的古寺,頓然間“樓閣飛為埃扮,堂殿聚為瓦礫”,“僅存者十不三四”。在這一災變的背景下,“驕兵悍卒”橫沖直撞搶掠寶藏,而“殘僧”和“遺黎”則為此而掩泣嘆息。這種景象,就像是我們在戰爭影視片中常常看到的蒙太奇,是那樣的真實和形象。朱棄以文賦之筆記寫戰爭之景,在了解史實情狀的基礎上,給讀碑文之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與心靈感染。二是重點記寫普恩寺住持圓滿大師忍辱精進重建大寺的經過。圓滿大師少有慧根,前有宿因,入于佛門,精進勇猛,從不退轉,是一位堅定自信的佛教修行者。然而,面對遼末保大年間戰火對普恩寺的嚴重破壞,他帶領所存僧人“合謀協力”千辛萬苦化緣聚資,經過長年累月地努力,從金代天會六年(1128年)至皇統三年(1143年),用了整整15年的時間把殘毀的大普恩寺重新修建而成。其時的大普恩寺建筑,有大殿、東西朵殿、羅漢洞、文殊閣、普賢閣、前殿大門和左右斜廊,合計80余楹。從此記敘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圓滿大師的大功德,也可以體悟到朱棄由此而產生的輕松和愉快的心情。接下來朱棄用24句有詩賦特征的句子來描寫大殿和佛像的美妙與壯麗,來描寫前來瞻仰游覽者的欽佩與贊嘆。以此具體的大功德回照應證碑文伊始處對佛教利益眾生功德世間的議論的闡發,于文完整圓合矣。遞進而下,再寫已74歲的圓滿大師成此功德的艱難與不易。朱棄以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寫下圓滿大師為重新修建普恩大寺的種種努力,記事之下,情動于衷。二是點出自己撰此碑文的機緣,實事實寫,真情實感,讀來亦頗讓人感動。撰寫碑文的朱棄,落款署名為“江東朱棄”,所以后世人們將這通善化寺“金碑”稱之為“朱棄碑”。從提款得知,朱棄時任宋通問副使,與正使王倫一行前往北地問安兩宮(宋徽宗和宋欽宗),當他們行至西京時,被金人扣留,長達17年之久。在此期間,金人也曾以高官厚祿誘降,但朱棄終不為所動。做為南宋的一名官員,在北方沒有親人沒有自由的17年羈押,其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唯一能使他感到松暢和愉悅的就是他“遷于茲寺,因得與寺眾往來”的這14年。做為一個“親身見之”的當事人,他責無旁貸地擔當了普恩寺重新修建之后立碑以志的撰文者,為我們保存和傳達出豐富的歷史信息。在碑文的最后,朱棄又補敘了普恩寺的歷史,寺建于唐,唐明皇李隆基賜“開元”名號,五代后晉時更名大普恩寺,并對鐘樓上銅鐘的落款“清泰三年”做了考辯,對其網文做了說明,有主有次,事史圓整。公務員之家
3、文化之信息從本質上講,佛教藝術創作的一切活動,都是人類精神追求和心靈向往的一種表現,都是人類以創造的姿態美化人生的一種努力。佛教文化中的建寺塑像撰文刻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是一種文化信息的傳達。在善化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中,透露出一種莊嚴凝重的佛教文化信息,也透露著遼金時代的社會文化信息,流露出碑文撰寫者的人生際遇和感悟。從文化信息的角度看,善化寺“金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信息傳達:一是在朱棄看來,佛教中的佛菩薩在世俗生活中的出現與張揚,同以救弊求安求富為己任的世俗社會中的帝王是一樣的,不管他們表現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其所追求的利濟眾生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在佛家看來就是功德之事。不過,就功德而言,言的功德與行的功德顯然還是有區別的,那些以不力之體,經過千辛萬苦而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者,達到饒益社會與眾生的,才是最大的功德,重修大金西都普恩寺的圓滿大師就是這種大功德的實踐者。注重善的實踐,注重佛教修行的社會效益,提倡有為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種精神追求。像圓滿大師那樣,以古稀之身精勤修業募化建寺,這在江東才子朱棄看來就是無尚的大功德,是應該昭彰其功頌贊其德的。二是朱棄的筑館教授,為北地傳播文化教育。朱棄是《宋史》和《金史》皆有其傳的人物,在宋徽宗和宋飲宗被金人俘押到女真故地黃龍府后,他以吉州團練使的身份被朝廷選為首批赴金問安兩帝的通問副使。對其個人而言,命運便由此改變,歷史也因此有了宋金沖突糾葛的另一筆記載。當作為通問副使的朱棄和正使王倫到了西京后,卻被扣留于此地,前不能進,后不能歸,在金人的威逼與利誘面前,展現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動故事,期間的痛苦、孤獨、憤悶和磨難是可想而知的。當結束扣留,歸于南方的時候,他在北地西京已經度過了整整17年時光。在被扣留于西京3年后,他“筑館”當了傳道授業的教書先生,而且在西京還很有影響,即使是上層的女真貴族,也把子弟送人塾館中接受其教育。朱棄將深厚儒雅的江南文化帶人刀光劍影雄勁粗獷的西京之地,對文化的交流與知識的傳播做著默默無聞的貢獻。從他那文筆暢爽記議妙佳的碑文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江東才子的大氣與宏雅。三是遼與金的爭戰和金與宋的沖突。契丹和女真皆屬于東胡游牧民族,皆起于遼河與嫩江流域。契丹建立遼朝后,在行政區劃上設五京之制,而女真滅遼建立了金朝后,也沿襲前朝五京之制。遼在西京興建了大華嚴佛寺,并且以國家宗廟的格局“奉安諸帝石像、銅像”,皮藏佛教典籍與其他文化圖書,儼然像一個國家級的圖書館。金滅遼后,依然在西京之地重視佛教和文化上的建設,在被戰火毀壞的華嚴寺舊址上重構盛大的廟宇伽藍,采用遼的風格和習俗,再現了大華嚴寺過去座西朝東矗立于高大月臺之上的盛貌。就其規模和風格而言,可以見出其文化選擇和審美時尚的趨同性。盡管有那場保大年間的遼金大戰,但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觀念和歷史傳統,使得他們在西京華嚴寺的興建與重建上保持了高度的文化上的相通與一致,善化寺也是如此。金宋的戰與和,盡管也在碑文中顯露了出來,但表面上的沖突與糾葛并沒有斷殺他們在短暫安寧中的文化交流。朱棄在“筑館”授學中,在與善化寺僧眾長達14年的朝夕相處中,相互的感染和學習是必然的,朱棄碑文中表現出的儒佛共表、宗教與世俗同構、義理與文采相映的特點,便是這種文化交流的明證。
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蘊藏有豐富的佛教信息、歷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對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宗教、文化和民族的狀貌,定當會大有裨益。
- 上一篇:對外新聞中文化詞匯的轉換論文
- 下一篇:中西醫結合綜合治療小兒急性支氣管炎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