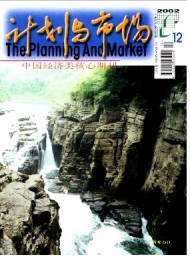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時間:2024-02-05 17:51:3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心理干預; 計劃生育手術; 焦慮對象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28.039
計劃生育手術雖然是小手術,但受術者是健康人群,為了采取避孕節育或避孕失敗的補救措施而要求手術,與醫院的患者為了治療疾病而采取手術治療性質完全不同,受術者心理也有很大差別。最突出的表現是術前因擔心手術會影響身體健康而出現焦慮癥狀,所以,心理干預在計劃生育手術中的應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對有焦慮情緒的服務對象進行心理干預也是體現計劃生育優質服務的一項重要措施。本文對160例來站要求行人工流產術,術前有焦慮癥狀的對象實施心理干預后進行對比觀察,現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3月1日-2012年3月1日來本站要求行人工流產術,且術前有焦慮癥狀的服務對象160例,隨機將其分為觀察組(心理干預組)80例和對照組(非心理干預組)80例。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術前常規詢問病史,按操作規范施術,術后送到休息室休息,不對服務對象進行特殊的心理干預。
1.2.2 觀察組 術前耐心地與服務對象交談,聽取她們的意見和要求,并對手術的安全性做出恰當的解釋,用恰當的語言,使對象在輕松自如的氣氛中了解手術過程中真實的痛苦體驗及對她們的具體要求,糾正其各種誤解和疑慮。手術室盡可能將所有醫療設備和器械盤遮擋,使對象走進來時不會感到害怕。術中術者盡量不要讓器械碰撞發出聲音。同時對服務對象采取分散注意法,派專人與服務對象主動交談,交談時語氣要柔和,要面帶微笑,盡量談一些她們關心的和一些讓她們高興的話題,讓服務對象沉浸在美好的回憶當中,轉移她們的注意力,如果中途服務對象仍有不適感覺,應對她們說一些鼓勵的話語,讓她們進行自我控制并教會她們控制呼吸,用鼻吸氣,用口呼氣,直到手術結束。術后陪其到休息室,感謝她們在手術過程中的配合,交待一些術后注意事項,并讓她們好好休息。
1.3 判斷標準 配合組:將術中注意力轉移,術中無,無痛苦表情,能較好配合手術;不配合組:術中焦慮、恐懼、、有痛苦表情,肢體扭動不配合手術。恐懼感組:術后恐懼、害怕、乏力疲倦,述說以后再也不做流產手術的對象;無恐懼感組:術后情緒正常,自述其實流產手術沒有想象中可怕的對象。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PEMS 3.1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采用 字2檢驗,P
2 結果
經統計學分析,觀察組與對照組服務對象在進入手術室后配合情況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焦慮是個體或集體在對一個模糊的非特異的威脅作出反應時所受到的不適感和自主神經系統激活狀態,它可由各種原因引起,并逐漸加重。國內外的研究者早就認識到:手術作為一種極具威脅性的應激源,常導致服務對象在手術前后產生焦慮、恐懼等心理應激反應,當反應過于劇烈時,會影響手術的順利進行及術后機體的康復[1]。心理干預能降低服務對象對手術的恐懼感,利于術中配合和術后恢復,人工流產手術作為一種避孕失敗的補救措施,一方面能減少人口出生,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另一方面,手術對服務對象來說是一種應激刺激,不僅有身體上的創傷性刺激,而且會產生一定的心理反應。嚴重的消極心理反應可直接影響手術效果引起并發證的發生。因此,積極主動對服務對象進行心理干預,可縮短彼此的距離,消除顧慮,減少陌生感,增加信任,便于相互溝通,更利于減輕服務對象對手術的恐懼感。另外,Stinshoff等觀察了男性和女性在接受侵入性醫學操作時,男性更多地從藥物減痛中獲益,而女性更多地從減痛解憂中獲益[2]。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在計劃生育手術過程中通過心理支持等手段,幫助服務對象克服焦慮和不適,減輕疼痛感既簡單、快速、有效,并且不會產生藥物鎮痛的副作用和并發癥。
3.2 實施心理干預最重要的因素是整個服務中心要有團隊意識。為了達到心理干預的最佳效果,要求整個服務中心必須建立一種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環境,以及設計一個過程,使服務對象從走進服務中心的最初階段直到她離開,都能減少焦慮和緊張[3]。在整個過程中,服務對象所接觸的工作人員(包括收款員、化驗室人員、B超室醫生、手術醫生和護士等),都必須有很強的責任心,能夠細心、耐心的解答服務對象咨詢的問題,熱心的幫助她們克服遇到的困難,使服務對象從進入服務中心開始就產生一種信任感、安全感,這樣更有利于手術前后的心理干預措施發揮最佳效果。
3.3 心理干預成功的另一關鍵要素是接診醫生除了要具備精湛的專業技術知識以外,還要掌握一定的醫學心理學知識。平時應特別注意積累一些應對特殊服務對象異常心理特點的技巧,醫生之間應經常互相交流心得。比如遇到如下服務對象:⑴愛挑剔,蠻橫不講理者;⑵曾經受過精神刺激、對疼痛特別敏感者;⑶喜歡道聽途說,容易接受反面經驗,別人說人工流產很痛苦,她就記在心里,導致意外懷孕時格外焦慮、擔心者;⑷似懂非懂,一知半解者;⑸神經質,容易對什么事都一驚一乍者;⑹對計劃生育工作有誤解者。遇到以上幾種服務對象,接診醫生除了應該更加細心、耐心以外,還要根據她們的心理特點,制定特殊的應對策略。比如:對于愛挑剔、蠻橫不講理者醫生一定要充分表現出自己的涵養,盡量不要與其發生正面沖突,耐心的等待她發完牢騷或挑剔完以后,再告訴她怎樣才是對的,往往這樣的服務對象最后都會感覺不好意思。對于曾經受過精神刺激、對疼痛特別敏感者,應該給予特別的關心,讓其感受到溫暖,并積極的鼓勵她配合手術[4]。
綜上所述,在計劃生育門診焦慮的服務對象手術前后,進行合理的心理干預對保證手術的順利進行及促進術后機體康復,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減少醫療糾紛,提高計劃生育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提高計劃生育服務的滿意度都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王瑛,黃海明,劉衛珍,等.無痛技術應用于輸卵管結扎術前后的焦慮情緒調查及干預[J].中國計劃生育和婦產科,2012,4(3):55-58.
[2] Stinshoff V J,Lang E V,Berbaum K S,et al.Effect of sex and gender on drug seeking behaviour during invasive medical procedures[J].Acad Radiol,2004,11(4):390-397.
[3] 戚其偉,于建政,張妮.青島市計劃生育服務人員心語疏通培訓的體會[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06,14(3):183-185.
篇2
從1950年代末期開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傳計劃生育,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從1971年國務院轉批《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并把控制人口增長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已經40多年;即使從1982年把計劃生育政策確定為基本國策,也已經30年了。而且,“十二五”期間也明確提出我國仍將堅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繼續維持“低生育率水平”。盡管如此,在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轉型、少子老齡化等人口矛盾日將嚴峻的新形勢下,重新審視和評估這項作為基本國策、實施時間如此之長且事關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是非常必要的。
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下降: 發達國家的事實
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轉變是人口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現象。所謂人口轉變,乃指人口由傳統社會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狀態,經歷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狀態之后,向現代社會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狀態的轉變過程。人口轉變由死亡轉變和生育轉變組成。其中,生育轉變,即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轉變的核心,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
考察和研究發現,人口轉變率先發生在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口轉變還只局限于歐洲地區。作為人口轉變核心的生育轉變,首先發生于西歐的法國,然后依次出現在西北歐、澳州、北美、東南歐等地區。大致到1930年代中期,歐美地區(或文化圈)的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轉變。此后,人口轉變又進一步向日本、韓國、新加坡及港臺等東亞國家或地區擴散,并先后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逐次實現。目前,這些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
為什么會發生人口轉變特別是生育轉變?學者們對此給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釋。如芝加哥學派認為,產業革命帶來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養育子女的相對成本上升,為了保證子女質量只能減少生育子女數,由此帶來生育率的下降;新家政學把婦女的生育行為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婦女為了參與就業競爭而減少生育。特別是卡爾德研究指出,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減少生育子女數。而且婦女受教育年數越多,生育子女數越少;諾特斯坦的現代化理論則認為是現代化帶來了生育水平的下降。盡管還有其他解釋,但主流觀點基本上都是認為,以生育轉變為核心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是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轉變的實現。
生育率下降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國的實踐
由于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下的人口發展還不應該完成人口轉變。但事實上我國卻早已完成人口轉變,目前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幾乎與日本總和生育率相近的低水平。顯然,我國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轉變的實現,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實踐已經說明,人口轉變并非僅如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經驗所看到的那樣,單純表現為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實施有效的計劃生育及人口出生控制政策,即使在低發展水平條件下也可以發生和實現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轉變。
回顧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我國從1950年代末期即開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傳計劃生育,1960年代開始提倡計劃生育。在這一階段,我國對計劃生育還只是宣傳和提倡,尚未作為國家政策實施,所以到197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還高達5.8。自此以后開始全面實行“晚(婚)、稀(生育間隔)、少(子女數)”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之推廣普及避孕節育藥具和技術,由此造成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79年已下降到2.75。在這10年期間,經濟發展基本上還是延續“”以來的停滯不前態勢,所以在此期間我國生育率的顯著下降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關系重大,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稱為計劃生育政策發揮作用的“黃金十年”。
1980年以來,除少數民族地區,我國開始實行嚴厲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并在兩個月后寫入新修改的《憲法》。2000年開始,“一胎化”政策有所緩和,如在上海等一些地區開始實行“雙獨生二胎”(即兩人都是獨生子女的男女結婚可以生育二胎)和農村戶籍人口結婚后第一胎為女孩的可生第二胎等生育政策。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我國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考慮到該普查的漏報并綜合各種數據測算,目前大概應該在1.5左右。即在此30年間,我國總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5左右,又幾乎實現了一次半減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已發展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并跨入中上收入水平國家行列。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此間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生育觀念的變化,應該對生育率的半減下降具有一定影響。但毫無疑問,此間實行的嚴厲的“一胎化”政策及目前仍在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半減下降也同樣具有重要影響。也就是說,1980年以來我國總和生育率的半減下降,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嚴厲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
篇3
[關鍵詞] 四聯療法;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
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為臨床常見消化性潰瘍類型,幽門螺旋桿菌為革蘭陰性菌,容易在胃竇黏膜上附著,引發消化性潰瘍,因而對于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治療的關鍵也在于根除幽門螺桿菌[1-2]。該研究選取2014年4月―2015年12月該院收治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中隨機抽取的150例,對四聯療法對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及不良反應發生率的影響進行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此次研究納入的對象來源于該院收治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中隨機抽取的150例,進行隨機分組。四聯組患者男38例,女37例;年齡區間21~74歲,年齡均數(45.34±2.13)歲。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分別35例和40例。三聯組患者男37例,女38例;年齡區間21~75歲,年齡均數(45.18±2.62)歲。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分別37例和38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有可行性。
1.2 方法
三聯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三聯療法治療,其中,克拉霉素(國藥準字H20051496)0.5 g/次,2次/d;阿莫西林(國藥準字H14020125)1 g/次,2次/d;奧美拉唑(國藥準字H19991122)20 mg/次,2次/d,上述藥物均為口服用藥, 十二指腸潰瘍治療2周,胃潰瘍治療4周。四聯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果膠鉍四聯療法治療。其中,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的用法、用量均同三聯組,而果膠鉍0.2 g/次,3次/d,口服用藥,十二指腸潰瘍治療2周,胃潰瘍治療4周。兩組患者均接受以上2周抗幽門螺桿菌治療,后繼續口服奧美拉唑+達喜抗潰瘍治療4周。
1.3 觀察指標和標準
比較兩組患者①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②不良反應發生率;③干預前和干預后患者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的差異。愈合的標準:經治療,患者疼痛等臨床癥狀和體征消失,潰瘍面積完全消失,潰瘍愈合,幽門螺旋桿菌陰性[3]。幽門螺桿菌消除:以幽門螺桿菌陰性為根除[4]。
1.4 統計方法
應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統計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數據,不良反應發生率、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以(%)表示,屬于計數資料,采取χ2檢驗。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以(x±s)表示,屬于計量資料,采取t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標準為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相比較
四聯組較之三聯組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更高,P
2.2 干預前和干預后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相比較
干預前兩組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相似,P>0.05;干預后四聯組較之三聯組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改善更顯著,P
2.3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相比較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為常見消化性潰瘍,可周期性發作,病程長,患者以上腹疼痛等為主要表現,其治愈難度大,跟幽門螺旋桿菌感染和耐藥的發生相關。幽門螺旋桿菌可通過多種方式為胃黏膜產生影響,可在胃黏膜細胞中粘附,引發局部炎性癥狀,導致上皮細胞潰瘍,因而治療的關鍵在于控制幽門螺旋桿菌,以降低復發率[5]。目前,三聯療法(主要為質子泵抑制劑、兩種抗生素)是治療消化性潰瘍的主要方法,而在三聯療法上增加果膠鉍治療為常見四聯療法,該研究應用的藥物組合為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果膠鉍,其中,克拉霉素可對細菌細胞白50 s亞基連接造成阻礙而發揮抑菌作用;阿莫西林可快速溶解細胞壁;奧美拉唑可發揮持久強效快速抑酸作用;果膠鉍則可對幽門螺桿菌細胞壁進行作用,使其胞漿出現空泡樣改變,導致幽門螺桿菌破裂而促使細菌死亡,還可對胃黏膜表面進行覆蓋,對受損黏膜有保護和修復作用,可避免其受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影響。另外,在PH為5的情況下,果膠鉍還可直接殺滅幽門螺旋桿菌,提高抗生素活性。該研究中,三聯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三聯療法治療,四聯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奧美拉唑、果膠鉍四聯療法治療。結果顯示,四聯組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更高,SF-36量表生活質量總分、SAS焦慮評分、SDS抑郁評分改善更顯著,P0.05。其中,四聯組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分別為97.33%、80.00%,而三聯組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分別為82.67%和70.67%,P
綜上所述,四聯療法對幽門螺旋桿菌消化性潰瘍患者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及不良反應發生率的影響大,可有效提高潰瘍愈合率、幽門螺桿菌消除率,不增加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改善患者負性情緒和生活質量意義重大,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1] 薛芙蕖.四聯療法治療幽門螺桿菌陽性消化性潰瘍療效觀察[J].中國基層醫藥,2011,18(19):2682-2683.
[2] 許曉燕.兩種四聯療法治療幽門螺旋桿菌陽性消化性潰瘍的療效對比[J].中國藥業,2013,22(11):74-75.
[3] 翟棟春.香砂六君子湯聯合四聯療法治療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潰瘍臨床觀察[J].亞太傳統醫藥,2014,10(16):112-113.
[4] 毛軍民,石鎮東,匡清清,等.調和解毒法聯合四聯療法治療幽門螺桿菌陽性消化性潰瘍的臨床研究[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6,25(19):2060-2062,2065.
[5] 艾永華.四聯療法治療幽門螺桿菌陽性消化性潰瘍的療效觀察[J].中國醫藥導刊,2014(1):99-100.
篇4
內容摘要 “單獨二孩”作為一個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有助于對未來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決策支持。研究發現,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效果的類似性,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仍然將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現實,從現在開始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調整是可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建議從2019—2020年開始,在“全面放開二胎”以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
關鍵詞 單獨二孩 全面放開二胎 新生兒-母親-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計劃
作 者任遠,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來,人口發展完成了人口轉變,而我國生育政策調整一直滯后于人口狀況和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態勢。六普數據表明,我國人口生育率水平實際上低于本世紀初國家人口戰略預測的結果,而人口內在萎縮的速度比預想更嚴重。近年來,雖然較多學者論證應該可以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來我國開始實施的是“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該政策到目前為止的實施效果是,全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萬,到同年8月底,只有70萬對申請生育二胎。全國不同地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況都遠低于預期的水平,符合“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實際生育水平不高,職能部門所擔心的“單獨二孩”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的人口反彈并沒有出現。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生育效應產生一定預判失誤的原因有:一是政策變動效果的跨年度效應,政策影響行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現出來。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進行生育預測,在數據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預測往往是以生育意愿來代替實際生育行為,而社會生活和經濟約束下的生育行為決策往往顯著低于生育意愿。我們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獨生子女一代年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在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口群體中選擇生育的比例相當低,一些研究論證這個比例大約在20%—30%。
“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整體上說是一個相對滯后的政策調整。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作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據此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進行預判,目前進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及其實施結果,可以對未來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發現和政策文持。對于“全面放開二胎”,國家仍然持謹慎態度和“沒有時間表”。前不久,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表示, “目前我們國家的生育勢能還是很大,現在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全國測算有1.5億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將近9000萬的家庭準備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現在普遍實施二孩政策,就會使中國的生育水平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會使國家制定的人口發展目標受到影響。他強調,中國人口多這個基本國情目前還不會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還不會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還不會改變。 為此,筆者擬利用已有的數據,估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究竟會對新增加的生育帶來多大影響,從而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據。
二
本文的研究假設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婦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是類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萬“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可以推斷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生育結果。
為了估計這種生育行為的影響,筆者設計了“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這是指當年新生兒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齡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類似一種倒推上去的隊列總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標。當然,這個指標也沒有考慮移民效應、母親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這種生育率水平和時期總和生育率(TFR)究竟誰高誰低,而是以此為工具來衡量生育政策調整對生育水平變化的影響,以及估算生育政策變化對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
對國家人口和生育來說,存在一個基本能夠反映當下生育政策約束的“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國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是28歲,可將2013年新生兒人口數1640萬人,與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萬的比值1.67,作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前計劃生育政策約束下的基線生育水平。其中, “單獨二孩”家庭中申請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兒數,與平均生育年齡前母親一代人中符合單獨政策人口數的比值,構成第二個“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2),這是所有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單獨二孩家庭的新增補償性生育,與平均生育年齡前國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數的比值,則構成第三個“新生兒一母親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兩相比較,基本能夠反映“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對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響。 (詳見表1)
假設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無顯著差異,我們用“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單獨二孩”政策調整對于生育水平的影響。“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是類似于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不適合直接和時期指標計算的總和生育率進行類比。參考郭志剛從時期生育行為對終身生育水平的去進度效應的估計,1990年代末婦女終身生育率TFR’約為1.7(近期的育齡婦女終身生育率水平應該更低)。即使用這個較高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來推算, “單獨二孩”可能使得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開二胎”會使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這個結果依然是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從生育政策調整來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水平,這也說明我國的生育率下降已經進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東亞諸多國家和地區類似,出現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難反彈”的風險。就此而言,對生育政策調整會帶來顯著的生育反彈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從長遠來看,人口與發展的主要風險不是生育水平過高的問題,而是生育水平過低的問題,為此,需要進一步放開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為背后的政策枷鎖。
圖1描繪了我國1980年代以來的年出生人口數。1980年代,我國年出生人口數基本都在2000萬以上,特別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響,形成了出生堆積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數達到2500萬以上。而1990年以后總體上出生人口數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穩定在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開二胎”,也就是說按照NM2來生育,那么通過“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結合過去各個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數,可以近似推斷出在平均生育年齡以后的未來各個時期“全面放開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詳見表2)
研究表明, “單獨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約年出生人口數會達到1983萬。“單獨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效應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萬左右。如果說中國總人口在2025—2030年將到達頂峰,我國峰值人口數量僅比現在高出2000萬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開二胎”會增加9000萬人口,不太可能出現。
四
我們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作為政策試驗,來預判“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影響,結果表明,對于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生育反彈實際上不必過分擔憂。值得擔憂的倒是,即使放開生育控制,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國可能已經進入生育率下降很難反彈的“低生育率陷阱”。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帶來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長。
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反彈,大約會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時,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比“單獨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實際是有限的,或者說“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效果并沒有顯著差別。 (圖2)這也再次說明,從“單獨二孩”到“全面放開二胎”的漸進改革有些“過于碎片化”的謹慎,實行“單獨二孩”或許僅僅在政策調整試驗上具有意義。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實施效果的類似性,實際上我們可以從現在起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對于生育反彈的影響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將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對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萬,2014年出生人口預期會達到1980萬,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將相對較高,在2000萬以上甚至達到2200萬。但是我們并不用過分擔憂,因為即使沒有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會出現年出生人口數增加,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應。我們千萬不要將這段時間人口出生的顯著增長歸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調整,避免將因為人口慣性帶來的生育反彈歸咎于政策調整造成了政策波動。同時,我們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數量將有較大增長,仍然顯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階段的出生人口數;而且,2019年以后,隨著上一波生育高峰開始下降,我國的出生人口數量也會隨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從現在開始實施“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我們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我國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務還沒有完成,因為“全面放開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體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將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長期不可持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我們需要在“全面放開二胎”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此時,我國自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完成了過渡期任務,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實現自主生育”的時間點建議放在“十三五”期間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會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應下維持較高水平,從而增加政策決策的不確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數就會顯著下降,如果利用這一年開始推動實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夠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幫助穩定人口的波動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2021年是建黨100年,用實現自主生育的民眾民主來作為全面小康的歷史里程碑,并為第一個100年獻禮,將使中國開啟一個全新的生育政策時代,標志著國家新人口政策的開端。
參考文獻:
[1]衛計委回應普遍放開二胎:現在還不是時候.中國網,2014.7.10.
篇5
11個省份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均延長了產假
目前,全國各地已進入地方計劃生育條例修改高峰期,“全面兩孩”政策更成為近日密集召開的地方會議關注熱點。截至28日,廣東、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個省份人大常委會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明確“全面兩孩”的具體實施政策。記者針對 “全面兩孩”落地的幾個焦點問題進行了追蹤。
生育意愿
兩孩生育意愿持續走低
各種壓力令不少家庭舉步不前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本該出現的出生人口增長卻沒有如約到來。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655萬,甚至比上年還少32萬。因此“全面兩孩”實施后,各地實際生育水平能否達到預期,引發不少地方會議代表委員熱議。
“國家衛計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減少的原因,認為是豬年生肖選擇與育齡婦女數量減少所致。但我個人分析,近年來越來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響更明顯。”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說,過去孩子只求吃飽帶大,現在還希望能養好成才,“各種壓力讓家庭對生育兩孩更加猶豫,或者直接放棄。”
2019年,全國29個省、區、市的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已有一個孩子的單獨家庭,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比例約為60%。國家衛計委表示,“單獨兩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對同樣人群做調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兩孩。
實際生育行為其實更會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東威海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家庭中,70%明確表示愿意生育兩孩,但實際申請量不足6%。
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干部學院教授張原震認為,從“單獨兩孩”的實施效果來看,“80后”年輕群體的生育意愿已顯著降低。
產婦權益
11個省份明確產假相應延長
有地方兩孩津貼減少,職場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的11個省份明確,女方產假在國家規定的98天基礎性產假基礎上,增加30天至60天。不少地區在修改后的計劃生育條例中明確,增加的產假,工資照發,福利待遇不變。
據介紹,生育保險包括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與生育津貼等組成部分。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門將根據其個人生育保險繳費基數除以30,再乘以產假天數來計算。比如產前每月工資為5000元,產假為128天,則總共可獲得2.1萬元左右的生育津貼。
記者采訪發現,全面兩孩放開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兩孩的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區的生育津貼額度卻有所減少。
天津、武漢兩地社保工作人員介紹,兩孩計算生育津貼產假天數仍只能按98天計算,“兩孩增加30天產假是計生部門的政策,社保部門尚未做出具體調整”。同樣按每月繳費基數 5000元標準計算,兩孩生育津貼要少5000元左右。
相較于生育補貼額度減少,職業女性關注的就業與晉升等方面的權利保障,在生育兩孩中所受影響更大。一位浙江省政協委員說,他在調查中發現,有15%受訪女性擔心生育兩孩會導致職位變動或影響職務升遷,生育加劇原本就存在的隱性就業歧視。
“到底是‘生’還是‘升’?”湖南省政協委員張琳說,生育是社會和家庭賦予女性的職責,因就業權利無法得到平等對待,很多女性正面臨著比生第一胎更艱難的抉擇。
生育政策
如果總和生育率下降明顯
可能出臺鼓勵生育措施
從2019年實施“單獨兩孩”到啟動“全面兩孩”,中間間隔僅兩年。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短期是否還會繼續進行調整引人關注。
業內專家表示,判斷生育數量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總和生育率1.8——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1.8個孩子,或將成為重要參考指標。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表示,1.8是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中根據基本國情確定的目標。
篇6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篇7
關鍵詞:(中)關鍵詞人口政策;人口老齡化;經濟效應;數值模擬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荊州人,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調查統計處主任科員。研究方向:應用統計學。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與我國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因對人口老齡化擔憂的考慮,引發了學者們對現有人口政策的爭論。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動態的,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落后,處于“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能夠有效控制人口增長,有助于經濟增長[1]。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漸凸顯,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作用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鄒至莊則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總量進行控制,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是微乎其微的,即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反倒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應。因為人口政策約束了人力資源總量的增長,并引起人口老齡化,不僅加重家庭的養老負擔,還減弱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與此同時,也縮短了人口紅利與人口消費紅利的跨期,這些都將對經濟發展有負面效應[7]。很多學者認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結果就是人口老齡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人口總量擴張并加重當代人的負擔,導致自然資源過度使用,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8~10]。
不論是人口政策的積極評價方還是消極評價方都以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總量的轉變為出發點論述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提升。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正是因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經濟發展進程下,才使得中國人力資本積累極大提高。認識這一點,對解決人口政策評價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數字模擬方法,從人口數量-質量替代效應角度出發,以研究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為目標,來分析在當前老齡化趨勢形成并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級標題二、理論模型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人口快速進入了低生育階段,在這種受約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觀家庭所面臨的收入預算約束必然會發生轉變,進而會對家庭消費、儲蓄、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產生影響。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需要充分考慮生育政策、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確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
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不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的限制,中國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內部代際支持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父母對幼年子女的撫養,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贍養。因此,本文以家庭內部代際支持機制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疊世代模型為理論基礎[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養兒防老機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數量受計劃生育政策控制的情況下,構建一個以家庭養老為主的,研究人口轉變過程中家庭儲蓄、消費和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框架。
二級標題1家庭效用最優決策模型
假定微觀家庭由三代人所組成,且每個人存活三期,分別是少兒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齡期(用t-1期表示)。少兒期不從事勞動,不為家庭帶來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積累人力資本存量。處于少兒期的子女不能自主決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決于處于成年期的父輩對其的教育投資(et)和父輩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存量(ht)。并假定兩要素的投入滿足要素邊際遞減規律,其形式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產出的技術常數,ht+1表示少兒期的人力資本存量,ht表示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人力資本存量,et表示父輩對處于少兒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資支出。
當個體人進入成年期,就產生生育、儲蓄及消費的決策行為。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數量(nt)為受限制給定的。對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僅需要撫養子女還需贍養老人,而這些會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時間支配的約束。假定成年期個人擁有標準化單位時間為1,照顧每個子女需要花費ν個單位時間,所以少兒期的子女總共耗費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時間為νnt。而照顧老年人所耗費的時間要視老年期的預期存活單位時間(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預期存活單位時間為p,而每個成年期的人用于贍養老年期的人的時間為p/nt-1,其中nt-1為t-1期家庭子女數,即父輩兄弟姐妹數。由此,每個成年期的人除去撫養少兒和贍養老人的時間就是其工作時間:
假定成年期的人單位時間人力資本存量的工資水平為t,則他獲得的總收入為Ithtt。除了耗費時間,成年期的人還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贍養處于老年期的父輩,假定比例為m,則每個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贍養預期支出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況下,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將作為遺產被后代所繼承,如果利率為rt,老年期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1,則養老儲蓄總額為It-1ht-1t-1st-1(1+rt)。每個成年期的人所繼承的遺產為:
假定成年期的人當期自身消費為ct,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當期消費額為總收入扣除儲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贍養老人費用,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
老年期后的消費為ct+1(遠期消費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勞動,其消費主要依賴在成年期時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和子女的贍養給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預期效用函數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遠期效用的貼現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數(nt-1)給定的情況下,總是追求自身當期和遠期消費以及子女數量與質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該期勞動人口數為上一期人生育數量總和,其他符號意義同前。
二級標題2經濟增長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經濟生產函數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其中勞動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來衡量,即:
其中,Yt表示總產出,D代表物質生產的技術常數,Kt表示物質資本存量,H表示物質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工資率t,(7)式中對ht求偏導,就為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同理,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資本租金率Rt,(7)式中對Kt求偏導,就為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假定在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出清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相等,社會總支出等于社會總產出。以上分析表明,社會總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費及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子女的撫養教育投資、老年人贍養費支出之和。即:
將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資本完全折舊的情況下,下一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代人的因養老而產生的儲蓄總額,且儲蓄的回報率等于物質資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級標題3家庭最優決策下經濟增長路徑模型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成年人無法自主選擇生育數量,但是能夠自主根據生育數量來決定自身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水平(et)。因此,對(3)式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求規劃的最優解,關于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et的一階條件為:
將(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質資本存量。
聯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養老儲蓄率st的增長路徑為:
以每個少兒期人的教育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教育投資率,記為re,則re=etIthtt。將(14)式代入得到:
將(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資率re的增長路徑:
假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分別為gh、gk,根據(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長,則聯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將(20)式代入(19)式,得到經濟增長速度g,則經濟增長路徑為:
一級標題三、數值模擬及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應用數值模擬方法來分析在計劃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間變量(子女教育投資、養老儲蓄率等)變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根據上述理論模型采用數值模擬方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路徑進行模擬。通過給定各變量的初始值,進行100次模擬以反映人口結構變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參考王金營等人的相關結論,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本產出彈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設定為0786[12]。對于遠期效用貼現率A~,參考賀菊煌的索羅折現率的取值來確定,成年人的消費效用的年折現率通常在001~002之間,而代際間隔通常是25年,故經過25年的折現,未來老年期的消費偏好效用的折現率取值為078[13]。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且許多城鎮地區的老人贍養仍然以家庭為主,所以筆者綜合考慮農村和城市的差異情況,并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
由國家統計局提供。計算中國60歲以上老人家庭贍養率為041,故本文將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贍養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設定為041。而根據張杰等人的研究,將照顧每個子女所花費的單位時間ν的初始值設定為003,將教育投資對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B設定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慮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故令教育部門及物質生產部門的技術水平常數的初始值A=D=145[15]。
二級標題1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齡化對中間變量(主要包括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在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確定,那么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給定總和生育率(TFR)為1、15和2的三種情況下,進行100次數值模擬,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結果見圖1、圖2和圖3。
圖1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儲蓄率的演變路徑。本文的理論模型中,養老儲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養老預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而子女教育儲蓄動機用家庭教育投資率來衡量,故儲蓄率會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長而變化。由養老儲蓄率s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養老儲蓄率呈先上升后趨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隨著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會增加養老儲蓄以維持將來的養老消費。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重,會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養老負擔,導致其當期收入下降,從而導致養老儲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下一代所能繼承的遺產將減少,從而也會降低成年人當期收入,進而使養老儲蓄率降低。數值模擬顯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達到72%的時候,養老儲蓄率達到最大值。
圖2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主要在三種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5和2)情況下進行了數值模擬。由圖2可以看出,總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資率越高,即少兒撫養比與家庭的教育投資率呈反比。這一結論已被大多數文獻從理論角度所證實。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對家庭教育投資率的影響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可以解釋為:由于家庭養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養老的主要資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應越高,那么未來將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所以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教育投資率會增加。但是當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到一定階段后,會增加成年人的養老負擔,且繼承的遺產也會減少,導致當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資率會下降。數值模擬顯示,當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為47%時,子女教育投資率達到最大值。
圖3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有著顯著的差異。當總和生育率TFR=1時,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養老負擔加重,經濟增長先快速增長后急劇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趨勢要平緩許多。由此說明在較低生育率水平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沉重的養老負擔將阻礙經濟的發展。
整體來看,經濟增長速度與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關系,圖3顯示,在老年人口預期存活率較低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隨著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當預期存活率超過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隨著預期存活率的增加而減速。在總和生育率TFR=1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3%;TFR=15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5%;在TFR=2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6%。這種演變趨勢特點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情況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成年人將會提高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同時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費水平將提高,這有利于經濟增長。當老齡化程度超過一定水平之后,家庭養老負擔越來越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照顧老人,同時成年人從老年人那里所繼承的遺產將減少,這些都將減少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從而使經濟增長受阻。
基于以上數值模擬結果來分析中國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各年齡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結果見表1,201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為9680%。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的結果,顯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將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而降低。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二級標題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轉換的原動力是微觀家庭對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權衡,所以研究微觀家庭生育水平與孩子質量的轉換關系,可以全面認識生育率下降與人力資本提高的轉變軌跡、發展趨勢以及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轉換路徑。國外關于家庭生育數量與孩子質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方面有豐富的成果。貝克爾(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經濟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約束下,家長將孩子視為經濟產品,以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最優組合[16~17]。
為研究人口數量與質量的替代效應,下面基于上述理論模型,對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進行數值模擬。圖4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與家庭單個子女的教育投資率呈負向關系,即隨著生育率的提高,每個孩子分攤到的教育資源越少。這是由于當期生育數量的提高,會減少家庭當期收入,因而減少后代的教育投資。
(中)圖題圖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變化趨勢
(中)圖題圖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值模擬值
圖5為不同總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本文模擬了三條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分別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圖可以看出: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會提高,反之則下降。而經濟增長速度隨著總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2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2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8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8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20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總和生育率TFR=118。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結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對經濟發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級標題3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變動機制理論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預期壽命卻呈延長趨勢。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長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人力資本的提高是經濟發展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圖2顯示,隨著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會逐漸提高,且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會逐漸提高。下面通過數值模擬在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貢獻率(1-H)及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1-B)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為結合實際,本文模擬了2010年六普數據結果總和生育率為118時和大多數文獻所公認的水平(16~18)中較高的水平18時,
(中)圖題圖6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趨勢
不同B和H值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結果如圖6所示。
圖6模擬了經濟增長在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經濟增速隨1-H的變大而變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隨著人力資本貢獻率的增大,經濟增長速度會加快。說明隨著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齡化加重的情況下,經濟仍有可能保持增長。由圖形還可以看出,經濟增長速度隨著B的變大而變大。由教育部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隨著物質資本投資貢獻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存量將更高,由此說明教育部門人力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物質資本投資越來越重要,人力資本的積累將越來越依賴于家庭教育投資額。從以上B和H的取值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反向影響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積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環,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又受物質資本投資的影響。由此說明,在相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盡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經濟仍是可持續發展的。
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必然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那么B和H值應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彌補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的損失呢?下面對TFR=118和TFR=180時,老年人口存活率從96%上升到98%時進行數值模擬,結果見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則人力資本投資對總產出的貢獻率(1-H)分別上升56%和3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同理,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B)分別需上升62%和8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
表2顯示,雖然目前中國處于低生育率狀態且人口老齡化加劇,但是如果能夠提高人力資本在總產出中的貢獻率,那么經濟增長隨人口老齡化而下降的趨勢可以緩解,經濟仍可能保持持續增長。
一級標題四、結論與建議
在當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逐漸顯現,中國家庭結構所呈現的倒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走向。未來人口總量增速將逐漸下降,老齡撫養比會繼續攀升,人口老齡化將日益嚴重。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總量規模超過了大多數國家。本文通過數值模擬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借助理論模型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包含家庭養兒防老的保障機制和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自然增長的控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將導致人口規模擴張的加速,并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但會降低人均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經濟發展方向最終由兩個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強弱對比而決定。主要研究結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隨著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養老儲蓄動機,家庭養老儲蓄率將提高,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劇,養老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過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況下)雖然在短期內能促進家庭教育投資的上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長期來看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據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處于最佳水平,能夠適應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穩定,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旦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會有大幅反彈。人口政策是社會政策的一種,從它形成的時候開始,一直就處在與時俱進的不斷調整和完善中。我國現行的政策并不是獨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樣政策的一個政策體系。因此,調整體系的結構比重,可以使生育率達到最適合經濟增長的水平,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勞動力資源的“二次開發”對于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將至關重要,“二次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不可否認“人口紅利”是促進當前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紅利”最終將轉為“人口負債”,勞動力將結束“無限供給”狀態,經濟增長則轉而依靠人力資本積累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成功地開發了沉淀于傳統農業部門和國有部門的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然而在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的今天,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削弱人口老齡化負面影響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國,知識和技能已得到了社會和家庭的一致認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因而是從經濟發展速度最優角度而非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續研究將從更加全面的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內容[1] 王桂新生育率下降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對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認識與思考[J]南京社會科學,2012,(10)
[2] 王金營,趙貝寧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完善和調整——基于公共政策視角[J]人口學刊,2012,(4)
[3] 都陽人口轉變的經濟效應及其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04,(5)
[4] 都陽中國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R]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工作論文系列,2005
[5] 趙進文中國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季刊),2004,(4)
[6] 蔡昉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
[7] 鄒至莊中國經濟轉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8] 鄔滄萍,王琳,苗瑞鳳中國特色的人口老齡化過程、前景和對策[J]人口研究,2004,(1)
[9] 鄔滄萍,謝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國的必然選擇[J]同舟共濟,2009,(4)
[10] 蔣正華,張羚廣新世紀、新階段人口研究和人口工作[J]中國人口科學,2003,(1)
[11] Diamond, P 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 (5)
[12] 同[2]
[13] 賀菊煌個人生命分為三期的世代交疊模型[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4)
[14] Zhang, J , J Zhang and R Lee Rising Longevity, Education, Savings, and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1)
[15] Zhang, J and J Zhang Long Run Effects of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with Earnings Dependent Benefit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3, (3)
篇8
“可愛的公民,請你們提高覺悟,給祖國多生孩子吧!”一些政府已經向他們的國民發出誠懇請求,人口萎縮開始讓這些國家感到擔憂。
20世紀80年代,就有一些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下稱“生育率”)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稱“更替水平”)以下,而且這種狀況不斷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國家。1997年,全球已有51個國家和地區、44%的人口處于低生育水平,而現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會中。
當然對于電國來說,人們擔憂的仍是人口太多。
然而,中國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這個事實,早己悄悄地發生,并且已持續近20年,只是至今仍舊很少進入公眾視野。
中國生育率早已降到低水平
“中國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確立的事實。”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說,1992年中國生育率調查結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調查都顯示生育率處于15以下,屬于“很低生育率”,并正在接近“極低生育率”。
在其他國家,低生育率走勢一經發現,往往會震動政府和公眾,引起高度關注。但在中國,情況卻很不一樣,盡管統計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經持續近20年,但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認為數據水分太大,中國實際生育率被嚴重低估。
中國自1990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計生數字和官員政績掛上鉤,從此漏報、瞞報數量劇增,數據質量越來越差。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僅國際社會不信任中國的計生數據,就連中國人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霧里,“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中國準確的生育率,只能靠估計。”陳衛說。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是,全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33,然而2006年國家計生委做的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調查,得到的結果是,2005年生育率為1.74。兩個全國性調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達到0.4之多,這為判斷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霧。
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認為,瞞報和低報的情況在現實中確實存在,但按照一般規律,即使當年存在出生漏報,后來的調查,尤其是人口普查,應當能夠推算出真實的生育率。然而現實是后期的調查不但沒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調查得到的低生育率。“可見漏報對統計結果不存在實質性、全局性的影響。”他說,中國總和生育率低于1.5的可能性很大。
對于中國實際總和生育率,還有幾種估計可供參考:聯合國人口司最近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了》提供的2004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4,美國人口咨詢局出版《2007世界人口數據表》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6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是1.6~1.7。
這些數字有_二個共同指向,中國生育率確已降到了低水平。郭志剛說:“如果中國生育率繼續保持在這一水平,在并不很遙遠的未來,下降。”
城市生育率極低
“世界上的極低生育率最早發生在中國的城市地區。”陳衛說,很低和極低生育率在中國的城市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已有20多年了。
根據歷次生育率調查,中國城市地區在1974年總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1.5以下,1984年以來(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
在中國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僅很早就達到了板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門一起,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達到極低生育率,200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
陳衛說,在過去的30多年里,西方和東亞的一些國家實現了從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極低生育率的轉變。與其他極低生育率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地區從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極低生育率的轉變更為迅速。
中國城市地區的這一轉變僅用了10年時間,而西班牙、德國、俄羅斯、日本則分別用去13年、32年、31年和46年。
上海是中國最早開始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目前中國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區之一。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變動就出現了負增長,進入21世紀,上海戶籍女性人口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穩定在0.8左右,達到了意大利人口學家Antonio Golini在1998年計算出的,一個人口規模足夠大的人口總和生育率所能達到的最低極限值:0.7~0.8。
中國城市地區生育率極低,除了長期以來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外,陳衛認為,經濟、社會發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特別是90年代以后,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來越削弱,而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因越來越加強了。”
他說,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生活方式變化、婦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職業結構的改變,城市地區的婚姻市場變化、生活和工作的風險。年輕人對新生活目標和生活品質的追求,以及養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都促使人們推遲婚育,少生孩子。
《新世紀周刊》聯合新浪網的調查顯示,在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調查者中,多數人是因為“經濟基礎不行,養不起”,“養孩子太累”。還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怕孩子壓力大,女性單方面承受太多,居住環境差,活著是受罪等。
而推遲婚育的一個結果有可能是,當你想要孩子的時候,卻發現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癥目前是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美國不孕率為10%~5%,歐洲的不孕率則達到20%,中國的不孕不育率由過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現代社會中環境變化,社會節奏加快。社會競爭加劇,增大了人們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都對生育有一定的影響。
一般來說,生育率下降會帶來人口數量的減少。但有趣的是,中國城市地區的生育率在長期處于極低的狀態下,總人口數還在不斷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比如上海,2007年戶籍人口1378.86萬,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長,原因在于這座城市還有660萬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帶來了城市人口的增長,也對城市地區的極低生育率有所貢獻。”陳衛說。
很長時間以來。一提到城市流動人口,人們就會想起“超生游擊隊”。“但20多年來,流動人口生育率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它構成了中國城市生育率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陳衛說,他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遷移與生育率的關系發現,1990年,流動人口生育率顯然顯著低于來源地農村人口,但明顯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卻證實,與農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來人口成為生育率最低的群體。
“大量流動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學生,她們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計
算只貢獻了分母,而沒有貢獻分子。”陳衛說,同時大量外來人口的進入,對城市人口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緩解了人口老齡化進程,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后果很嚴重
按照國際通行的老齡化標準,上海是中國最早進入老年型社會的城市,時間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戶籍人口的20.8%,5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80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戶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勞動力總量正在接近峰值。”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彭希哲發現,2007年度上海市戶籍人口中的勞動適齡人口已經開始出現負增長。“如果沒有重大的戶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勞動力供應總量將開始減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也在不斷上升,年輕勞動力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說。
人口結構老化和勞動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最直接的人口學后果。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座教授王豐說,目前,中國有高達1億多作為經濟發展主力的流動人口,同時也有1.4億60歲以上的老人。而這兩個人口群的規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流動人口群體將不斷縮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規模在日趨擴大。
他推算,僅5年后,也即從2013年開始,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口(20~24歲)的規模將開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內,也即至2023年,達到這個年齡組的人口規模比2013年時的要小1/4以上。“而這個年齡組的勞動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創造力的人群。這個人群規模大幅度縮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遠大于一般性勞動力規模縮小的影響。”
王豐說,長時間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將導致對養老與醫療健康體系的挑戰,影響整體勞動生產率與整個經濟的競爭性。當撫養負擔日趨加重時,人口老化也影響到代際關系,甚至社會的整合與民族的興衰。
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性別比失調幾乎成為東亞國家特有的現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陳衛說,在西方國家,低生育率并不會導致性別比失調,但在東亞國家,兩者是有因果關系的。“原因是性別選擇。”他說,在東亞文化中,男性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被認為要比女性高,因此在只想生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很多人會通過性別選擇來生男孩。
而性別比失調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婚姻擠壓,即婚齡男子找不到對象,由此又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比如單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問題、性犯罪、非婚生育與私生子問題、獨身者養老、社會穩定問題。50年代,中國臺灣地區的男性婚姻擠壓曾導致了大量“老兵人口”的養老問題、“山地社會”童養媳問題、離婚率上升問題和當時臺灣社會風氣墮落等。
生育率下降也會帶來家庭結構的變化。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產生了所謂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即一個子輩、兩個父輩、四個祖輩這樣的倒金字塔結構。陳衛說,雖然未來嚴格意義上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在多大規模內出現,還是個疑問。但家庭子女數趨少,人口壽命延長卻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意味著子女負擔父輩和祖輩的養老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四二一”的家庭結構為獨生子女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成長環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說,這種環境的本質特點是沒有兄弟姐妹,缺少手足之情。“沒有親兄弟姐妹之間的游戲,兒童會缺少很多重要的心理體驗。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而這些對于兒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可或缺。”他說,缺少手足之情的童年,幸福感會大打折扣。
陳衛說,關注極低生育率的嚴重后果,就需要盡早進行理論研究和制度準備。一些極低生育率的歐洲國家出現的人口負增長和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警示。“由于人口發展具有周期性、人口問題具有長期性,把握不好低生育率的‘度’,將會導致難以逆轉的長期后果。”
篇9
關鍵詞:初育年齡;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終身生育率;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訂日期:2015-01-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地區)合作與交流項目“人口變化,城鄉人口流動,和中國的農業與農村發展”(71361140370);江蘇省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PAPD)。
作者簡介:鐘甫寧,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農業大學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亞楠,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變遷一般規律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進入9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并沒有帶來人口的迅速減少,2012年全國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長水平。這主要是由于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對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在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即人口年齡結構中育齡婦女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結果。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會導致未來人口的減少,一旦人口正增長慣性的作用消失殆盡,負增長慣性取而代之發揮作用,便會加劇人口減少的速度。為避免因到時再來提高生育水平而無法有效及時地抑制人口負增長以及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政府已經頒布并開始實施適當鼓勵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例如允許“雙獨”、“單獨”家庭生育二胎。可見,探究掩蓋于人口年齡結構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長水平以及蘊藏在人口年齡結構內部的人口增長慣性,對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長期發展趨勢,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內已有學者關注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以及人口增長慣性問題,研究發現,早在1990年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就已由正變負,人口負增長慣性正在逐漸積累起來[1-2]。總體而言,這類研究基本是針對不同時期人口增長趨勢的分析與模擬,盡管能夠直觀地給出具體一段時間內或某個時間點上的人口總量,但卻需要建立在穩定人口的假設之上,即年齡別生育率與死亡率保持長期穩定不變<sup>[3]</sup>,也就是要求同一時期各年齡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顯然這在現實中難以滿足,尤其是在社會變遷比較明顯的時期。
從本質上講,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實際測度的是代際間的年均更替率。婦女終身生育率、出生嬰兒性別比、婦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間隔是構成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主要參數。但是,平常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未結束生育期的年齡組(隊列)婦女的終身生育率,而能夠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齡組(隊列)婦女當年生育率并加總得到
總和生育率。這是很多研究會直接應用總和生育率分析時期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而非應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角度的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對于前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方面,應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結果無法代表任一真實人口隊列的增長水平;另一方面,總和生育率的較強波動性將難以對長期人口發展趨勢進行穩定的預測。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問題,雖然無法直接刻畫出不同時期的人口規模,但至少能夠作為時期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的一個有益補充,根據各年齡人口的真實變化趨勢分析具有不同年齡結構的人口的長期發展規律,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未來人口的變化方向及增減速度。然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縮短甚至消除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強的實際意義?
隨著研究者們對總和生育率的深入認識和分析方法的不斷改進,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實現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規的總和生育率會因為時期生育年齡的變動(所謂的進度效應)而產生顯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簡稱BF方法<sup>[4]</sup>,該方法一經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學界的廣泛熱議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一些研究對于這一指標到底在測量什么提出了質疑[5-7],因為它既不是對時期生育水平的估計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終身生育率<sup>[8]</sup>。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對該指標進一步改進的方法,并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比較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和終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隊列生育率變化很慢,沒有顯著波動,而時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狀變化也很小的當代歐洲人口<sup>[9]</sup>。顯然,這種轉換方法也并不適用于任何一類人口群體。
筆者在一項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進行測度的嘗試,并驗證了該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sup>[10]</sup>。作為后續研究,本文將進一步以預測效率和穩定性為標準,比較初育年齡測度法與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討上述兩種方法在預測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的差異。以此為依據,本文將從隊列視角揭示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并結合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征探討未來中國人口可能的發展趨勢。目的在于與時期性質的人口變動水平進行對比,從另一個側面為長期人口預測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合理的理論依據。
二、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1.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及其對終身生育率的估計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就已研究發現總和生育率無法準確反映生育數量的變化:受生育時間變化的影響,即使實際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不發生改變,年度間的總和生育率也會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應用一個人口中每個隊列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化量對這一扭曲進行調整的思想<sup>[11]</sup>,在此基礎上,邦戈茨和菲尼進行了進一步的提煉,將這種扭曲稱之為生育進度效應,并運用某一時期前后兩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齡差異作為調整系數,試圖用來消除該效應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數量水平<sup>[4]</sup>。具體的調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數學表達形式做出解釋: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從上述公式可知,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僅根據不同胎次年齡別生育率數據進行調整,并不需要額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齡,ri是調整系數,公式(2)是經過整理后的簡便表達形式,其計算依據是以當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齡的平均數作為平均生育年齡年初值,以當年與下一年的均值作為年末值,最終用年末與年初的差值表示當年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如果當期的總體生育時間表現為向后推遲的狀態,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將大于TFR,也就是說實際的生育勢能并沒有在當期完全釋放出來,而是向后累積,觀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實的生育水平。當然,可能會出現ri>1、TFR*為負的異常現象,即平均生育年齡的變動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長溶運用中國的經驗數據證實的確會存在這種可能性<sup>[12]</sup>。雖然這與數據的質量有一定關系,但主要應是由于該方法要求年齡別生育率曲線形狀不變、各年齡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齡的年變化幅度相等,一旦現實與這一強假設條件相差較遠,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的穩定性會變得很差<sup>[13]</sup>。
隨著對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斷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礎上將生育率替換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種綜合考慮孩次結構與進度效應的調整指標TFRp*,并用歐洲多國的數據驗證了其較TFR*具有更強的穩定性<sup>[9]</sup>。一般來說,新指標的穩定性如何是多數研究探討的焦點,因為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標準而難以對其效度進行評價。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備計算所需的數據,因此,暫時難以將TFRp*應用于中國生育研究中<sup>[14]</sup>。
不過,邦戈茨認為,在特殊條件下,調整的總和生育率與那些在同時期內已達平均生育年齡婦女隊列滯后取得的終身生育率值還是可以比較的。例如,1965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5歲,那么該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對應的是1975年調整的總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總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動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終身生育率。盡管該方法較為粗糙,而且中國生育水平變化的實情確實很難滿足二者的可比條件,但這卻是目前為止最能夠簡單有效地將總和生育率轉換為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將其簡稱為總和生育率轉換法。
2.利用初育年齡對終身生育率的模擬
筆者在另一項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后一生育事件的發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礎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規律,另一方面根據初次生育時間選擇和終身生育數量的決策機制,推斷屬于前期生育行為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高度相關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而且在統計學上得到了強力支持<sup>[10]</sup>。該方法的具體思路是根據可獲得的時期跨度較大的15-49歲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分別計算出不同隊列的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采用雙對數模型進行模擬,另外需加入時間變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對終身生育率的影響,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過去高生育水平時期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率的擬合結果并不意味著可以簡單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時期的預測,關鍵在于人們對二胎生育的改變情況。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數人的最少生育數量為兩個孩子,那么當終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時,很難再按照過去的水平隨著初育年齡繼續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夠接受1個孩子的最少生育數量,那么二胎會同多胎一樣與初育年齡的變化高度相關,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緩下降速度。在中國,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鎮,同時計劃生育政策也相對寬松,并且其生育觀念也較為傳統,2個孩子仍可能是多數農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數量需求。而在城鎮,僅生育一胎的家庭則會更多。當然,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鎮遷移,以及城鄉間人口流動的加速,農村人口的生育行為會與城鎮人口逐漸趨同。因此,可以模擬當社會總體的終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時,未來人口全部遵循城鎮和農村人口兩種極端情況下的生育水平變化趨勢,并且根據農村和城鎮人口比重對其進行加權平均,從而得到更可靠的預測結果。
3.兩種估計方法的結果比較
既然初育年齡測度法和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均可以得到終身生育率的估計值,那么就能夠以真實值為標準對不同方法的結果進行穩定性和有效性的檢驗。根據1950-2012年中國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可以計算得到1950-1978年開始進入生育期的29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數據上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終身生育率呈現穩定下降的趨勢,而1977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數值則出現了略微上升的現象,為考察這一變化是新的趨勢還是數據的異常情況,我們進一步估計了1979年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假設其相應的缺失49歲生育率數據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實際上是應用1950-1979年30個完整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對上述兩種方法的結果進行評價,比較結果如圖1所示。
圖1初育年齡測度法與總和生育率轉換法估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
注:根據總和生育率轉換法計算1951-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需要對應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剛.時期水平指標的回顧與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據歷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年齡別生育率數據整理計算而得。
其中,CFR是30個育齡婦女隊列終身生育水平的真實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別表示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對應的隊列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從穩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顯CFR*呈現出穩定的下降趨勢,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動性較高,且偏離CFR。調整過的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規總和生育率,體現為更加平穩的變化趨勢,但仍然明顯不如CFR*。從效度方面看,CFR*與真實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規和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在1951-1967年15歲的17個育齡婦女隊列中與真實值的偏差較大,而這些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恰好對應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總和生育率的修勻值,相對于其他時期而言,該時期總和生育率變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生育年齡的女性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與真實值之間的誤差有所縮小,并且變化相對穩定,這與中國進入80年代后總和生育率變動幅度小相關。反向預測表明,應用總和生育率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歲一胎年齡別生育率數據計算初育年齡,則可以預測出198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12個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從圖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歲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水平繼續平緩下降。雖然對于這部分預測值而言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終身生育率以驗證預測的準確性,但可以與meanTFR*和meanTFR進行對比,結果顯示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介于兩者之間,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變化趨勢,說明其預測結果至少不會與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產生較大偏差。
計算終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測度相對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從穩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個區間都遠遠優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與去進度效應和常規總和生育率修勻值相比,初育年齡法能提供對婦女終身生育率更穩定的預測值,因而更接近穩定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過去的經驗表明,由初育年齡預測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具有更高的準確性,但是,我們不僅無法觀察到婦女未來的實際終身生育率,甚至無法統計1980年以后年滿15歲的婦女的終身生育率,因而無法用實際觀察值來驗證預測值。然而,正因為無法得到觀察值而又需要預測,我們才需要相對準確的方法。如果解釋過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預測未來,則初育年齡測度法不失為一種相對較好的方法。
三、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盡管已有不少研究對時期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了分析,并將其與常規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進行比較,說明隱藏在背后的人口內在增長勢能[1,3]。但從長期來講,應用終身生育率等隊列指標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人口增長潛力的表達。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齡測度法相比總和生育率估計法能夠有效、穩定地對終身生育率進行預測,這一結果能否繼續在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分析中得以體現,隊列角度的潛在人口增長水平究竟如何,這是進一步將要探討的內容。
1.涵義及計算方法
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r與凈再生產率NRR的計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齡的女嬰生育函數m(a)和存活函數p(a)。嚴格來說,有一點明顯不同的是,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是穩定人口假設下測量人口增長潛力的時期性質的指標;而人口的凈再生產率則表示育齡婦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數,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婦女能否在數量上“復制她們自己”,似乎作為隊列指標更為合理一些。若要將二者聯系起來進行分析,首先必須統一研究對象為真實隊列還是假設隊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討真實人口隊列的潛在增長水平,因此,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涵義將被解釋為兩代人之間的年增長率,具體的計算參數也均應用相應的隊列指標。
洛特卡將r與NRR的關系表示為如公式(6)所示,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等同于凈再生產率的對數與平均世代間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凈再生產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終身生育率CFR、出生嬰兒中女嬰所占比例S,以及育齡婦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齡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積<sup>[15]</sup>,見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計算過程前面已有討論;假定年齡別性別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為一個不隨年齡變化的常數,這種近似也較為合理;而p(Am)的計算要相對復雜一些,需要通過構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為凈再生產率與粗再生產率GRR(不考慮婦女死亡情況)之比,引用王豐等測算的中國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sup>[1]</sup>,便可以得到歷年的p(Am)值。由于缺乏關于早期全國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統調查,因而無法轉換得到隊列性質的p(Am)指標。鑒于死亡水平的變化幅度不大,暫且以p(Am)的五年移動平均值代替在對應年份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的p(Am)值。
科爾(Coale)證明平均世代間隔近似等于穩定人口和靜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兒年齡的均值,同時也證明了當死亡率曲線不是異常時(如戰爭、瘟疫),可以由年齡別生育率近似求得<sup>[16]</sup>,具體表達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綜合公式(6)-(8),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可以表示為:
r=lnCFR+lnS+lnp(Am)T(9)
根據基礎的年齡別生育率數據、出生嬰兒性別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凈再生產率數據得到的用于計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各參數指標值如表1所示。
2.隊列角度的中國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
由表1中的各參數值計算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即1950-1991年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間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據終身生育率真實值、利用初育年齡和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預測得到的估計值計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總體而言,圖2中所顯示的不同增長率曲線形狀與各自對應的終身生育率曲線形狀類似,說明與人們的預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內在增長潛力的最主要的指標。然而,隨著生育數量逐漸穩定維持在較低水平,平均世代間隔的延長會成為促進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
圖21950-1991年15歲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同表1。
從圖2中可以看出,隊列角度的人口潛在增長水平始終保持穩定下降的趨勢,20世紀50年代15歲的育齡婦女從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間,這兩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進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現負增長現象,也就是說從1970年15歲的育齡婦女這一代人開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規模小于母親這一代的規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進入負增長時對應的女性終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間,高于普遍應用的2.1的更替水平,這主要與中國偏高的男女性別比有關,女嬰比例過低會造成人口提前進入負增長時期,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樣指出考慮高性別比在內的更替水平也應提高<sup>[17]</sup>。
對于整個20世紀70年代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真實的以及由初育年齡測度得到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均為負值,代際之間的人口迅速減少;而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得到的數值則體現為接近零增長水平的長期波動,直至80年代初期才開始出現負增長,明顯這與在其他參數指標變化不顯著時生育水平持續下降的事實相違背。雖然預測部分兩種方法的估計值水平較為接近,但仍可以從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變化態勢中看出,初育年齡測度法比總和生育率轉換法具有更強的穩定性。由初育年齡預測的20世紀90年代初15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數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減少。由于鼓勵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開始實施,而且最多也僅放寬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據過去的發展趨勢粗略外推,對于本文無法預測到的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而言,其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將會繼續下降。
四、未來中國人口變化趨勢的簡要分析
結合前面對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齡婦女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的估計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嘗試對中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進行簡要的分析。
圖32010年全國人口年齡結構
數據來源:《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11》。
注:為方便結合隊列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行分析,這里的縱坐標解釋為對應年份15歲的人口隊列。
如圖3所示,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形狀并不規則,有幾處明顯的缺口,從上至下的第一個缺口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導致出生人口減少,然而隨后便出現生育的反彈,經過周期性重復,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減少,并且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展,第二個缺口有所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經過一輪世代更替,第三個缺口已經并不明顯,人口數量的變化趨于穩定。在這樣一個人口結構中,2010年處于生育期的育齡婦女(2010年15歲至1975年15歲)占有較高比重,對應類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過圖2可知,從1970年15歲的隊列開始,真實的人口增長就已進入負增長狀態,但從傳統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水平來看,中國人口至今仍表現為正增長。可見,父母一代的龐大基數掩蓋了子女規模不斷縮小的事實,從而保持總人口數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也是引起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進入老齡階段,這一因素對人口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更為明顯。
然而,由過去高生育水平積累起來的人口正增長慣性正在慢慢消失,總人口中比重較高的人群逐漸退出生育期,比重較低的隊列進入生育期,同時人口內在增長水平處于負增長階段,因此,中國人口逐步減少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現階段較低的生育水平又進一步為未來積累負的增長慣性,在兩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規模縮小的態勢將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例如,從2010年開始推測15年后的情況,也就是位于圖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個隊列整體進入生育期,即使終身生育率能夠恢復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難通過新生人口實現總人數的增長。正如前面所述,人們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會對人口增長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時也難以抵消負增長的勢頭,并且會加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初實行的以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為目的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數的增加,但卻無法及時地抑制人口正增長慣性所產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實施的40多年間中國人口規模仍在不斷擴大。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關注的重點,但由其帶來的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會長期影響人口金字塔底部數量,更是不容忽視的。
運用初育年齡估計終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將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縮短十幾年,也就是說在2010年的人口結構中,終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能夠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進入生育期的隊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進一步依據初育年齡的估計值預測更年輕的育齡婦女隊列的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進而再結合生育模式便能夠模擬不同年齡結構下的人口變化情況。這樣既可以對過去人口增長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也能夠為預測未來人口變化提供一種較為科學的思路。
五、結論及建議
年度間的人口增長水平實際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內在增長潛力和由年齡結構決定的人口增長慣性兩方面的作用。為充分認識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本文以真實的人口隊列為研究對象,運用兩種不同方法得到的終身生育率估計值,對中國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通過與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對終身生育率估計的方法相比較,證明初育年齡測度法在反向“預測”過去時具有明顯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現在和正向預測未來時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因而更有利于進行長期人口預測。初育年齡測度法的最大優勢在于有效縮短了終身生育率的時滯期限,增強了運用終身生育率分析隊列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的實際可能性。
研究同時證明,在估計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方面,初育年齡測度法同樣要優于總和生育率估計法。研究表明,以隊列為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已經下降: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所生育女孩的規模已經小于其本身的規模,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進入負增長時期。根據我們的預測,90年代初期進入生育期的育齡婦女,其生育的女兒數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減少。另外,研究還發現,對應正增長到負增長轉換臨界年份的育齡婦女隊列的終身生育率為2.28,高于普遍認為的2.1的更替水平。這與中國偏高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相關,因為新生嬰兒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婦女更高的終身生育率才能維持整個人口的替代率。
有關人口的決策一方面需要對人口的內在增長水平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年齡結構作用的人口慣性增長。結合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繪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中國總人數仍呈增加態勢的原因主要是處于育齡期的人口占有較高比重,以及人們預期壽命的延長,在未來后者可能會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不僅需要充分認清其對現有人口增長水平的作用,還要考慮到對未來年齡結構的影響。
人口再生產達到并穩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發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國人口政策的目標。面對低生育水平的現實,過去人口政策中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在現在被適當放寬。然而,本
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初育年齡與終身生育數量具有顯著的負向關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應注意對生育時間的控制,如果人們的意愿生育時間越來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許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理想目標。一些歐洲人口的經驗研究也同樣主張尤其要阻止越來越晚的生育趨勢來影響人口發展<sup>[18]</sup>。
參考文獻:
[1] 王豐,郭志剛,茅倬彥. 21世紀中國人口負增長慣性初探[J]. 人口研究,2008(6):7-17.
[2] 茅倬彥. 60年來中國人口慣性變化及趨勢[J]. 人口與經濟,2010(6):1-6.
[3] 宋健,范文婷. 慣性增長下的人口再生產:全國及省級變化[J]. 人口研究,2013(4):33-42.
[4] BONGAARTS J, FEENEY G.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8(2): 271-291.
[5] KIM Y J,SCHOEN R.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limits to BongaartsFeeney adjustment[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0(3): 554-559.
[6] VAN I E,KEILMAN N.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 comment[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0(3): 549-553.
[7] ZENG Yi, KENNETH C L.Adjusting period tempo changes with an extension of ryder’s basic translation equation[J]. Demography,2002(2): 269-285.
[8] 郭震威. 對“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TFR′)方法”的一點看法[J]. 人口研究,2000(1):19-21.
[9] BONGAARTS J ,SOBOTKA T. A demographic explanation for the recent rise in European fertili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2(1):83-120.
[10] 王亞楠,鐘甫寧.利用初育年齡測度終身生育率的探索[J].人口學刊,2015(2):5-14.
[11] RYDER N B.Problems of trend determination during a transition in fertility[J].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56,34:5-12.
[12] 郝娟,邱長溶. 對去進度效應總和生育率的檢驗與討論[J]. 人口研究,2012(3):81-88.
[13] 曾毅. 對邦戈茨―菲尼方法的評述、檢驗與靈敏度分析[J]. 中國人口科學,2004(1):68-80.
[14] 郭志剛. 常規時期生育率失真問題及調整方法的新進展[J]. 人口研究,2012(5):3-14.
[15] SAMUEL H P,PATRICK H, MICHEL G. 人口統計學:人口過程的測量與建模[M].鄭真真,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39-141.
[16] 曾毅,張震,顧大男,鄭真真.人口分析方法與應用[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42-243.
篇10
作者:梅志強 史雅萍 單位:山西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山西省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
在分析中學歷與職業可能存在混淆,職業分類有交叉,如調查的在校研究生群體,就受教育程度來說他們屬高學歷者,就職業來說他們是學生,其實學生并非是一種職業,只是人生成長的一個階段。但是學歷和職業有一定關聯性,學歷層次越高,就越可能從事復雜勞動職業。但是隨著教育的普及,關聯程度會逐漸減弱,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將逐漸消失。
學歷和職業對意愿生育數量的影響過去人們認為,文化水平越低,孩子就生的越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和農民生的孩子多,國家干部生的孩子較少[2]。縱觀20世紀50~60年代我國婦女的生育情況也確實如此[3]。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兒女雙全”傳統生育觀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提倡的鼓勵生育政策作用。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知識女性曾給鄧穎超寫信,要求政府提供避孕措施,節制生育。而當時的工人、農民文化層次普遍不高,大多是半文盲和文盲,他們既沒有避孕節育知識,更沒有避孕節育的手段,“性”福與生育必須兼得成為她們無奈的選擇[4]。作者曾在農村做過調查:50~60年代農村育齡婦女都希望兒女雙全,但數量以3個為宜,最多4個,過多生育并非是她們的主觀意愿。而他(她)們的子女,即80后父母的生育觀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總和生育率從他(她)們母親的5.8下降到她們自己的2.47[5,6]。有作者對我國解放后居民生育意愿的變遷進行了考察,發現居民理想子女數隨時展而逐年降低[7,8],特別是調查了1974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發現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與同齡的非獨生子女沒有差異,處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狀況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基本相同。從生育數量上看,約1/3青年希望生育兩個孩子,60%的青年希望生育1個孩子,5%的青年不打算要孩子,希望生育3個以上的不足1%[9]。本次調查結果,不論從調查者學歷還是從職業分析,96%以上生育孩子數量都選擇在1~2個,且選擇生育2個者多于生育1個者約10個百分點。打算不要孩子或愿意生育≥3個者均以研究生居多,自由職業和無業者不要孩子的比例高于其它職業者,其原因需進一步研究。
職業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且向多元化發展。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觀念會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發生變化,追求多元化、個性化、舒適化成為這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生育已不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表現出能生而不愿多生;二是撫養成本不斷增大,當“房奴”、“車奴”而不愿再當“孩奴”,表現出想生而不敢多生;三是政府和市場提供了良好的避孕節育藥具,性和生育完全可以按照主觀意愿調控,成為不想多生而能不生;四是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對80后的影響將繼續下去,不愿違規生。“想生”與“不想生”是人的主觀意愿,而“敢生”與“不敢生”是人的客觀承受能力,理論上兩者不該相互影響。但主觀意愿常常會受客觀承受力和生育政策的影響,使得實際生育數往往小于意愿生育數,以經濟基礎為主導的實際生育數量是理想生育數量的具體體現[1]。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已進入老齡化時期[10]。經濟和人口如何均衡發展,誰來養老已成為國家面臨的大問題。面對改革開放、社會多元、生存壓力加大,已經不愿多生的新一代,作者建議,應盡快把生育的國家計劃調整為家庭計劃,真正體現計劃生育徽章所賦予的含義。國家可根據不同時期的人口規模、人口結構,用獎勵等多種方式提倡少生或多生,使人口結構保持在合理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