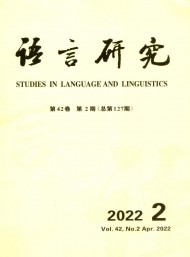語言的藝術(shù)范文
時(shí)間:2023-04-02 14:49:26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語言的藝術(shù),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版式即指版面形式,是一種形式的語言;而這種“形式”,是具有內(nèi)容的形式,是和內(nèi)容不可分離的聯(lián)系著的形式。
從狹義上講,報(bào)紙版式是一種技藝,一種編排技藝。從廣義看,報(bào)紙版式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shù),版式語言也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shù)語言。版式語言的作品,要求設(shè)計(jì)者熟練地掌握其語言元素、語言結(jié)構(gòu)、語言規(guī)范及其語言藝術(shù)手段、技巧,準(zhǔn)確地把握其語言的審美原則。在報(bào)紙版面有限的平面上,一幅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shù)性的版式語言作品,其容量之大、空間之廣、寓意之深,充分地體現(xiàn)著其設(shè)計(jì)者的知識(shí)之廣泛、修養(yǎng)之深厚、智慧之聰敏。
一般來說,構(gòu)成報(bào)紙版式語言的元素有文字、標(biāo)題、圖片、線條、底紋、刊頭、欄頭、插圖、題圖、報(bào)花等等,其中一些基本元素尚可劃細(xì)為更微小的元素單位。從版式語言運(yùn)用角度分析,這些版式語言的基本元素中,文字可按其重要性輕重與否分為若干等次,亦可視其長短之別依次分檔;標(biāo)題作為版式語言的“點(diǎn)晴”之筆,無論其如何變幻,均可歸入橫、豎二類;圖片基本可按所占版幅以大、中、小分之;線條包括花線與直線兩大類;底紋種類繁多;刊頭、欄頭、插圖、題圖、報(bào)花等等,更是形式多樣。
報(bào)紙的版式設(shè)計(jì),具有自左至右、自上至下、自右至左三種基本的視線走向規(guī)律。按照這三種視線走向規(guī)律在版式語言結(jié)構(gòu)中的不同作用,科學(xué)地、藝術(shù)地運(yùn)用版式語言手段和措施,便可創(chuàng)造出版面空間中引起受眾心理活動(dòng)更加強(qiáng)烈的條件,促使編輯從各類稿件不同語言結(jié)構(gòu)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并體現(xiàn)出自身的重要性,即新聞價(jià)值。由此而言,熟練地掌握并運(yùn)用好版式語言的手段和措施,對(duì)于報(bào)紙版式語言的總體構(gòu)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報(bào)紙版式語言的措施包括兩個(gè)方面,即技術(shù)措施和藝術(shù)措施。所謂技術(shù)措施是保證版式語言手段實(shí)施的條理化、規(guī)范化的操作方法。藝術(shù)措施是版式語言手段在實(shí)施中更加活躍和富有吸引力,給受眾以形象的直觀感和美的魅力的操作方法。
“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 版式語言措施中對(duì)我們的規(guī)范化要求,一般包括如下一些不能違背的規(guī)則:斷欄,即通常所言欄與欄拉通;碰題,即或橫或豎同一線上題與題相接;碰文,即等長欄或上下或左右相碰;雙轉(zhuǎn),即同欄中一文甩至另一文尾;以及并肩、斷行、遞轉(zhuǎn)、脫節(jié)等等。
毋庸置疑,好的版式語言作品當(dāng)然應(yīng)給人以美感。報(bào)紙的版式語言有它的獨(dú)特性,它既能與報(bào)紙的內(nèi)容、性質(zhì)、色彩取得一致,又可以以其整體表達(dá)形式的美,引發(fā)受眾的喜愛,打動(dòng)受眾的心靈,使讀者沉浸在審美愉悅之中。
篇2
對(duì)于繪畫語言運(yùn)用的不同,產(chǎn)生多姿多彩、風(fēng)格各異的繪畫作品。在歐洲,自繪畫大師達(dá)芬奇開始,就形成了傳統(tǒng)的寫實(shí)主義畫法,通過研究光線揭示形式的方式,發(fā)展和運(yùn)用直線透視法,來獲得景深幻覺的規(guī)則,通過研究人體解剖,給作品注入全新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感。他們的作品弘揚(yáng)了人文主義精神,在繪畫的總體風(fēng)格上,姿勢(shì)華麗、典雅、宏偉、和諧,寫實(shí)技術(shù)嫻熟,形成了“古典主義”畫風(fēng)。 區(qū)別與古典畫風(fēng)的印象派畫家們,用光、色描繪自然和抒發(fā)自己的感情。他們擅長表現(xiàn)陽光和色彩,對(duì)瞬息萬變的光色變化非常敏感,注重色彩的表現(xiàn),運(yùn)用分色技術(shù),將色彩合理組合,使畫面變得明快絢麗。印象派畫家不再因襲傳統(tǒng)的畫法,其作品詮釋了光色的功用形。在色彩的表現(xiàn)里,印象派畫家完美地表現(xiàn)了一種抒情風(fēng)格,他們很好地運(yùn)用了繪畫語言,給作品注入了抒情性外表美。在西畫造型過程中,主要使用形體和色彩語言,即便沒有線的使用,其造型行為不會(huì)受到重大影響,依然能構(gòu)架繪畫形態(tài);即便使用線界定輪廓,如在輪廓外輔上調(diào)子,就會(huì)成為立體畫面。因此,西畫中線是作為表現(xiàn)形體的特殊手段。
總之,各類畫派的藝術(shù)大師,都借助語言形式來體現(xiàn)作品的情感。繪畫語言的不同運(yùn)用,產(chǎn)生了不同風(fēng)格的繪畫作品。中國畫崇尚文、意、趣,是通過筆墨技巧來體現(xiàn)的。筆墨本身是形式的因素,有引起形象的聯(lián)想和意趣的感受功能。正如藍(lán)色和紅色能引起冷暖的視覺感受一樣,在宣紙上粗糙的筆墨,能畫出老人蒼老的視覺感受;水分飽滿、行筆流暢的筆跡,給人春天般滋潤的視覺感受;流利靈活用筆,能喚起灑脫歡暢的聯(lián)想;快速多變的用筆,能令人有蛇龍飛舞的遐想。這些筆墨形式,是藝術(shù)家們獨(dú)特風(fēng)格在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表現(xiàn)。通過構(gòu)思構(gòu)圖,合理運(yùn)用筆墨虛實(shí),水韻、墨色和運(yùn)筆產(chǎn)生的肌理,形成有個(gè)性的繪畫語言。虛實(shí)的表現(xiàn),是美術(shù)家們靈氣的表現(xiàn),是對(duì)畫理的悟性。畫要有筆墨,無筆墨就不成畫,筆墨技巧要與表現(xiàn)內(nèi)容有機(jī)的結(jié)合起來,才能創(chuàng)作出最佳作品。這種藝術(shù)法已成為中國獨(dú)有的繪畫語言。
繪畫語言是有機(jī)的形式體現(xiàn),是構(gòu)成繪畫藝術(shù)中多種可視因素的總結(jié)構(gòu),是一種在長乘寬的二維平面上,利用點(diǎn)、線、面或黑、白、灰和色彩、肌理等手段,傳達(dá)美術(shù)家對(duì)精神文明的追求。繪畫是人類藝術(shù)追求的一種方式,它有其獨(dú)特的語言和表達(dá)技巧,就繪畫來說,不同的表現(xiàn)題材和工具材料都有其特殊規(guī)律、表現(xiàn)語言和表現(xiàn)方式,凡是符合繪畫本體的藝術(shù)規(guī)律的任何題材、表現(xiàn)語言和表達(dá)方式,對(duì)人類精神文明起到推動(dòng)作用,符合人類追求審美觀的任何繪畫語言方式都應(yīng)該發(fā)揚(yáng)光大。
藝術(shù)家們對(duì)繪畫中的情態(tài)和語言形態(tài),在不斷地尋求繪畫觀念和語言上的轉(zhuǎn)型,揚(yáng)棄繪畫語言在生活上淺淡的東西,努力在繪畫語言、圖式和動(dòng)機(jī)上出現(xiàn)新的形態(tài),形成有個(gè)性的繪畫語言成為美術(shù)家們的共同追求,并探索繪畫形象與象征符號(hào)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演變和發(fā)展,在多層次上探討了藝術(shù)的本質(zhì)問題,豐富和創(chuàng)造了人類的視覺形象語言,改變著人們觀察世界的審美方式。
篇3
由于不同的藝術(shù)家對(duì)繪畫語言具有不同的運(yùn)用,必然會(huì)產(chǎn)生多姿多彩、風(fēng)格各異的繪畫作品來。縱觀繪畫史,我們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差異。在歐洲,自達(dá)芬奇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傳統(tǒng)的寫實(shí)主義畫法,藝術(shù)家通過“研究光線揭示形式的方式,通過發(fā)展并運(yùn)用直線透視法來獲得景深幻覺的規(guī)則通過研究人體解剖,藝術(shù)家給他們的作品注入了一種全新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感。”他們的藝術(shù)作品弘揚(yáng)了“人文主義”,在繪畫的總體風(fēng)格上,姿勢(shì)華麗、典雅、宏偉、和諧,寫實(shí)技術(shù)嫻熟,形成了我們稱之為“古典主義”的畫風(fēng)。區(qū)別與古典畫風(fēng)的印象派畫家們,用光與色描繪自然和抒發(fā)自己的感情,他們擅長表現(xiàn)陽光和色彩。他們對(duì)瞬息萬變的光色變化非常敏感,注重色彩的表現(xiàn),畫家運(yùn)用分色技術(shù),將色彩合理組合,使畫面變得明快絢麗。印象派畫家不再因襲傳統(tǒng)的畫法,他們的作品則替我們?cè)忈屃斯馍墓τ眯巍T谏实谋憩F(xiàn)里,印象派畫家完美地表現(xiàn)了一種抒情風(fēng)格,他們很好地運(yùn)用了繪畫語言,給作品注入了抒情性外表美。在西畫造型過程中,主要使用形體與色彩語言,即便沒有線的使用,其造型行為不會(huì)受到重大影響,其繪畫形態(tài)的構(gòu)架依然能成立。即使用線界定輪廓,如在輪廓之外輔上調(diào)子,馬上就會(huì)成為很立體的畫面。可見西畫中線依然作為表現(xiàn)形體的一種特殊手段。
無論何類畫派的藝術(shù)家,他們都是借助其獨(dú)特的語言形式來完成作品的情感體現(xiàn)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繪畫語言的不同運(yùn)用,則產(chǎn)生出不同風(fēng)格的繪畫作品。中國畫崇尚文、意、趣,而這一切都是通過筆墨技巧來體現(xiàn)出來的。在這里,筆墨本身不是“具象”的,相對(duì)具體塑造的藝術(shù)形象來說,它是形式的因素,但卻有著引起形象的聯(lián)想和意趣的感受的功能。正如藍(lán)色和紅色能引起冷暖的視覺感受一樣,在宣紙上粗糙的干筆能引起樹干及老人似的蒼老的視覺感受;水分飽滿、行筆流暢的筆跡能引起春天般滋潤的視覺感受;徐緩的用筆能引起持重含蓄的聯(lián)想;流利靈活用筆能引起灑脫歡暢的聯(lián)想;快速而多變的用筆引起蛇龍飛舞的聯(lián)想。賀天健總結(jié)筆法有:“筆直中鋒,臥筆中鋒,倒筆卷上,倒筆提上,臥筆旋拖,放筆直下,仰筆伸縮滾擦,垂筆揩擦,側(cè)鋒聽昕下筆重,仰筆剔掠,仰筆旋拖,臥筆拖擱,臥筆橫拖戰(zhàn)動(dòng)。”墨法有:“烘、染、渲、破、飛、揉、積、漬。”實(shí)際上何止這許多,臨池潑墨,變化萬千,風(fēng)雪晴雨,因人而異。中國筆墨這種形式因素,是畫家的獨(dú)特風(fēng)格在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主要表現(xiàn)。藝術(shù)家們常“借筆墨以寫天地”。通過構(gòu)思構(gòu)圖,合理運(yùn)用筆墨虛實(shí),水韻,墨色和運(yùn)筆而產(chǎn)生的肌理形成有個(gè)性的繪畫語言。虛實(shí)處理,仍然是當(dāng)代畫家構(gòu)成新的屬于自己藝術(shù)語言的要素。虛實(shí)的表現(xiàn),就是畫者靈氣的表現(xiàn),是對(duì)畫理的悟性。中國畫家歷來認(rèn)為畫必須有筆墨,無筆墨就不能與畫。并且筆墨技巧還要與表現(xiàn)內(nèi)容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才能產(chǎn)生好的作品。這種代代沿襲的藝術(shù)法則即所謂傳統(tǒng),已成為中國所獨(dú)有的繪畫語言。
當(dāng)繪畫喚起人類的審美情感時(shí),作用于人們的是一種繪畫所獨(dú)有的語言形式。繪畫語言由多種要素構(gòu)成,這里涉及到的視覺因素有:點(diǎn)、線、形、光、色彩。“點(diǎn)”:是最小的視覺實(shí)體,對(duì)于探討視覺形式的作用,點(diǎn)是一個(gè)很好的著手處。一個(gè)可視的點(diǎn)是一個(gè)吸引視覺注意力的小元素,點(diǎn)既可以被表現(xiàn)出來,也可以被暗示。它可以構(gòu)成一個(gè)情趣的中心或一幅構(gòu)圖中被強(qiáng)調(diào)之處。甚至處在一個(gè)表面上的一個(gè)點(diǎn)就像是在一座靜謐的屋子里的聲音,它與周圍形成一種關(guān)系,它使這個(gè)空間有了生機(jī)。“點(diǎn)”,從物理形態(tài)上講,是視覺聚焦的核心;從觀念形態(tài)上說,是思想呈現(xiàn)之源。點(diǎn),在東方哲學(xué)中,具有最大的內(nèi)張力和最大的延展性。從點(diǎn)出發(fā),可深入、可輻射。點(diǎn)——解釋一切,代表一切。“線”:線可以被描述為點(diǎn)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它是一個(gè)可視的行動(dòng)軌跡,一條線表現(xiàn)著劃線的人或物的精神。一幅畫的筆觸,穿過風(fēng)景的一條蜿蜒的河流,被撕破的線的參差不齊的邊緣,一個(gè)草葉的曲線,這每一條線正如同每一位畫家或書法家的充滿個(gè)性的、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一樣,是獨(dú)具特色的。線——人們認(rèn)識(shí)和反映自然形態(tài)時(shí)最簡(jiǎn)明的表現(xiàn)形式,有長短、粗細(xì)、曲直之分。線可以在長度、寬度及方向上的不同,線也可以是連續(xù)不斷的或間斷的,粗的或細(xì)的,有規(guī)律的或無規(guī)律的,靜止的或運(yùn)動(dòng)的,直線的或曲線的,或者是這些線的諸多形式的不同的結(jié)合體。在一個(gè)平面上,線能界定各種形狀,暗示體積或顯示所繪物體質(zhì)量的獨(dú)立元素。我們能通過線條的組織來創(chuàng)造圖案、肌理或描繪陰影。線是闡明視覺形式的基本手段,它通常是對(duì)所目睹、感受或想像到的事物的一種速寫,線是在兩維空間表面的長度標(biāo)準(zhǔn),或者說它們是在兩維或者三維空間里的物體邊緣的感知,每一條線或物體邊緣都有其自己的表現(xiàn)特征,這些表現(xiàn)形式在視覺交流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視覺藝術(shù)中,線條一直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極富有意味,在中國的繪畫藝術(shù)中,線條的功用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事實(shí)上,中國繪畫在相當(dāng)程度上是以富有骨氣韻味的線條來取勝的。線條的運(yùn)用,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愈來愈富有含蓄性、表現(xiàn)性、象征性與抽象性。線條形狀各異,功能有別。“形”:形式關(guān)于一種被視為平面的存在形式,即一種二維的空間區(qū)域或平面是一種剪影或陰影形式的外觀。當(dāng)一條線勾畫出一個(gè)區(qū)域或當(dāng)一個(gè)面積表面的顏色或肌質(zhì)發(fā)生變化時(shí),其面積與周圍的面積相分離,形便成了可視的存在。千變?nèi)f化的形可被概括為兩大類,即有機(jī)形和幾何形,雖然二者之間有明顯的界限。在自然界的大部分形是有機(jī)形,它是柔和的、輕松的、曲線性的和無規(guī)律的。在人的世界中最普通的形是有機(jī)形、生硬的、刻板的、有規(guī)律的,而且常常是長方形的。總而言之,形這個(gè)詞表示了人眼感覺到的客觀事物的外部形態(tài),所以又稱為視覺形。另外,光與色彩也是繪畫藝術(shù)最主要的造型因素。點(diǎn)、線、形、光、色,作為繪畫藝術(shù)的構(gòu)成要素是相輔相成和不可分割的。在繪畫實(shí)踐過程中任何顧此失彼的表現(xiàn)方式都會(huì)有損于整體美。
篇4
關(guān)鍵詞: 語言; 藝術(shù); 交流
中圖分類號(hào): G62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009-8631(2012)07-0142-01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藝術(shù)首先包括談話的藝術(shù)”。因此,教師的育人、教學(xué)效果都離不開語言的智慧藝術(shù)。
一、語言力求生動(dòng)有趣
在我看來,作為一個(gè)教師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說話,要練習(xí)自己的口才。口才是一個(gè)人最大的資本。一個(gè)教師,即使做不到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最起碼要讓我們的語言生動(dòng)有趣,學(xué)生才會(huì)喜歡我們的課。一個(gè)說話沒有標(biāo)點(diǎn)、沒有抑揚(yáng)頓挫、不懂激趣的老師,縱有再高深的知識(shí),也很難讓學(xué)生喜歡聽你的課。所以要想做一名出色的老師,就要想法設(shè)法錘煉自己的語言,力求生動(dòng)幽默,激發(fā)起學(xué)生的興趣。
傳說清朝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有個(gè)遠(yuǎn)房親戚,他去參加鄉(xiāng)試,由于不學(xué)無術(shù),試卷到手卻什么也不會(huì),最后到交卷的時(shí)候沒轍了,就在試卷末尾寫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我是李鴻章大人的親妻”,可是他不會(huì)寫“親戚”的“戚”竟寫成了“妻子”的“妻”。這位主考官就相當(dāng)?shù)挠哪悴滤趺礃优牡模克肆鶄€(gè)字“所以我不敢娶”,他將錯(cuò)就錯(cuò),把錄取的“取”寫成娶妻的“娶”。大家想一想,在我們批閱學(xué)生的日記和作文時(shí),是不是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你又是怎樣批改的呢?有沒有讓人過目不忘的批語呢?
教育家孔子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xué)生在參與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如果能夠達(dá)到樂此不疲的境地,就歸功于教師語言趣味性。教師在引導(dǎo)學(xué)生參與語文學(xué)習(xí)過程中,如果能夠用妙趣橫生的語言激發(fā)他們,讓學(xué)習(xí)的全程活動(dòng)生動(dòng)活潑,必然能夠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效率和教學(xué)效率。教學(xué)語言的首要前提是動(dòng)情,然后有趣。趣味性的語言是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積極性的一個(gè)重要因素。
教師的教學(xué)語言不僅要講究藝術(shù),更要注意說話技巧。在進(jìn)行教學(xué)活動(dòng)時(shí),要注意聲調(diào)的變化,發(fā)音輕重,速度快慢,抑揚(yáng)頓挫,起伏跌宕等都要有講究。同時(shí)還要根據(jù)教材文本內(nèi)容的主次,詳略,難易程度不同,確定自己相適應(yīng)的語速語調(diào)變化,力爭(zhēng)教師的教學(xué)語言和教學(xué)內(nèi)容和諧,與教學(xué)過程和諧。避免貧乏、呆板、干癟、枯燥的無色語言,忌諱表達(dá)含糊,闡述不明,含混不清,半吞半吐,或者具有語法錯(cuò)誤、邏輯錯(cuò)誤的毛病語言、無效語言,那樣會(huì)影響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興趣。
二、語言要純潔、文明、健康
語言純潔就是要講普通話,要使用規(guī)范化的語言,不夾雜方言土語,不生編硬造誰也不懂的詞匯,不濫用縮略語和外來語,語言文明,就是用語要文雅、優(yōu)美,語調(diào)要和諧、悅耳、語氣要親切、和藹,使學(xué)生聞后能夠產(chǎn)生愉,樂于接受師訓(xùn)和教誨,語言健康,就是在使用語言時(shí),要切忌一切低級(jí)庸俗,粗魯無禮的污言穢語,特別是在批評(píng)教育學(xué)生的不良行為時(shí),切忌使用侮辱性的語言去訓(xùn)斥和辱罵學(xué)生,更不能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去諷刺、挖苦和嘲弄學(xué)生,這不僅不利于學(xué)生改正錯(cuò)誤,而且會(huì)傷害學(xué)生的自尊心,給學(xué)生的心靈留下長久的傷痕,影響學(xué)生的成長和發(fā)展,教師的語言行為對(duì)學(xué)生的道德品質(zhì)修養(yǎng)和審美修養(yǎng)產(chǎn)生極大影響,因此,要啟迪學(xué)生的心靈,陶冶學(xué)生的情操,教師就要以醇美的語言去觸動(dòng)學(xué)生的心弦,給學(xué)生以美的享受,使其形成純潔文明健康的心靈世界。
三、語言要準(zhǔn)確、鮮明、簡(jiǎn)煉
所謂準(zhǔn)確,就是要觀點(diǎn)明確,語言清晰,發(fā)音標(biāo)準(zhǔn),遣詞得當(dāng),造句符合文法,推理合乎邏輯,用語具有專業(yè)性和學(xué)術(shù)語,教師的語言如不準(zhǔn)確,詞不達(dá)意,言不傳情,語言不連貫,缺乏邏輯性,層次性,學(xué)生聽起來就倒不得要領(lǐng),就會(huì)給教育和教學(xué)信息的傳遞帶來障礙,所謂鮮明,是指語言要褒貶分明,飽含真情實(shí)感,愛什么、恨什么、贊揚(yáng)什么、反對(duì)什么、涇渭分明,所謂間煉,是指語言簡(jiǎn)潔明快,精辟透徹,言簡(jiǎn)意賅,論述簡(jiǎn)明扼要,提剛挈領(lǐng),分析絲絲入扣,見解深刻獨(dú)到,令人耳目一新,這樣的語言才會(huì)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如細(xì)雨般流入學(xué)生的心菲,同時(shí)把美好的思想情感、知識(shí)一同輸入學(xué)生的心靈。
四、教師語言要熱情、誠懇、富于激勵(lì)性,飽含親和力
語言作為一種感人的力量,它的真正的美,是離不開言辭的熱情、誠懇、富于激勵(lì)性,教師的語言一旦脫離了自己的真情實(shí)感,只講“官話”,“套話”,言不由衷,毫無個(gè)人的感彩,那他縱有滿腹經(jīng)綸,辭藻華麗,聲音動(dòng)聽,也會(huì)失去激動(dòng)人心的教育力量,因此,教師一定要努力把活生生的靈感和思想貫徹到自己的話語中去,于漪:“語言要做到優(yōu)美生動(dòng),除了知識(shí)素養(yǎng)、語言技巧之外,還必須傾注充沛,真摯的感情,情于中而言溢于表,只有對(duì)所教學(xué)科,所教對(duì)象,傾注滿腔熱情,教學(xué)語言才能顯示其生命力,熠熠放光彩,打動(dòng)學(xué)生心,使學(xué)生產(chǎn)生強(qiáng)列的共鳴,受到強(qiáng)列的感染。”
教師語言充沛的感彩,來源于教師科學(xué)的世界觀、人生觀,來源于教師對(duì)教育事業(yè)的無限熱愛,對(duì)科學(xué)文化知識(shí)的強(qiáng)烈渴求和對(duì)學(xué)生的赤誠之愛,只有具備了這些知識(shí),教師的語言才能時(shí)如和煦春風(fēng),吹進(jìn)心扉,時(shí)如滔滔激流,感人肺腑,時(shí)如春雨菲菲,沁人心田,時(shí)如長法東去,催人奮進(jìn),富于激勵(lì)性,更是教師語言特色,在教育和教學(xué)中,表現(xiàn)好的學(xué)生期望得到教師的表揚(yáng)和鼓勵(lì),有了過錯(cuò)的學(xué)生則害怕教師的挖苦和冷落,這就需要教師多使用激勵(lì)性語言,該表揚(yáng)的,就實(shí)事求是地予以表揚(yáng),并提出新的期望,鼓勵(lì)其向更高目標(biāo)奮進(jìn),該批評(píng)的,則要注意分寸,動(dòng)這以情,曉之以理,通過批評(píng)鼓勵(lì)學(xué)生上進(jìn),這樣,才能充分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積極性,提高教學(xué)效果。
五、語言要含蓄,幽默富于啟發(fā)性
在教育過程中,干癟貧乏的語言,毫無色彩的詞句,學(xué)生聽了就會(huì)覺得乏味,提不起興致,激不起靈感,也就不能很好地啟迪他們的智慧,震撼他們的心靈,相反,讓學(xué)生置身于語言美好環(huán)境和氛圍之中,學(xué)生就會(huì)感到心情愉快,興味盎然,氣氛活躍,思維敏捷,就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和教學(xué)效果。
六、語言要具有激勵(lì)性
篇5
一、真實(shí)坦誠
廣告必須講究語言的真實(shí)性,切忌名不符實(shí),給人以浮夸的感覺。這一點(diǎn)是廣告制作的前提和基礎(chǔ),千萬馬虎不得。如果一則廣告胡說一通,吹得天花亂墜,給消費(fèi)者許下種種承諾,表面看上去似乎很吸引人,可實(shí)際上,它容易給消費(fèi)者一種懷疑的心理。而一旦這些所謂的承諾不能一一兌現(xiàn),玩弄文字游戲的伎倆曝光后,無疑會(huì)損害自己企業(yè)和產(chǎn)品的聲譽(yù)。因此,廣告的語言要力求做到真實(shí),是怎么樣就怎么樣,以誠相見,不怕說出缺點(diǎn)而取得成功的廣告不勝枚舉。日本的一個(gè)鐘表商推銷一種新型手表,收效甚微,一度陷入窘境,后來他在廣告語言上痛下功夫,寫下了這么一句:“這種手表走時(shí)不太準(zhǔn)確,一晝夜會(huì)慢24分。”從此,一向被人冷眼相等的手表反而供不應(yīng)求了。一家作風(fēng)老實(shí)的營造公司以其務(wù)實(shí)的“工程不嫌小,太大吃不消”的廣告而獲得了良好的聲譽(yù),生意異常興隆。以上這些廣告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在揭自己的短,而實(shí)際上是宣傳了自己產(chǎn)品的真實(shí)程度,它雖然沒有那種掛羊頭買狗肉的廣告詞藻來得華麗,但它能促使消費(fèi)者產(chǎn)生一種信任感,從而最終贏得市場(chǎng)。
廣告用語如果能誠心誠意替消費(fèi)者著想,就能引起消費(fèi)者心理的共鳴,從而贏得廣大消費(fèi)者。日本有家小吃店,門前廣告牌沒寫什么“味美價(jià)廉”之類的話,而寫著“請(qǐng)到這里來用餐吧!否則你我都要挨餓了”。這坦誠而又有趣的語言吸引了顧客,使得小店生意興隆,門庭若市。有一家小商店,無論是商品的花色品種、價(jià)格、還是門面的大小、裝潢、衛(wèi)生狀況及所處位置等條件,都不比其他鄰近的商店出色,然而它的生意卻比其他商店興隆。其奧妙竟在該店店門的一副對(duì)聯(lián):“童叟無欺,人品重于商品;貨真價(jià)實(shí),賣貨不賣良心”。誠招天下客,這副對(duì)聯(lián)突出了一個(gè)“誠”字,體現(xiàn)了該店以誠待人的服務(wù)宗旨,加上踏實(shí)的經(jīng)營作風(fēng),自然贏得了遠(yuǎn)近顧客,生意也就自然興隆了。
“將你心換我心”,堅(jiān)持以真實(shí)為廣告前提。語言坦誠,處處為消費(fèi)者著想,從心靈深處征服消費(fèi)者的廣告語言,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二、簡(jiǎn)潔明快
廣告應(yīng)該講究語言的簡(jiǎn)潔明快,切忌拖泥帶水,否則不容易讓消費(fèi)者記住,甚至?xí)顾麄兎锤校a(chǎn)生抵觸情緒。心理學(xué)家認(rèn)為,一個(gè)人的記憶容量是有限的,過多的內(nèi)容,特別是抽象、枯燥的內(nèi)容不易被記住。因此,廣告用詞要特別注重精煉簡(jiǎn)潔,重點(diǎn)突出。獲國際博覽會(huì)金獎(jiǎng)的中意電冰箱,其廣告詞語十分簡(jiǎn)練:“中意冰箱,人人中意”。臺(tái)灣一家經(jīng)營礦泉水的公司,其廣告為“口服,心服”,語意雙關(guān),生動(dòng)簡(jiǎn)潔,堪稱一絕。獲全國銷量第一的威力洗衣機(jī),其廣告用語也十分簡(jiǎn)潔,凡電視觀眾,無人不曉“威力威力,夠威夠力”。“出手不凡鉆石表”,這一條廣告字?jǐn)?shù)則更少,只有七個(gè)字,既把“手”與“表”聯(lián)系起來,又把“鉆石”與“不凡”聯(lián)系起來,確實(shí)收到簡(jiǎn)練明快的效果。以上這些廣告的精煉,以少勝多,避免了文字的繁瑣。從廣告語言內(nèi)容的容量來看,也不允許其文字過多,過多反而會(huì)弄巧成拙,產(chǎn)生一種消極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則成功的廣告是與它廣告語的簡(jiǎn)潔明快分不開的,簡(jiǎn)潔明快是優(yōu)秀廣告語言的根本。
三、優(yōu)美動(dòng)人
好的廣告詞,其實(shí)就是一句發(fā)人深省的格言,一首耐人尋味的詩歌,一幅恬靜優(yōu)美的圖畫。優(yōu)美動(dòng)人的廣告詞,讓消費(fèi)者沉醉于情感的空間,遨游在溫馨的世界,廣告宣傳的目的當(dāng)然為了介紹產(chǎn)品,使產(chǎn)品進(jìn)入尋常百姓家。但物極必反,有時(shí)企業(yè)越是賣勁地為產(chǎn)品涂脂抹粉,消費(fèi)者越是不搭理,在這種情況下,一則帶有感彩的廣告往往能打動(dòng)消費(fèi)者的心,有創(chuàng)意的廣告設(shè)計(jì)家著意于用情絲去撥動(dòng)消費(fèi)者的情感心弦,產(chǎn)生共鳴效應(yīng),讓消費(fèi)者沉醉于甜甜的柔情之中,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它。
某娛樂中心廣告:“時(shí)光不復(fù)倒流,雅趣可以倒回,溫馨的世界將與您的記憶永恒”。如同情真意濃的散文詩,令人心馳神往。日本有一種乳酸飲料的廣告詞是“初戀的味道”,簡(jiǎn)短的五個(gè)字,伴隨著乳酸飲料的味道,把消費(fèi)者帶入了初戀時(shí)的甜蜜時(shí)光。“威力洗衣機(jī),獻(xiàn)給母親的愛”,帶給你一個(gè)溫馨親切的故事。臺(tái)灣酸梅汁廣告:“小別意酸酸,歡聚心甜甜”,都帶給了消費(fèi)者無盡聯(lián)想的空間,不愧為廣告語中的佳句。服裝廣告“不要太瀟灑”,一句甜甜的嗔怪,似與你柔聲細(xì)語,把你帶入了往日的溫馨。“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給了你不盡遐想的空間。
篇6
長安求仕不利期
身在生機(jī)勃發(fā)的大唐盛世,孟浩然也對(duì)社會(huì)對(duì)人生懷有積極的抱負(fù)和理想,曾到長安應(yīng)舉,并在《長安早春》中抒發(fā)及第后的歡喜,然而事與愿違。落第之后他不僅沒有立即返回家鄉(xiāng)反而選擇留在長安等待新的機(jī)會(huì),三載過去也終無結(jié)果。但他寫下了《歲晚歸南山》《留別王維》等不朽名篇。《歲晚歸南山》北闋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發(fā)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這是一首困頓失意之作,在“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嘆息里可以體會(huì)出孟浩然的獨(dú)特個(gè)性:感嘆自己是因?yàn)椤安徊拧倍姉売诿髦鳌L迫藢?duì)人生窮通的思考談得最多的是“時(shí)”“才”“命”,沒有對(duì)自己的才華失去信心的他此刻沒有傷時(shí)嘆命,只把失意歸為“不才”足見他的胸襟和氣度。“多病故人疏”一句既是作者對(duì)于得不到薦舉的牢騷話也表達(dá)一種與世疏闊的情懷。本詩前四句語勢(shì)陡健,后四句轉(zhuǎn)入回味深長之筆。清人朱之荊稱:“結(jié)句是寂寥之甚,然只寫景,不說寂寥,含蓄有味。”(《增訂唐詩摘抄》)總體來看,這首詩抒發(fā)了作者進(jìn)仕無門的窮途失意之悲,但語言溫厚,語意沒有流于狹隘的怨刺,顯示出盛唐士人慷慨磊落的精神風(fēng)貌。經(jīng)過了仕途磨練的孟浩然此時(shí)的詩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雖無太大變化,但語言更加高妙,詩作內(nèi)涵更加深厚,反映的精神面貌更加健朗。
漫游與短暫入幕期
長安無意而歸家的孟浩然在家中閑居一年便再次離家,先北上洛陽后南下吳越,游歷山水排解心中不快之意。吳越的青山碧水陶冶了他的心胸,使他對(duì)隱居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放棄功名的誘惑,在家園里保持人格的純潔。此時(shí)的詩作也無不呈現(xiàn)出清曠的意境和高潔的品格。《早發(fā)漁浦潭》東旭早光芒,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拔。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飲水畏驚猿,祭魚時(shí)見獺。舟行自無悶,況值晴景豁。這是作者溯浙江西上,行近富陽時(shí)的一個(gè)清晨,面對(duì)江潭晨景而創(chuàng)作的詩歌。夜色盡,曉色來,人間任何一個(gè)清晨的魅力都在于生機(jī)的復(fù)蘇。徒有生機(jī)尚不足言其妙,只有在倦怠中逐漸復(fù)蘇的生機(jī)才是清晨最動(dòng)人的地方。詩人在驚禽拔橈的聲響中感到了晨光初至的腳步,其中一個(gè)“暗”字用得最具功力。船家清晨起航,本無需遮掩,橈聲之暗,是詩人在清晨初醒時(shí),睡意尚未完全褪盡,聽起聲來不免朦朧斷續(xù)。一個(gè)生機(jī)盎然的清晨在詩人殘睡未消的朦朧中拉開序幕。接下來的詩句,將生機(jī)復(fù)蘇的晨意點(diǎn)染得更加開闊。在初日的照耀下,夜間的霧氣散開,詩人這才發(fā)現(xiàn)江面竟是如此開闊,一個(gè)“始”字,寫出了詩人在夜晚不知江面寬窄,而在清晨才發(fā)現(xiàn)的新鮮感受。接下來寫女子梳洗,猿猴飲水等更是在進(jìn)一步渲染清晨的勃勃生機(jī)。表面上看,詩的語言平淡,構(gòu)思也似乎沒有奇特之處,所以明代鐘惺曾說:“浩然之詩常為淺薄一路人藏拙。”(《唐詩歸》)但詩出古體,并且都押仄聲韻,又運(yùn)用典故,就使詩在平淡中具有了高雅脫俗的品格。林庚先生在《唐詩綜論》中說:“盛唐氣象最突出的特點(diǎn)就是朝氣蓬勃,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這首詩正是一個(gè)最生動(dòng)的代表,平淡的語言卻能表現(xiàn)出無盡的生機(jī),足見詩人才力之高。
回鄉(xiāng)歸隱期
從王維在《送孟六歸襄陽》的歸勸中以及孟詩《留別王維》的內(nèi)容中都可以看出仕途的無意促成了他回鄉(xiāng)歸隱。而他的隱居絕非有意避世,只是一種“適性”的表現(xiàn)。“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夜歸鹿門歌》就是詩人向往恬淡,高雅世外生活最好的寫照。《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chǎng)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這是家喻戶曉的一個(gè)作品,詩中滿是濃郁的田家氣息,詩人和友人賓主歡洽,充滿爽朗高雅的情趣。“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兩句運(yùn)用了五言律詩的“二二一”句式,同時(shí)將“綠樹”、“青山”放在句首,而結(jié)尾的“合”、“斜”帶有動(dòng)詞性,這就不僅僅是描寫,而仿佛綠樹的環(huán)繞青山的橫斜,都是出于“綠樹”、“青山”的主動(dòng)情意。詩的后半部刻畫了賓主高雅的情趣,詩人和故人雖然說的是桑麻之事的農(nóng)家語,但使人不覺柴米油鹽的瑣碎,只覺恬然快樂。結(jié)尾重陽賞菊的相約進(jìn)一步顯露了詩人與友人的高雅意趣。一個(gè)“還”字說出了詩人的戀戀不舍,這種留戀又以極親切自然的態(tài)度流露,沒有故作高雅的意味。而末句用得最妙的是“就”字,清人朱之荊云:“就”字百思不到,若用“看”字,便無味矣。(《增訂唐詩摘抄》)究其原因,一個(gè)“就”字寫出了詩人對(duì)的喜愛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親切感情,不是故作名士風(fēng)度,這與詩中恬淡融洽的田園風(fēng)情十分協(xié)調(diào)。此時(shí)的孟浩然正在家鄉(xiāng)鹿門安享寧靜高潔的塵外生活,詩作的語言越發(fā)歸于典雅恬淡,詩意也越發(fā)清曠、淡然。
結(jié)語
篇7
關(guān)鍵詞:英語教師,語言,藝術(shù)
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也是人類思維和文化的載體之一。教學(xué)中,語言的交流在學(xué)生認(rèn)知發(fā)展的過程中起著非常特殊的作用。因?yàn)榻處煵粌H僅通過語言來傳遞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有目的地影響學(xué)生的認(rèn)知過程,促進(jìn)和提高學(xué)生進(jìn)行接受教育的質(zhì)量。課堂教學(xué)語言的藝術(shù)美,能增強(qiáng)學(xué)生積極參與學(xué)習(xí)活動(dòng)的意識(shí),提高學(xué)習(xí)興趣、領(lǐng)略成功的喜悅, 在融洽的教學(xué)氛圍中得到全面的發(fā)展,取得教與學(xué)的最佳效果。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教師的教學(xué)語言修養(yǎng)在極大程度上決定著學(xué)生在課堂上腦力勞動(dòng)的效率。”對(duì)于英語這一門語言學(xué)科來說,幾乎所有英語教師的母語是漢語,因此,教學(xué)語言對(duì)于英語教師來說至關(guān)重要。那么英語教師在語言藝術(shù)上應(yīng)注意什么問題呢?
一、語言要規(guī)范,簡(jiǎn)練,富于邏輯性和美感
英語教師的語言是一種專業(yè)語言,要在簡(jiǎn)明、準(zhǔn)確、形象、生動(dòng)、幽默、風(fēng)趣和韻律、節(jié)奏等方面下工夫。講課的藝術(shù)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為語言的藝術(shù)。要提高課堂教學(xué)的藝術(shù)性就需精心修煉課堂語言的藝術(shù)特色,像一位教師在進(jìn)行課堂提問后,讓回答一對(duì)一錯(cuò)的兩位同學(xué)坐下時(shí),分別用了“Sit down, please.”和“Sit down.”兩句口語,一詞之差含義不同,恰到好處,反映出該教師課堂語言的精練和準(zhǔn)確。
此外,英語教師必須堅(jiān)持用英語教學(xué),讓學(xué)生用英語來想英語。同時(shí),相應(yīng)的“body language”(體態(tài)語) 要盡可能符合英美人的習(xí)慣,這種"仿真",使學(xué)生產(chǎn)生新奇感,并置身于英語語言環(huán)境之中,以滿足學(xué)生語言美之心理需求。英語教學(xué)的語言不僅要具有與其他學(xué)科教學(xué)語言一樣的形象性與確鑿性,還應(yīng)追求語言的韻律感、幽默感和新鮮感。比如學(xué)點(diǎn)洋腔洋調(diào),注重語意與語境、語調(diào)與語速的配合。自然規(guī)范的語音、語調(diào),將為有效的口語交際打下良好的基礎(chǔ)。當(dāng)教師在課堂上講英語時(shí),具有節(jié)奏感的語調(diào),聽起來像外國人特有的那種韻味會(huì)讓學(xué)生從聽覺上感受到語言的另一種美。學(xué)生在欣賞中獲得了令人陶醉的美感,就會(huì)增強(qiáng)說英語的欲望。
二、語言要富有情感
“若要使人心動(dòng),必先使已動(dòng)情。”在教學(xué)中,師生的情感交流必不可少。教師要說服學(xué)生、感化學(xué)生,必須講究語言的豐富情感性,把握好語詞的情感色彩。
語言的情感性有一定的技術(shù)參數(shù)。心理學(xué)家發(fā)現(xiàn)有的情感因語詞刺激發(fā)生波動(dòng),造成皮膚血管收縮和汗腺的變化,導(dǎo)致皮膚導(dǎo)電率的相應(yīng)變化。皮膚電反射強(qiáng)度即可說明語言符號(hào)的情感性效應(yīng)的大小。由此證明,教師的語言藝術(shù)的情感性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教師滿懷情意,單調(diào)的教學(xué)就能讀得有聲有色,學(xué)生聽到的就不是枯燥乏味的單詞、句子,而似乎是種深情的訴說。
英語教師語言的情感性一般表現(xiàn)在語調(diào)的平、升、降、曲四方面。“平”表示淡漠、莊嚴(yán)、悲痛和沉郁的感情;“升”,表示疑問、憤怒、驚異、召喚等語氣;“降”,表達(dá)堅(jiān)定、感嘆、祝愿、祈求等情緒;“曲”,表示幽默、懷疑、調(diào)侃和諷刺和語意。
此外,英語教師語言情感還體現(xiàn)在語氣的變化上,通過不同的聲音和氣息可以表達(dá)不同的語言。如“氣徐聲柔”,給學(xué)生以溫暖感;“氣滿聲高”給學(xué)生以喜悅感和激勵(lì)感;“氣短聲促”給學(xué)生以緊迫感。
三、語言要有激勵(lì)性
激勵(lì)性語言簡(jiǎn)潔明快,生動(dòng)形象,感染力強(qiáng),針對(duì)明顯。教學(xué)中常常發(fā)現(xiàn),當(dāng)學(xué)生答不出問題時(shí),不少教師不是搭橋引導(dǎo),而是另請(qǐng)高明;或者“恨鐵不成鋼”,語言中帶有批評(píng),語調(diào)上帶有責(zé)備,情緒中帶有煩躁等。這使學(xué)生遭受失敗的體驗(yàn),從而情緒低落,課堂教學(xué)氣氛沉悶,未能很好地參與教學(xué)過程中。心理學(xué)家贊可夫說:“教學(xué)法一旦觸及到學(xué)生的情緒和意志領(lǐng)域,觸及到學(xué)生的精神需要,這種教學(xué)法就能發(fā)揮高度有效的作用”。亞里士多德也說:“教學(xué)的藝術(shù)不在于傳播知識(shí),而在于激勵(lì),喚醒和鼓舞。”所以,教師要在課堂語言中善于給學(xué)生打高分,激勵(lì)他們的學(xué)習(xí)熱情,激發(fā)他們的斗志。
英語教師語言的激勵(lì)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對(duì)比激勵(lì),贊美激勵(lì)和夸張激勵(lì)等方面。人比人,激勵(lì)人。教師常在班上倡導(dǎo)比、學(xué)、趕、超的學(xué)風(fēng),比字當(dāng)頭,極富鼓動(dòng)性,它能使學(xué)生心底的激情噴發(fā)而出,使一些紛繁難題峰回路轉(zhuǎn)。此外,也可以用一些成功人士,如俞敏洪,馬云等學(xué)英語的例子來激勵(lì)學(xué)生。這種"比"就像一桿路標(biāo),激勵(lì)引導(dǎo)學(xué)生朝著目標(biāo)前進(jìn)。除了運(yùn)用對(duì)比手法來激勵(lì)學(xué)生外,對(duì)學(xué)生的贊美也是一種很大的激勵(lì)。曾經(jīng)我的班里有一個(gè)學(xué)生英語成績(jī)很差,對(duì)英語也很厭惡,但是他的英語書法特別漂亮。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說“XXX’s handwriting is very beautiful! We should learn from him.”并把他的作業(yè)展示給全班同學(xué)。沒想到從那以后,他對(duì)英語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開始認(rèn)真聽課學(xué)習(xí),成績(jī)也一點(diǎn)點(diǎn)變好。從那件事上我意識(shí)到:教師的哪怕是一點(diǎn)點(diǎn)的贊美表揚(yáng)都很可能成為激勵(lì)學(xué)生上進(jìn)的巨大動(dòng)力。此外,在適當(dāng)?shù)那闆r下,教師還可以有意識(shí)地用超出客觀事實(shí)的說法來表達(dá)、突出、強(qiáng)調(diào)某種思想,從而激勵(lì)學(xué)生在短時(shí)間內(nèi)做出迅速的反應(yīng)。
語言的魅力無處不在。在進(jìn)行新課程改革的今天,在新的教育天地里,我們每個(gè)教師都應(yīng)努力修煉自己的語言藝術(shù),讓其具備濃厚的美育意識(shí),創(chuàng)設(shè)多姿多彩的美育情境,把大自然中的美、生活中的美、語言中的美、教材教法中的美化作陽光,變成雨露,深深地滲透到學(xué)生心里,讓學(xué)生在英語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感悟美、賞析美、體驗(yàn)美,進(jìn)而創(chuàng)造出美,寓教于樂,寓教于美。
參考文獻(xiàn):
[1]王曾選,1987:《中學(xué)英語教學(xué)法[M]》,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
篇8
關(guān)鍵詞:繪畫藝術(shù) 語言形態(tài)
繪畫是運(yùn)用線條、色彩、造型、構(gòu)圖和一定的形式進(jìn)行搭配組合而成,完成傳達(dá)精神內(nèi)涵的任務(wù)。繪畫作品的主題有表現(xiàn)形式的作用、有作品內(nèi)容和作者精神的體現(xiàn)。繪畫的內(nèi)容和形式,密切相連,形式是觀念、情感和技術(shù)的體現(xiàn)。繪畫語言包含技巧、形式和內(nèi)容的有機(jī)融合,它是相互制約和滲透的有機(jī)整體,美術(shù)工作者的感情是靠繪畫語言來表現(xiàn),這種語言的運(yùn)用,是根據(jù)美術(shù)工作者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來彰顯出藝術(shù)水準(zhǔn)。
美術(shù)工作者對(duì)繪畫語言運(yùn)用不同,而產(chǎn)生多姿多彩、風(fēng)格各異的繪畫作品。在歐洲,自達(dá)?芬奇開始,就形成了傳統(tǒng)的寫實(shí)主義畫法,美術(shù)工作者通過研究光線揭示形式的方式,發(fā)展和運(yùn)用直線透視法,來獲得景深幻覺的規(guī)則,通過研究人體解剖,給作品注入全新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感。他們的作品弘揚(yáng)了人文主義精神,在繪畫的總體風(fēng)格上,姿勢(shì)華麗、典雅、宏偉、和諧,寫實(shí)技術(shù)嫻熟,形成了“古典主義”畫風(fēng)。
區(qū)別與古典畫風(fēng)的印象派畫家們,用光、色描繪自然和抒發(fā)自己的感情,他們擅長表現(xiàn)陽光和色彩,對(duì)瞬息萬變的光色變化非常敏感,注重色彩的表現(xiàn),美術(shù)家運(yùn)用分色技術(shù),將色彩合理組合,使畫面變得明快絢麗。印象派畫家不再因襲傳統(tǒng)的畫法,其作品詮釋了光色的功用形。在色彩的表現(xiàn)里,印象派畫家完美地表現(xiàn)了一種抒情風(fēng)格,他們很好地運(yùn)用了繪畫語言,給作品注入了抒情性外表美。在西畫造型過程中,主要使用形體和色彩語言,即便沒有線的使用,其造型行為不會(huì)受到重大影響,依然能構(gòu)架繪畫形態(tài);即便使用線界定輪廓,如在輪廓外輔上調(diào)子,就會(huì)成為立體畫面。因此,西畫中線是作為表現(xiàn)形體的特殊手段。
各類畫派的美術(shù)家,都借助語言形式來體現(xiàn)作品的情感。繪畫語言的不同運(yùn)用,產(chǎn)生了不同風(fēng)格的繪畫作品。中國畫崇尚文、意、趣,是通過筆墨技巧來體現(xiàn)的。筆墨本身是形式的因素,有引起形象的聯(lián)想和意趣的感受功能。正如藍(lán)色和紅色能引起冷暖的視覺感受一樣,在宣紙上粗糙的筆墨,能畫出老人蒼老的視覺感受;水分飽滿、行筆流暢的筆跡,給人春天般滋潤的視覺感受;流利靈活用筆,能喚起灑脫歡暢的聯(lián)想;快速多變的用筆,能令人有蛇龍飛舞的遐想。這些筆墨形式,是美術(shù)工作者獨(dú)特風(fēng)格在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表現(xiàn)。美術(shù)家們通過構(gòu)思構(gòu)圖,合理運(yùn)用筆墨虛實(shí),水韻、墨色和運(yùn)筆產(chǎn)生的肌理,形成有個(gè)性的繪畫語言。虛實(shí)的表現(xiàn),是美術(shù)工作者靈氣的表現(xiàn),是對(duì)畫理的悟性。畫要有筆墨,無筆墨就不成畫,筆墨技巧要與表現(xiàn)內(nèi)容有機(jī)的結(jié)合起來,才能創(chuàng)作出最佳作品。這種藝術(shù)法已成為中國獨(dú)有的繪畫語言。
繪畫語言在視覺方面由點(diǎn)、線、形、光、色彩要素構(gòu)成。“點(diǎn)”是最小的視覺實(shí)體,有探討視覺形式的作用。一個(gè)可視的點(diǎn)是一個(gè)吸引視覺注意力的小元素,點(diǎn)可以被表現(xiàn)出來和暗示,可以構(gòu)成一個(gè)情趣的中心,或一幅構(gòu)圖中被強(qiáng)調(diào)的部分,處在一個(gè)表面上的一個(gè)點(diǎn),好似屋子里的聲音一樣,使空間有了生機(jī)與活力。點(diǎn)可以解釋和代表一切。
“線”是描述點(diǎn)的運(yùn)動(dòng)軌跡,一個(gè)可視的行動(dòng)軌跡,一條線表現(xiàn)出劃線人的精神。一幅畫的筆觸,穿過風(fēng)景的一條蜿蜒的河流,被撕破的線的參差不齊的邊緣,一個(gè)草葉的曲線,每一條線好似每一位畫家充滿個(gè)性、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一樣,是獨(dú)具特色的。線是人們認(rèn)識(shí)和反映自然形態(tài)時(shí)最簡(jiǎn)明的表現(xiàn)形式,線有長短、粗細(xì)、曲直之分,有長度、寬度和方向上的不同,是連續(xù)不斷的或間斷的,粗的或細(xì)的,有規(guī)律的或無規(guī)律的,靜止的或運(yùn)動(dòng)的,直線的或曲線的,線是諸多形式不同的結(jié)合體。
在一個(gè)平面上,線能界定各種形狀,暗示體積或顯示所繪物體質(zhì)量的獨(dú)立元素。通過線條的組織來創(chuàng)造圖案、肌理,描繪陰影。線是闡明視覺形式的基本手段,是對(duì)目睹、感受和想象到的事物的一種速寫,線是在兩維空間表面的長度標(biāo)準(zhǔn),每一條線或物體邊緣都有它的表現(xiàn)特征,其表現(xiàn)形式在視覺交流中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國繪畫藝術(shù)中,線條的功用表現(xiàn)尤為突出,中國繪畫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富有骨氣韻味的線條取勝的,線條的運(yùn)用,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愈來愈富有含蓄性、表現(xiàn)性、象征性和抽象性。
“形”是一種被視為平面存在的形式,一種二維的空間區(qū)域,平面是一種剪影或陰影形式的外觀。當(dāng)一條線勾畫出一個(gè)區(qū)域,或當(dāng)一個(gè)面積表面顏色和肌質(zhì)發(fā)生變化時(shí),其面積與周圍的面積相分離,形便成了可視的存在。形分有機(jī)形和幾何形,二者間有明顯的界限。自然界的大部分形是有機(jī)形,是柔和、輕松、曲線性和無規(guī)律的。在人的世界中,最普通的形是有機(jī)形、生硬、刻板和有規(guī)律的。形表示了人眼感覺到的客觀事物的外部形態(tài),又稱視覺形。光與色彩也是繪畫藝術(shù)最主要的造型因素。點(diǎn)、線、形、光、色作為繪畫藝術(shù)的構(gòu)成要素是相輔相成的。
篇9
言意之辨的歷史變奏: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歷史基礎(chǔ)
言與意的關(guān)系,這是歷代文論爭(zhēng)辯的焦點(diǎn),這對(duì)關(guān)系也正是語言藝術(shù)的學(xué)科研究基礎(chǔ)。言以足志與言不盡意構(gòu)成了矛盾的雙方,相互推動(dòng)著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建立。
(一)“名實(shí)之爭(zhēng)”到“言意之辨”
為了探索言語的表情達(dá)意能力,中國思想界很早就掀起“名實(shí)之爭(zhēng)”,而在名實(shí)之爭(zhēng)提出之后,春秋戰(zhàn)國諸家論說不一,看法時(shí)有促進(jìn)。古人所謂“觀物取象,立象盡意,設(shè)象喻理,取象比類”。《易經(jīng)!系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意有矛盾,欲歸于一致,關(guān)鍵在于“立象”,《系辭上》假借孔子之名說,“圣人立象以盡意,設(shè)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而對(duì)于立象,則“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自此之后,因“言意之辨”而導(dǎo)致的“言以足志”與“言不盡意”一直成為中國語言學(xué)界討論言語表情達(dá)意能力的永恒主題。在卜辭中,“言”與“音”為一字,在先秦亦常通用。“言”,甲骨文中為口上加辛(薪),即口中所發(fā)出的叢雜的聲音。②從字源學(xué)上講,言在內(nèi)則為“意”。孟子說,“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色就是神色,即語言學(xué)上的體態(tài)語;聲就是有聲語言,在運(yùn)用語言上,語言存在不足,需要“體態(tài)語”進(jìn)行補(bǔ)充,二者兼具,則可以達(dá)到言達(dá)而意通。莊子則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語言可以表現(xiàn)事物的大略,而思想才可以把握事物的精微之處。到了魏晉時(shí)期,名實(shí)之爭(zhēng)進(jìn)一步深入,興起了“言意之辨”,并且最終將語言學(xué)與文學(xué)連接起來。三國時(shí)期魏國的荀粲認(rèn)為,“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yùn)而不出也。”這里的“言不盡意”,是指物象、語詞難以表達(dá)的微妙之處,如此說來,“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不能用言語表達(dá)的,王弼則從《周易!系辭上》出發(fā),認(rèn)為“盡意莫若象,盡象莫如言”,“言”是達(dá)意的手段,而非“意”之本身,所以在《周易略例•明象章》極力推崇“得意忘言”,他認(rèn)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當(dāng)然,將言意關(guān)系僅僅看做類似“魚”與“筌”的手段與目的的關(guān)系,失之妥當(dāng),語言僅僅是達(dá)意的一種手段嗎?如果得其“意”,則已忘其“言”,與“意”相比,“言”是次要的部分,而非根本,次要的部分如何能夠展示出根本的部分呢?所以從邏輯上就可以推演出“言不盡意”的觀點(diǎn),面對(duì)類似宇宙這樣的抽象事物直接就是“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真”,而對(duì)具體事物,則是“各有其義,未盡其極也”,盡管“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言下之意,“名”要基于此事物區(qū)別于彼事物的地方,“稱”則基于指稱該事物的主觀意圖,可見“名”難以概括此事物的全部,主觀的稱謂自然也不能窮盡該事物的內(nèi)蘊(yùn),所以基于言而致的“名”、“稱”自然在表達(dá)上就存在局限,那“言”自然就難以盡意。③從過程上看,無論所觀之“象”是一個(gè)抽象概念還是一個(gè)具體事物,心象都體現(xiàn)為一個(gè)具體意象。對(duì)于抽象的所觀之“象”,由心象到觀象的投射經(jīng)過了一個(gè)由“抽象”到“具體”的取象過程;而對(duì)于具體的所觀之“象”,則經(jīng)過了一個(gè)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過程。理論上的邏輯推演似乎很嚴(yán)密,但是西晉末年的歐陽建則冒天下之大不韙,寫了《言盡意論》,認(rèn)為存在的事物,并不以名、言而轉(zhuǎn)移,闡釋了名、言在辨別事物和交流思想中的作用:“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shí)不顯。鑒識(shí)顯而名品殊,言稱物而情志暢。”可見,“名”、“言”是辨別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必要條件,而“辨名”和“暢志”恰恰就是名、言自身本有的性能:“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fā)響應(yīng),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茍其不二,則無不盡。”物遷則名變,理變則言異,語詞的功能就在“因理而變”,語詞要適應(yīng)意思的變化而變化,雖然如此,似乎只能說明言意“不得相與為二”,尚未證明言如何能夠“盡意”,看來,歐陽建的論述并未充分證明,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言盡意論》有點(diǎn)牽強(qiáng),索性他直言“吾以為盡矣”,幾乎就變成了個(gè)人的一個(gè)主觀判斷。先秦圣哲不僅主張“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同時(shí)也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論斷,而魏晉時(shí)期的言意之辨,根本就在于討論言語究竟能否盡意,語言表達(dá)能力究竟可以達(dá)到何等程度。④所以陸機(jī)(261—303)擔(dān)心“意不稱物,文不逮意”⑤,力求意能稱物,文可逮意。原來歐陽建的名、物關(guān)系與言、理關(guān)系,至陸機(jī)這里則成為物、意、文三者的關(guān)系。相較之下,陸機(jī)的認(rèn)識(shí)更高出一籌。劉勰則將陸機(jī)的“物、意、文”改為“情、辭、事”,以此構(gòu)建整部《文心雕龍》的創(chuàng)造論框架,據(jù)此觀察言意之辨,其客觀的依據(jù)就是:語詞是否能夠盡意,還是難以盡意,需要根據(jù)語詞所要表現(xiàn)的對(duì)象的性質(zhì)而定。⑥劉勰曰:“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狀辭可得喻其真。”⑦形而上,指的是無形之物,謂之“道”;形而下,指的是有形之物,謂之“器”,可見,言語形式對(duì)道和器的效能難以一致,道者,意義也,器者,對(duì)象也,神妙的“道”怎可描摹?最為精微的語言恐怕也難以得其妙處,而具象的“器”則易于描繪,運(yùn)用描寫的語言就可以呈現(xiàn)其真實(shí)面貌。⑧有形可見、有體可觸的東西,語言的效力明顯,無形可追的意義領(lǐng)域,言語的效能自然就大為弱化。推論至此,劉勰將“言意之辨”的討論總結(jié)為,面對(duì)“神道難摹”,語詞“不能追其極”,自然“言不盡意”,而對(duì)“形器易寫”,語詞才“可得喻其真”,自然也就“言以足志”。同樣一個(gè)問題,就看從哪個(gè)角度進(jìn)行認(rèn)識(shí)與觀照,這種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使得中國的理論思辨難以“片面得深刻”。所以后世仍然一直存在著言可盡意與言不盡意兩個(gè)派別。杜甫(712—770)主張的語詞能夠“毫發(fā)無遺憾”地表情達(dá)意,宋代歐陽修(1007—1073)從語言表達(dá)的角度論之道:“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胡奇光先生認(rèn)為,歐陽修此論,與“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相比,看到了“書不盡言之煩,言不盡意之委曲”,而與“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相比,又看到了“書盡其要,言盡其理”⑨,可謂二者優(yōu)點(diǎn)兼具,實(shí)現(xiàn)了“fairplay”。楊萬里(1127—1206)從語言效果的角度,領(lǐng)會(huì)“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實(shí)質(zhì):“圣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圣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不敢盡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言下之意,書不盡言與言不盡意是有意為了給人們留出想象的空間與意思上的空白,以便人們進(jìn)行填補(bǔ)。所以楊萬里將書不盡言與言不盡意理解為語言表達(dá)的特殊手段,能夠運(yùn)用“暗示”之法,激勵(lì)人們進(jìn)行深入思索。瑏瑠這些都成為“言意之辨”的不同變奏,“言意之辨”即語言符號(hào)效能的二重性。瑏瑡胡奇光先生認(rèn)為,由于語言是文學(xué)的第一要素,因此對(duì)于語言表情達(dá)意能力的不同觀點(diǎn),就使得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呈現(xiàn)出不同的表現(xiàn)風(fēng)格,主張言以足志即“言可盡意”的人,文學(xué)上重在“再現(xiàn)”(顯示),而強(qiáng)調(diào)“言不盡意”的人,文學(xué)上則重在“表現(xiàn)”(暗示)。瑏瑢莊子認(rèn)為,“言”只能表現(xiàn)“物之粗者”,而“意”才可以把握“物之精者”瑏瑣,語言的運(yùn)用,確實(shí)不應(yīng)該僅僅著眼于語言形式上的設(shè)計(jì),而應(yīng)隨意而變,正如《莊子!天道》所言:“語之所貴者,意也”,而不是如孔子(前551—前479)所說的那樣,“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魯迅(周樹人,1881—1936)在《漢文學(xué)史綱要》中提出了“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瑏瑤的觀點(diǎn),可見,作為語音的“言”,就是通過聲音現(xiàn)象表達(dá)人的心理活動(dòng),這就是“言”所表達(dá)的“意”,所以從造字法上看古文“意”字從言從心,到小篆才改為從音從心,但是表達(dá)的意義完全一致,這是傳統(tǒng)語言學(xué)之不同于現(xiàn)代語言學(xué)之處,或許也正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xué)價(jià)值之所在。
(二)“言意之辨”到語言效能的二重性
語言在表達(dá)作者寫作意圖時(shí)存在著語言本身的形式與所要表達(dá)內(nèi)容的關(guān)系的問題,根據(jù)作者不同的寫作喜好,語言形式千差萬別,然而在寫作意圖和表達(dá)效果上卻有著類似的目標(biāo)理想。孔子的辭達(dá)說可以作為我國散文語言原則的奠定瑏瑥。古語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的辭達(dá)說即要求文與言的“足”,修辭立其誠,因此語辭的表達(dá)應(yīng)該是真心實(shí)意,直抒胸臆,以情動(dòng)人,因此,辭達(dá)說奠定了語言表達(dá)的基調(diào),為后世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規(guī)定了準(zhǔn)則。到了文學(xué)自覺時(shí)期的魏晉六朝,言意之辨發(fā)展為語言效能的二重性。言能否盡意,沈德潛《說詩晬語》里說:“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托物類以形之。郁舒,天機(jī)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復(fù)唱嘆,而中藏之飲歡愉慘戚,隱隱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這些文字旨在說明語言的二重性,語言對(duì)“道”與“器”有著不同的效能,神妙的“道”難以摹寫,即使用精微的語辭也不能窮盡它的妙處,而具體的“器”就易于描繪,運(yùn)用廓大的語辭可以顯現(xiàn)它的真實(shí)面貌。這樣說來,越到有形可見、有體可觸的范圍,語言的效能就越大,越到無聲無色或未成形的境域,語言的效能也越小。瑏瑦語言在表達(dá)微妙的感情時(shí)與表達(dá)具體的事物時(shí)所產(chǎn)生的不同效果,也說明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含蓄內(nèi)斂給語言表達(dá)帶來了影響。正如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是文人所追求的一種精神品質(zhì)和素養(yǎng),而多少年來卻很少有人能用語言準(zhǔn)確統(tǒng)一地定義這樣一股存乎天地宇宙之間的氣。語言作為意義的載體,不管多么精妙絕倫都會(huì)對(duì)意義產(chǎn)生束縛和限制,葉燮曾說:“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言不盡意的原因還有一個(gè)就是情,感情到語言并不是線性的發(fā)展,而是由隱到顯的變化過程。言首先不能盡意,從動(dòng)態(tài)上看,轉(zhuǎn)化為有文字表達(dá)的意也發(fā)生變化,經(jīng)層層遞減,情由隱而顯,卻因顯而隱。當(dāng)專注于語言去發(fā)掘意義時(shí),這意義已經(jīng)與原初的不盡相同了。瑏瑧語言效能的二重性是一把鑰匙開啟了語言藝術(shù)的大門,為日后創(chuàng)作的文人提供了更廣闊的創(chuàng)作平臺(tái),同時(shí)也因?yàn)檎Z言的二重性,使得語言藝術(shù)的美有了更多的表現(xiàn)方式。中國古代語言藝術(shù)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古漢語的形式美之上的,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戲曲無不與語言形式有著重大的關(guān)系。從對(duì)偶、對(duì)稱到聲律、平仄,格律詞牌到戲曲創(chuàng)作中的各種規(guī)則,語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語言美的展現(xiàn)。對(duì)偶的產(chǎn)生,先要有對(duì)事物辯證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加上漢語本身具有便于組成偶句的性能。詩歌的聲律則是漢語四聲的藝術(shù)產(chǎn)物,創(chuàng)造了新的語言藝術(shù)形式之美。在詩歌中運(yùn)用的賦比興手法更是對(duì)于語言奧秘的新探索,同時(shí)也能更好地表現(xiàn)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形式美的追求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看法,新的表現(xiàn)手法,說明在寫作中,作者們對(duì)于語言藝術(shù)的孜孜追求,以求用更多的形式從而更貼切地表現(xiàn)內(nèi)心的情感,讓讀者感同身受,同時(shí)也希望通過語言藝術(shù)來傳達(dá)他們的美學(xué)理論,來傳達(dá)他們心中的美。正因?yàn)槿绱颂圃姷囊繇嵑椭C、平仄相對(duì)才會(huì)如此朗朗上口傳唱千古,就算語音有所改變,可是今人仍然能感受它所傳達(dá)的意境,所以語言形式的美從最早的句式到語音、文體都在不斷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有著中國古代語言藝術(shù)獨(dú)特之處,是其理論基礎(chǔ)的重要組成部分。
多元信息的表達(dá):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目標(biāo)
創(chuàng)造多重信息的語言,成為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一大目標(biāo)。劉勰把“隱秀”視為語言藝術(shù)的精髓,到唐代,釋皎然說:“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簡(jiǎn)直可看作多重信息語言的界說。從語言運(yùn)用的事實(shí)看,不論是雙關(guān)、諧音、通感、復(fù)義等手法,還是比興、諷喻、指代、比擬、委婉、互文等手法,均有創(chuàng)造多重信息語言的效能。這多重信息的語言,實(shí)即“一中見多”的語言。瑏瑨詩歌是中國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一個(gè)重要體式,重在表達(dá)一種意境,表達(dá)詩人的一種情緒、理想和信念。司空?qǐng)D倡導(dǎo)的韻味說把詩歌所展現(xiàn)的韻外之致導(dǎo)入研究鑒賞的視角。文學(xué)語言追求的是詞外義,司空?qǐng)D倡導(dǎo)的“不著一字,盡得風(fēng)流”、“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即在強(qiáng)調(diào)語言的形式是為了表達(dá)的內(nèi)容,這一觀點(diǎn)是語言藝術(shù)的一大法寶,文字技巧并不是文人所追求的,因?yàn)檎嬲玫脑姼枋强床怀鑫淖旨记啥芷肺兜阶髡哒鎿吹那樾裕屛恼律倭巳斯せ暮圹E。司空?qǐng)D的《詩品》是一部詩歌的美學(xué)著作,講求語言藝術(shù)的辯證法,提出了詩歌的言外之致,引入了他對(duì)語言辯證法,揭示了形與神、有與無、濃與淡、熔與裁等文學(xué)范疇的辯證關(guān)系。可以說,詩歌很好地展現(xiàn)了語言的多重信息的特性,韻味的營造和意象的多指,都是作者寫作的目的,讓讀者把詩中所要表達(dá)的多重含義,投射到自身的人生軌跡中,從而得到慰藉。文章的韻味是不論詩歌還是別的文學(xué)體裁都在追求的目標(biāo),它揭示了語言藝術(shù)的追求并且也是審美和創(chuàng)作的準(zhǔn)則,讓人們更能把握作品的本質(zhì),讓作者所要表達(dá)的情志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元明清時(shí)期,文學(xué)成就漸漸以戲曲和小說為主,這一時(shí)期語言藝術(shù)有了新的變化。語言藝術(shù)從元明清開始了對(duì)人性的關(guān)注,開始發(fā)掘人的內(nèi)心世界,普通的市井百姓進(jìn)入了文人的創(chuàng)作視野,因此文學(xué)語言藝術(shù)也隨之發(fā)生了改變。文學(xué)體裁開始以更能表現(xiàn)人物性格和內(nèi)心活動(dòng)的戲曲及小說為主,戲曲的唱白給了文人更多的發(fā)揮空間,讓讀者可以體味人物細(xì)膩的心理活動(dòng),小說則以大篇幅和以故事情節(jié)為主的特征讓文人筆下的主人公更加鮮活,更具有層次性,給予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戲曲語言比結(jié)構(gòu)還要繁雜,有唱詞、賓白等各種舞臺(tái)專用語言,它具有詩歌語言的特點(diǎn),同時(shí)也有戲曲語言本身的特色,如本色、當(dāng)行、文采。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舞臺(tái)語言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的第一個(gè)總結(jié),制定了北曲用韻的標(biāo)準(zhǔn)與法則,著重提出了“作詞十法”:知韻、造語、用事、用字、入聲作平聲、陰陽、務(wù)頭、對(duì)偶、末句、定格。王驥德與李漁等人在周德清的基礎(chǔ)上更對(duì)戲曲語言的煉格、雅俗適度等戲曲語言藝術(shù)的準(zhǔn)則進(jìn)行了探究,使戲曲語言日趨成熟。小說作為一個(gè)新興文體出現(xiàn)在明清時(shí)期,讓人們眼前為之一亮。周秦時(shí)期已經(jīng)有了小說的雛形,即神話傳說,到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說,宋代的話本小說,語言上從文言文向白話文轉(zhuǎn)變。明末清初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金圣嘆對(duì)于小說的研究讓小說語言藝術(shù)達(dá)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他對(duì)《水滸傳》的點(diǎn)評(píng)給小說語言藝術(shù)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礎(chǔ)。金圣嘆認(rèn)為《水滸傳》的一個(gè)很大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把一百零八個(gè)人的性格都寫得各不相同,讓語言有了性格的特征,讓讀者從語言里感悟到這一百零八個(gè)英雄好漢各不相同的個(gè)性,為小說語言的性格化理論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語料分析。同時(shí),金圣嘆對(duì)于小說的排篇布局也提出了相關(guān)的理論見解,他認(rèn)為《水滸傳》中的人物出場(chǎng)、人物傳之間的銜接、事件的發(fā)展等部法都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色,是小說布局中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這樣的部法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凸顯。在章法上金圣嘆認(rèn)為在開展情節(jié)時(shí)要注意起承轉(zhuǎn)合,一部分要服務(wù)于情節(jié),一部分要服務(wù)于人物。而在描寫人物的章法上,有正比、反比、映襯等類型,把人物寫得盡量飽滿有生命力。我國小說的最高峰即曹雪芹的《紅樓夢(mèng)》,這部小說對(duì)人物的語言藝術(shù)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里面的人物如林黛玉、賈寶玉、王熙鳳等人都是中國小說人物史上的重要形象。在《紅樓夢(mèng)》中人物開始從原先的單面單線到多面多線條,壞人也有可愛的一面,而好人也有讓人接受不了的缺點(diǎn),開始了圓形人物的新創(chuàng)作手法。脂硯齋作為《紅樓夢(mèng)》最早的評(píng)論家,從語言和生活的關(guān)系入手來評(píng)論,就抓住了研究的根本。小說是來源于生活的,只有是生活的才有了語言藝術(shù)所追求的真,才能讓看的人產(chǎn)生共鳴。現(xiàn)實(shí)生活是小說的來源,小說里的主人公是現(xiàn)實(shí)中人的投影,所以對(duì)于小說評(píng)論要與生活聯(lián)系起來。正因?yàn)椤都t樓夢(mèng)》的語言來源于生活,它的人物原型來源于現(xiàn)實(shí),所以字字看來皆是血淚,最能撥動(dòng)讀者的心弦,用字遣句也符合情理,所以對(duì)人物的性格描寫與塑造是語言藝術(shù)不可忽略的一點(diǎn)。
形式內(nèi)容的統(tǒng)一:語言藝術(shù)學(xué)科的操作原則
古代語言藝術(shù)有著在實(shí)踐創(chuàng)作中積累形成的理論基礎(chǔ),在各朝各代都得到了總結(jié)和歸納。在理論基礎(chǔ)形成的同時(shí),語言藝術(shù)的研究方法也日益成熟成形。語詞要與表達(dá)內(nèi)容一致,呈現(xiàn)出同一性原則,《文心雕龍•情采》認(rèn)為立文之道有三:形文(詞藻修飾)、聲文(音律調(diào)諧)、情文(內(nèi)容情感)。在研究文獻(xiàn)作品時(shí)音韻、詞匯、句法是三個(gè)主要考察對(duì)象,正如聞一多先生倡導(dǎo)的“三美”:建筑美、音樂美、繪畫美,即是對(duì)語言藝術(shù)研究對(duì)象的一個(gè)考察標(biāo)準(zhǔn)。所以文章中“韻”的音響效果、平仄聲調(diào)的交錯(cuò)、雙聲疊韻的安插、音節(jié)的解析都是研究者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而音韻的研究多集中于詩歌這個(gè)傳統(tǒng)文學(xué)體裁,詩歌注重平整規(guī)格、押韻合規(guī)、平仄合度,這些都是一首好詩必須具備的條件,再深入研究應(yīng)該關(guān)注詩歌傳達(dá)的意境、用了怎樣的意象來傳遞信息,以及詩人在其中傳達(dá)了怎樣的思想感情,這些是研究的重點(diǎn)也是難點(diǎn),如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詩歌就成為了浩瀚的詩歌世界中最難讀懂的詩歌之一。李詩的意象復(fù)雜奇巧,故意模糊了他所要表達(dá)的本意,讓后人猜測(cè)紛紛,這也成為了語言藝術(shù)中難以達(dá)到的高峰,即一千個(gè)讀者有一千哈姆雷特,每次的品味都可以帶來不同的畫面意境。所以詩歌的研究方法不僅要考慮法度,更應(yīng)該挖掘埋藏在法度條條框框下詩人豐富的情感世界和想象世界。在戲曲的創(chuàng)作中,語言形式對(duì)于戲曲的整體結(jié)構(gòu)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王驥德就提出:修辭,當(dāng)自煉格始(《論章法》),煉格猶如對(duì)整體戲劇的布局,使得戲劇語言達(dá)到舞臺(tái)性和藝術(shù)性的統(tǒng)一,如人物語言的性格化,從而讓形式與內(nèi)容更好地傳遞整體思想情感。詞匯的研究是研究的重點(diǎn),詞匯是最具生命力的語言要素,它不僅可以反映歷史,也可以傳遞感情,每個(gè)作者都有自己一套獨(dú)特的常用詞匯體系,這套體系反映作者的審美趣味、語言風(fēng)格、寫作特點(diǎn),因此對(duì)于詞匯的研究是一把打開作者創(chuàng)作特色大門的鑰匙。宋人對(duì)杜甫語言的研究就專注于探索杜詩的獨(dú)到之處,并且深入到句法以至于字法上。在對(duì)杜詩的定量研究后,宋人更是總結(jié)出了屢用字、用字法則這樣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并且在句法上杜詩常常采用的互體、倒句、拙句,在篇章之法上,杜詩的依次順接法、隔句順接法、斷續(xù)法、四句通義法都說明了杜詩鮮明的語言表達(dá)形式。這些語言風(fēng)格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更加透徹地了解杜詩的藝術(shù)性。詞匯研究有擬聲詞的應(yīng)用、重疊詞的應(yīng)用、方言俗語的應(yīng)用、典雅詞或古語詞匯的應(yīng)用、外來詞的應(yīng)用、詞匯結(jié)構(gòu)狀況、虛詞的狀況、詞匯的情感色彩、新詞的創(chuàng)造力、詞類活用狀況、熟語的應(yīng)用、共存限制的放寬等等。作者的獨(dú)特詞匯風(fēng)格形成了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這不僅僅與作者自身的價(jià)值觀、人生觀、世界觀有關(guān),更與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環(huán)境密不可分,所以詞匯也有地域色彩,比如騷體詩人作家群的作品就有著獨(dú)特的南國方言特點(diǎn)。詞匯還受到了文體的限制,正式文體中的詞匯和非正式文體中的詞匯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小說文體與詩歌體裁中的詞匯也有著不同,這些都需要系統(tǒng)的研究歸納后才可以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從而探究其本質(zhì)。組詞成句,句法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gè)入手點(diǎn)。文法是約定俗成的,在相對(duì)統(tǒng)一嚴(yán)密的文法下,作者可以通過創(chuàng)造和變化在大的準(zhǔn)繩沒有越出的前提下對(duì)文法做出各種調(diào)整,以表達(dá)情志和實(shí)現(xiàn)語言美。造句類型的狀況、句子省略的狀況、文言或白話句式、句法的偶化狀況、韻散使用的狀況、對(duì)話的安插狀況、詩歌重沓反復(fù)的形式、走樣句的狀況、對(duì)偶句的假平行等這些都是常常需要研究的句法現(xiàn)象。句法的研究應(yīng)該類型化、具體化、文體化,在古代學(xué)者的研究中句法研究常常被忽略,這不僅是由于中國傳統(tǒng)語言藝術(shù)研究缺少整體觀、系統(tǒng)觀的影響,同樣也是句法本身的隱蔽性導(dǎo)致的。人們常說最高明的文字技巧是叫人看不出文字技巧之所在,這是因?yàn)樵娭械奈淖忠讶哭D(zhuǎn)化為表現(xiàn)情性的信息了。德國文藝?yán)碚摷胰R辛曾經(jīng)這樣論述:“詩人還要把他想在我們心中喚起的意象寫得就像活的一樣,使得我們?cè)谶@些意象迅速涌現(xiàn)之中,相信自己仿佛親眼看見這些意象所代表的事物,而在產(chǎn)生這種逼真的幻覺的一瞬間,我們就不再意識(shí)到產(chǎn)生這種效果的符號(hào)或文字了。”
結(jié)語
篇10
關(guān)鍵詞:藝術(shù)語言;藝術(shù)終結(jié)論;爆破
中圖分類號(hào):J0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5312(2015)08-0025-01
一、藝術(shù)終結(jié)論
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觀點(diǎn)由來已久,從黑格爾到阿瑟丹托再到現(xiàn)在文藝界對(duì)于藝術(shù)終結(jié)的討論從未停止。這一美學(xué)論題的提出始于1828年黑格爾所發(fā)表的美學(xué)演講。黑格爾認(rèn)為“浪漫型藝術(shù)就到了它發(fā)展的終點(diǎn),外在方面和內(nèi)在方面一般都變成偶然的,而這兩方面又是彼此割裂的。由于這種情況,藝術(shù)就否定了它自己,就顯示出意識(shí)有必要找出比藝術(shù)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實(shí)。”由此可見,黑格爾認(rèn)為藝術(shù)是為精神理念服務(wù)的。藝術(shù)是精神理念發(fā)展環(huán)節(jié)的低級(jí)階段,而哲學(xué)宗教才是精神理念發(fā)展的高級(jí)階段。在黑格爾看來,藝術(shù)是低于宗教哲學(xué)的存在,它作為表達(dá)精神理念的工具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是會(huì)被哲學(xué)和宗教所取代的。換言之,黑格爾認(rèn)為,藝術(shù)語言諸如雕塑語言、繪畫語言等都無法表達(dá)更高的精神理念,終將被拋棄。顯然將藝術(shù)單純的作為表達(dá)意識(shí)形態(tài)的附屬工具是錯(cuò)誤的,黑格爾否認(rèn)了藝術(shù)語言(與宗教哲學(xué)對(duì)等)的本體地位。
在黑格爾之后的藝術(shù)發(fā)展過程中,諸多藝術(shù)流派仍在探索藝術(shù)語言的可能性,藝術(shù)語言的本體地位并未被動(dòng)搖。到了后現(xiàn)代藝術(shù)階段,藝術(shù)的地位重新受到質(zhì)疑,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亞瑟?丹托將歷史看作一種敘事,在他的敘事里,他認(rèn)為藝術(shù)發(fā)展到后現(xiàn)代(即后歷史時(shí)代),關(guān)于藝術(shù)的宏大敘事終結(jié)了,也就是敘事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史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按他自己的話說藝術(shù)進(jìn)入了一個(gè)“在這一時(shí)代,只要合格,什么都行”的時(shí)期。在這一時(shí)期“藝術(shù)沒有了任何的風(fēng)格限制或哲學(xué)限制。沒有藝術(shù)品必須體現(xiàn)的特殊方式。”亦即藝術(shù)語言沒有了固定的創(chuàng)作范式,藝術(shù)家不再刻意尋求藝術(shù)語言的創(chuàng)新,尋求藝術(shù)語言的內(nèi)在范式邏輯結(jié)構(gòu)都已成為過去式,藝術(shù)語言的本體地位被動(dòng)搖。這也是后現(xiàn)代藝術(shù)與現(xiàn)代藝術(shù)、古典藝術(shù)的本質(zhì)區(qū)別。由此可見亞瑟丹托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并沒有否定藝術(shù)將繼續(xù)存在下去這一事實(shí),他所提出的藝術(shù)終結(jié)的觀點(diǎn)雖然在關(guān)于為什么藝術(shù)會(huì)終結(jié)及如何發(fā)展問題上模糊不清,但卻確切的描述了后現(xiàn)代藝術(shù)不再尋求藝術(shù)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邏輯范式的藝術(shù)現(xiàn)象。阿瑟丹托提出藝術(shù)終結(jié)論時(shí),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已經(jīng)開始,各種藝術(shù)形式迸發(fā),這種迸發(fā)其本質(zhì)上是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
后現(xiàn)代藝術(shù)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表面上看實(shí)現(xiàn)了藝術(shù)形式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只有“量”沒有“質(zhì)”,并在事實(shí)上造成了藝術(shù)語言“碎片化”,也就是指藝術(shù)語言的內(nèi)在范式邏輯結(jié)構(gòu)的解構(gòu),因?yàn)樵诤芏嗨囆g(shù)家看來,拋棄范式是為了擴(kuò)大藝術(shù)的表達(dá)空間,在他們看來藝術(shù)范式限制了藝術(shù)觀念的表達(dá)的寬度和緯度,但是這種后現(xiàn)代的觀點(diǎn)值得懷疑。在藝術(shù)語言爆破,碎片化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眾多的藝術(shù)表達(dá)形式,但這并未緩解藝術(shù)終結(jié)的危機(jī),原因在于很多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刻意的避開藝術(shù)范式,甚至有些人認(rèn)為無范式的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高于有范式作品的藝術(shù)價(jià)值,這就加劇了藝術(shù)終結(jié)的危機(jī)。藝術(shù)之所以獨(dú)立的成為一種門類,就在于它運(yùn)用自己獨(dú)有的藝術(shù)語言形式來進(jìn)行表達(dá),如果藝術(shù)語言本身被輕視,并且藝術(shù)家不再探索藝術(shù)的范式邏輯的話就意味著藝術(shù)的自立性動(dòng)搖了,也就是藝術(shù)語言的本體地位被動(dòng)搖了。
二、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
無論是黑格爾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還是丹托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都有具體表現(xiàn),一種是通過藝術(shù)語言形式的消解(黑格爾派)進(jìn)行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另一種是藝術(shù)語言形式的“繁殖爆炸”(丹托派)來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本質(zhì)上而言,這兩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行為都是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造成的,一種是“爆破”后藝術(shù)形式消逝于無形,另一種是“爆破”后藝術(shù)語言形式被炸成碎片,失去了自身的范式邏輯。也就是說,藝術(shù)進(jìn)入后現(xiàn)代階段后,古典藝術(shù)和現(xiàn)代藝術(shù)尋求藝術(shù)語言內(nèi)在范式邏輯的傾向已經(jīng)過時(shí)了,代之以藝術(shù)語言形式的“爆破”,這種“爆破”自然會(huì)帶來藝術(shù)本身受到質(zhì)疑。
第一種“爆破”將藝術(shù)語言形式消解于無形,其代表是觀念藝術(shù)(Conceptual Art),它與黑格爾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不謀而合,都認(rèn)為藝術(shù)只是表達(dá)觀念或者說精神理念的工具媒介,當(dāng)出現(xiàn)比藝術(shù)語言更為有效高級(jí)的表達(dá)方式時(shí),藝術(shù)語言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消解的。
索爾?李維特認(rèn)為觀念是藝術(shù)的發(fā)動(dòng)機(jī);觀念藝術(shù)不依賴于藝術(shù)家精湛的技藝,好的觀念藝術(shù)源自好的觀念,藝術(shù)語言技藝的運(yùn)用應(yīng)該盡可能的簡(jiǎn)單,精湛的技藝反而會(huì)成為觀念的束縛;文字語言如果能表達(dá)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觀念也可以作為一件藝術(shù)品。托尼?戈德弗魯也明確提出觀念藝術(shù)無關(guān)乎形式或材料,它不可能被定義為任何媒介風(fēng)格。它的出現(xiàn)通常被認(rèn)為始于馬歇爾?杜尚的“現(xiàn)成品藝術(shù)”,最為有名的就是他的小便池《噴泉》。觀念藝術(shù)的出現(xiàn)讓藝術(shù)終結(jié)論似乎成為了一種可能。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dāng)精神觀念完全替代藝術(shù)語言成為藝術(shù)本體時(shí),藝術(shù)事實(shí)上可以被文字、語言等等一切非藝術(shù)形式所替代,換句話說,藝術(shù)區(qū)別于它物質(zhì)形式的獨(dú)特性與獨(dú)立性被消解了,藝術(shù)也就不必是藝術(shù)。所以觀念藝術(shù)在短時(shí)內(nèi)便走入了死胡同。
而另一種“爆破”是將藝術(shù)語言碎片化,這種藝術(shù)則充斥于后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角角落落,我們無法給予準(zhǔn)確的定義,他們的共同特點(diǎn)是用無規(guī)則、無邏輯的藝術(shù)語言形式去創(chuàng)作,藝術(shù)作品看起來似乎是無意義的材料拼裝,而非有內(nèi)在邏輯的形式。從極簡(jiǎn)主義到波普藝術(shù)到當(dāng)代藝術(shù)均有藝術(shù)家極力創(chuàng)新藝術(shù)語言形式運(yùn)用各種新型材料尋求與眾不同的藝術(shù)效果,創(chuàng)作第一無二的藝術(shù)作品。
例如2014年在紐約蘇富比拍出上億高價(jià)的極簡(jiǎn)主義作品《無題》便是一件比較典型的無內(nèi)在邏輯的抽象藝術(shù)作品。《無題》全幅用以白色的顏料堆砌成厚薄不一的肌理鋪滿整個(gè)畫面,間雜一些藍(lán)綠的顏色。無論是白色肌理也好,還是星星點(diǎn)點(diǎn)的藍(lán)綠色,單獨(dú)的看都是沒有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的無意義的語言符號(hào)。這種無意義符號(hào)簡(jiǎn)單的堆積能夠造成一定的視覺沖擊。這種視覺沖擊在欣賞者眼中能造成短暫而強(qiáng)烈的印象,從而達(dá)到創(chuàng)作者的某種目的。但當(dāng)語言形式被分化為單獨(dú)的語言符號(hào),其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和邏輯聯(lián)系就被完全瓦解了。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cè)谒囆g(shù)材料的處理上強(qiáng)調(diào)偶然性、無序性、反結(jié)構(gòu)、反中心化,這就又造成了藝術(shù)家必須不斷更新藝術(shù)形式,且這些紛繁復(fù)雜的“爆破”后的藝術(shù)形式并不具有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和邏輯。縱觀《無題》的創(chuàng)作者藝術(shù)家羅伯特?雷曼的創(chuàng)作生涯在相同時(shí)間段內(nèi)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作品幾乎沒有一幅是完全相似的,這就是典型的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勢(shì)必造成藝術(shù)語言的碎片化。
總之,后現(xiàn)代藝術(shù)所帶來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危機(jī)本質(zhì)上是藝術(shù)語言“爆破”帶來的結(jié)果,當(dāng)藝術(shù)語言的內(nèi)在范式邏輯被否定之后,藝術(shù)語言的本體地位自然會(huì)被動(dòng)搖,進(jìn)而帶來藝術(shù)消亡的可能,要想挽救藝術(shù)本身,必須停止對(duì)藝術(shù)語言的“爆破”,回歸藝術(shù)語言的內(nèi)在范式探索。
參考文獻(xiàn):
[1]亞瑟?丹托(美),歐陽英(譯).藝術(shù)的終結(jié)[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
[2]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píng)[M].北京: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3.
熱門標(biāo)簽
語言學(xué)論文 語言文字論文 語言變化 語言研究論文 語言藝術(shù)論文 語言得體 語言與文化論文 語言表達(dá)能力 語言變異 語言文字 無公害 無功補(bǔ)償 無公害蔬菜 無公害養(yǎng)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