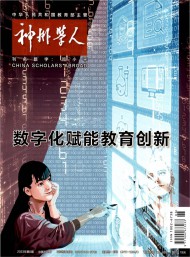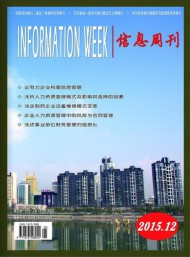周國平人生哲思錄范文
時間:2023-04-08 07:46:37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周國平人生哲思錄,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dāng)代著名學(xué)者、作家、哲學(xué)研究者,是中國研究哲學(xué)家尼采的著名學(xué)者之一。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1981年畢業(yè)于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哲學(xué)系。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哲學(xué)系在職讀博士研究生課程,畢業(yè)后獲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2009年受聘為西南政法大學(xué)兼職教授。
2、著有:《尼采:在世紀的轉(zhuǎn)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xué)》,散文集《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圣路》《安靜》《善良豐富高貴》,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偶爾遠行》《寶貝,寶貝》,隨感集《人與永恒》《風(fēng)中的紙屑》《碎句與短章》,詩集《憂傷的》,以及《人生哲思錄》《周國平人文講演錄》等,譯有《尼采美學(xué)文選》《尼采詩集》《偶像的黃昏》等。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篇2
關(guān)鍵詞:莊子;生死觀;達觀;逍遙;現(xiàn)代人;啟示
一、 莊子的生死觀
《列御寇》篇記莊子將死時的一段話說:“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廓,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濟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生死變遷在一般人看來是相當(dāng)嚴重的,但莊子說來卻淡似,了然無痕。對于自己的死生看得如此輕淡,所以對于妻子之死,他就“箕踞鼓盆而歌了”(莊子?至樂篇)。究其何以臻此境地,《至樂篇》記莊子回答惠施關(guān)于生死見解時說:“察其而來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行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借此可以知莊子視死生變遷,不過如春秋冬夏四時變遷而已,于自然的變化是不可抗拒無以逃避的,只有順從依隨,才是人間至道。我們借此而說莊子是達生主義者。他是無生無死與天地為一體的,他是上與天地主宰同游,下與看破生死不分始終的人為友的,他是視死生為一化的。所以妻子死而歌,已死不哀。循著這一基點追循莊子的生死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曰:等生死,齊榮辱;二曰:物我同一;三曰:安天樂命;四曰:道遙自由。現(xiàn)分述之。
莊子認為生未必樂,死未必苦,生與死只是物理的過程。因此不樂生,不苦死,不以得而榮,不以失而辱。他在《在樂篇》里借髑髏之口說:“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就無事實之事,徒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之樂不能過也。”莊子是于生無所戀,于死有所懷。莊子生于戰(zhàn)國,人人皆處于險惡的戰(zhàn)爭世界,水開火熱,生即是苦,即是痛。可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恭然疲彼,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齊物論)。他認為晨死,內(nèi)生之可樂也。既然生活至苦,人生少樂,那死也就沒什么可以恐怖的了。莊子以死為歸家,如生無所苦,對之當(dāng)有所戀,既以生為哀,以死為返(庚桑楚篇),以為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則不能不說莊子對于亂世的生活方式有所厭惡。
莊子未因惡生懷死而自殺,這里邊潛藏著這樣的臺詞:莊子的生死觀是矛盾的。莊子固然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他主張養(yǎng)生,乃是順乎自然,全其天守,凝其精神,不竟外物,不溺私欲。這是他養(yǎng)生的宗旨。否則徒然養(yǎng)形而已,一般世人注重物質(zhì)形式,雖終身役役,終有之盡的一天。不如棄世而修心:“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無累,無累剛正平,正平則彼更生,更生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累。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剛精不高,只形全精復(fù),與天為一”(達生)。不但要棄世而修心,最好能外生而不戀生,已外生產(chǎn),而后能朝撤,朝撤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不生不死其實上就是要取消個體的主體性。個體之存在以形為載體,形修心正意味了莊子要超越形體以求得生命的本質(zhì)性存在。那便是融于道之中,道家學(xué)派自老子將道作為其學(xué)術(shù)的核心范疇伊始,到了莊子,道已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詩意狀態(tài)。道無所不在,人對于道的企及便是使自己物化。所謂物化也即是個體取消自己的主體性存在狀態(tài),融入到客體之中。
莊子書中《大宗師》《知北游》二篇所論者,為內(nèi)圣之道,以無心為妙用,以泯全天人,冥絕死生,而達于坐忘之境為空極。其實所謂坐忘之境,即是極端內(nèi)在修養(yǎng)的人,于外在一切死生成毀的變化,不能擾亂其內(nèi)心的寧靜,亦即置現(xiàn)實於不成顧,寓心虛無渺茫。《人間世》說:“一若志,無聽之以身,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于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章也。”此于心齊坐忘之境言之已明。不以身聽,而以心聽,心聽者,以之所想;自聽者物象之真,心章者,虛而待物,此即是說拾物象之真而入于幻想,惘事物之變而虛靜以待。《大宗師》說:“忘其膽肝,遺其耳目……芒然,徘徊乎垢塵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yè)”。《知北游》說:“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是舍現(xiàn)實之垢塵,任精神之幻想,“知忘是否,以這適也”(達生篇)。可以說坐忘而達到物我同一的境地。從全社會之角度講是一種消極幻化的冥想,但作為修養(yǎng)卻不妨姑妄聽之。而后世禪宗的修練,也多少吸取了莊子養(yǎng)生論的養(yǎng)份。
莊子列《逍遙游》于篇首,并不是隨便的,逍遙者,不以物累,不以已悲,游形于物外,無所結(jié)而自由在也。一語蔽之,及由必然進入自由之明道也。鯤,魚子也,鵬,麻雀也。以魚子之小而喻無窮之大,以麻雀之微而致無極之遠。是等大小,等大小目的是取消道主體之獨立性。主體的存在是需要依恃的,這便是有待,便是不自由了。所以《逍遙游》在顛覆了一切現(xiàn)存價值的羈絆,使精神達到無拘無束的自然狀態(tài)。莊子所想達到的境界無疑是藝術(shù)化的境界。
莊子的生死觀中的“坐忘”與“逍遙”,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境界是異曲而同工的,人固不能選擇生與死,但對于生對于死的詮釋是每個活人的權(quán)利。
二、莊子生死觀的啟示
莊子的生死觀對于現(xiàn)代人有著有益的啟示的一面,對自己生命應(yīng)珍惜,懷著達觀的態(tài)度對待生死。
死亡,這是每一個人都無法逃避的哲學(xué)命題。
人來自塵土,最后必然要歸于塵土,土地才是我們永遠的“母親”,人的出生是偶然的,死亡確實必然的,中國古代君主多么希望自己長生不老,用盡了各種方法,最后都被歷史的洪流帶走,再活五百年知識人類的可笑空想。
既然生命最后結(jié)局都是死亡,裸地來,裸地去,在塵世只留下親人無限的回憶與哀思。同時死亡注定是孤獨的,即使再親近的人也沒有辦法陪伴左右,作用親人陷入漠然、凄冷境地,內(nèi)心充滿憐憫與痛苦。沒有人會不懼怕死亡,在去世之前大腦必然經(jīng)歷著重重煎熬,思想異常活躍,進入哲學(xué)境界,只有自己知道,告別了塵世的牽掛,洗去了生前的勞累,一個人孤零零走向大自然。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原生態(tài)表現(xiàn),是佛教所說的輪回,對死亡我們應(yīng)該抱著生之也幸,死亦亦然,接受上天的“賜予”,抱一種達觀態(tài)度,在有生之年養(yǎng)生,減慢死亡的步伐,保持更長時間的健康,做更有意義的事。“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才是最好的選擇。
死者安息,生者節(jié)哀,對于生者,前面要走的路還很長,更堅強、堅定去努力去奮斗去成功,不可過度沉溺于悲痛之中。況且死者幽靈的話也不希望如此,以自己的更大意義的成功去祭祀死者之念,保持健康,一往直前!
參考文獻:
[1]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冊)[M].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42,132.
[2] (春秋)老子.道德經(jīng)[M].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43.
[3] 安繼民,高秀昌.莊子[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4] 馮友蘭.十家論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3.
[5] 陳鼓應(yīng).名家品莊子[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7.157.
[6] 林繼平.孔孟老莊與文化大國[M].臺灣: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90.394
[7] 于丹.莊子心得[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