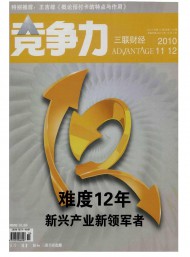一個人的村莊范文
時間:2023-03-19 01:48:1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一個人的村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孤單的筆觸,蒼涼的景物。黃沙梁,沙漠中的小小綠洲。像一個知理明事的老者隱于繁華之外,守著幾分孤獨,守著幾分自在,守著幾分寂寞,守著幾分愜意。
想象這樣一幕場景,黃沙漫漫,飄在村莊以外的天空。茅草屋和木屋興許新竣工興許早已破敗。黃沙梁的人站在天地間,望著春華秋實的萬物,望著春種秋收的麥子,麥香濃郁。就這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安分守己的生活,睡下與醒來就是一輩子。,村莊里的草青了又黃,來年又是青草。星星升起又落下就是永遠。
有一個人,叫張三,叫李四,或者叫劉三。他不種田,他幾乎什么都不干,他只蹲在一面破墻根吸煙,從太陽出來到太陽落下,就這樣蹲著,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有一個人,叫張三,叫李四,或者叫劉三。他孤身一人,早些年在要搬遷的人家手里買了房子,就這么住著。天長日久。門破了,煙囪堵了,他不去管,就讓房子和自己一起老去吧。人們在五千栽樹,等木頭長成了便用來做房梁,等房子蓋成了自己便安然老去。人們在村邊種田,夜里嗅見稻香了便可以收獲。人們養著牲畜彼此不相干涉,等變老就一起消失在漫漫黃沙中。
書中有那樣一段話,有一個漢子,皮膚黝黑,在烈日下,他揮舞著鐮刀,不知時間。我突然體會到了時間的流逝,它流過我們的身邊,我們忙于播種或者收獲,無暇顧及,只是突然間有一刻心酸的感覺。我們悲,卻不明所因。也許悲傷時間如白駒過隙,也許悲傷村莊的千年無聲,也許悲傷此時自己心無大志,也許悲傷孤獨無可阻擋。這是一種很蒼涼的感覺,抬頭仿佛看到青灰色的天躲在黎明里,雞鳴劃破天空,朝陽明艷似血。再抬頭卻又已是落日余暉,沒有壯美,只有黃昏時的淡淡孤獨。
一個人的村莊。我想會是一種很美的感覺。若說孤單也該是一種美麗的孤單。我總是想若漫漫余生有機會我一定會去一個村莊,守一份寂寞,品一段時光。人生有太多時光要打發,與其在繁華中虛妄不如在荒蕪中清晰。村莊是一個很古樸的地方,人畜共居,有院子的小,,門前有天羅瓜的架子,爬山虎爬了滿墻,風仙花開的紅艷艷,在昆蟲的鳴叫中入眠,在雞鳴中醒來。偶爾你會被鳥聲吵醒,初冬的早晨,一些似雪非雪的降水過后,薄霜鋪滿瓦檐,著水珠,鳥兒就開始爭鳴了。也許初冬早晨和煦的陽光讓它們以為是春天來了。去看看列列西風中無葉的杉樹,葉已落盡枝椏在半空中顯得突兀,也許一天傍晚你會發現北風中有成排的小鳥站在枝椏上,像是一株長鳥的樹。這樣的村莊也是一個人的村莊,你可是會喜歡,孤獨且美好的村莊。
去一所一個人的村莊,無論破舊與敗落,聽細雪聲如碎玉,聽細雨聲如囈語。瓜田李下,柳暗花明。春意盎然。夏樹成蔭,秋雁南飛,冬雪陣陣。像一個隱者。用超然脫俗的淡泊隱逸,去一所一個人的村莊拋棄所有人世美好于不顧,怡然自足,多好的日子,不遷怒不怨恨,應當是如水的時光。
一個人的村莊,不知道作者本初的一年,也許是厭倦了俗世,想念起了家鄉,那個村莊,一個人的村莊。我也不知道看完這本書后又有怎樣的感想,只是突然想到了這些,也寫下了這些。
篇2
關鍵詞:劉亮程 《一個人的村莊》 文化超越性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許多作家都以畢生心血傾注在對故鄉的無盡回味中,譬如沈從文、汪曾祺、蕭紅等,劉亮程也是其中一位。他們的共性在于:在對故土的深情注視中實現精神家園的皈依,在異質文化的反思中完成對生命本體價值的定位,在知識分子的身份焦慮中發現道德良知的悲憫。而劉亮程的特別之處在于,以“道”的絕勝氣質為出發點,走向“儒”對生命痛感的深情吟詠。
芳芳在給《一個人的村莊》寫的跋中有這樣一段話:“亮程的野心似乎更大,他似乎想通過讓時間靜止的方式,以他自己來來去去行走的“閑錘子”的方式,切近村莊以及生存本身這個母題。他做得貌似漫不經心卻處心積慮;貌似語無倫次自說自話卻是在慘淡經營……亮程的‘荒原而不為人知的村莊’的封閉性似乎也不僅僅是地域使然而更像有意為之的。”可見,劉亮程筆下的“村莊”還是一個富于文化內涵和精神超越意義的意象世界。
一
村莊“慢而長”的時間觀構成第一重“超越”。“風四十年吹舊一扇門上的紅油漆。雨八十年沖掉墻上的一塊泥皮。”“多少年來我似乎忘記了生長。”一切事物的改變都可以忽略不計,村莊就是一個在歷史河流中靜止的世界,在等待中以求生命輪回。更重要的是,即使“變化”也不再有它的意義,因為“更緊迫的勞動在別處開始”。勞動,把這里的世世代代永久而沉重的束縛在荒涼貧瘠的土地上,周而復始,沒有開始和結束;但也造就了這里人虛心、務實的生活態度。他們無需羨慕外面世界瞬息萬變的精彩,即便永遠面對一成不變的生活,也對生命恒常持有信念。正如古語“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又何羨乎?”
二
村莊里錯位的空間想象構成第二重“超越”。一望無邊的荒野構成一個精神的“荒原”,人如麥垛一樣都是其中的隱匿者,人亦被視為與所有生命平等的物。貧窮使人失去物質欲念,轉而迫切需要在精神上攫取尺寸之地。一方面,人就在貧瘠土地的深處去汲取精神養料,使無法向外伸展的欲望往縱深處扎根,讓生命站成一個個獨立體。另一方面,貧瘠終無法改變人內心孤單、寂寞和恐懼的心理寫照。“荒原”既是空間上的,又是精神的。渺小的個體實難走向廣袤西北大地的邊界,更無法與之產生對話和共鳴,從而產生存在的虛無感和情感的荒漠感。無形的空間存在于人們的想象深處,當人與空間的相對關系無法確認時,或將其想象成“無限大”而變得自傲,或因無法掌控而膽小、逃避,以致產生封閉心態。“在這個村莊里,睡一百年,都不會有人喊醒你”,這種“不跟你玩”的心態正是邊緣苦感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傲的畸形結合,但也是他們對惡劣生存空間的精神超越。
三
以上兩種“超越”只是為“村莊”注入了時空觀基礎,比較淺層。而更深層次的“超越”在于其消弭物我之界限,與自然共生共融的生態觀。“如果我還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棵草的事情,一粒蟲的事情,一片云的事情。”這恰好反映了莊子“我與萬物合而為一”的人格理想:主體人格通過客觀自然的無限廣大來實現絕對自由。莊子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亮程筆下的村莊就充滿了這種接近于無限本體的“大美”,與主體人格理想密切相連,與天地精神獨往來。在這里,弱小的生命還獲得了獨特的審美觀照:驢不再是永遠跑不過馬的小畜,人們羨慕它的悠閑;小蟲也值得尊重,它們走過的路不多,卻能抵達人無法看到的世界……生命有情,這是第三重“超越”。它接近于生命本體的表達是“道”的完勝:其一,所謂“自然無限美,人生何渺茫”,相對于人際關系的斤兩算計,它獲得了更開闊的審美視野。其二,它以“人的自然化”為審美旨趣,追求物我之平等。其三,人從與其它生命的距離走向對自然及生命的和解。“我從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為弄懂了它們,其實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們。” 與草木蟲魚親近而保持距離的狀態便是“和解”的真正內涵:親而不膩,是為對生命的敬重。這是農耕文明的精神產物,更是農耕文明對城市文明的超越。
四
第四重“超越”是一種“儒”的超越。它源自對這片精神沃土難于舍棄的情懷,也源于對生命本身孤獨與荒涼的和解,更兼智慧與深情。亮程有他“一生難以走出這村莊”的原因:其一,城市“不過是另一個村莊”,城里人是“另一種形態的農民”,無論走到哪里總還是扔不掉手里的“鐵锨”和“羊鞭”。他對“城市”和“城里人”概念的置換從根本上掏空了對城市的其它注解,解構了后現代社會的城市文明。其二,人際關系的裂隙和人性的疏離,使亮程的腳步更加沉重。與父親之間難言的陌生,母親獨自在冬天的透心寒冷,偷苞谷的賊逃命的可憐,冬夜里凍死路邊的老者……“心地才是最遠的荒地,很少有人一輩子種好它。”認識到人性荒蕪的難以除,體現了儒者深徹的悲憫。其三,認識到精神荒原內在的艱難性。“真正進入一片荒野其實不容易,荒野曠敞著,這個巨大的門讓你努力進入時不經意已經走出來,成為外面人。它的細部永遠對你緊閉著。但亮程從不回避它,他從對“物”的觀照轉向對“人”的觀照,由對人性內部的發掘去實現最終的“超越”。這種終極超越的可貴在于:他沒有放棄“人”,而是進入“人”,哪怕身處一片“荒原”也要在其中建立希望,并且堅信唯有在此中才能尋找到村莊的全部歸宿。
結語:
筆者以為,由“道”的自然化走向“儒”與對人性的和解,此為“超越”的本質和精髓。
參考文獻:
[1]劉亮程 《一個人的村莊》 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6.1
篇3
——劉亮程《對一朵花微笑》
劉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沙灣縣的一個小村莊里,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長大后種過地、放過羊,當過十幾年鄉農機管理員。勞動之余寫點文字,大多寫自己生活多年的一個村子。在這個人畜共居的村莊里,房子被風吹舊,太陽將人和牲畜曬老,所有事物都按自然的意志伸葉展枝。作者在不慌不忙中敘述著一種人類久違的自然生存。著有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和《風中的院門》,圖文集《庫車行》。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于1998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次年引起了新疆文壇的熱切關注和巨大反響,被譽為20世紀最后的文學景觀。劉亮程本人被譽為“20世紀中國最后一位散文家”和“鄉村哲學家”。
風中的院門
書名:風中的院門
作者:劉亮程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01年1月
頁數:425
內容簡介
《風中的院門》文字樸素、沉靜而又博大豐富,內容分為“風中的院門”、“我的村莊”、“永遠的黃沙梁”三輯,收有“風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誰的影子”、“共同的家”、“剩下的事情”、“別人的村莊”、“只有故土”等40余篇散文。
這是一本始終把人和村莊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散文集。作者劉亮程雖然才過而立之年,卻經歷了中國農村的世事滄桑。莊稼人、牲畜、田野、小麥和樹林……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榮。他在《住多久才算是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自白:“我一直慶幸自己沒有離開這個村莊,沒有把時間和精力白白耗費在另一片土地上;在我年輕的時候、年壯的時候,曾有許多誘惑讓我險些遠走他鄉。但我留住了自己,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沒讓自己從這片天空下消失。”
書名:一個人的村莊
作者:劉亮程
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06年1月
頁數:280
一個人的村莊
內容簡介
《一個人的村莊》講述了劉亮程是真正的作家,也是真正的農民,是真正的農民作家。
作為農民,寫作真正是他業余的事情;而作為作家,他卻無時不在創作,即使在他扛著一把鐵锨在田間地頭閑逛的時候。在他的村莊里,在與他一樣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村民們的眼里,這個無事扛著鐵锨閑逛,到處亂挖,常常不走正道卻偏要走無人走過的草叢中的人一定是個難以捉摸、有些古怪的人吧。在他們眼里,這個說不出卻總覺著有點不一樣的人是不是有點神秘呢?當然,他們也許不知道這個人在跟他們一樣的勞作之外,還喜歡偷偷觀察著村里的人,以及驢、兔、飛鳥、螞蟻、蚊子,以及風中的野草和落葉,甚至村東頭以及村西頭的陽光……
這本書的封面上印有一行字:“后工業化社會的鄉村哲學”,后工業化社會和貧窮的生活面貌之間,存在著何等尖銳的對立與鮮明的反差。
《一個人的村莊》突出了其醒世的、不可漠視的人文價值;突出了人類命運,家園史詩與人的靈魂檔案的意義。“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對于真正已達到“五谷不分”的某些“新新人類”來說,劉亮程的書就是一本人性歷史的“備忘錄”。
書名:鑿空
作者:劉亮程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2010年4月
頁數:257
鑿空
內容簡介
篇4
一個衣著艷麗服裝的佤族婦女
邁著不大不小的步子
走過山溝里的玉米地
剝開一個個玉米棒子
隨手扔進背簍里
半小時后
玉米裝滿了背簍
背簍里散發出的泥土氣息
慢慢滲進她的血液里
不遠處是她的村莊
我站在村莊附近的山坡上
聽不到家畜家禽的叫聲
也看不到有人從村莊里走出來
一切一切都非常的安靜
只是我不敢想
佤寨的孩子們
佤寨的男人們
還有佤寨的老人們
他們都哪去了
這個村莊真成了她一個人的佤寨
若是
我愿與她牽手
當上佤寨寨主
木鼓
以紅毛樹、花桃樹或麻栗樹樹干為原料
按一定形狀掏空
佤寨的標志克羅克橫空出世
集傳統祭祀工具、樂器和報警器具的木鼓
分為公鼓、母鼓
公鼓的音節偏低,音色粗重
母鼓的音節較高,音色清脆
木鼓房是佤寨重要的標志性建筑物
一個佤寨都有若干個
用六根柱子三根橫梁及竹片
或茅草搭建而成
四周沒有墻壁
木鼓房不大結構簡單
存放木鼓的地方
便有其他民族廟宇的功能與地位
木鼓是佤族的 “通神之器”、“通天之鼓”
阿佤人說生命靠水,興旺靠木鼓
往日
沉重的木鼓聲響起時
必有人頭落地
今昔
木鼓多是靜靜的躺在木鼓房
只有祭祀報警或節日喜慶等
才能聽到木鼓的響聲
司崗里
樹洞
山洞
巖洞
甚至是一個小小的泥坑
可能是佤族先民的司崗里
從里面走出來的萬物
眾生平等
的阿佤先民飽一頓饑一頓
與野獸為伍
后來
是媽儂教育了阿佤先民學會了尋找食物
阿佤先民吃上了甜蜜的野果
吃上了香味可口的獸肉
從此便頑強地在瀾滄江流域繁衍生息下來
在勐梭龍潭邊想起你
十年前
在勐梭龍潭邊喝完最后一杯水酒
那夜你我醉在湖邊
美好的約定
十年后在此相聚
我如期而至
卻沒有等到你的消息
手機、微信和QQ現代媒介里
都沒有我們的聯系方式
相信一個緣字
就這樣
為了一個美好的承諾
在心里彼此堅守了十年
也是同一個日期
也是在晚霞映照湖邊的傍晚
我孤身一人靜靜地坐在湖邊
思緒飛到你的身邊
只是原來喝的水酒換成二鍋頭
讓我靜下來
讓我沉醉
一潭湖水
一個人的世界
一個人的舞蹈
那夜
你光著腳丫跳啊跳
黝黑長發甩啊甩
舞臺上的你是美和力量的化身
我不能構造意境,營造氛圍
我渴望像你一樣的解脫
渴望一種原始的放縱
渴望與美麗的佤族女葉子再次相遇
在勐梭龍潭邊想起你
想起你的眼神
想起你的笑容
想起你的長裙
想起你的長發拂過我的臉頰
我傷感
我渴望
渴望來世成為會跳甩發舞蹈的佤族姑娘
根據地
根據地是勐梭龍潭邊上的一個冷飲店
普通的佤族小樓
中午
和來自麗江的文友楊春山先生走進小店
選擇面對龍潭公園大門的桌子坐下
漂亮的佤族女老板問喝點什么
老板手里沒有點菜單
也沒有紙和筆
只是很友好地看著我們
我問她有什么喝的
她答
酒水類有自烤酒泡酸木瓜
有水酒
還有啤酒等
飲料類有檸檬汁、葛根汁……
聽完
要了一盤黃瓜
兩盅白酒
一次又一次的碰杯
時而
談著一些與云南文學有關的話題
從彭荊風、于堅、雷平陽、夏天敏……
再到《婚誓》、《廬山戀歌》、《阿佤人民唱新歌》……
時而
又靜靜地凝視遠處的勐梭龍潭
聽人講過
勐梭龍潭里曾有水怪出現
篇5
風是透明的,它撫摸一棵草的時候,看不見風的樣子,這棵柔弱的草,搖了搖手臂,像是自我陶醉,和風沒有一點關系。風撞到一棵樹上,有些氣咻咻地掉轉頭,穿過幽深靜謐的樹林,樹葉子嘩嘩地響,熱烈的夏天,變得緩慢、抒情,風引來了蟬歌,陰下來一方清涼。這是婉約的風,充滿女性的陰柔,它走過的田野、草和莊稼從土縫里探出頭,鄉間的野花,猶疑著露出淺淺的微笑。低微而洪大的蟲鳴,被風捎到更遠的地方,一片秋天的黃葉,被風吻過后,旋轉低落到泥土上。院門被風推開,院落里橫著豬食槽子,斜靠著雞食盆子,地面上有匆忙的腳印,和遺落的麥草……對于風來說,雜亂的院落沒有秘密。風和村莊的人一樣,性別,年齡、高矮、脾氣秉性,各個不同。籠統地稱它們風的時候,就像是含糊概括地說樹林的樹,說村莊的莊稼。風肆虐狂放的時候,可能掀起一垛草,可能把一棵樹攔腰折斷……斷肢殘臂,紛紛下墜,橫尸遍野的戰場一般,可惜,油綠的葉子依舊青春般地閃亮。麥熟的時候,或者刨掉玉米,大地一片空曠的時候,容易刮起旋風,風緊貼著地皮,開始時只是斗笠般大小,輕揚起草屑,微塵,莊稼的葉子,陀螺一樣不停地旋轉著往前跑。漸漸地風勢越來越猛,像一只巨大的漏斗,像一個細腳伶仃大腹便便的巨人,成捆的麥草,玉米秸,桑叉,干松的牛糞……輕而易舉地成為風捕獲的對象。我的祖母,忙著吐幾口唾沫,惡狠狠地詛咒幾句。一個旋風便是一個不能轉世的荒魂野鬼,我的祖母用大衣襟把我的半個身子掩上,她緊緊地摟著我,她不讓那些荒魂野鬼沾到我的身上,滄桑的老樹皮一樣的手掌捂著我的臉,蓋上我的眼皮。
雨來之前,風便來了,雨走之后,風還是百般的留戀。躲在屋子里聽雨,聽風。雨聲悠遠,風聲遼闊。風摩擦著一面土墻,帶著混濁的喘息,風把輕輕挑起的兩根電線,吹得嗚嗚作響。南園子果樹林里有一口井,多年前一個因為婚嫁而輕生的年輕貌美的女人,跳井而亡,風漫過這口井的時候,多了些纏綿,多了些幽怨,風在井口前踟躕不前。有風的時候,你爬到井跟前,會聽到低微的時斷時續的哭泣。誰也不能證實真實的情況,大人還沒走到這口井跟前就繞個彎,走開了;孩子們懷著好奇走近的時候,多半被大人呵斥住了,即使真的走到跟前,因恐懼逃離出來,手腳慌亂,耳朵也慌亂得什么都聽不到。夏日里,在大門洞里搭一塊門板,上面鋪麥草編織的草墊子,打赤膊,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穿堂風一陣陣,從很遠的地方吹過來,有些清涼,或者還有些甜爽,風里有樹木的氣息,有泥土的氣息,有牲畜的氣息。門洞里墻壁楔進幾根釘子,掛著一把彎鋤,幾辮子蒜,和一張豬皮,就那么躺著,傾聽著風聲,和風私密地約會。
田地里的風大一些,順風時,風推著你往前跑,即使背著柴火,卻一樣的輕松,好像走路的腳不是自己的,不花力氣就動了,狠的時候,還能推你一個趔趄。頂風時,艱難得像是推著沉重的磨。從村莊到莊稼地的鄉道,走著我的祖父,走著我的父親,走著父親的祖父,走著祖父的祖父……我的祖父背著破草筐,手里握著一把鐮,鐮刀的黃楊木把被汗漬和手上的繭花磨得油光閃亮。早些年,他還牽著一頭溫順的黃牛下地,牛蹄印在泥道上,沉穩持重的牛像是把風踩碎,風吹過它的眼睛的時候,兩只銅鈴般的濕潤的眼睛,安詳隱忍,與世無爭,好像它的眼神來自另外的世界,這些風悄悄地寫進了牛清澈的眼眸。牛老了,我的祖父也老了,牛派不上什么用場,送到了屠宰場,我的祖父依舊在田間行走,握不了沉重的锨,就拿一把輕巧的鐮。他盡最大的努力彎下腰,用雙手撮起一團牛糞,或者割掉一把青草。祖父彎著腰,漸漸地再也直不起來,我懷疑真正的兇手不是莊稼與土地、莊稼與土地上不分晝夜的操勞,分明是田間的風,一點一點把他的體形吹成了弓形。我真的希望這些風朝著相反的方向運作,讓祖父的腰背奇跡般地挺立起來。祖父曾經潮濕的黑發,被風吹干了,灰撲撲的,干成了一蓬枯柴。他身上平展的含有水的柔韌富有彈力的肌膚,被風吹皺了,吹皺了的一池秋水一樣,皺紋滿面,皺紋壓著皺紋,皺紋間掩藏著無盡的滄桑。
篇6
關鍵詞:生命 家園 存在
蘇教版“月是故鄉明”這一板塊都是圍繞著“家”“家園”等一系列關于“家園之思”這一命題展開。對故鄉山水、風土人情的眷戀,對鄉村生活的美好回憶以及對精神家園的一次次找尋,無不體現了每一個作家的鄉土情結。但是,當我在讀《今生今世的證據》這篇文章的過程當中,覺得這篇文章不僅僅停留在了對故土的眷戀,而是更深一層地以借助追憶、找尋故土的形式來叩問人類生命的本質。已經將對故土的思考上升到了一個探尋生命存在的哲學命題。
一.叩問生命的存在
關于“存在”,從哲學命題上來說是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在《今生今世的證據》中,那不斷出現的院墻、樹木等許多事物都構成了作者的生命存在。這些生活中的平常事物深深地烙印著人的印記。但是,即使是這些深懷眷念、視為珍寶的事物,作者卻有一天對它們的存在也抱有一種難以闡明的懷疑。表面上是在懷疑,可實質上作者卻在以叩問的形式去印證自己的生活,讓生命的存在在叩問中再次得到確證。
如果讀過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就會發現,在作者心頭不斷閃現的事物正是作者切身經歷過的事物,那些事物正代表了故鄉的一切。作者從鄉村走來,成為了一個游離在城市與鄉村的作家。當他再次踏上回鄉的旅途,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那種恍如隔世之感便會自然而然涌上心頭。當時間定格為“現在”,也許已經沒有人記得過往的一切了,當能夠證明自己生命存在的事物消失的時候,一個人怎能不產生對存在的疑問?
可是,作者又為何不叩問現在,甚至是未來,為何不向現在與未來找尋“今生今世的證據”呢?如果說從食指的《相信未來》中,我讀到的是對“現在”的深切懷疑,那么從劉亮程《今生今世的證據》中,我讀到的就是對現在與未來的困惑。作者劉亮程活在了不能自拔的屬于自己的過往年歲里,也許在那樣的年歲里他才能切實感受到生命的實在。
二.廢失家園的痛心
當時光的鐵蹄無情地踏過村莊,在歲月沖刷磨洗下的家園注定走向荒蕪。物質的存在總有行將消失的一天。面對家園廢失,任何一個人都是痛心疾首。也許這種荒蕪并非實質意義上的“荒蕪”,不過它確實已不再是從前所熟識的模樣了。作者是在用回憶去找尋一個不復存在的村莊。
僅從這篇文章我們無法得知作者為何“會對以往的一些產生懷疑”?但我們可以聯想到其他作品,例如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野夫的《鄉關何處》……一代代文人、學者懷著濃濃的情意反復述說著家園之殤,當祖祖輩輩苦苦經營與守護的故園,在現代社會中碎了一地的時候,是否也意味著人的根本價值的失格?當家園廢失,一個人是否會像丟失農具一樣丟失了自己的過往?在現在文明社會中,我們無法否認的現實是人類似乎總存在一種無根的感覺。就是這種無根的感覺讓這位從鄉村走來接受現代文明洗禮的作家對以往產生深切的追問。現代文明的沖擊甚至讓他對以往產生一種恍若隔世的虛無縹緲之感。作者是在借文字告訴我們要及時找回故土。字里行間流露著對原始鄉村生活逝去的淡淡的哀傷。
三.另一種存在
其實,劉亮程找到了一個最好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生命存在,那就用文章來承載著漸行漸遠的故土。
一代代文人、學者懷揣著那抹之不去,揮之還來的“鄉愁”,以厚重的筆觸四處找尋自己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他們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生命的存在發出本質的叩問。也許這一過程充滿艱辛與苦澀,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對生命的再次確證。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劉亮程亦是以寫作的方式來證明自己,以為此生留下“證據”。人的生命猶如蜉蝣寄世,在歷史的長河中終將湮沒。當一切不復存在,沒有人和物可以證明你此生的時候,能夠留下的也許就只有那斑斑墨跡留存的點點心曲了。
列夫?托爾斯泰說過:“寫你的村莊,你就寫了世界。”當故土的一切變得面目全非,將再也找不到那熟悉的場景,“今生今世的證據”不可再得,找不到生命的源頭,一個人或許離成為沒有根的孤魂不遠了。或許只有用文字記錄,才能讓自己的“孤魂”得到些許安慰。
篇7
從前,有一個十分美麗的小村莊,那里有一大片森林,還有潺潺的流水,十分美麗。但是,那里十分貧困,他們唯一的財富就是樹,所以,那里年年都很美,沒有發生過災難。
有一天,一個大財主來到這里,要在這里修建一個造紙廠,需要大量的木材。于是,他就讓工人去山上砍樹。村民制止他們,但經不住錢財的誘惑,也加入了砍樹的行列中來。
山上的樹一天一天地在減少,很快就只剩下光禿禿的十幾根樹木了。大財主就派一個人去把那些樹砍光。那個人在樹下抽著一根煙,用一把鋒利的斧頭砍一棵大樹。他眼里充滿了金錢的誘惑,滿腦子都是錢。一只啄木鳥飛到掉錢眼里的那個人的脖子上,啄了啄他的頭。那人因為想得太投入了,竟沒發覺。啄木鳥心想:這段木頭里一定有蟲子。那人的頭動了動,啄木鳥才驚奇地發現,這是個人!啄木鳥急忙驚慌地飛走了,一溜煙就不見了。
篇8
例1 如圖,一條公路的兩側有六個村莊,要建一個車站,要求到六個村莊的路程之和最小,應該選在哪里最合適?如果在[P]的地方增加了一個村莊,并且沿著地圖的虛線修了一條小路,那么這時車站設在什么地方好?
證明 以公路為數軸,設六個村莊在數軸上的坐標分別為[a1,a2,a3,a4,a5,a6].如果車站建在[x]處,由絕對值不等式得,
[S(x)=|x-a1|+|x-a2|+…+|x-a6|]
[≥|(x-a1)+(x-a2)+(x-a3)-(x-a4)-(x-a5)-(x-a6)|]
[=|a4+a5+a6-a1-a2-a3|].
等號在[x∈[a3 ,a4]]時取到,所以應在第三個或第四個村莊之間建造車站.如果在[P]處再增加一個村莊,同理知建在[D]處較好.
點撥 本題顯然是一道實際應用問題,其中所用的數學知識不多,但注重分析能力.所謂分析問題,就是把事實看清楚,把道理說明白,說得有頭緒,說得恰到好處.把問題解決以后,可以再想一想,如果有[n]個村莊怎樣?如果還是六個村莊,但是要考慮乘車人數又怎樣?這類問題叫做原題的推廣.為了提高我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積累我們的知識,應當注意用這種推廣的方法來進行學習.
基本不等式
例2 若正數[a,b,c]滿足[a+b+c=1],
求證:[(a+1a)(b+1b)+(c+1c)≥100027].
分析 在學習“不等式的證明”時,大多都證明過這樣的習題:若正數[a,b]滿足[a+b=1],求證:[(a+1a)(b+1b)≥254].解決這道習題并不困難,現簡證如下:先得到[0
證明 因為本題的不等式,當且僅當[a=b=c=13]時取等號,為了使[a+1a=a+1ma+1ma+…+1ma](共[m]個[1ma])能使用平均值不等式且等號能夠取到,須[a=1ma]且[a=13],得[m]=9.所以有如下證法:
[a+1a=a+19a+19a+…+19a](共9個[19a])
[≥10a(9a)910].
同理,有[b+1b≥10?b(9b)910,c+1c≥10?c(9c)910] .
所以[(a+1a)(b+1b)(c+1c)≥103?abc(93abc)910].
再由[0
[(a+1a)(b+1b)(c+1c)≥100027](當且僅當[a=b=c=13]時取等號).
柯西不等式
例3 設[a1>a2>…>an>an+1],求證:[1a1-a2+][1a2-a3+…+1an-an+1+1an+1-a1>0].
分析 前[n]個式子都大于零,第[n+1]個式子小于零,可將原不等式化為[1a1-a2+1a2-a3+…+][1an-an+1>1a1-an+1],即[(a1-an+1)(1a1-a2+1a2-a3+…][+1an-an+1)>1]. 再由[a1-an+1=(a1-a2)+(a2-a3)+…+][(an-an+1)]結合柯西不等式證明.
證明 原不等式可化為
[(a1-an+1)?(1a1-a2+1a2-a3+…+1an-an+1)>1],
又[a1-an+1=(a1-a2)+(a2-a3)+…+(an-an+1)],
于是[[(a1-a2)+(a2-a3)+…+(an-an+1)]?(1a1-a2+][1a2-a3+…+1an-an+1)≥n2>1],
[即(a1-an+1)?(1a1-a2+1a2-a3+…+1an-an+1)>1,]
[1a1-a2+1a2-a3+…+1an-an+1>1a1-an+1].
故[1a1-a2+1a2-a3+…+1an-an+1+1an+1-a1>0].
點撥 使用柯西不等式時,既要注意它的數學意義,又要注意它的外在形式.當一個式子與柯西不等式的左邊或右邊具有一致形式時,就可以考慮使用柯西不等式對這個式子進行縮小或放大.
排序不等式
例4 有10個人各拿一只水桶去接水,設水龍頭注滿第[i]([i]=1,2,…,10)個人的水桶需要[ti]分鐘,假定這些[ti]各不相同.問只有一只水龍頭時,應如何安排10個人的順序,使他們等候的總時間最少?這個最少的總時間等于多少?
解析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需要將它數學化.若第一個接水的人需[t1]分鐘,接這桶水時10人所需等候的總時間是[10t1]分鐘;第二人接水的人需[t2]分鐘,接這桶水時9人所需等候的總時間是[9t2]分鐘;如此繼續下去,到第10個人接水時,只有他一個人在等,需要[t10]分鐘.所以,按這個順序,10個人都接滿水等待的總時間(分)是[10t1+9t2+…+2t9+t10].
篇9
有一次,彼得問他的爺爺:“爺爺,咱們村里那條沒人走的路到底通往哪里呀?”爺爺也皺了皺眉頭,說:“其實我也不清楚。”即善良又愛冒險的小彼得這下來了精神,心想:我一定去看看。
轉天早上,天還沒亮,彼得就瞞著爺爺,偷偷的背著自己的行李走上了那條路。小彼得走著走著,已不知各種意想不到的困境正悄悄的靠近著他。望著那比人都高的草叢,不覺有些膽戰心驚,彼得定了定神,就繼續往前走了。突然,眼前出現了一個會飛的怪人,耳邊飄過一道聲音:“我是掌管生死的神,你不要害怕,你的前面有個村莊,那里的村民得了瘟疫,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不過,你要記住,只有用你的血液才能救他們,他們的生命就在你的一舉了。”彼得走進了村莊,看到那些窮苦又得了瘟疫的村民們,彼得心想:如果用我一個人的生命能拯救這一群人,那我愿意!彼得在獻出生命之前是多想見他爺爺一面呀!彼得費盡了千辛萬苦終于拯救了村民們,可自己卻倒下了。
當彼得醒來時,發現自己還沒死,而且也并不存在什么村莊和村民。可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輛馬車,馬車里全是金銀珠寶。不一會兒,那個死神又說話了:“我等你已經等了百萬年了,你是一個勇敢善良的小男孩,并有著一顆舍己為人的心,這些珠寶是你應得的,去回村子吧。”原來剛才是死神在考驗他。
村子里的人都很擔心彼得,當見到彼得后都很開心。彼得把得來的珠寶分給了每一個村民,讓村里富了起來,并一五一十得把自己的經過告訴了村民。村民聞訊就都紛紛去那條路尋寶,可誰都沒有看見那個死神,他們個個都是“竹籃子打水——空手而歸”。
漸漸的村里的人又都淡忘了那條路。
篇10
我的小村莊坐落在雁蕩山麓,它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竹源。村莊居群山之間,綠水之濱,翠竹隱隱,四季常青。那條悠長綿延的鄉間小徑,有著荷鋤歸來的農夫,騎牛吹笛的牧童,池塘浣衣的村婦,還有提籃擇菜的老嫗。稀稀疏疏的一座一座木屋后面是一條小溪,流水潺潺,魚蝦嬉戲。夏天時,這里是孩子們的樂園,可以盡情玩水,捕捉魚蝦。小溪也是一條最動人的線條,它流暢、空靈,它智慧、偉大,它造就了文明,它源源不斷。鄰居們友好相處,相互往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陽光照著山坳里的小小村莊,沒有風,炊煙直直地上升,仿佛一幅簡筆畫,意境古典而又悠遠。
院子里,母雞匍匐在松軟暖的稻草之上,它的眼神慈祥,透射著母親般的溫暖。它的身邊圍著幾只羽毛還沒有長全的小雞,用紅色的小嘴蹭著母親的翅膀,好像要找到比陽光更厚的暖。大黃狗總愛守在家門口向村口望去,好像在等一個人的到來,又似在回憶以往歡樂的時光,它也偶爾嬉戲,累了便躺在草坪上沐浴陽光。老牛在一旁悠閑地臥著,它老了,再也不能工作了。那斑駁蹄子上滿是歲月的痕跡,是勤懇的象征。昔日的它是村中的大功臣,它眺望著這富饒的鄉村景象,仿佛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健壯的它在烈日下,在風雨中,耕犁一塊塊田地,走過了無數的春秋。陽光照著老牛金黃的歲月。
古色古香的祠堂,有些年代了,散發出神秘的幽香,木質的門窗貼著“慎終追遠”的虔誠祭語,那頂梁的微微裂痕,昭示著歲月和子孫的忠誠。墻壁上祖祖輩輩的照片,還有那一墻的榮譽,會讓人生起自豪感。陽光灑滿古典的金黃,祖先滿臉安靜和慈祥。
這里的每一個人在山外的大都市都見過繁華,聽過喧囂。但一回到這里,所有人都安安靜靜的,不會打擾這里的緩慢和安詳。
(指導老師:閆繼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