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權(quán)的探析論文
時間:2022-10-18 10:28:00
導(dǎo)語:人格權(quán)的探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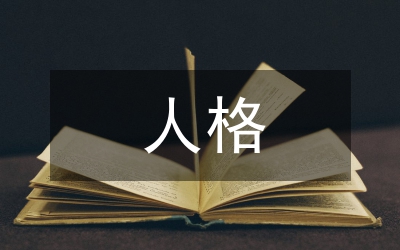
【摘要】人權(quán)是憲法和民法確認和保護人格權(quán)的共同價值基礎(chǔ),人格權(quán)是人權(q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xiàn)代法律體系中,憲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發(fā)展自然會受到憲法的約束,但這種約束只能是間接的。憲法中有關(guān)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的規(guī)定只能通過其體現(xiàn)的人權(quán)價值間接影響民法人格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它只能為民法上人格權(quán)的存在和發(fā)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據(jù),民法上人格權(quán)仍應(yīng)由民法來確認。
【關(guān)鍵詞】人權(quán)憲法權(quán)利人格權(quán)
人格權(quán)是社會個體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是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種基礎(chǔ)性權(quán)利。現(xiàn)代世界各國憲法均將人格權(quán)的保護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別人格權(quán)或一般人格權(quán)的規(guī)定。同時,根據(jù)各種人權(quán)國際公約和人權(quán)法學(xué)理論,人格權(quán)也是人權(q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xiàn)代社會,盡管人們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確認和保護人格權(quán)的重要性,但對其性質(zhì)仍有爭論,即人格權(quán)究竟是人權(quán)、憲法權(quán)利還是民事權(quán)利。本文擬通過對人權(quán)、憲法權(quán)利與民事權(quán)利三者關(guān)系的分析,探討不同法領(lǐng)域中的人格權(quán)性質(zhì)有無差異。
一、何謂人權(quán)
在現(xiàn)代社會“人權(quán)”概念既是一個非常流行的用語,也是一個理解上非常混亂的概念。有學(xué)者通過考察,指出人們往往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quán)一詞,用來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張。例如,有的在道德意義上使用,將人權(quán)與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聯(lián)系起來;有的在法律意義上使用,將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利甚至國家意志等同;有的強調(diào)人權(quán)中的個人自由和政治權(quán)利,以致僅在此意義上使用;有的則強調(diào)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quán)利,尤其是民族自決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1正如國外學(xué)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權(quán)的神圣名義,不論其可能意味著什么,都能被人們用來維護或反對任何一個事物”,“人權(quán)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這句話既道出了人權(quán)概念之所以紛繁復(fù)雜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權(quán)概念的不易。確實,各個國家、民族、階級、派別、個人,由于經(jīng)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fā)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對人權(quán)概念的理解也會有所不同;同時人權(quán)本身作為一個學(xué)術(shù)概念也過于寬泛和復(fù)雜,對人權(quán)及其歷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jīng)濟、法律、哲學(xué)、宗教、倫理諸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歷史的解釋。3
但是,人權(quán)作為一個被人們接受的概念,對其內(nèi)涵和外延的理解應(yīng)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有學(xué)者通過對西方人權(quán)歷史和學(xué)說的考察,認為二戰(zhàn)以前西方的人權(quán)學(xué)說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義兩種思想為基礎(chǔ),戰(zhàn)后的人權(quán)學(xué)說除了繼承和改造戰(zhàn)前的自然法學(xué)說和功利主義思想之外,還增加了從自然法思想演變而來的抽象的正義論和人本主義思想;通過西方學(xué)者對人權(quán)定義的分析,認為其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一、他們大多以人本主義思想為基礎(chǔ),也即人權(quán)是人之所以為人所享有的權(quán)利;二、他們大多主張人權(quán)是一種道德或倫理權(quán)利,只有當它由實在法加以規(guī)定時,才同時具有法定權(quán)利的性質(zhì)。4在對人權(quán)概念的認識上,對人權(quán)哲學(xué)有深入研究的英國法學(xué)家米爾恩(A·J·M·Milne)認為,《聯(lián)合國世界人權(quán)宣言》中對人權(quán)的認識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為基礎(chǔ),其所提出的人權(quán)的理想標準主要是由體現(xiàn)自由主義民主工業(yè)社會的價值和制度的權(quán)利構(gòu)成的,但基于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其他國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會的模式,其所確定的人權(quán)標準也不一定適合這些國家,它們應(yīng)該根據(jù)自己的國情確定自己的人權(quán)制度;但畢竟所有的國家都是人類社會,每一個國家的成員都應(yīng)享有僅僅因為是人而享有的權(quán)利,這就是米爾恩所說的“最低限度標準的概念”,“它是這樣一種觀念:有某些權(quán)利,尊重它們,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的要求”,而這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是以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為前提的,它的普遍適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權(quán)利獲得普遍承認,但同時它所要求的普遍權(quán)利也必須根據(jù)特定場合來解釋。5由此可見,米爾恩所主張的人權(quán)是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權(quán)利,同時它也是要求各個國家根據(jù)自己的國情變通吸收的權(quán)利。從這種意義上講,雖然這種人權(quán)并不對各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國采納人權(quán)制度的指導(dǎo)思想和價值基礎(chǔ)。美國學(xué)者杰克·唐納德(JackDonald)通過對權(quán)利行使的分析,認為人權(quán)是個人僅僅因為它是人而擁有的權(quán)利,但它是一種“最終訴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來不能發(fā)揮作用或者已經(jīng)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權(quán)的保護;同時,人權(quán)是一種道德上的權(quán)利,其要求在本質(zhì)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現(xiàn)存的制度、實際活動或者規(guī)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戰(zhàn),或者改變它們。6因此,他所講的人權(quán)也不是一種法律權(quán)利,而是一種與法律權(quán)利并列的并對法律權(quán)利起補充作用的道德權(quán)利。
我國學(xué)者在對人權(quán)概念的分析上,雖然具體的認識不盡一致,但在對人權(quán)包括應(yīng)有權(quán)利這一點的認識卻是相同的。這里的應(yīng)有權(quán)利中“應(yīng)有”的含義就是指,根據(jù)某種淵源或基礎(chǔ)人們應(yīng)該享有的權(quán)利。如有學(xué)者認為,人權(quán)有三種基本形態(tài),即應(yīng)有權(quán)利、法定權(quán)利和實有權(quán)利,其中人權(quán)在它的本來意義上是一種應(yīng)有權(quán)利,法定權(quán)利是應(yīng)有權(quán)利的法律化,是一種更有保障的人權(quán),實有權(quán)利是人們實際能夠享有的權(quán)利;從本質(zhì)上講,人權(quán)是受一定倫理道德所支持和認可的人應(yīng)當享有的各種權(quán)益。7也有學(xué)者認為,人權(quán)有四種存在的形態(tài):(1)應(yīng)有權(quán)利;(2)法定權(quán)利;(3)習(xí)慣權(quán)利;(4)現(xiàn)實權(quán)利。8還有學(xué)者認為,人權(quán)是每個人都享有或應(yīng)該享有的權(quán)利,它是在道德權(quán)利、普遍權(quán)利和反抗權(quán)利這三種意義上使用的。9還有學(xué)者通過對西方和我國學(xué)者對人權(quán)的認識的分析,認為人權(quán)即人的權(quán)利,是人(或其結(jié)合)應(yīng)當享有和實際享有的,并被社會承認的權(quán)利的總和。10一般來說,西方的學(xué)者多從自然法的角度來論證人權(quán)的應(yīng)有的含義,而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dǎo)的我國學(xué)者多從社會發(fā)展的角度來論證,但無論如何,都認為人權(quán)與實定法所確認的,特別是憲法所確認的具體權(quán)利是不同的,人權(quán)雖然有一部分表現(xiàn)為法定權(quán)利,而且人權(quán)發(fā)展的最終目的就是不斷地將其轉(zhuǎn)化為法定權(quán)利,但人權(quán)始終是高于法定權(quán)利的,它既可以用來為法定權(quán)利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依據(jù),也可以用來批判法定權(quán)利,促使法定權(quán)利的制定符合人權(quán)的要求。
二、人權(quán):憲法和民法的共同價值基礎(chǔ)
在現(xiàn)代社會,人權(quán)與憲法的關(guān)系日益密切,因為憲法從法律效力秩序上來講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guī)范,為體現(xiàn)對人權(quán)的重視,多數(shù)國家都在憲法中對基本人權(quán)有所規(guī)定,有的國家甚至將憲法權(quán)利直接視為“基本人權(quán)”,如日本。從現(xiàn)代世界各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人權(quán)內(nèi)容來看,憲法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原則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11一是既明確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原則,又以公民具體權(quán)利的形式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的內(nèi)容,這是多數(shù)國家憲法采取的形式,如日本憲法和孟加拉國憲法。二是不明文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原則,只是規(guī)定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如美國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的原則,卻在修正案中具體規(guī)定了公民的權(quán)利。此外,還有比利時、丹麥和荷蘭等國的憲法也是如此。三是原則上確認基本人權(quán),但對公民基本權(quán)利的內(nèi)容卻較少規(guī)定,如法國現(xiàn)行憲法雖然在序言中確認人權(quán)原則,但只對公民的選舉權(quán)利作了規(guī)定。各國憲法對人權(quán)的規(guī)定并沒有改變?nèi)藱?quán)的性質(zhì),人權(quán)在本質(zhì)上仍是一種道德權(quán)利,不是法定權(quán)利。人權(quán)作為道德權(quán)利與法定權(quán)利之間存在著辯證關(guān)系:“作為道德權(quán)利,人權(quán)只有表現(xiàn)為社會的(國內(nèi)社會和國際社會)權(quán)利,才會取得實效;作為法定權(quán)利,社會權(quán)利只有以人權(quán)為根據(jù),才能保持其道德上的正當性并增強其適應(yīng)效力。”就人權(quán)與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權(quán)來講,“公民權(quán)是人權(quán)在法律上的表現(xiàn),人權(quán)是公民權(quán)的道德根據(jù),憲法則是公民權(quán)的法律根據(jù)。”12人權(quán)入憲雖然沒有改變其本質(zhì),但卻為憲法中公民基本權(quán)利體系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由于憲法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條件的產(chǎn)物,隨著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憲法對公民基本權(quán)利體系的規(guī)定應(yīng)該呈現(xiàn)開放性,不斷地吸納新的人權(quán)為法定權(quán)利,而人權(quán)保障條款的入憲則為公民基本權(quán)利體系的開放性提供了憲法根據(jù)和制度保障。13因此人權(quán)作為一個內(nèi)涵和外延都在發(fā)展的概念,其入憲有利于立法者或者憲法的適用者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確認新的憲法權(quán)利。
無論現(xiàn)代法律制度如何發(fā)展,人權(quán)在本質(zhì)上都是一種道德權(quán)利,它不僅是作為公法的憲法的價值基礎(chǔ),也是整個法律秩序的價值基礎(chǔ),對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內(nèi)的整個法律體系都會產(chǎn)生影響。有學(xué)者指出,根據(jù)考察基本權(quán)利的歷史時期和考察重點的不同,對基本權(quán)利性質(zhì)的問題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樣:我們可以證明,基本權(quán)利僅以國家為規(guī)范對象;或者相反,我們也可以確認,在更早以前時代關(guān)于自由的討論中,法(包含私法)的牽連是廣泛的,如康德認為私法適用一個人的自由與其他人的自由一致的原則;《普魯士一般邦法》則保障人民(譯者此處所指的“人民”應(yīng)與“公民”同義——筆者注)的當然自由,得以在不損及他人權(quán)利的情況下追求并營造自身的幸福;卡爾·羅特塞克(Carlv·Rottceck)也指出,國家作為法的機制應(yīng)承認并維護所有人民的自由,且應(yīng)將自由認為是在所有活動領(lǐng)域中人民僅以其作為人的地位就已經(jīng)擁有的權(quán)利;如果國家并沒有侵犯人民的權(quán)利,它還須保護人民不受到來自于人民相互間、在其交往關(guān)系上可能發(fā)生的侵害;國家還應(yīng)該通過完善的法律以及法律的認真執(zhí)行,來消除對于人民一直存在的其他自由侵害,特別是在家庭中私人權(quán)力以及社會權(quán)力的濫用。14因此,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中,自由呈現(xiàn)出多面向的特征,它既反對國家權(quán)力對其加以限制,也反對私人之間的相互侵害。
但是隨著時間的經(jīng)過,個人之間的私法關(guān)系卻越來越少的被一般自由權(quán)以及基本權(quán)的討論所觸及。這與實證主義以及按照當時的社會情境能保障自由與平等的私法法典的制定有關(guān)。根據(jù)當時的自然法思想,對于個人自由與平等權(quán)的保護而言,主要關(guān)注的是對國家權(quán)力的限制,并通過立法加以表達,這種思想反映在歐洲各國的基本權(quán)利宣言中,就形成了近代憲法為“限權(quán)法”的理念;以這些宣言為導(dǎo)向的古典基本權(quán)利概念,被認為是維護個人的消極自由地位、反制公權(quán)力、認為個人擁有某種不受國家干預(yù)領(lǐng)域的權(quán)利,并以限制國家侵害個人權(quán)利領(lǐng)域的權(quán)限為主。15因此,從歷史沿革來看,人權(quán)或者上述引文中的基本權(quán)利本來是整個法律體系所要保護的對象,不僅應(yīng)該受到公法的保護,在私法中也應(yīng)該有所體現(xiàn)。但由于當時處于資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基于強調(diào)個人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需要,就把人權(quán)或者基本權(quán)利僅僅視為是針對國家的權(quán)利,將之載入憲法,并基于公私法的劃分,將其稱為公民享有的公權(quán)利。但就其本質(zhì)而言,人權(quán)并不是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法定權(quán)利而是一種道德權(quán)利,它是公法和私法共同的價值基礎(chǔ),如德國基本法和德國民法典都以倫理人格為精神基礎(chǔ),并以之指導(dǎo)基本法與民法的發(fā)展。
三、人格權(quán):憲法權(quán)利抑或民事權(quán)利
人權(quán)作為人之所以為人所享有的權(quán)利,其內(nèi)容廣泛,而人格權(quán)則是人權(quán)最為重要的內(nèi)容。現(xiàn)代世界各國基于對人格權(quán)的重視,都在憲法和民法中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制度。從其內(nèi)容來看,憲法中的人格權(quán)和民法中的人格權(quán)大部分在名稱、內(nèi)容方面都是相同的,如兩者都對生命、健康、身體、隱私等人格權(quán)作出規(guī)定。在民法上的人格權(quán)制度不完善的國家,司法者通過引用憲法中的人格權(quán)條款來發(fā)展民法中的人格權(quán)制度,最為典型的就是德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依據(jù)德國基本法第1條和第2條關(guān)于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的規(guī)定創(chuàng)制出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制度。因此,民法上規(guī)定和保護的人格權(quán)與憲法關(guān)系密切,但能否得出人格權(quán)就是憲法權(quán)利的結(jié)論呢?這需要我們具體分析。
1、對人格權(quán)性質(zhì)的爭議及其具體分析
有學(xué)者通過考察認為,早期各國民法典之所以未對人格權(quán)作出正面的賦權(quán)性規(guī)定,而僅僅作出概括的或者具體的保護性規(guī)定,是因為在這些民法典的編纂者看來,自然人人格的普遍確認是整個近代法律制度的基礎(chǔ)和起點,而人格權(quán)或者為一種自然權(quán)利,或者為一種法定權(quán)利,根本就不是源于民法的授予,人格權(quán)的地位高于民事權(quán)利,民法的任務(wù)僅僅在于用產(chǎn)生損害賠償之債的方式對之予以私法領(lǐng)域的法律保護;同時,該學(xué)者還通過考察德國聯(lián)邦法院借助基本法的規(guī)定創(chuàng)制一般人格權(quán)的事實,認為人格權(quán)從來就不是一種由民法典創(chuàng)制的權(quán)利,而是一種具有憲法性質(zhì)的權(quán)利;該學(xué)者還認為,德國民法中在侵權(quán)行為法中已經(jīng)規(guī)定了具體的人格權(quán)類型,如生命、身體、健康、自由、信用、婦女貞操等,如果德國民法典的編纂者不是將人格權(quán)真正視為民事權(quán)利,那么,具有“抽象化偏好”的德國人沒有理由不去建構(gòu)內(nèi)容如此豐富的人格權(quán)體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人格權(quán)是一種應(yīng)該由基本法直接規(guī)定的權(quán)利,民法可以“分解”這種權(quán)利加以保護,但民法不是“創(chuàng)設(shè)”這種權(quán)利的上帝。16也有學(xué)者認為,根據(jù)德國法院創(chuàng)制“一般人格權(quán)”的思維,人格權(quán)的觀念發(fā)生了根本性的革命,由以前的“民法典權(quán)利”一躍而成為“由憲法保障的基本權(quán)利”,人格權(quán)的類型及其內(nèi)容不再是狹窄地以民法典為基礎(chǔ),而是可以直接援引憲法規(guī)范為支持。17
筆者認為僅憑上述考察,就認為人格權(quán)不是民事權(quán)利而是憲法權(quán)利是不充分的。早期法國民法典之所以沒有對人格權(quán)加以規(guī)定,是因為此時以維護人格尊嚴思想為基礎(chǔ)的人格權(quán)概念尚未產(chǎn)生,它直到康德的倫理主義哲學(xué)將人類尊嚴與法律人格概念結(jié)合之后才有可能出現(xiàn),如此要求法國民法典的編纂者規(guī)定人格權(quán),未免不切實際。因此,當時法國的立憲議會議員從未想過要就人格權(quán)提出什么宣言。18
其實德國民法典中之所以沒有規(guī)定一般人格權(quán),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人格權(quán)是所謂的憲法權(quán)利,而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可能承認一項“對自身的原始權(quán)利”,否則就會得出存在一項“自殺權(quán)”的結(jié)論;第二,債的產(chǎn)生以財產(chǎn)價值受到侵害為前提,而對人格權(quán)的侵犯如果產(chǎn)生金錢損害賠償之債,在當時人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認為這將會導(dǎo)致人格價值的商品化,貶低了人格尊嚴;第三,人格權(quán)的內(nèi)容和范圍無法予以充分明確地確定。19正因為如此,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才未采取當時已經(jīng)有學(xué)者提出的一般人格權(quán)概念。而且,對于一般人格權(quán)的保護及規(guī)定問題,第42屆德國法學(xué)會議于1957年提出討論,匯為專冊,并建議制定特別法以保護人格權(quán),聯(lián)邦德國司法部接受法學(xué)會議的決議,于1958年起草“修正民法上保護人格及名譽規(guī)定草案”,但該草案在于1959年提交國會后,也未能為國會所接受。20即使是到現(xiàn)在,雖然第一個理由和第二個理由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已經(jīng)不再是反對制定一般人格權(quán)條款的主要理由,但第三個理由即人格權(quán)的內(nèi)容和范圍難以界定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這個法學(xué)理論上的特別是法律技術(shù)上和實踐上的難題仍然阻礙著一條保護人格的一般性法律規(guī)定的產(chǎn)生。21也正因為這些難題,偏好抽象的德國人難以抽象出人格權(quán),因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者關(guān)注的不僅是概念的抽象性,還有概念的確定性和可把握性,而一般人格權(quán)的概念難以符合這些要求。
對于人格權(quán)在民法制度中的發(fā)展,有些學(xué)者僅僅看到了德國依據(jù)基本法創(chuàng)制一般人格權(quán)的情形,而忽視了考察其他國家的民法典中的人格權(quán)制度發(fā)展的實際。如瑞士民法典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民法典均明確規(guī)定了一般人格權(quán),在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人格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中,并不需要依據(jù)憲法來創(chuàng)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雖說德國法創(chuàng)制一般人格權(quán)的依據(jù)是基本法,但一般人格權(quán)并不是直接依據(jù)基本法的條文創(chuàng)造的,而僅是依據(jù)基本法第1條和第2條所體現(xiàn)的客觀價值創(chuàng)造的,這種客觀價值是整個法律秩序而不僅僅是作為憲法的基本法的價值基礎(chǔ),聯(lián)邦法院最終認定的一般人格權(quán)也不是憲法上的權(quán)利而是一種民事權(quán)利。因此,對人格權(quán)性質(zhì)的認定,我們不能僅憑德國民法制度中一般人格權(quán)的確立和發(fā)展模式,就認定人格權(quán)是憲法權(quán)利,這樣理解是不妥當?shù)摹?/p>
2、憲法中的人格權(quán)與民法中的人格權(quán)
人格權(quán)作為社會個體享有的一項基本人權(quán),不僅私人之間會互相損害它,而且掌握著比私人大得多的強制力量的國家對它造成損害可能會更大,因此,對于人格權(quán)的保護不僅是調(diào)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民法的任務(wù),也是限制國家權(quán)力的憲法的任務(wù),相應(yīng)的也就會產(chǎn)生民法上的人格權(quán)和憲法上的人格權(quán),因其人格權(quán)所調(diào)整的社會關(guān)系不同,兩者應(yīng)屬于性質(zhì)不同的權(quán)利。當我們將人格權(quán)看作是自然人(和法人)針對其他私人所享有的權(quán)利時,它是一項民事權(quán)利;當我們將其看作公民個人對抗國家公權(quán)力的權(quán)利時,它是一項憲法權(quán)利。憲法上的人格權(quán)雖然與民法上的人格權(quán)名稱相同,但我們不能將兩者混同,前者作為公民享有的基本權(quán)利旨在保護公民免受國家強制力的損害,后者作為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權(quán)旨在調(diào)整民事主體之間發(fā)生損害的情形。在德國,對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聯(lián)邦憲法法院僅僅是認為,并不存在憲法層面上的反對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但是由于兩者有著同樣的名稱,這就隱藏著一種危險,“即在法律適用時忽略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而且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在某種程度上正變得模糊,這是因為“一般人格基本權(quán)利被賦予了直接的輻射效力”,而且即使“我們拒絕承認具有這種直接的輻射效力,我們?nèi)匀豢梢酝ㄟ^下列方式影響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即根據(jù)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確立積極的給付請求權(quán):要么使用合憲性解釋的方法,要么選擇清晰無比的法治國家途徑即修改法律”;當然,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通過混淆侵權(quán)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概念與憲法上的一般人格基本權(quán)利概念的方法,來達到后者的直接輻射效力”,但這種混淆概念的做法卻存在著下述危險:即法官法過分強烈的干預(yù)立法者的職責。22因此,憲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與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權(quán)性質(zhì)不同,保持兩者的區(qū)別對于整個法律體系秩序的維護具有重要的意義,即堅持立法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的合理分立,有利于防止法官擁有過度的自由裁量權(quán),以維護私人領(lǐng)域的自治性。
對于人格權(quán)而言,雖然可以將其區(qū)分為憲法上一般人格權(quán)與民法上一般人格權(quán),但兩者又因為人權(quán)而發(fā)生必然的聯(lián)系,即憲法基本權(quán)利通過其所體現(xiàn)的人權(quán)價值影響民法人格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這點在德國憲法法院在“路特案”的判決中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在該案的審理中,憲法法院認為,在基本權(quán)利中可以發(fā)現(xiàn)“客觀價值秩序”,這種價值秩序遍及全部的法律體系,特別強烈的影響那些以有約束力的規(guī)則代替當事人意志的法律領(lǐng)域;這些客觀價值對公共利益是根本性的,應(yīng)該被保護防止不管來自何方——公的或私的侵害;在這里,憲法法院不再宣稱基本權(quán)利的規(guī)定對私人關(guān)系具有直接效力,而是主張憲法秩序“影響而不是管制私法規(guī)范”。23這里所謂的“客觀價值秩序”實際上就是道德意義上的人權(quán),憲法規(guī)范不能直接適用于私人之間的法律關(guān)系,只能通過其所體現(xiàn)的人權(quán)價值影響私法的解釋和適用。有學(xué)者認為,私人之間在彼此的交往時之所以必須相互尊重對方的生命、名譽與財產(chǎn),并非是因為所有人都應(yīng)受憲法基本權(quán)利拘束的結(jié)果,而是源自于人類共同生活的傳統(tǒng)常規(guī),這個傳統(tǒng)常規(guī)是最基本的,連基本權(quán)利都要以它為基礎(chǔ)來建構(gòu);同時,“無論是根據(jù)基本權(quán)利的客觀法面向或其他方法,都舉不出堅強理由說明為何基本權(quán)利也可以在私法領(lǐng)域類推適用。只有支配整個法秩序,同時也表現(xiàn)在基本權(quán)利上的有關(guān)人類圖像(Menschenbild)的價值判斷,才能影響民法的立法者以及適用概括條款的民事法院的法官。”24這里的“傳統(tǒng)常規(guī)”、“人類圖像的價值判斷”實際上也是道德意義上的人權(quán),它既影響憲法基本權(quán)利的發(fā)展也影響民法的制定。
綜上所述,人格權(quán)作為人權(q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證的法律體系中可以分為憲法上的人格權(quán)和民法上的人格權(quán),兩者是不同性質(zhì)的權(quán)利。雖然在現(xiàn)代社會,人權(quán)中的法定人權(quán)主要在憲法中規(guī)定,但在本質(zhì)上作為一種道德權(quán)利的人權(quán),體現(xiàn)的是整個法律體系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它對憲法上的人格權(quán)和民法上的人格權(quán)都具有指導(dǎo)意義。現(xiàn)代法律實踐只能根據(jù)憲法基本權(quán)利條款所體現(xiàn)的人權(quán)價值來影響民法人格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憲法在這里只是提供了民法人格權(quán)制度存在和發(fā)展的合法性、合理性依據(jù),民法上人格權(quán)的確認和保護仍應(yīng)由民法來完成。
(本文發(fā)表于《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5期)
【注釋】
1、3、9、12參見夏勇:《人權(quán)概念起源》,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原版序言部分,第176頁、第221、222頁。
2Holleman:《theNaturalRightMovement》PragerPublishers,1987.p4.轉(zhuǎn)引自沈宗靈:《比較憲法》,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
4參見沈宗靈:《比較憲法》,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7頁。
5A·J·M·米爾恩:《人的權(quán)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quán)哲學(xué)》,夏勇、張志銘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導(dǎo)論部分。
6杰克·唐納德:《普遍人權(quán)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7—12頁。
7參見李步云主編:《憲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438頁。
8張文顯:《論人權(quán)的主體與主體的人權(quán)》,《中國法學(xué)》1991年第5期。
10羅玉中、萬其剛、劉松山:《人權(quán)與法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11殷嘯虎主編:《憲法學(xu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頁。
13焦洪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的憲法分析》,《中國法學(xué)》2004年第3期。
14、15[德]克里斯提安·史塔克:《基本權(quán)利與私法》,林三欽譯,載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編輯:《當代公法新論》(上冊),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00、401頁、第401頁。
16尹田:《論人格權(quán)的本質(zhì)》,《法學(xué)研究》2003年第4期。
17龍衛(wèi)球:《論自然人格權(quán)及其當展進路》,《清華法學(xué)》(第2輯),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18[法]薩瓦第埃:《當代私法的社會與經(jīng)濟條件的變化》,第336頁。轉(zhuǎn)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闖譯,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八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頁。
19、21、22[德]穆格丹:《德國民法典立法資料匯編》(第2卷),第1072頁、第1077頁、第1119頁;(第3卷),第61頁。轉(zhuǎn)引自[德]霍爾斯特·埃曼:《德國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權(quán)制度》,邵建東等譯,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頁、第413頁、第469-471頁。
20施啟揚:《從個別人格權(quán)到一般人格權(quán)》,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81頁。
23MarkesinisBS:Alwaysonthesamepath:essaysonforeignlawandcomparativemethodology,vol.2.Hart,2001.p135.
24ChristianStarck:《基本權(quán)利的解釋與影響作用》,許宗力:《法與國家權(quán)力》,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01頁。
- 上一篇:國外民法中形成權(quán)探究論文
- 下一篇: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探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