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學與藝術設計研究
時間:2022-02-13 04:37:00
導語:建筑學與藝術設計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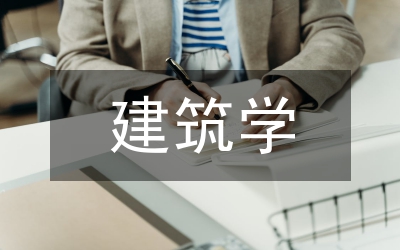
翻開建筑史和工藝美術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建筑學這一有著悠久歷史的專業學科與許許多多的藝術設計門類如:紡織品、工業產品、家具設計等,存在著某種不容忽視的緊密聯系。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琪羅、達·芬奇、拉菲爾,以及其后的貝爾尼尼等,歷史上的許多藝術家都曾涉足建筑設計領域,并有很高的建樹。即便是在近現代,馬克斯·比爾(建筑師、設計師、畫家、雕塑家)創建的“烏爾蒙設計學院”(,950年)、格羅皮烏斯的“包豪斯學校”,都不僅在建筑設計,還在多方面的其它藝術設計領域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和創作活動。二十世紀西方,幾乎所有的藝術設計運動(如:歐洲的藝術與手工藝運動、現代運動、后現代主義等),建筑學在其中都起著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建筑學為設計提供的思想家遍及20世紀”【1]。引導現代西方藝術設計新思潮的許多團體如意大利的“Arehizoom聯合會”、“超級工作事”、“全球工具”、英國的“Arehigram”、“NATO(今日敘事體建筑)”、美國的“構成運動”、“后現代主義”··,…都開端于建筑設計思想的新變化,但又都不只局限于建筑設計,并迅速涉及到了藝術設計的各個門類。僅舉一例:意大利的“Archiz。。m”這一激進設計運動首先是由建筑師們發動的,“正確的為他們自己設計”是他們的口號,但這一團體并非只限于建筑設計,他們對服裝和紡織物表面裝飾構成以及日用品的探索性研究,同樣引人注目。在意大利,不知是由于教育體制的使然,還是因為取得了某種成功經驗后的選擇,幾乎所有的設計師們都受過建筑方面的訓練。其實不僅在意大利,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有著建筑學教育背景的設計師們從大到汽車、家具、日用品、服裝,小到字母字體設計都作出過顯著貢獻,例不勝舉(但是,在我們國內這種現象卻很少見,建筑師們、受過建筑學教育的人們幾乎絕少涉足其它的藝術設計門類)。僅僅用“建筑學”與“藝術設計”同屬“設計”范疇,緊密相連、互通,似乎還難以全面解釋這種有普遍性的現象,因為這種“互通”似乎常是單向性的:搞服裝設計、產品設計的設計師們極少向建筑設計領域涉足。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建筑學之于我們常說的工藝美術類的藝術設計到底意味著什么?建筑學對藝術設計的作用及影響是在那些方面?或建筑學是如何與藝術設計“相通”的?疑問的產生是必然的,探討這些問題則無疑還是有必要的,尤其對于國內的設計界現狀而言。
‘建筑學具有歷史造成的強勢地位:在今天,認為建筑學也是一種藝術設計,僅在概念上也許并不存在異議。但如果在學科設置上把建筑學置于一個從屬于藝術設計的分支地位上,爭議就必然產生了,這是有原因的。這不僅是因為建筑學在歷史上、在今天早已是一個各方面完備且自成體系的專門技藝,而且因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賦予了建筑學某種高于藝術設計其它門類的強勢地位:
1.在人類歷史上直到今天,無論是對帝王或對貴族,甚至對平民而言,建筑工程都是一件大事,不論建筑物是用來供奉祀祠還是炫耀、居住,相較其它的藝術設計門類,建筑都必需涉及到大量的財力、人力、物力、技術并需要投人大量的精力,而且建筑物相較于其它設計物品時間更長,影響力更大,就這一點而言,對建筑術(建筑學)的重視是必然的。
2.人對建筑的感受源于人的基本生存機能,即建筑不僅是滿足了人的某些使用要求,同時是提供了某種生存環境—而人對環境的判斷、感知能力是生物生存根本的機能之一,建筑的藝術性和審美可能正是建基于此。
3.普遍的人類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研究對建筑學也有偏重。傳統藝術史與理論每在提到“art’’藝術一詞時,它都是包指繪畫、雕塑、建筑三者,這一點今天也仍然被人們廣泛接受。瓦薩利在其《藝術家傳略》中,最先將以上三者以同一步調展開論述,而且他第一次從中歸納出了一條共同的標準:三者都是“artofdesign”“設計的藝術”(或“結構藝術”)以及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視覺藝術的內在統一性,他還認為建筑這種非模仿性藝術要比再現性藝術處于更優越的地位12】。由此,就造就了建筑學成為藝術設計門類的總領這樣一個地位。早在14世紀,在其它藝術設計門類中如陶瓷、紡織領域,設計者已經比制造者更加引人注意,但他們在理論上、在社會中從未能取得象建筑師那樣的地位,“藝術設計”則更是一個近現代才出現的學科概念。
4、建筑學是藝術與科學的聯系紐帶。把“建筑學”與繪畫、雕塑并列是有一定的思想背景的。從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排斥藝術開始,人們總是視純藝術(繪畫、雕塑等)會有一種過分放縱的可能性,而建筑卻與他們不盡相同,建筑術不僅切合“art”藝術的原義(技巧、技藝),而且它還是一種被當時人們傾慕的實用技術。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對建筑的涉足,源于一種追尋科學的沖動,也隱含著通過這種“涉足”提高自身地位的要求(畫家在文藝復興前地位不高)。對建筑學本身的理論研究更提供了這種科學性的“佐證”:建筑與數學的關系,建筑與人、與宇宙萬物的關系,比例,尺度,風格變化的規律……今天的人們對這些“佐證”的科學性當然已有了與前人大不相同的認識,但這種影響仍在,我們今天也仍在講:對比、變化、比例、構圖、主從關系等等。這些“科學理論”對藝術設計其它門類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所有與藝術設計有關的門類中,建筑學方面的理論是最豐富、系統、全面的,對藝術設計其它門類產生的輻射作用是顯著和必然的。
5.建筑學是具有包容性和借鑒性的。建筑設計從來不是一種單純的技術活動,它更是一種融合性極強的藝術活動,建筑不能是一個空殼,它要包含陳設、家具、布藝、雕飾、燈具……許許多多的其它藝術設計門類,它和這些藝術設計門類必然會互動式的相互促進借鑒。建筑物實際上是基于某種共通設計理論基礎、社會需求的各種藝術設計制造物的整合環境。無論我們今天認為公正與否,建筑學之于藝術設計的這種強勢地位都是一種歷史使然(也是一種必然),但也許未必是一種未來的必然。
*建筑學直指藝術設計的核心:
挪威設計師昆特·伊安認為:“一個設計師在實現自己的意圖之前,必須認識到使用者的意圖”,他暗示出了藝術設計的核心問題:功能與形式的融合。“功能與形式”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它并不總是表現為矛盾沖突的兩個方面,但也不是只側重其一就可全面解決問題的。一個優秀的設計是可以兩者兼顧,平衡并不著痕跡的。建筑學在這一問題上雖然沒有一種萬能的解決方法,但卻提供了一種思維訓練程序。正如貢布里希所說:”建筑應該是證實任何一種關于人造物結構的裝飾理論的實例,因為在建筑中我們能夠從任何水平上去研究功能層次與裝飾層次之間的張力”[3】應該說,對于建筑設計的整個流程而言,功能與形式問題比其它藝術設計門類都強烈、復雜,并貫穿始終:從開始著手設計時對地域、環境、人文、水土、總體造型考慮;設計中對人流路線、功能分區、結構可行性、個人與群體的功能需求、空間感受、構件造型的逐項分析、與水、電、氣的功能協調;直到建設中與完工后的使用與美觀方面的反饋分析。
功能與形式總是交織并重在一起,需要時時注意給予通盤考慮。在多種復雜的限定條件下滿足使用功能又使之具有宜人的美感形式一這種要求與創作訓練,無疑也會對進行其它門類的藝術設計大有裨益。
建筑設計中,功能與形式密不可分的特點是被用于創造具有某些使用功能的“空間”的。建筑“空間”這一概念出現于十九世紀末,但創造空間這一活動卻與建筑的歷史一樣長。建筑師是用某種思維能力—“空間感”去完成這一工作的。在建筑設計中,“空間感”是建筑師的“神游”性的想象力,即如菲利普·約翰遜的“行徑FOO下戶RINT’’、柯布西耶的“路線ROU下E”。簡而言之,即建筑師在設計中不單單是去構想建筑中的“面”的組合,也不單單去構想“體”的嵌接,而是以想象力“行進”、穿梭于建筑各部分、內與外、高與低,多視角的預見一番設計的視覺及使用效果。穆哈利·納基認為:“空間的體驗并不僅作于少數的天才的專利,而是屬于一種生物學的機能”[4〕,這種能力以及對這種能力的訓練,建筑學是很有其長處的(當然,這并不等于說不經過建筑師的訓練就不可能具有這種能力),而這種能力對許多藝術設計如:服裝、汽車、日用品甚至許多平面設計(大型招貼所需要的多視角考慮)都是極重要的。我們從西彼勒·克歇爾(《。ltVetti》,990年)對意大利Olivetti設計公司的介紹中得知,意大利的設計師們通常首先創}陳作為建筑師,然后試圖更肯定他們作為獨立藝術家的角色,“戲劇”被視為設計過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所說的“戲劇”實際上與英國設計師們提倡的敘事體和比喻特征相類似,都是一種加上了時間程序、節奏、視覺上的情節鋪墊,沖突、矛盾、高潮起伏等,“戲劇話語趣味”的“空間感”想象化的設計。
應該說,當設計師具備了在多種復雜限制下全面考慮功能與形式的思考方式,多視角、多層面體會觀察的空間感受能力以及以趣味化、戲劇化吸引人的構思,那么這些能力就已經不只可以用來完成建筑設計,而且更可兼顧幾乎任何門類的藝術設計了。
*建筑學的社會性:
建筑常是令人矚目的社會生產活動。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大投人(財力、人力、技術力量),另一方面是因為建筑活動是創造一種人工環境的行為,而人對環境的感受是一種強于對其它藝術物品感受的本性化感知能力,這一點可能追溯到人作為環境中的生物物種的生存本能。可能基于以上兩方面,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建筑物還常常被賦予許多思想上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甚至是世界觀、哲學上的含義。建筑物常常被用來表達某種思想,并集中體現出歷史傳統、時代、社會風貌及審美趣味(這一點在學術上還有爭議)。人類歷史早期對神抵的尊崇(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主義”建筑風格所反映的“人文精神”,由于政治原因18世紀英、法“古典復興”對古希臘、古羅馬建筑風格針對性的選擇,以及二十世紀現代派建筑風格對時代風貌的追求·,·…用建筑來反映思想也許要比其它藝術品更能引人注目,更強烈并更具“歷史標志性”。所以在西方,建筑思想常常被上升為某種“哲學觀念”(這與音樂學有某種相似性,音樂學最終也被升華為哲學)。
建筑師則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被賦予許多社會責任。實際上,在建筑設計活動中,建筑師的確也常能感受到這種自身的能力,通過某些規劃與設計,建筑師常能限制或引導、控制許多人類社會或個人活動,創造某種氛圍或破壞某種環境。在上個世紀中葉,建筑師又被視為”社會工程師”(雖然今天人們已經可以開始比較理智地看待這一論斷),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建筑師的這種社會責任感,使其自身的創作行為總是被置于一種引人矚目的社會性的大背景之下,敏銳地與社會新動態、新思想相聯系,也就成為主動或被動性的必然,所以,新的藝術設計思潮常由建筑師或建筑評論所提倡,引導并擴大到其它設計領域。象洛可可風格之于“啟蒙主義”等等,意大利的“ArChjzoom”及反設計的“全球工具”等許多激進設計團體就都與上世紀在西方大學校園中“馬克思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傳播有關。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其它的設計門類中,設計師就沒有或無力挑起新的藝術設計思潮,只是由于他們被賦予的社會責任感范圍較小,或不太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還有就是有些藝術設計品的更新速度太快了。
抬高“建筑學”的學科理論或社會地位,更無意去作一番“地位”的對比。實際上,建筑學也應屬于一個大的藝術設計的范疇。建筑設計活動與其他門類的藝術設計并無本質的區別。建筑學在藝術設計中的某些特殊表現,一方面與其專業特性有關,如復雜限制條件下的“功能與形式”結合、空間感知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歷史等原因造成的。在我國由于歷史因素,建筑學一直被歸于高度專業性的工程類學科中,使其難以與其它藝術設計門類互通,借鑒,這種情況對藝術設計及建筑學本身的發展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們應該多提供這些方面的引導,多指出這方面的可能途徑。所幸這種情況在今天已有了某些改觀,如中央美術學院就新設置了“建筑與環境設計”專業。在我國隨著社會的發展,建筑學與其它藝術設計門類的互通應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這會成為一種雙贏的新局面。
- 上一篇:在經濟工作報告會的發言材料
- 下一篇:小城鎮建設總結表彰會講話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