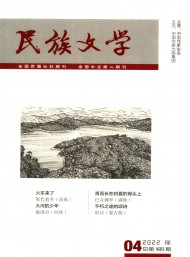民族主義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8 14:34:1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民族主義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與建設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中國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百代千年,綿延不絕!那種奉現代西方以“一族一國”為其基本信條的政治民族主義為圭臬,并因此而否認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其獨特的民族主義形式存在的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它不僅連帶抹殺了現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多樣性(如經濟的和文化的民族主義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華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和發展上早熟的事實。為了說明中國民族主義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特點,清當前中國大陸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脈絡,簡略地回顧一下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對此,筆者已經著文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作《試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載《當代中國研究》1997年第2期和論文集《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及其在近、現代的流變
從其起源上看,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早熟的華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統”(“大”在這里是動詞,表“重視”和“尊崇”之意)與其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統”的現實和觀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針對北方游牧民族的襲擾,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基于對周邊各族群之居高臨下的無比的文化優越感和自信心,同時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這種帶有濃烈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按照這種“泛中華”的文化民族主義,“亡國”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國”。因為即使國家亡了,中國固有的文物制度和倫理道德猶可倡明於天下,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為職志的士大夫們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說,“尊王攘夷”是前現代、即君主時代東西方民族主義所共有的一種異化了的表現形式(“尊王”成為民族統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則是古代中國所獨有的。孔子所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便一語道盡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所獨具的和平主義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寬容和建設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陰柔”補充了體現於“攘夷”的“陽剛”,賦予華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別的堅韌性,使之即便在身處逆境甚至亡國的環境下,猶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堅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負重,在與其它民族的共處和交往中,通過對本民族文化始終不渝地執著、傳布和發揚光大來保存自己,發展自己,終于在上下幾千年的艱苦歷程中,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即以華夏族群為主體凝聚而成的漢族;華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夠成為迄今整個古代世界碩果僅存的一種文明!中國古代的民族主義於近代的終結,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沖擊。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從而使他那種徹底反傳統和民族復仇的革命民族主義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國藩之衛道的文化民族主義,一方面是對洪秀全這種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種本能的瘋狂反動,同時也是為他自己在當時已極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塊遮羞布。只有當孫中山先生以“民權”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進而從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為古代的民族主義注入“民族平等”的觀念,并將後者推廣於國際間的民族關系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才真正獲得了與現代文明相一致的嶄新面貌!
孫先生的這一貢獻,集中地體現於他在從民國建立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這一期間逐步形成的關於以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締造或建設統一的中華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內亂不已,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壞的一面,即以對外反帝、對內反分裂和反割據為其主題。在此後長約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民族主義雖然被東西方之間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所掩蓋和沖淡,但是經由臺灣的反蘇反共和“”,以及中國大陸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臺灣”所透露出來的民族主義的意向和情緒,無論是對外或是對內,依然是對抗性、破壞性的。
(二)新霸權主義: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國際背景
隨著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已經成為一個令全球矚目的熱點問題。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關涉到兩大強國--中、美之間的關系及其未來走向,關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未來的國際社會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臺海危機在全球所引起的強烈震動和西藏問題在國際間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們特別的關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幾年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然首先是一種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進一步衰落相伴隨的現象。在這種意義上,它對官方的意識形態無疑具有某種代償功能的作用。這一點顯而易見,無需贅言。那麼,其國際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種短暫的“泡沫”現象?其性質和趨向怎樣?我們又應當采取甚麼樣的對策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與以前諸時代相比,國際政治的軸心問題在後冷戰時生了甚麼樣的變化。所謂冷戰時代,其實就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爭奪勢力圍的霸權主義時代。與之相比,後冷戰時代似可稱作新霸權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體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原來的美蘇兩極霸權正在被以美國為龍頭的發達國家之“共和霸權結構”所代替;核武器雖然仍具有相當大的威攝力量,但其研制、生產、使用和輸出(擴散)等等,已在保證西方國家享有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高尖技術的常規武器日益上升為構成發達國家之軍事優勢的最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的自顧不暇和中國大陸的孤掌難鳴,使得發達國家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國際關系領域的政治優勢,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運用和發揮其所擁有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擴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們自認為合適的安全政策和經濟政策強加給別國,達到操縱甚至包辦國際安全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說:“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實際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縱,世界經濟事務則是美、德、日說了算。這些國家相互間保持密切接觸,排斥較弱小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會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決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團利益決定的外衣。”(1)局部戰爭當然還是解決國際沖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戲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貿易,已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賴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為重要的國際角逐方式。與上述種種變化相對應,各種國際組織和自然資源也越益成為國際爭奪的“搶手貨”。君不見,不僅日本和德國,甚至連南非都躍躍欲試,想要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嗎?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現在幾乎已無人不曉,“‘世界社團’這個詞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為使反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行動獲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詞藻”(2)。至于由近幾年各國之間,如日本與韓國,西臘與土耳其,南海周邊諸國以及中日之間圍繞領土和海洋經濟專屬區等等而發生的頻繁爭執所顯示出來的資源爭奪在後冷戰時期的特殊重要意義,更是眾所周知的不爭的事實。讀者從各時代的下列對比中不難清楚地看出這些深刻的變化:時代
美國民族主義探究
對民族主義的價值視而不見
在美國,民族主義是一個骯臟的字眼,人們公開鄙棄之,認為民族主義與舊世界的狹隘和自視優越相關。但是,這些懷疑美國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士樂意承認,美國人總體而言是非常愛國的。當要求他們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時,這些懷疑論者也許會不情愿地承認二者之間區別細微,并無實質性差別。政治學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證明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他們將愛國主義等同于對國家的忠誠,而將民族主義定義為種族—民族優越感的情緒。實際上,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心理及行為表現而言,二者之間難以區分,它們對政策的影響亦然如此。
民意測驗組織的定期調查顯示,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強烈。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攻擊之前,90%接受民意測驗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更愿意成為美國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一員。”38%的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像美國人,則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襲擊之后,同意以上觀點的人分別上升為97%和49%。)美國密歇根大學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TheWorldValuesSurvey)的測驗結果與此相近,70%以上的被調查者宣稱他們對自己作為美國人“非常自豪”。與此相對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包括法國、意大利、丹麥、英國和荷蘭,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調查者對他們的國籍“非常自豪”(參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對自己國籍“非常自豪”的民眾比例)
國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國5349
民族主義論文
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學說、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種情緒,或者說是一種情緒化的意識形態,是影響過當今所有重要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近現代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盡管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對民族忠誠和民族團結的強調由來已久,但民族國家的出現卻是近現代的事情。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太系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它強調特定民族的具體文化傳統的殊別性,強調民族利益至上,保護和傳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義又是當代所有意識形態中最不依賴繁瑣理論的意識形態,所以它傳播地域廣、最能抓住普通民眾的心。民族主義是一種最簡單、然而又是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它在理論的系統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沒有受過理論訓練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說,不懂民族主義,就根本無法理解近現代的世界。在中國,漸受青睞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引起了學術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關注和不休的爭論。面對這種情形,本文擬從比較民族主義的長處和民族主義的隱憂、分析民族主義的性格和民族主義的出路等四個方面談談筆者對民族主義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義的長處與優勢
民族主義的核心是承認并伸張每個民族的自決權,認為每個民族都有權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情緒與運動往往發韌于傳統與現代、及本土與異域碰撞之際。民族主義核心內容是反對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紀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主義運動中,眾多的弱小民族,擺脫了異族統治和殖民統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決,反對異族統治也正是中國近現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據和目標。
民族主義是強化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喚起人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民族主義提倡英雄主義、塑造榮譽感和犧牲精神,可以在社會中造就一種向上、奮進、自強、團結一心,甚至是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義的最強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認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員的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義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豐富一個社會的價值資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義強調每一個民族,或者說強調自己民族在歷史、語言、文化甚至物產上的獨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樣而豐富的人類文化遺產。對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有助于恢復和保存豐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在這一傳統由于受到長期的清洗和毀滅而幾至失墮之際。這樣,長期被強制地與民族文化傳統隔離開來的中國人有機會重溫、復興自己的文化傳統。民族主義強調對民族特性和民族傳統的認同與尊重,這就為政治統治提供了某種合法性基礎。在現代社會,每個國家的統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種強勢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對立的意識形態的挑戰,或是由于本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德文化的變遷,為統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導意識形態會走向衰敗。這時,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由于舊的意識形態的衰敗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從而可以維持統治秩序的穩定,并用民族主義情緒來抵擋外來意識形態的沖擊。民族主義的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戰后的世界大范圍崛起的重要原因。
民族主義分析論文
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學說、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種情緒,或者說是一種情緒化的意識形態,是影響過當今所有重要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近現代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盡管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對民族忠誠和民族團結的強調由來已久,但民族國家的出現卻是近現代的事情。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太系統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它強調特定民族的具體文化傳統的殊別性,強調民族利益至上,保護和傳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傳統和疆界的完整。
民族主義又是當代所有意識形態中最不依賴繁瑣理論的意識形態,所以它傳播地域廣、最能抓住普通民眾的心。民族主義是一種最簡單、然而又是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它在理論的系統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沒有受過理論訓練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說,不懂民族主義,就根本無法理解近現代的世界。在中國,漸受青睞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引起了學術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關注和不休的爭論。面對這種情形,本文擬從比較民族主義的長處和民族主義的隱憂、分析民族主義的性格和民族主義的出路等四個方面談談筆者對民族主義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義的長處與優勢
民族主義的核心是承認并伸張每個民族的自決權,認為每個民族都有權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民族主義的情緒與運動往往發韌于傳統與現代、及本土與異域碰撞之際。民族主義核心內容是反對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正是在二十世紀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主義運動中,眾多的弱小民族,擺脫了異族統治和殖民統治,走上了獨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決,反對異族統治也正是中國近現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據和目標。
民族主義是強化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獨立,喚起人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民族主義提倡英雄主義、塑造榮譽感和犧牲精神,可以在社會中造就一種向上、奮進、自強、團結一心,甚至是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義的最強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認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員的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義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豐富一個社會的價值資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義強調每一個民族,或者說強調自己民族在歷史、語言、文化甚至物產上的獨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樣而豐富的人類文化遺產。對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有助于恢復和保存豐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在這一傳統由于受到長期的清洗和毀滅而幾至失墮之際。這樣,長期被強制地與民族文化傳統隔離開來的中國人有機會重溫、復興自己的文化傳統。民族主義強調對民族特性和民族傳統的認同與尊重,這就為政治統治提供了某種合法性基礎。在現代社會,每個國家的統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種強勢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對立的意識形態的挑戰,或是由于本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德文化的變遷,為統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導意識形態會走向衰敗。這時,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由于舊的意識形態的衰敗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從而可以維持統治秩序的穩定,并用民族主義情緒來抵擋外來意識形態的沖擊。民族主義的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戰后的世界大范圍崛起的重要原因。
民族主義源流論文
民族主義在中國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百代千年,綿延不絕!那種奉現代西方以“一族一國”為其基本信條的政治民族主義為圭臬,并因此而否認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其獨特的民族主義形式存在的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為它不僅連帶抹殺了現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多樣性(如經濟的和文化的民族主義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華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和發展上早熟的事實。為了說明中國民族主義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特點,清當前中國大陸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脈絡,簡略地回顧一下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對此,筆者已經著文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作《試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源流》,載《當代中國研究》1997年第2期和論文集《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及其在近、現代的流變
從其起源上看,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早熟的華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統”(“大”在這里是動詞,表“重視”和“尊崇”之意)與其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統”的現實和觀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針對北方游牧民族的襲擾,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基于對周邊各族群之居高臨下的無比的文化優越感和自信心,同時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這種帶有濃烈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按照這種“泛中華”的文化民族主義,“亡國”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國”。因為即使國家亡了,中國固有的文物制度和倫理道德猶可倡明於天下,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為職志的士大夫們的真正“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說,“尊王攘夷”是前現代、即君主時代東西方民族主義所共有的一種異化了的表現形式(“尊王”成為民族統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則是古代中國所獨有的。孔子所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便一語道盡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所獨具的和平主義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寬容和建設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陰柔”補充了體現於“攘夷”的“陽剛”,賦予華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別的堅韌性,使之即便在身處逆境甚至亡國的環境下,猶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堅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負重,在與其它民族的共處和交往中,通過對本民族文化始終不渝地執著、傳布和發揚光大來保存自己,發展自己,終于在上下幾千年的艱苦歷程中,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即以華夏族群為主體凝聚而成的漢族;華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夠成為迄今整個古代世界碩果僅存的一種文明!中國古代的民族主義於近代的終結,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沖擊。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從而使他那種徹底反傳統和民族復仇的革命民族主義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國藩之衛道的文化民族主義,一方面是對洪秀全這種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種本能的瘋狂反動,同時也是為他自己在當時已極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塊遮羞布。只有當孫中山先生以“民權”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即以“建立共和”代替了“尊王”,進而從政治和文化兩方面為古代的民族主義注入“民族平等”的觀念,并將後者推廣於國際間的民族關系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才真正獲得了與現代文明相一致的嶄新面貌!
孫先生的這一貢獻,集中地體現於他在從民國建立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這一期間逐步形成的關於以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締造或建設統一的中華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內亂不已,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壞的一面,即以對外反帝、對內反分裂和反割據為其主題。在此後長約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民族主義雖然被東西方之間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所掩蓋和沖淡,但是經由臺灣的反蘇反共和“”,以及中國大陸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臺灣”所透露出來的民族主義的意向和情緒,無論是對外或是對內,依然是對抗性、破壞性的。
(二)新霸權主義: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國際背景
隨著冷戰的結束,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已經成為一個令全球矚目的熱點問題。由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關涉到兩大強國--中、美之間的關系及其未來走向,關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未來的國際社會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臺海危機在全球所引起的強烈震動和西藏問題在國際間擁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們特別的關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幾年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顯然首先是一種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進一步衰落相伴隨的現象。在這種意義上,它對官方的意識形態無疑具有某種代償功能的作用。這一點顯而易見,無需贅言。那麼,其國際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種短暫的“泡沫”現象?其性質和趨向怎樣?我們又應當采取甚麼樣的對策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與以前諸時代相比,國際政治的軸心問題在後冷戰時生了甚麼樣的變化。所謂冷戰時代,其實就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爭奪勢力圍的霸權主義時代。與之相比,後冷戰時代似可稱作新霸權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體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原來的美蘇兩極霸權正在被以美國為龍頭的發達國家之“共和霸權結構”所代替;核武器雖然仍具有相當大的威攝力量,但其研制、生產、使用和輸出(擴散)等等,已在保證西方國家享有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高尖技術的常規武器日益上升為構成發達國家之軍事優勢的最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的自顧不暇和中國大陸的孤掌難鳴,使得發達國家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國際關系領域的政治優勢,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運用和發揮其所擁有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來擴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們自認為合適的安全政策和經濟政策強加給別國,達到操縱甚至包辦國際安全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說:“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務實際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縱,世界經濟事務則是美、德、日說了算。這些國家相互間保持密切接觸,排斥較弱小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聯合國安理會或國際貨幣基金會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決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團利益決定的外衣。”(1)局部戰爭當然還是解決國際沖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戲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貿易,已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賴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為重要的國際角逐方式。與上述種種變化相對應,各種國際組織和自然資源也越益成為國際爭奪的“搶手貨”。君不見,不僅日本和德國,甚至連南非都躍躍欲試,想要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嗎?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現在幾乎已無人不曉,“‘世界社團’這個詞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為使反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利益的行動獲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詞藻”(2)。至于由近幾年各國之間,如日本與韓國,西臘與土耳其,南海周邊諸國以及中日之間圍繞領土和海洋經濟專屬區等等而發生的頻繁爭執所顯示出來的資源爭奪在後冷戰時期的特殊重要意義,更是眾所周知的不爭的事實。讀者從各時代的下列對比中不難清楚地看出這些深刻的變化:時代
民族主義趨勢論文
民族主義是預測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盡管有學者預言“當20世紀末臨近的時刻,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是‘好的共同體’這樣一個現代的正統觀念提出了挑戰”(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學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但冷戰后民族主義浪潮的重新泛起,卻使人們覺得這樣樂觀的預測未免太早,與此同時,對民族主義這種隨著資本主義而產生,并隨著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而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沖擊的意識形態,它在未來一個世紀中將會有何種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一民族主義的定義與分類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定義都涉及到極為廣泛的層面,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在預測民族主義的未來趨勢時,回顧對民族主義的性質的爭論是十分有益的。
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堅持政治與民族的單位必須一致”;并斷言,沒有現代的國家政權,就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注: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爾大學1983年版,第1—5頁。)。漢斯·科恩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即個人對民族政權的忠誠高于一切。這種心理狀態是同生養他的土地、本地的傳統以及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權威等等聯系在一起的(注:漢斯·科恩:《民族主義:它的含義與歷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紐約1961年版,第1-8頁。)。哈維丁·凱卻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自上而下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現代國家政權在近代初期歐洲西部地區的特殊的環境下長期行使權力而產生的(注:哈維丁·凱:《歷史、階級與民族國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倫敦1988年版,第138頁。)。漢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樣,是一個光輝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所謂民族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民族主義情緒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紀才發展成為要求每個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權的政治原則(注:伊利·凱多爾:《民族主義》(ElieKedourie,Nationalism),紐約1961年版,第1、15-18頁。)。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等人的論述,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是一種對自己民族的偏愛。民族主義是可以分為進步與反動的兩種類型的,但從本質上講,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觀的核心,因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逐步消亡(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頁;《列寧全集》第22卷,第319頁。)。
可見,民族主義是一個外延和內涵都相當復雜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對民族主義的含義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無法對民族主義的未來走向進行有意義的預測。事實上,每一個學者都是在從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義的本質,強調民族主義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客觀上已經分為了幾個大類,而在研究中,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各種含義不同的“民族主義”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和論述,這就使人很難在一個共同的基點上相互理解對方的觀點。為避免這種語焉不詳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按各個學者強調的不同重點而將民族主義大致地分為以下幾類。
(一)政治民族主義
當代民族主義及其未來趨勢
民族主義是預測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盡管有學者預言“當20世紀末臨近的時刻,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是‘好的共同體’這樣一個現代的正統觀念提出了挑戰”(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學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但冷戰后民族主義浪潮的重新泛起,卻使人們覺得這樣樂觀的預測未免太早,與此同時,對民族主義這種隨著資本主義而產生,并隨著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而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沖擊的意識形態,它在未來一個世紀中將會有何種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一民族主義的定義與分類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定義都涉及到極為廣泛的層面,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在預測民族主義的未來趨勢時,回顧對民族主義的性質的爭論是十分有益的。
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堅持政治與民族的單位必須一致”;并斷言,沒有現代的國家政權,就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注: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爾大學1983年版,第1—5頁。)。漢斯·科恩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即個人對民族政權的忠誠高于一切。這種心理狀態是同生養他的土地、本地的傳統以及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權威等等聯系在一起的(注:漢斯·科恩:《民族主義:它的含義與歷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紐約1961年版,第1-8頁。)。哈維丁·凱卻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自上而下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現代國家政權在近代初期歐洲西部地區的特殊的環境下長期行使權力而產生的(注:哈維丁·凱:《歷史、階級與民族國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倫敦1988年版,第138頁。)。漢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樣,是一個光輝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所謂民族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民族主義情緒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紀才發展成為要求每個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權的政治原則(注:伊利·凱多爾:《民族主義》(ElieKedourie,Nationalism),紐約1961年版,第1、15-18頁。)。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等人的論述,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是一種對自己民族的偏愛。民族主義是可以分為進步與反動的兩種類型的,但從本質上講,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觀的核心,因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逐步消亡(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頁;《列寧全集》第22卷,第319頁。)。
可見,民族主義是一個外延和內涵都相當復雜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對民族主義的含義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無法對民族主義的未來走向進行有意義的預測。事實上,每一個學者都是在從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義的本質,強調民族主義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客觀上已經分為了幾個大類,而在研究中,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各種含義不同的“民族主義”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和論述,這就使人很難在一個共同的基點上相互理解對方的觀點。為避免這種語焉不詳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按各個學者強調的不同重點而將民族主義大致地分為以下幾類。
(一)政治民族主義
國外民族主義論文
美國遭受恐怖主義攻擊近兩年之后,國際公共輿論從對美國的衷心同情轉向公開厭惡。這一轉變的直接觸媒是美國對伊拉克的強硬政策。但是,當今強烈的反美主義不僅代表著對美國的決心或一個胡作非為的霸權普遍表示恐懼,而且代表著對美國深深的憂慮,可視為全球對塑造和推動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做出的強烈反應。
探究反美主義更深層的根源,應該從反省美國民族主義開始。但是,美國對此內省反應冷淡,因為這意味著美國的國家性格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美國民族主義存在如下兩種悖論:第一,盡管美國是一個擁有強烈民族主義的國家,但它自己并不視之為民族主義;其次,盡管美國社會中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但美國決策者非常不重視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力量,在應對海外民族主義時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對民族主義的價值視而不見
在美國,民族主義是一個骯臟的字眼,人們公開鄙棄之,認為民族主義與舊世界的狹隘和自視優越相關。但是,這些懷疑美國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士樂意承認,美國人總體而言是非常愛國的。當要求他們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時,這些懷疑論者也許會不情愿地承認二者之間區別細微,并無實質性差別。政治學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證明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他們將愛國主義等同于對國家的忠誠,而將民族主義定義為種族-民族優越感的情緒。實際上,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心理及行為表現而言,二者之間難以區分,它們對政策的影響亦如此。
民意測驗組織的定期調查顯示,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強烈。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攻擊之前,90%接受民意測驗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更愿意成為美國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一員。”38%的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像美國人,則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襲擊之后,同意以上觀點的人分別上升為97%和49%。)
美國人不僅對自己的價值觀非常自豪,而且認為這些價值觀是普世性的。根據皮歐全球態度調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調查結果,79%接受民意調查的美國人同意“美國觀念和習俗在全球推廣是有益的”;70%的人說他們“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即使在作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另一個堡壘的西歐,這些觀點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歐公司發現,在西歐國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測驗的人贊同美國觀念和習俗的傳播,不到50%的人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
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論文
現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應該是民族的(national,此詞既有"民族的"之意,又有"國家的"之意--譯注)。
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中,從現代時期之始,君主國家(princelystate)就取代了中世紀的等級制度(estatesystem)。君主制國家的唯一政治觀念就是統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國家"就最精煉地表達了此一觀念,這種觀念在歐洲三大帝國宮廷一直延續到晚近的劇變為止。魁奈的學說盡管引發了新的國家觀念,不是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寫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paysan,Pauvreroyaume;pauvreroyaume,pauvreroi.。在他看來,僅僅揭示國家的富裕繁榮有賴于農民的富裕繁榮是不夠的,他一直認為,還必須揭示出:只有當農民富足之后,國王才能富裕起來,由此他證明了采取措施提高農民福利的必要性。國家(所應約束)的目標恰恰應該是君王。
與君主制國家相抗衡,18世紀和19世紀,自由的理念勃然興起,使古代共和與中世紀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復蘇。它與monarchomachs之反對君主連結在一起;它以英國的先例為榜樣,英國的君主在十七世紀就已經徹底失敗;它利用一整套哲學、理性主義、自然法來戰斗,它通過文學征服了群眾,使之完全服膺于這套理念。專制君主最終屈服于自由運動的進攻,從而出現了君主立憲制,出現了共和國。
君主制國家是沒有自然邊界的,不斷增加家族的財產是君王們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奮斗試圖使自己留給后代的土地廣于他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土地。不斷獲取新的領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樣強大甚至比他更強大的對手為止,這就是國王的使命。他們對于土地的貪婪,使他們根本不知邊界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為及捍衛君主制國家理念的文獻中的觀點都能證明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則威脅著所有弱小國家之生存,它們之所以還能維持生存,則應歸功于大國之間彼此嫉妒,這些大國高度警惕著不想讓任何一個變得更強大。這就是歐洲均衡的概念,構成了它們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合縱連橫。小國被毀滅也有可能不危及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蘭。君主們看待國家的方式,跟地產主看待其森林、牧場、農地的眼光沒有任何不同。他們出售國土、也交換國土(即為了"使邊界更齊整"),而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統治權也隨之變換。根據這種解釋,共和國就是一種無主財產,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這種政策到19世紀達到了頂峰:1803年的《神圣羅馬帝國代表議定書》,拿破倫的國家制度,維也納會議的決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們看來,土地和人民無非就是君主所有權的對象而已:前者構成了主權的基礎,而后者則是土地所有權的附屬物。對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們要求其服從和忠誠;他把人民差不多就當成自己的財產。而把他和他轄下之每個人連結起來這一契約(bond)也是使所有人連接為一體的唯一途徑。專制統治者認為他的臣民之間自行組成任何社會組織都是危險,因此他總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傳統的團結合作關系,只要不是根據他所頒布的國家法令設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會組織之形成,甚至連俱樂部,都不得存在;同時他也不允許不同地區的臣民感覺到作為一個君主統治下的臣民的那種同志情誼。不過,當然,君王們撕裂了構成其臣民的貴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一切階級聯系,使整個社會陷入原子化,從而也為新的政治情感的興起創造了前提條件。臣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于認為自己并不是什么狹窄小圈子的成員,而是一個人,是民族的一員,是國家和世界的一個公民,從此開辟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
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與君主制正相反,反對君主對土地的貪欲和用領土討價還價。這種理論首先發現,國家與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當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顛--典型的自由國家,法國--為自由而戰斗的經典之作。這種情況看起來是理所當然,自由主義國家理論也就未在此多費筆墨,因為國家與民族本來就是一致的,也沒有必要改變它,當然就不存在什么問題。
肖邦與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綜述
肖邦,波蘭作曲家、鋼琴家。作品以波蘭民間歌舞為基礎,同時又深受貝多芬、巴赫等作曲家的影響,多以鋼琴曲為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題材緊扣波蘭人民的生活,曲調熱情奔放、和聲豐富多彩、結構靈活自如。他的練習曲作品訓練目的明確,藝術形象鮮明;他的圓舞曲作品,賦予溫柔抒情的情感;他的前奏曲作品,可將風格迥異的個曲,自由結合為組曲;他的諧謔曲成為獨立的作品感情激動、富裕戲劇性;他的馬祖卡舞曲作品,曲調單純、和聲簡樸、明朗歡快;他的夜曲作品,充滿幻想、情調深沉。就是這樣一個愛國的肖邦,使他的作品有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最完美的交融!
肖邦的創作可分為4個時期,即華沙時期、華沙起義時期、在巴黎的全盛時期、晚期。
華沙時期的創作除少數作品外,在肖邦的整個創作中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是肖邦一生創作的起點,其中已經閃耀著民族感情和民族風格的光輝。就是這個時期,肖邦深深的受到了民族解放思想和文學浪漫主義的影響。奠定了他作為一個民族主義音樂家的基礎。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1830年作的兩部鋼琴協奏曲:《第二鋼琴協奏曲》、《第一鋼琴協奏曲》
華沙起義時期,肖邦的創作出現了一個飛躍。《b小調諧謔曲》寫于逗留維也納時期。起義激起的愛國熱情同對祖國親人的思念交織在一起,構成一首既嚴峻又溫存的音詩。《c小調練習曲》(別稱《革命練習曲》),《d小調前奏曲》則寫于得知華沙淪陷之后,激憤、悲痛之情同嚴整洗練的藝術形式之間達到高度完美的統一,成為肖邦早期音樂創作中的杰作。
在巴黎的全盛時期的創作中,深刻的民族內容、富于獨創性的藝術形式和嫻熟的音樂風格使他的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創作涉及到鋼琴音樂的各種體裁,波洛奈茲舞曲是肖邦在這個時期創作中民族精神體現得最為強烈的體裁。《降A大調波洛奈茲舞曲》是同類體裁樂曲中性格最剛毅、豪邁,氣勢最宏偉、磅礴的一首。它的主題具有果斷、剛健的節奏,熱情豪邁的旋律以及明亮的大調式和聲,體現著不屈不撓的民族英雄豪杰的形象。
晚期的創作呈現出明顯的衰退趨勢。《g小調馬祖卡舞曲》、《f小調馬祖卡舞曲》是肖邦最后的兩部作品。前者是一首親切、溫存的歌,表達了對生活的最后一點眷戀;后者在淡淡的哀愁中傾訴著對故國和親人的最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