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范文
時(shí)間:2023-03-26 13:48:58
導(dǎo)語(yǔ):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汪曾祺散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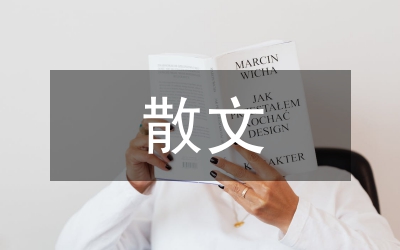
篇1
關(guān)鍵詞:汪曾祺 自我 幽默 語(yǔ)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dāng)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于西南聯(lián)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kāi)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xué)國(guó)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lián)、中國(guó)民間文學(xué)研究會(huì)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xué)》等刊物。1962年調(diào)入北京京劇團(tuán)(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xué)評(píng)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yù)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guó)最后一個(gè)純粹的文人,中國(guó)最后一個(gè)士大夫”。
對(duì)于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dāng)其沖,如孫郁所對(duì)他的評(píng)價(jià):“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復(fù)了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品格,將非我的藝術(shù),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這種精神上的調(diào)整,可以說(shuō)是從他開(kāi)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shí)儒,他對(duì)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shí)踐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散文和現(xiàn)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xiàn)。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fēng)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chóng)魚(yú)、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tài)度親切,不矜持作態(tài)。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píng)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diǎn)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píng)價(jià),有益于我們對(duì)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gè)特點(diǎn):
一.融自我于其中,蘊(yùn)濃厚個(gè)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shuō)要貼著人物來(lái)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無(wú)論是記人類、游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guò)“我”的情感浸潤(rùn)的,有鮮明的個(gè)人特點(diǎn)。他說(shuō)過(guò)“畢竟,人和自然的關(guān)系,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yè)),他不會(huì)把自己淹沒(méi)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guò)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shí)無(wú)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yàn)樘┥教蟆N覍?duì)泰山不能認(rèn)同。我對(duì)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diǎn)格格不入”,我“更進(jìn)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來(lái)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fā)現(xiàn)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dān)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云霧,也無(wú)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lái)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gè)接一個(gè)典故,說(shuō)古考據(jù),卻沒(méi)讓人感覺(jué)到味同嚼蠟的“吊書袋”,原因即在于這些故紙堆里的考據(jù)并非死的學(xué)問(wèn)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gè)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yùn)藏的博學(xué)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zhǎng)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顯不動(dòng)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lái)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duì)視,莞爾一笑。他對(duì)幽默的見(jiàn)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jué)得很意思。有時(shí)一個(gè)人坐著,想一想,覺(jué)得很有意思,會(huì)噗噗笑出聲來(lái)。把這樣的事記下來(lái)或說(shuō)出來(lái),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wú)關(guān)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dòng)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說(shuō)古考據(jù)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shuō)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lái),時(shí)不時(shí)以幽默來(lái)調(diào)劑。《跑警報(bào)》中的“人生幾何,戀愛(ài)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恒”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報(bào)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duì)災(zāi)難不在乎,讀者于笑中體會(huì)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里鮮活起來(lái)。金岳霖聚會(huì)時(shí)捉虱子的自嘲,80歲時(shí)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fā)童心……讓我們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于世俗生活中發(fā)現(xiàn)樂(lè)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shuō)成:“今天我們培養(yǎng)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yè))“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shī),布朗底的小說(shuō),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卜”的聯(lián)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yè))
三.文言與現(xiàn)代白話于一爐的獨(dú)特語(yǔ)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píng)價(jià)汪曾祺的語(yǔ)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qiáng)烈的張力中達(dá)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第355頁(yè)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yǔ)言特色,他在語(yǔ)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jié)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jīng)典的熏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yǔ)》,父親請(qǐng)當(dāng)?shù)孛飨蛩麄魇诠诺湮膶W(xué)。他自己閱讀甚廣,中國(guó)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ài)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xué)功底,使他在語(yǔ)言方面簡(jiǎn)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guó)畫的計(jì)白當(dāng)黑。對(duì)民俗的體察,對(duì)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guān)注,又使他的語(yǔ)言充滿口語(yǔ)化,讀來(lái)不覺(jué)俗氣,反覺(jué)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yú)、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shuō)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yú),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yú)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來(lái)我知道:塘鱧魚(yú)就是虎頭鯊,嗐!”一個(gè)“嗐”字,讀來(lái)過(guò)癮。類似的還有《故鄉(xiāng)的食物》寫到高郵咸蛋“筷子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lái)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zhǔn),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guò)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風(fēng)……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了然,事實(shí)的陳述,簡(jiǎn)單明確,仿佛過(guò)于直白口語(yǔ),但看無(wú)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yǔ)傳遞的獨(dú)特魅力在這里展現(xiàn)出來(lái)。融文言與現(xiàn)代白話于一爐,漢語(yǔ)的表現(xiàn)力被展現(xiàn)和增強(qiáng)了。
篇2
一直都去追尋,一種可以真正寄托心靈的文字,
可能不是那么的華麗,可能不是那么的與眾不同,
只是大眾化的,讓所有人都能感覺(jué)到,
我文字里的真誠(chéng),我想與你分享的情緒。
一直都在尋覓,一個(gè)可以真正可以交流的地方,
可能那里有著許多傷感的故事,可能那里有著許多花開(kāi)花敗的情感,
沒(méi)有太利益的東西,只是讓所有被現(xiàn)實(shí)弄疲憊的人們,
聊以慰藉的地方,讓我們能夠找到一個(gè)文字的世外桃源。
一直不愿意去回憶很多不該回憶的往事,一直不愿意去追尋自己想去追尋的軌跡。
可能會(huì)怪紅塵引路人,把我引領(lǐng)到你的身旁,看你不屑一顧的眼。
可能會(huì)怪黃泉路上那塊三生石旁,為何會(huì)留下痕跡,一輩子都擺脫不掉的糾纏,
當(dāng)心充斥滿滿的累,當(dāng)情感再不堪重負(fù)時(shí),
篇3
在搜集中、閱讀中,在重新學(xué)習(xí)中,終于覺(jué)得,若要真正懂得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不了解汪曾祺是無(wú)論如何也說(shuō)不過(guò)去的。
作家簡(jiǎn)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任中學(xué)教師、北京市文聯(lián)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上頗有成就。被譽(yù)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guó)最后一個(gè)純粹的文人,中國(guó)最后一個(gè)士大夫”。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shuō):《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shuō)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shù)小品集:《汪曾祺:文與畫》;
文學(xué)評(píng)論集:《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
京劇:《范進(jìn)中舉》;
文集:《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汪曾祺》。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
“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shí)候都需要的。”
“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fēng)格,不喜歡繁復(fù)濃重的風(fēng)格,對(duì)畫,對(duì)文學(xué),都如此。”
篇4
1、中國(guó)經(jīng)典名著:《老子》《莊子》《論語(yǔ)》《孫子兵法》《史記》《紅樓夢(mèng)》《三國(guó)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人間詞話》《唐詩(shī)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詩(shī)選》《杜甫詩(shī)選》《蘇軾詞選》《西廂記》《世說(shuō)新語(yǔ)》《浮生六記》等等。
2、新課程標(biāo)準(zhǔn)推薦:《論語(yǔ)》《三國(guó)演義》《紅樓夢(mèng)》《吶喊》《女神》《子夜》《家》《雷雨》《圍城》《談美書簡(jiǎn)》《哈姆萊特》《堂·吉訶德》《歌德談話錄》《巴黎圣母院》《歐也妮·葛朗臺(tái)》《匹克威克外傳》《復(fù)活》《普希金詩(shī)選》《老人與海》《泰戈?duì)栐?shī)選》。
3、名家名作: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史鐵生《我與地壇》;張中行《負(fù)暄瑣話》;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朱光潛《談美》《談文學(xué)》;梁實(shí)秋《雅舍小品》;沈從文《邊城》《湘行散記》;《雷雨》;張承志《黑駿馬》《北方的河》;顧城《顧城的詩(shī)》;舒婷《舒婷的詩(shī)》;食指《食指的詩(shī)》;韓少功《馬橋詞典》;賈平凹《賈平凹散文選》;周作人《雨天的書》;林雨堂《生活的藝術(shù)》;柏楊《丑陋的中國(guó)人》;傅雷《傅雷家書》;余光中《余光中散文》;林清玄《林清玄散文》;曹文軒《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郁達(dá)夫《郁達(dá)夫散文》;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巴金《隨想錄》;張愛(ài)玲《張愛(ài)玲散文全編》;錢鐘書《圍城》《寫在人生邊上》;董橋《舊時(shí)月色》;張煒《古船》《九月寓言》;王蒙《王蒙散文選》;余華《活著》;蘇童《蘇童文集》;老舍《茶館》;楊絳《我們仨》;阿來(lái)《塵埃落定》;實(shí)《白鹿原》;周濤《周濤散文選》等。
(來(lái)源:文章屋網(wǎng) )
篇5
中國(guó)人歷來(lái)信奉“吃”這一字真訣,林語(yǔ)堂在《吾國(guó)與吾民》中說(shuō),西方人對(duì)待吃,僅把它看成是給機(jī)器加油料,而中國(guó)人則視之為人生至樂(lè)。“吃”字不上桌,中國(guó)文化的肚子就會(huì)癟下去,也少了許多色香味。
可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文人說(shuō)茶,不會(huì)油膩了滿腹詩(shī)書,論及其他就嗆了煙火氣,吃下去是個(gè)好,說(shuō)出來(lái)卻是個(gè)俗,挺尷尬的。“是真名士自風(fēng)流”,食物不能閉口不吃,當(dāng)然也決不能閉口不談。蘇軾被貶黃州時(shí),發(fā)明了“東坡肉”,還樂(lè)呵呵地向人們傳授他的烹調(diào)經(jīng)驗(yàn),“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shí)它自美”,既是在做菜,也是在做心境。金圣嘆臨刑前,悄悄告訴兒子說(shuō),“豆腐干與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大災(zāi)禍輸給了小詼諧,死倒不是個(gè)事了。清代袁枚也是個(gè)美食家,他曾作了一首詩(shī),名曰《雞》:“養(yǎng)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主人計(jì)固佳,不可使雞知。”雞若知道了,當(dāng)啐他一臉米。近代還有梁實(shí)秋,寫《雅舍談吃》,卻不怕這“吃”字太過(guò)霸道,張著大口把“雅”字饕餮了。而把“吃”寫“雅”了,那又是一種境界。
然后,施施然走出來(lái)一個(gè)汪曾祺。汪曾祺是“中國(guó)最后一個(gè)士大夫”,同時(shí)也被譽(yù)為“最后一位文人美食家”。他寫了許多美食散文,平淡似大碗茶,自然若一茬春韭,家常如小蔥拌豆腐,字里行間都能榨出味來(lái),在鼻孔里、心尖上亂撓。談美食,斷不能寫成菜譜,白開(kāi)水一般,香不起來(lái)。汪曾祺在做美食散文這盤菜時(shí),暗暗放了一味作料——情,具體來(lái)說(shuō)就是鄉(xiāng)土情。他是沈從文的弟子,師徒二人都害了鄉(xiāng)土相思病,這一病就入了膏肓,扁鵲也難治。沈從文的鄉(xiāng)土散文具有抒情性,汪曾祺則淡化感情,著墨于“記人事,寫風(fēng)景,說(shuō)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昆蟲(chóng)”,以平淡出之。它不是醬醋,上了色,一眼瞧見(jiàn)端倪;而是化在菜里的鹽,欲知滋味,得夾一筷子,慢慢嚼。如《故鄉(xiāng)的野菜》一文,他寫了好幾種故鄉(xiāng)的野菜,先用白描,看不出悲喜,但寫至灰菜,鄉(xiāng)土情再也撇不開(kāi)、捺不住了,感情逃出了“文字獄”。你終于知道,他最懷念的一種野菜,叫家鄉(xiāng)。
《海味·南方》一文中,小作者從大師傅和爺爺?shù)男χ凶x到了相同的含義——“高興于他人對(duì)自己家鄉(xiāng)美味的肯定,感動(dòng)于他人對(duì)自己鄉(xiāng)土風(fēng)情的共鳴”。海味,南方,我的家。
無(wú)論是野菜抑或海味,味到濃時(shí)即家鄉(xiāng)。
篇6
摘 要:新筆記小說(shuō)是誕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持續(xù)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種小說(shuō)文體類型。它一反以往當(dāng)代小說(shuō)追求宏大敘事和鮮明政治訴求的趨向,轉(zhuǎn)而開(kāi)掘獨(dú)特的人性深處的美感。更為突出的是,新筆記小說(shuō)自覺(jué)借鑒中國(guó)古記傳統(tǒng)的寫作和審美資源,將其融入到當(dāng)代小說(shuō)藝術(shù)的表達(dá)范圍以內(nèi),形成了自身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特點(diǎn)。
關(guān)鍵詞:新筆記小說(shuō) 生成機(jī)制 概念界定
作者簡(jiǎn)介:袁曉斌,江蘇警官學(xué)院管理系,碩士講師,研究方向: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南京師范大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0)-20-0176-01
80年代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一個(gè)黃金時(shí)代,單就小說(shuō)而言,“傷痕”、“反思”、“尋根”、“先鋒”、“新寫實(shí)”等,這些小說(shuō)主潮之外,還存在著許多沒(méi)有在文學(xué)史的表述中占有大面積話語(yǔ)或與這些主潮小說(shuō)存在交叉的小說(shuō)類型。它們也參與構(gòu)成了80年代以來(lái)小說(shuō)寫作的繁榮。新筆記小說(shuō)就是這樣的一種小說(shuō)類型。新筆記小說(shuō)是一種小說(shuō)類型,而不是一種創(chuàng)作潮流。類型,是針對(duì)小說(shuō)文體的共同寫作特征所進(jìn)行的歸類劃分,往往最終落實(shí)為某一特定的小說(shuō)文體。新筆記小說(shuō)并不是緊密圍繞著作家創(chuàng)作的特定理念形成的一股強(qiáng)勁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勢(shì)頭,而是以小說(shuō)文體為核心,思考小說(shuō)作為藝術(shù)形式的種種建樹(shù)。從新筆記小說(shuō)的實(shí)際創(chuàng)作情況來(lái)看,應(yīng)該把它界定為一種小說(shuō)文體類型。
新筆記小說(shuō),顧名思義,繼承了中國(guó)古記傳統(tǒng)的美學(xué)風(fēng)范。對(duì)于不同作家來(lái)說(shuō),他們對(duì)中國(guó)古記傳統(tǒng)的汲取是有層次區(qū)分的。首先,有一部分作家確實(shí)在自己對(duì)古記的閱讀中受到了啟迪,或熏陶出了新鮮的創(chuàng)作方法。汪曾祺說(shuō):“我寫短小說(shuō),一是中國(guó)本有用極簡(jiǎn)的筆墨摹寫人事的傳統(tǒng),《世說(shuō)新語(yǔ)》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絕如縷。我愛(ài)讀宋人筆記甚于唐人傳奇。《夢(mèng)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歡。歸有光的《寒花葬志》、龔定庵的《記王隱君》,我覺(jué)得都可以當(dāng)小說(shuō)看。”孫犁也說(shuō):“我學(xué)習(xí)小說(shuō)寫作,初以為筆記小說(shuō),與這一學(xué)問(wèn)有關(guān)。”另外,1980年代的年輕作家中陳軍也表示過(guò):“文學(xué)觀先喜洋玩藝。卡夫卡、加謬及法國(guó)新小說(shuō),拉美‘爆炸文學(xué)’和福克納等,都看了些,不精。但總覺(jué)得洋拳術(shù)偷不來(lái),與氣脈打不通,才發(fā)覺(jué)自己的秉性還是黃種的。于是再回老祖宗處請(qǐng)罪,讀《諸子集成》,品歷記,漸漸地,覺(jué)得大小周天似乎有了些氣感。于是嘗到點(diǎn)文化的醇味,也滋潤(rùn)出小小的野心。”陳軍對(duì)中國(guó)古記的借鑒也與對(duì)汪曾祺等作家的閱讀有關(guān)。他在小說(shuō)中借人物之口點(diǎn)出了受到的啟發(fā):“而讀汪曾祺、老舍、古記則不然,他們懂得‘知白守黑’這畫理,作品也似青花瓷器般空靈有后味。”
新筆記小說(shuō)作為一種文體類型,一經(jīng)樹(shù)立,就會(huì)為其他作家提示一種現(xiàn)存的寫作經(jīng)驗(yàn),一種小說(shuō)寫作的新的可能性,也會(huì)吸引其他作家的興趣來(lái)嘗試這種文體。所以,正是因?yàn)檫@個(gè)原因,更多的新筆記小說(shuō)的作者往往并非專擅這樣一種小說(shuō)文體,而是在許多不同的小說(shuō)文體上都有所涉足。這些默默寫作的新筆記小說(shuō)的作者們的創(chuàng)作,構(gòu)成了理論宣講之外的對(duì)新筆記小說(shuō)強(qiáng)有力的創(chuàng)作支持。作為一種新的小說(shuō)文體類型,新筆記小說(shuō)有著自身獨(dú)特的文體要求。汪曾祺說(shuō):“凡是不以情節(jié)勝,比較簡(jiǎn)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說(shuō),不妨都稱之為筆記體小說(shuō)。”其中的“筆記體小說(shuō)”,就是本文所談的新筆記小說(shuō)。汪曾祺的話對(duì)新筆記小說(shuō)的文體要求概括得比較全面,但是還稍有紕漏。筆者認(rèn)為,新筆記小說(shuō)的文體要求首先反映在篇幅上。新筆記小說(shuō)一般不支持短篇以外的創(chuàng)作,所以標(biāo)以這一名目的作品幾乎全是短篇,中篇非常罕見(jiàn),幾乎沒(méi)有,更不用說(shuō)長(zhǎng)篇了。一般的新筆記小說(shuō),字?jǐn)?shù)通常控制在10000字以內(nèi)。除了篇幅上的要求,新筆記小說(shuō)的內(nèi)容往往非常廣博,包羅社會(huì)歷史的時(shí)遷,不同地域的風(fēng)物人情,或志人,或志怪。這一點(diǎn)也恰是汪曾祺沒(méi)有提及的。廣博的內(nèi)容,有時(shí)被作為人物活動(dòng)的外在環(huán)境,但卻往往是作者審美觀照、審美表現(xiàn)的重點(diǎn)和核心,而不是單純機(jī)械地?fù)?dān)當(dāng)塑造人物、烘托心理的工具,具有獨(dú)立的文化價(jià)值和審美價(jià)值。這種駁雜的內(nèi)容可能是對(duì)某地民俗的靜態(tài)陳列,也可能追蹤某些習(xí)俗的動(dòng)態(tài)變遷,但廣博多樣的背后通常傳達(dá)了厚重的傳統(tǒng)中國(guó)的鄉(xiāng)土經(jīng)驗(yàn)。汪曾祺筆下故鄉(xiāng)高郵的醬菜園、米鋪、得月樓和如意樓、各種家鄉(xiāng)小吃,何立偉筆下的偏僻閉塞的小城,林斤瀾筆下矮凳橋紐扣市場(chǎng)的人物鄉(xiāng)情,等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具備了內(nèi)容上的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新筆記小說(shuō)。比如鄧友梅的《那五》、馮驥才的《神鞭》之類的作品就很難歸于此類。原因在于,新筆記小說(shuō)不以情節(jié)的繁復(fù)取勝,往往要求淡化故事的含量,更多地表現(xiàn)出散文化和詩(shī)化的追求。它更強(qiáng)調(diào)淡化的情節(jié)和故事背后的人性張力和文化蘊(yùn)涵。另外,新筆記小說(shuō)的語(yǔ)言也頗具特色。盡管不同作家的語(yǔ)言有不同的風(fēng)格,或簡(jiǎn)潔明了,如孫犁,或古雅老道,如汪曾祺,或生澀有怪味,如林斤瀾,或地域色彩鮮明,如何立偉,總之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對(duì)語(yǔ)言逼真描繪功能的要求,追求語(yǔ)言水墨淋漓的寫意效果。這四個(gè)方面的綜合,才構(gòu)成了新筆記小說(shuō)作為文體類型的內(nèi)在要求,也是判斷、遴選新筆記小說(shuō)的標(biāo)準(zhǔn)和依據(jù)。
有的論者也提出過(guò)新筆記小說(shuō)與一般短篇小說(shuō)、小小說(shuō)等的區(qū)別。嚴(yán)格意義上,新筆記小說(shuō)作為一種小說(shuō)文體類型,它與短篇小說(shuō)、小小說(shuō)等是依據(jù)不同的邏輯尺度進(jìn)行的分類,而不是同一標(biāo)準(zhǔn)下劃分出來(lái)的不同類屬,不處在同一個(gè)層面上,不能展開(kāi)地位對(duì)等的區(qū)分比較。新筆記小說(shuō)的劃分以小說(shuō)的文體特征為依據(jù),而短篇小說(shuō)、小小說(shuō)等的區(qū)分依據(jù)主要是小說(shuō)的篇幅。由于在不同向度上劃分類屬,因而新筆記小說(shuō)就會(huì)很自然地與短篇小說(shuō)、小小說(shuō)存在著廣泛的交叉。大多數(shù)新筆記小說(shuō)就是短篇小說(shuō),一些文字少、篇幅小的作品就是小小說(shuō)。而一些與“尋根文學(xué)”的觀念相呼應(yīng)或受其影響才應(yīng)運(yùn)而生的作品,也就是“尋根小說(shuō)”。所以,本文將不再對(duì)新筆記小說(shuō)與其他層面上的小說(shuō)概念之間進(jìn)行不必要的比較區(qū)分。綜上所述,新筆記小說(shuō)是一種誕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延續(xù)至今的,受到中國(guó)古記傳統(tǒng)影響的,篇幅短小,內(nèi)容廣博,淡化情節(jié)和故事,有著散文化和詩(shī)化特征并努力追求寫意化語(yǔ)言的小說(shuō)文體類型。
參考文獻(xiàn):
[1] 汪曾祺、施叔青:《作為抒情詩(shī)的散文化小說(shuō)》,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
[2] 賈平凹:《太白山記》,《上海文學(xué)》,1989年第8期。
[3] 汪曾祺:《故里雜記》,《北京文學(xué)》,1982年第2期。
[4] 馮暉:《汪曾祺:新筆記小說(shuō)的首先發(fā)聲者》,《云夢(mèng)學(xué)刊》,2001年第3期。
[5] 孫犁:《談筆記小說(shuō)》,《孫犁全集 第8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6] 陳軍:《小說(shuō)氛圍初悟》,《西湖》,1990年第4期。
篇7
摘要:在許多評(píng)論家看來(lái),《受戒》是一部田園牧歌式的作品,有著世外桃源般的逃避。筆者認(rèn)為,《受戒》飽含抗?fàn)幰庾R(shí),小說(shuō)表現(xiàn)出對(duì)自由向往。
關(guān)鍵詞:受戒;沈從文;抗?fàn)?/p>
《受戒》寫于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是汪曾祺在60歲時(shí)的作品,可以說(shuō)是藝術(shù)上的純屬之作。小說(shuō)沿襲了作者一貫的散文一般的語(yǔ)言,詩(shī)一般的意境,向人們講述一個(gè)世外桃源的故事。很多評(píng)論家認(rèn)為《受戒》是一部田園牧歌式的作品,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無(wú)關(guān)。本文認(rèn)為,汪曾祺是一位關(guān)心人的疾苦的作家,《受戒》看似平淡,實(shí)則包含著作者對(duì)社會(huì)的期待。
《受戒》中作者贊頌了對(duì)束縛人性的反抗。庵趙莊,從名字就可看出寺廟在這個(gè)村莊是不容忽視的。庵本是對(duì)尼姑住所的稱呼,但是這個(gè)庵里居住的卻是和尚。在庵趙莊人的眼中,庵與寺也許并無(wú)分別。或者他們知道分別,卻并不在意。在他們的眼中,和尚和種田、做生意并無(wú)分別,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和尚們也儼然把出家當(dāng)做一種職業(yè)。在庵里,方丈不叫方丈,而是叫“當(dāng)家的”——他也確實(shí)干的是當(dāng)家職務(wù)。他屋里擺著賬簿和算盤,“經(jīng)營(yíng)”著庵里:做法事要收錢,廟產(chǎn)租給人種要收租,還要放債。這些看起來(lái)與方丈工作想去甚遠(yuǎn),更像是當(dāng)家的工作。他們并不遵守佛門的種種清規(guī)戒律。他們吃葷,最守清規(guī)戒律的老和尚普照平日里吃齋,“過(guò)年時(shí)除外。”他們不戒殺生——“他們吃肉不瞞人。年下也殺豬。殺豬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樣,開(kāi)水、木桶、尖刀。”如此“明目張膽”地殺生,可見(jiàn)佛規(guī)并沒(méi)有束縛住和尚們的心。他們不戒女色:二師父有老婆,三師父有相好的。正像小說(shuō)中所說(shuō)的那樣——這個(gè)庵里無(wú)所謂清規(guī),連這兩個(gè)字也沒(méi)人提起。
《受戒》中處處顯示出對(duì)自由的向往和對(duì)權(quán)威的不盲從。明海在當(dāng)和尚之前讀書,“每天寫一張仿”。村里人夸明海字寫得好——“寫得很黑。”這句讓人忍俊不禁的話包涵著作者的深意——對(duì)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莊稼人”來(lái)說(shuō),字的內(nèi)容不是重要的,他們要的只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nóng)生活。孟子與他們無(wú)關(guān),論語(yǔ)與他們無(wú)關(guān),甚至百家姓也與他們無(wú)關(guān),他們想要的只是自由地過(guò)著他們的生活。庵里的方丈仁山說(shuō)當(dāng)一個(gè)好和尚的三個(gè)條件,他自己一個(gè)也不符合——黃、胖,打牌老輸,整日衣衫不整。
早在“五四”時(shí)期,魯迅曾對(duì)佛門禁欲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的第一個(gè)師父》中,魯迅對(duì)愛(ài)吃葷又不戒色的和尚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好感,避而遠(yuǎn)之的確是修身禁欲、正襟危坐的大師兄。汪曾祺和魯迅都不贊成禁欲,主張遵從人性。只不過(guò)兩個(gè)人選擇的方式不同而已,一個(gè)溫和,一個(gè)激烈。但是,溫和的汪曾祺在小說(shuō)中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他在溫和的字里行間表現(xiàn)出反抗的姿態(tài),呼喚人性的回歸。
篇8
文章一開(kāi)頭,就寫了一個(gè)教授講課講到跑警報(bào)結(jié)束的故事,還寫了一個(gè)學(xué)生跑警報(bào)帶上一壺水,夾著溫庭筠或者李商隱的詩(shī)卷,從容自在地度過(guò)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嗎?寫這樣的故事,雞毛蒜皮的,和空襲警報(bào)的緊張環(huán)境好像不協(xié)調(diào)。這是抒的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嚴(yán)肅了?文章不是要善于剪裁嗎?作家為什么不把這些個(gè)事情省略掉呢?拉拉雜雜,在文章中有什么價(jià)值呢?
讀散文,欣賞散文,遇到現(xiàn)成的理論、概念不能解決的問(wèn)題,不能拘泥于理論和概念,而要從閱讀的經(jīng)驗(yàn)出發(fā),閱讀的“實(shí)感”,特別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覺(jué)或者叫做“初感”出發(fā)。我們讀這樣的文章最初的感覺(jué)是什么呢?是不是覺(jué)得挺有趣的?無(wú)論是教授還是學(xué)生都挺有趣。有趣在哪兒?空襲、轟炸、死亡的威脅,不但沒(méi)有讓他們恐懼,相反,他們挺悠閑,挺自在。這樣的事情寫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寫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這樣的空襲中,人們不緊張、不痛苦、不殘酷,相反,很好玩。如果不是這樣悠閑,不是這樣自在,就不好玩,就沒(méi)有趣味了。
是不是可以說(shuō),本文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種趣味,一種超越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的嚴(yán)酷性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這種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報(bào)的地點(diǎn)上。
在山溝里的古驛道上,有趕馬幫的口哨,有風(fēng)土化的裝束,有情歌,有馬項(xiàng)上的鈴聲,“很有點(diǎn)浪漫主義的味道,有時(shí)會(huì)引起遠(yuǎn)客的游子的—點(diǎn)淡淡的鄉(xiāng)愁”。
很顯然,趣味里滲透著感情。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民俗的欣賞,是情感和趣味的結(jié)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較適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幾個(gè)“點(diǎn)”。古驛道的一側(cè),“極舒適”,可以買到小吃,“五味俱全,樣樣都有”。溝壁上,有一些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來(lái)的對(duì)聯(lián)是“人生幾何,戀愛(ài)三角”,還有“見(jiàn)機(jī)而作,入土為安”。作家對(duì)這樣的對(duì)聯(lián)的感慨是:“對(duì)聯(lián)的嵌綴者的閑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佩服”的對(duì)象是“悠閑的情致”,也就是情感和趣味,但這樣的情趣和我們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這個(gè)“佩服”的妙處,在于其中的意思好像不太單純,不但有贊賞的意思,而且有調(diào)侃的意味。這種調(diào)侃,讓我們感到,這種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點(diǎn)詼諧,應(yīng)該是另一種趣味,如果把它叫做“諧趣”可能更加貼切。
這里透露出一點(diǎn)信息,作者所追求的,應(yīng)該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諧趣。富有諧趣的散文,就不應(yīng)該屬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這一點(diǎn),從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跑警報(bào)居然成了“談戀愛(ài)的機(jī)會(huì)”,男士還帶上花生米、寶珠梨等。“危險(xiǎn)感使兩方的關(guān)系更加親近了”,“女同學(xué)樂(lè)于有人伺候,男同學(xué)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xiàn)一點(diǎn)騎士風(fēng)度”,“從這一點(diǎn)來(lái)說(shuō),跑警報(bào)是頗為羅曼蒂克的”。
人的情感通過(guò)和諧的表現(xiàn)容易達(dá)到美化、詩(shī)化的境界,如若情感和環(huán)境的嚴(yán)酷不和諧,明明是血肉橫飛的戰(zhàn)事,卻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情調(diào),這就不和諧了。不和諧的趣味就有點(diǎn)好笑,有點(diǎn)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詩(shī)化、美化的方向去升華,而是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這就是諧趣,就是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論中,不和諧構(gòu)成幽默感是一個(gè)基本范疇,英語(yǔ)叫做“incongruity”。
到此為止,我們大概可以假定:這篇散文為幽默散文。接下去,認(rèn)真檢驗(yàn)一番,這個(gè)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報(bào)結(jié)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專門為女同學(xué)送傘的故事。作家這樣評(píng)述:
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bào)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恒。
本來(lái),“定例”的指稱與一定的規(guī)章條例習(xí)慣有關(guān),是一種規(guī)定、一種約束,有一定強(qiáng)制性,不能不執(zhí)行的。而這里卻是自覺(jué)奉獻(xiàn)的。至于“貴在有恒”,本來(lái)是指以頑強(qiáng)的意志堅(jiān)定地追求一種學(xué)業(yè)上、道德上的目標(biāo),而這里卻是為了討好女性。這是顯而易見(jiàn)的不和諧、怪異,給人以用詞不當(dāng)之感,但是,就在這種用詞不當(dāng)之中,讀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領(lǐng)悟了作家對(duì)此人的調(diào)侃。文章的幽默感隨著類似的怪異以及不和諧程度的強(qiáng)化而不斷加深。
跑警報(bào)的人大都帶著貴重的金子。哲學(xué)系的某個(gè)學(xué)生作出這樣的邏輯推理:
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huì)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huì)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他跑警報(bào)時(shí),特別是解除警報(bào)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dāng)真兩次撿到過(guò)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xué)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這位同學(xué)撿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但作家卻用一種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不和諧的邏輯把它說(shuō)成是必然的。這里邏輯的不和諧在于:有人丟掉金子必有人撿到金子,這不是必然的。有一種可能是丟掉了,并沒(méi)有給人撿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會(huì)撿到金子”更是不合邏輯的推理。這條推理要能成立,必須大前提是周延的,也就是沒(méi)有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撿,我是人,故我一定能撿到金子。如果只有個(gè)別人能夠撿到金子,并不能推出:我是人,就一定能撿到金子。不合邏輯的推演是荒謬的、不和諧的。這明顯是一種歪理歪推。因?yàn)槠淅碇幔棚@得不和諧、可笑,然而又有事實(shí)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諧趣在這則故事中顯得更濃了,幽默感也更強(qiáng)了。
跑警報(bào),有這么多趣事;不跑警報(bào),也有趣事。一個(gè)女同學(xué)利用這個(gè)機(jī)會(huì)洗頭;一個(gè)男同學(xué)利用這個(gè)機(jī)會(huì)煮蓮子,即使飛機(jī)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蓮子。文章寫到這里,幾乎全是趣事,輕松無(wú)比。忽然筆鋒一轉(zhuǎn),說(shuō)飛機(jī)也炸死過(guò)人,田地里死過(guò)不少人,但沒(méi)有太大的傷亡。這一筆,從文章構(gòu)思上來(lái)說(shuō),可以叫做補(bǔ)筆。飛機(jī)空襲本來(lái)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作家的文風(fēng)卻追求輕松、幽默,一連串寫了許多輕松的故事,幽默隨著不和諧感的強(qiáng)化而強(qiáng)化。但讀者也可能發(fā)生疑問(wèn):在這樣的民族災(zāi)難面前,作家怎么能夠幽默輕松得起來(lái)?作家的這一筆,應(yīng)該是一個(gè)交代。因?yàn)闆](méi)有太大的傷亡,所以才幽默得起來(lái)。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橫飛,尸橫遍野,再這樣輕松幽默就是歪曲現(xiàn)實(shí)了。魯迅在世時(shí),對(duì)林語(yǔ)堂提倡幽默一直懷著警惕,就是擔(dān)心把劊子手的兇殘化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個(gè)很有思想的作家,他對(duì)這一點(diǎn)是很有警惕的。除了這一筆以外,還有一筆,那是最為重要的一筆:
日本人派飛機(jī)來(lái)轟炸昆明,其實(shí)沒(méi)有什么實(shí)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guò)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chǎn)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guó)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gè)民族,長(zhǎng)期以來(lái),生于憂患,已經(jīng)很“皮實(shí)”了,對(duì)于任何猝然而來(lái)的災(zāi)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bǔ)”的精神對(duì)待之。這種“儒道互補(bǔ)”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yuǎn)征不服的。
篇9
汪曾祺是個(gè)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的小說(shuō)筆觸清新自然,語(yǔ)言凝練傳神,“以一種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散文化的隨意敘說(shuō)的語(yǔ)氣,將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人生片斷和社會(huì)層面溶入自我心境,向讀者談生活,講風(fēng)俗,簡(jiǎn)潔樸拙,娓娓動(dòng)聽(tīng)”。《珠子燈》的美,就在于自然平淡的敘述筆調(diào)下實(shí)則暗流洶涌,因?yàn)楣适略矫篮茫綍?huì)讓人覺(jué)得悲哀;作者敘述越節(jié)制,悲劇意蘊(yùn)越發(fā)深沉。
通篇來(lái)看,小說(shuō)中對(duì)娘家送燈的風(fēng)俗花了三大段的筆墨進(jìn)行了詳盡的描寫,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幅江南鄉(xiāng)間風(fēng)俗畫,特別是對(duì)珠子燈的描寫,如夢(mèng)亦幻;而對(duì)人物本身則采用白描手法,對(duì)孫小姐和王常生外貌、神態(tài)、日常生活均略去不提,只提到孫小姐婚前聽(tīng)從王常生的話放了腳,婚后讀書填詞,與王常生錦瑟和鳴,是一對(duì)幸福眷侶。這樣一濃一淡的反向處理,使小說(shuō)前半部分洋溢著生活的氣息和情趣,在喜慶吉祥的大環(huán)境中,孫小姐也愈發(fā)顯得恬淡,靜美,而后半部分的悲劇也愈發(fā)顯得悲涼。
但是,作者自始至終是與小說(shuō)與讀者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對(duì)于孫小姐夫亡后的生活、思想,汪曾祺沒(méi)有采取是批判還是贊揚(yáng)的態(tài)度,只是平淡地?cái)⒄f(shuō):“她變得有點(diǎn)古怪了,她屋里的東西都不許人動(dòng)。”“她病了,說(shuō)不清是什么病。”“她就這么躺著。”“她這樣躺了十年。”“她死了。”……這些句子沒(méi)有一個(gè)形容詞,全是短句,冷靜、客觀、簡(jiǎn)練地?cái)⑹隽藢O小姐由衰而亡的歷程,卻并未對(duì)孫小姐喪夫之痛做正面描述,并未對(duì)造成孫小姐悲劇命運(yùn)的原因痛心疾首,義憤填膺。這些汪曾祺都習(xí)慣于交給讀者自己去創(chuàng)造補(bǔ)充。
小說(shuō)中留白手法的運(yùn)用,沖淡了小說(shuō)的悲劇意識(shí),也解構(gòu)了那份深沉的悲哀與痛苦,使小說(shuō)的敘述平靜、節(jié)制,作者越是不說(shuō),我們?cè)绞悄芟胂髮O小姐如何在孤獨(dú)、冷清、隱忍中凋謝生命之花,就會(huì)對(duì)她寄予更深切的同情,在這種眼冷心熱的敘事中,小說(shuō)充滿了人性的溫情,保證了全文基調(diào)的和諧。
難點(diǎn)指津
由于汪曾祺習(xí)慣隱藏作品的傾向性和自己的態(tài)度,因此,對(duì)小說(shuō)主旨的把握正是本文的難點(diǎn)之一。傳統(tǒng)的解讀認(rèn)為,作者通過(guò)對(duì)孫小姐悲劇命運(yùn)的敘述,批判了封建禮教對(duì)人性的扼殺和摧殘。但是,汪曾祺曾說(shuō)過(guò),他的作品追求的是和諧、溫情、真、善、美、樂(lè)觀,這也是他回避政治問(wèn)題的結(jié)果,因此,將批判封建禮教作為本文的主題實(shí)際上是不太符合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理念。其實(shí)深入小說(shuō)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更深層次的意蘊(yùn)。首先,我們來(lái)仔細(xì)看看作者對(duì)對(duì)珠子燈的描寫:“灑下一片淡綠的光,綠光中珠幡的影子輕輕地?fù)u曳,如夢(mèng)如水,顯得異常安靜。”這樣詩(shī)意的語(yǔ)言將珠子燈描寫得異常美好,我們仿佛看見(jiàn)搖曳的淡綠燈光下,孫小姐和王常生或深情凝望或嬌羞打俏的幸福。而后作者馬上說(shuō)“元宵的燈光擴(kuò)散著吉祥、幸福和朦朧曖昧的希望”,在人們心中,作者眼里,珠子燈代表著“吉祥”、“幸福”和“希望”,因而并非普遍認(rèn)為的“因?yàn)橹樽訜羝砬蠖嘧佣欠饨ǘY教的象征”,相反,珠子燈是孫王夫妻二人幸福和諧的見(jiàn)證。其次,傳統(tǒng)地解讀認(rèn)為孫小姐為丈夫守節(jié)是受到了封建禮教的毒害和桎梏。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婚前孫小姐為什么會(huì)聽(tīng)從王常生的建議放了腳?如果孫小姐的“書香門第”的娘家真的是封建頑固,又為什么會(huì)教孫小姐讀詩(shī)詞,讀《西廂記》呢?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西廂記》是一本教人自由戀愛(ài),勇敢追求愛(ài)情的書呢!更何況,孫小姐婚后還讀了一些王常生帶回的新思想的書,思想自然會(huì)受到她所閱讀的書籍的影響,因此,說(shuō)孫小姐受到封建禮教毒害至深才導(dǎo)致了自身的悲慘命運(yùn)是不妥的。最后,在王常生病逝后,作者對(duì)孫小姐的敘述中,我們其實(shí)可以看出孫小姐對(duì)王常生那深沉的愛(ài)。但是孫小姐的希望在時(shí)光的流逝中消磨殆盡,眼里看不到愛(ài)人,便再也容不下別人,于是她便不再看,只聽(tīng),聽(tīng)各種聲響,風(fēng)箏響,斑鳩聲,麻雀打鬧聲,大蜻蜓振動(dòng)翅膀聲,老鼠咬嚙木器聲,還有珠子散落在地的聲音。讀到這里,凄涼感達(dá)到頂峰,讓人對(duì)她產(chǎn)生了無(wú)限的同情,并且對(duì)她對(duì)愛(ài)情的堅(jiān)守唏噓不已。這樣看來(lái),在封建禮教尚存的大環(huán)境中,守節(jié)就一定是件值得批判的事情嗎?人性與體制,究竟誰(shuí)的力量更大?這也許是留給我們思考的問(wèn)題。
考點(diǎn)訓(xùn)練
1.聯(lián)系文本,談?wù)剬?duì)這篇小說(shuō)主題的理解。
2.小說(shuō)關(guān)于珠子燈的描寫有什么作用?
附:參考答案
篇10
真正的主角應(yīng)該是能欣賞更多優(yōu)秀作品,乃至自己動(dòng)手創(chuàng)作
的學(xué)生!
一、賞析閱讀教學(xué)的定義
首先,自主欣賞。對(duì)于給定的作品,作為讀者的學(xué)生自主品味,這樣的閱讀是不帶任何先見(jiàn)的,到底是不是佳作,有沒(méi)有亮點(diǎn)――吸引你眼球的地方;其次,合作分析。將閱讀上升到理性的、更高一層的文化內(nèi)涵上,當(dāng)然,這種分析的結(jié)果是完全可以顛覆最初的閱讀感受。而在此期間教師的參與角色顯得尤為重要。以至最終達(dá)到激發(fā)學(xué)生的拓展閱讀與創(chuàng)作沖動(dòng)。這樣的教學(xué),我稱之為“賞析閱讀教學(xué)”。
二、賞析閱讀教學(xué)的過(guò)程
自主欣賞的環(huán)節(jié)側(cè)重對(duì)文本的最初體驗(yàn),通過(guò)視線掃描和聽(tīng)覺(jué)沖擊,學(xué)生從作者的語(yǔ)言文字中感受到了什么?汲取了什么信息?你喜不喜歡這樣的文章?
欣賞的方式有很多,但一定要給足學(xué)生時(shí)間:默讀文章,聽(tīng)范讀,自由大聲地朗讀,各有千秋。我更傾向于自由大聲地朗讀,北京大學(xué)錢理群教授在南京師大附中講授“閱讀魯迅”時(shí)曾說(shuō):“文學(xué)的教育,有時(shí)聲音極其重要,這聲音是對(duì)生命的一種觸動(dòng)。文學(xué)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所以,讀,讓學(xué)生感動(dòng),用心朗讀是感受文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方式。”
以汪曾祺《端午的鴨蛋》為例,對(duì)文章內(nèi)容的解讀并不難,學(xué)生能汲取到的信息點(diǎn)有:家鄉(xiāng)的習(xí)俗――獨(dú)特,家鄉(xiāng)的鴨蛋――有名,端午的鴨蛋――情趣。文章的趣味盎然,從容散淡完全取決于作者對(duì)語(yǔ)言的講究,那么本文欣賞的重點(diǎn)當(dāng)然放在品味汪曾祺散文的語(yǔ)言魅力上。哪些語(yǔ)句是你欣賞的,為什么會(huì)喜歡?這種方式需要建立在對(duì)學(xué)生閱讀感受的尊重上,才更容易激起學(xué)生的參與性。而對(duì)汪氏語(yǔ)言特色的歸納也水到渠成,一節(jié)課下來(lái),學(xué)生都在興致勃勃地選讀自己喜歡的文句。
合作分析環(huán)節(jié)是對(duì)作者為什么這樣寫而不那樣寫的探究,包括寫作目的、寫作背后的文化價(jià)值取向。只有深入地理性分析了這些,才算真正讀懂了文章,也才能真正“把每個(gè)學(xué)生都領(lǐng)進(jìn)書籍的世界,培養(yǎng)起對(duì)書的酷愛(ài),使書籍成為智力生活中的指路明星!”
“讀,便是體驗(yàn)作者的生活,體驗(yàn)作者從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抽象出的生活,也是在聯(lián)系并感受著我們自己的生活。”而這也恰恰成為我們分析作品的切入口。
同樣以《端午的鴨蛋》為例,文章如此津津樂(lè)道“咸鴨蛋”有意義嗎?參考答案說(shuō)是日常生活富含生活情趣、人生意味。生活中并不總是驚濤駭浪,也未必處處正襟危坐。只有充分感受生活中的種種快樂(lè)、悲苦、平淡以及詩(shī)意,我們才算真實(shí)地體驗(yàn)到生活的滋味。所以,在平淡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情趣、發(fā)現(xiàn)詩(shī)意,在小小咸鴨蛋里嘗出生活的滋味,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而當(dāng)我聯(lián)系到今年的端午節(jié)會(huì)讓每個(gè)中國(guó)人感到尷尬,韓國(guó)“江陵端午祭”于2005年向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申報(bào)“世界無(wú)形遺產(chǎn)”。發(fā)源于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倘若被聯(lián)合國(guó)認(rèn)定成別國(guó)的文化遺產(chǎn),不得不說(shuō)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悲哀。那么,一個(gè)小小的咸鴨蛋牽動(dòng)的僅僅是作者的思鄉(xiāng)情懷嗎?它背后所蘊(yùn)含的傳統(tǒng)文化還能再被下一代忽視、淡忘嗎?有了這樣理性的分析,學(xué)生學(xué)到的會(huì)更多!也許這在當(dāng)時(shí)是作者沒(méi)法預(yù)料的,但又何妨呢?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的結(jié)合,不正體現(xiàn)了分析閱讀的價(jià)值嗎?
三、賞析閱讀教學(xué)存在的問(wèn)題
賞析閱讀教學(xué)對(duì)于激發(fā)學(xué)生閱讀體驗(yàn),提高學(xué)生語(yǔ)文素養(yǎng)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當(dāng)然,作為初次實(shí)驗(yàn)難免遇到不小的阻力,畢竟教學(xué)過(guò)程是個(gè)互動(dòng)的環(huán)節(jié),現(xiàn)將問(wèn)題提出來(lái)期待更進(jìn)一步的研究!
1.既是完全擺脫傳統(tǒng)的老師講學(xué)生聽(tīng)的模式,就特別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的配合。如何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參與熱情仍是我需要努力的方向。
2.大部分同學(xué)的賞與析能不謀而合,學(xué)生的思維相差也不會(huì)太大,但問(wèn)題在于不知用什么樣恰當(dāng)?shù)恼Z(yǔ)言來(lái)表達(dá),每次學(xué)生都會(huì)無(wú)奈地說(shuō):“我知道意思,但不會(huì)說(shuō)。”能賞析出作品的味道,說(shuō)不出來(lái),或許能成為另一個(gè)研究課題。
3.合作分析環(huán)節(jié),怎樣防止走走過(guò)場(chǎng),讓學(xué)生真正在交流中獲
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也是迫切要解決的問(wèn)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