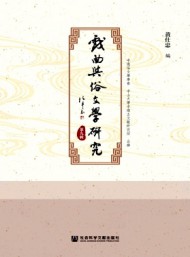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范文
時(shí)間:2023-07-04 17:24:27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guān)鍵詞】戲曲;樂隊(duì);審美;特征;民族;地域;創(chuàng)新
中圖分類號:J818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0-0058-01
戲曲樂隊(duì)是戲曲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guān)系到整個(gè)戲曲藝術(shù)的優(yōu)劣成敗。從美學(xué)的視角與高度來研究戲曲樂隊(duì)的審美特征,對于戲曲樂隊(duì)乃至整個(gè)戲曲藝術(shù)美學(xué)品位的提升,既具有重要的理論思考價(jià)值,又具有重要的實(shí)踐參考意義。為此,本文專門對戲曲樂隊(duì)的審美特征進(jìn)行全面系統(tǒng)、深入細(xì)致的探討與研究,以期引起關(guān)注與討論。
具體來說,戲曲樂隊(duì)的審美特征,可以分解為以下三個(gè)層面來進(jìn)行系統(tǒng)化解讀與探討。
一、民族性
戲曲樂隊(duì)的第一大審美特征,是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藝術(shù)共有的審美特征,也是一切藝術(shù)的核心特征。19世紀(jì)的俄羅斯著名作家赫爾岑明確指出:“詩人和藝術(shù)家們在他們的真正的作品中總是充滿民族性的。”[1]
戲曲樂隊(duì)的民族性審美特征,是十分鮮明的:其一,戲曲樂隊(duì)從本質(zhì)上講屬于民族樂隊(duì)范疇。其二,戲曲樂隊(duì)中的所有樂器,均是民族樂器。戲曲樂隊(duì)的傳統(tǒng)叫法是“場面”,又分“文場”與“武場”兩大類。“文場”指的是樂器中的吹、拉、彈、撥等各種管弦樂器,例如京胡、二胡、板胡、三弦、月琴、琵琶、笙、管、笛、簫、嗩吶等;“武場”指的是樂器中的打擊樂,例如堂鼓、大鑼、小鑼、鐃鈸、撞鐘等。其三,戲曲樂隊(duì)伴奏的唱腔或演奏的曲牌,也都是民族樂曲。其四,戲曲樂隊(duì)的演奏風(fēng)格,也是民族風(fēng)格,包括講究韻律與意境,推崇蘊(yùn)蓄、婉曲、諧調(diào)、中和、簡約、適度,追求“氣韻生動(dòng)”,強(qiáng)調(diào)“以情帶聲,聲情并茂”……如此等等,不一一贅述。
二、地域性
戲曲樂隊(duì)的第二大審美特征,是地域性。
地域性是民族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地域性特色愈鮮明,民族性特色也就愈強(qiáng)烈。魯迅先生早就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dòng)有利。”[2]古今中外的許多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作品,都以鮮明的地域性作為亮點(diǎn)與看點(diǎn)。例如《紅樓夢》的北京味兒、《金瓶梅》的山東味兒。
戲曲樂隊(duì)的地域性,更以我國各地方戲曲的地域性為依托。例如京劇的京味兒、川劇的川味兒、越劇的江浙味兒、呂劇的山東味兒、豫劇的河南味兒、晉劇的山西味兒、河北梆子的河北味兒、秦腔的陜西味兒、粵劇的廣東味兒、湘劇的湖南味兒、贛劇的江西味兒、黃梅戲的安徽味兒……而所有這些地方戲曲的樂隊(duì),當(dāng)然以鮮明的地域性為其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三、創(chuàng)新性
戲曲樂隊(duì)的第三大審美特征,是創(chuàng)新性。
創(chuàng)新是一切藝術(shù)、文學(xué)、科學(xué)的生命,“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人類一種高級的、特殊的、復(fù)雜的精神生產(chǎn)活動(dòng)。藝術(shù)的生命就在于創(chuàng)造和創(chuàng)新。沒有創(chuàng)造,沒有創(chuàng)新,就沒有藝術(shù)。這就意味著藝術(shù)家必須不斷地超越前人,超越同時(shí)代人,以及不斷地超越自己。”[3]
事實(shí)上也的確如此,中國戲曲樂隊(duì)的發(fā)展史,就是一個(gè)不斷創(chuàng)新的歷史。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最早將二胡引進(jìn)到京劇樂隊(duì)之中,增強(qiáng)了京劇樂隊(du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粵劇最先將西洋樂器小提琴引進(jìn)到粵劇之中,也增強(qiáng)了粵劇樂隊(du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京劇琴師徐蘭沅,創(chuàng)造出用優(yōu)美和諧的“過門”和巧妙的“托腔”“墊頭”,為梅蘭芳的演唱起到云托月的伴奏效果。王少卿也為京胡伴奏創(chuàng)造出許多新技術(shù)、新技巧。楊寶忠、李慕良等京劇琴師,也都創(chuàng)造出獨(dú)特的伴奏風(fēng)格。京劇鼓師白登云,曾先后為京劇名家楊小樓、梅蘭芳、王鳳卿、譚小培、郝壽臣、程硯秋等司鼓,以技藝精湛、善于創(chuàng)新著稱。
綜上所述,戲曲樂隊(duì)的審美特征,以民族性、地域性、創(chuàng)新性為三大支點(diǎn)。而這三大支點(diǎn),又是緊密結(jié)合、三位一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參考文獻(xiàn):
[1]赫爾岑.往事與沉思[A].赫爾岑論文學(xué)[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27.
篇2
戲曲藝術(shù)在表演上有一套完美的以手、眼、身、法、步為法則的程式套路,一個(gè)演員從上場到下場他的舉手投足、一招一式在音樂鑼鼓的伴奏下,起承轉(zhuǎn)合,連綿不斷,氣韻貫通,清晰流暢。戲曲和其他舞臺(tái)藝術(shù)種類相比,有一個(gè)獨(dú)特的美學(xué)特征,即韻律美。
戲曲的韻律美不光表現(xiàn)在表演上,也表現(xiàn)在劇本結(jié)構(gòu)、時(shí)空轉(zhuǎn)換等方面。“曲”即音樂性,是戲曲的本質(zhì)屬性。有了“曲”才有了“歌”,有了動(dòng)作就有了“舞”(即“無聲不歌、無動(dòng)不舞),以歌舞演故事,一貫到底,全劇自始至終處于音樂的律動(dòng)之中,呈現(xiàn)著韻律美。
然而,當(dāng)戲曲走入現(xiàn)代生活之后,在表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的表演方法上,受到了“斯氏”表演理論的影響,講究“生活、真實(shí)”等,這使我們的戲曲現(xiàn)代戲在表演上、在舞臺(tái)虛與實(shí)的處理上,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等方面走入了更改和實(shí)踐的誤區(qū);舞臺(tái)上“話劇加唱”的現(xiàn)象至今依然存在,失去了戲曲藝術(shù)獨(dú)特的美學(xué)特征——韻律美,造成了戲曲藝術(shù)的極大缺撼。有的戲雖然抓住了可以舞蹈的情節(jié),使勁地“舞”了一把,但總體表演上并沒有解決好“動(dòng)作的舞蹈性、造型性”等問題,不過是話劇加“唱”加“舞”而已。
如何解決這個(gè)問題,我們認(rèn)為首先應(yīng)該從戲曲美學(xué)的高度,提高對戲曲藝術(shù)審美特征的再認(rèn)識(shí)。戲曲有很多審美屬性,而戲曲的音樂屬性應(yīng)是它的本質(zhì)屬性。戲曲的這一特質(zhì),決定了戲曲把舞臺(tái)上的一切表演要素都納入到音樂的律動(dòng)之中,如場與場之間、二幕的開合、燈光的切換、時(shí)空的轉(zhuǎn)換,尤其是人物的表演在音樂的伴奏下,所有動(dòng)作的起、承、轉(zhuǎn)、合,形成一個(gè)動(dòng)作鏈條,雖然有停頓亮相、造型,但形斷意不斷。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講,“戲曲演員的舞臺(tái)表演動(dòng)作是流動(dòng)的造型、造型的流動(dòng)”。音樂伴奏下的造型流動(dòng)必然呈現(xiàn)韻律美。可以說,有沒有韻律美的動(dòng)作是演員表演水平高低的檢驗(yàn)標(biāo)準(zhǔn)。
另外,對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再認(rèn)識(shí)。生活的真實(shí)是生活,藝術(shù)的真實(shí)是藝術(shù),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是對生活的選擇、提純整合和升華,經(jīng)過這個(gè)過程才讓生活走上舞臺(tái)成為藝術(shù)。鑒于這一共同認(rèn)識(shí),我們認(rèn)為人物在舞臺(tái)上必然是藝術(shù)的生活著,而非真實(shí)的生活著,人物的表演動(dòng)作,必然是夸張的、變形的、符合藝術(shù)法則的、有節(jié)奏的、帶有生活內(nèi)涵的藝術(shù)表演動(dòng)作,而非生活原始形態(tài)的動(dòng)作。所以,老藝術(shù)家們說:“裝得像強(qiáng)似唱”,裝就是裝扮,裝就是藝術(shù)的表現(xiàn)生活。所以,藝術(shù)的生活在舞臺(tái)上的人物表現(xiàn)動(dòng)作流程,是帶有生活根據(jù)的、藝術(shù)加工過的、音樂化的動(dòng)作流程,時(shí)時(shí)呈現(xiàn)著韻律美。而在舞臺(tái)上強(qiáng)調(diào)生活真實(shí)的表演動(dòng)作,必然是散亂的、晦澀的,從而缺乏韻律美。
解決了以上認(rèn)識(shí)的問題之后,我們進(jìn)入實(shí)際表演操作層面。演員對人物的生活體驗(yàn)到之后,對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認(rèn)識(shí)到位之后,就要對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進(jìn)行藝術(shù)動(dòng)作即舞臺(tái)藝術(shù)表演動(dòng)作的選擇,對生活動(dòng)作的夸張和升華,但夸而有度,升而有根,雖離開了生活原則形態(tài),但“形相遠(yuǎn)”“意相近”,似與似之間,做到“情要真”“意要切”。藝術(shù)家們說:“不像不是戲,真像不是藝”,實(shí)際上就是指的這種藝術(shù)形態(tài)。生活藝術(shù)化,藝術(shù)生活化,表演動(dòng)作達(dá)到看不見程式的“程式”,看不見做派的“做派”,表“情”準(zhǔn)確,表“意”生動(dòng)。
在去掉生活真實(shí)對我們表演的羈絆之后,我們進(jìn)入操作的第二個(gè)層面。那就是對某一所表現(xiàn)內(nèi)容的布局謀篇,手、眼、身、法、步在這里大顯身手;第一個(gè)表演動(dòng)作從何地方“起”,用什么動(dòng)作去“承”,用什么身形去“轉(zhuǎn)”,用什么動(dòng)作去“合”,而下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在舞臺(tái)什么方位,最后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落到什么地方,留下下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的切入口,如此綿延不斷流轉(zhuǎn)開去,節(jié)奏分明,盡顯韻律。
我們從戲曲本質(zhì)屬性上尋求韻律之美之根,從藝術(shù)真實(shí)和生活真實(shí)中尋求韻律之美,從戲曲表演的章法上尋求韻律之美之法,是強(qiáng)調(diào)韻律之美在戲曲表演藝術(shù)中的根本性存在。戲曲不失去“曲”即音樂之存在,必然就有韻律,舞臺(tái)表演藝術(shù)始終流動(dòng)著的韻律之美,是戲曲舞臺(tái)表演藝術(shù)的極致。
中圖分類號:J614.9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戲曲藝術(shù)在表演上有一套完美的以手、眼、身、法、步為法則的程式套路,一個(gè)演員從上場到下場他的舉手投足、一招一式在音樂鑼鼓的伴奏下,起承轉(zhuǎn)合,連綿不斷,氣韻貫通,清晰流暢。戲曲和其他舞臺(tái)藝術(shù)種類相比,有一個(gè)獨(dú)特的美學(xué)特征,即韻律美。
戲曲的韻律美不光表現(xiàn)在表演上,也表現(xiàn)在劇本結(jié)構(gòu)、時(shí)空轉(zhuǎn)換等方面。“曲”即音樂性,是戲曲的本質(zhì)屬性。有了“曲”才有了“歌”,有了動(dòng)作就有了“舞”(即“無聲不歌、無動(dòng)不舞),以歌舞演故事,一貫到底,全劇自始至終處于音樂的律動(dòng)之中,呈現(xiàn)著韻律美。
然而,當(dāng)戲曲走入現(xiàn)代生活之后,在表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的表演方法上,受到了“斯氏”表演理論的影響,講究“生活、真實(shí)”等,這使我們的戲曲現(xiàn)代戲在表演上、在舞臺(tái)虛與實(shí)的處理上,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等方面走入了更改和實(shí)踐的誤區(qū);舞臺(tái)上“話劇加唱”的現(xiàn)象至今依然存在,失去了戲曲藝術(shù)獨(dú)特的美學(xué)特征——韻律美,造成了戲曲藝術(shù)的極大缺撼。有的戲雖然抓住了可以舞蹈的情節(jié),使勁地“舞”了一把,但總體表演上并沒有解決好“動(dòng)作的舞蹈性、造型性”等問題,不過是話劇加“唱”加“舞”而已。
如何解決這個(gè)問題,我們認(rèn)為首先應(yīng)該從戲曲美學(xué)的高度,提高對戲曲藝術(shù)審美特征的再認(rèn)識(shí)。戲曲有很多審美屬性,而戲曲的音樂屬性應(yīng)是它的本質(zhì)屬性。戲曲的這一特質(zhì),決定了戲曲把舞臺(tái)上的一切表演要素都納入到音樂的律動(dòng)之中,如場與場之間、二幕的開合、燈光的切換、時(shí)空的轉(zhuǎn)換,尤其是人物的表演在音樂的伴奏下,所有動(dòng)作的起、承、轉(zhuǎn)、合,形成一個(gè)動(dòng)作鏈條,雖然有停頓亮相、造型,但形斷意不斷。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講,“戲曲演員的舞臺(tái)表演動(dòng)作是流動(dòng)的造型、造型的流動(dòng)”。音樂伴奏下的造型流動(dòng)必然呈現(xiàn)韻律美。可以說,有沒有韻律美的動(dòng)作是演員表演水平高低的檢驗(yàn)標(biāo)準(zhǔn)。
另外,對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再認(rèn)識(shí)。生活的真實(shí)是生活,藝術(shù)的真實(shí)是藝術(shù),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是對生活的選擇、提純整合和升華,經(jīng)過這個(gè)過程才讓生活走上舞臺(tái)成為藝術(shù)。鑒于這一共同認(rèn)識(shí),我們認(rèn)為人物在舞臺(tái)上必然是藝術(shù)的生活著,而非真實(shí)的生活著,人物的表演動(dòng)作,必然是夸張的、變形的、符合藝術(shù)法則的、有節(jié)奏的、帶有生活內(nèi)涵的藝術(shù)表演動(dòng)作,而非生活原始形態(tài)的動(dòng)作。所以,老藝術(shù)家們說:“裝得像強(qiáng)似唱”,裝就是裝扮,裝就是藝術(shù)的表現(xiàn)生活。所以,藝術(shù)的生活在舞臺(tái)上的人物表現(xiàn)動(dòng)作流程,是帶有生活根據(jù)的、藝術(shù)加工過的、音樂化的動(dòng)作流程,時(shí)時(shí)呈現(xiàn)著韻律美。而在舞臺(tái)上強(qiáng)調(diào)生活真實(shí)的表演動(dòng)作,必然是散亂的、晦澀的,從而缺乏韻律美。
解決了以上認(rèn)識(shí)的問題之后,我們進(jìn)入實(shí)際表演操作層面。演員對人物的生活體驗(yàn)到之后,對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認(rèn)識(shí)到位之后,就要對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進(jìn)行藝術(shù)動(dòng)作即舞臺(tái)藝術(shù)表演動(dòng)作的選擇,對生活動(dòng)作的夸張和升華,但夸而有度,升而有根,雖離開了生活原則形態(tài),但“形相遠(yuǎn)”“意相近”,似與似之間,做到“情要真”“意要切”。藝術(shù)家們說:“不像不是戲,真像不是藝”,實(shí)際上就是指的這種藝術(shù)形態(tài)。生活藝術(shù)化,藝術(shù)生活化,表演動(dòng)作達(dá)到看不見程式的“程式”,看不見做派的“做派”,表“情”準(zhǔn)確,表“意”生動(dòng)。
在去掉生活真實(shí)對我們表演的羈絆之后,我們進(jìn)入操作的第二個(gè)層面。那就是對某一所表現(xiàn)內(nèi)容的布局謀篇,手、眼、身、法、步在這里大顯身手;第一個(gè)表演動(dòng)作從何地方“起”,用什么動(dòng)作去“承”,用什么身形去“轉(zhuǎn)”,用什么動(dòng)作去“合”,而下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在舞臺(tái)什么方位,最后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落到什么地方,留下下一個(gè)起、承、轉(zhuǎn)、合的切入口,如此綿延不斷流轉(zhuǎn)開去,節(jié)奏分明,盡顯韻律。
篇3
關(guān)鍵詞:梅蘭芳;表演美學(xué);解釋;錯(cuò)位
中圖分類號:J801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對梅蘭芳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實(shí)際上只有兩個(gè)路向,一個(gè)是從20世紀(jì)初至30年代梅蘭芳訪日、訪美、訪蘇前后,歐美、日本學(xué)界、演藝界對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中國戲曲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這種解釋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jì)90年代;另一個(gè)是50年代初梅蘭芳自己開始以口述的方式對自己的舞臺(tái)生活四十年加以回憶,這其中包括對自己的表演美學(xué)精神的解釋,這種解釋(包括他所寫的一些文章)一直持續(xù)到60年代初他去世之前。但細(xì)細(xì)考量這兩種解釋,雖然解釋的對象是同一個(gè),可解釋的內(nèi)涵卻是極其錯(cuò)位的。梅蘭芳對自己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并不是從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內(nèi)在特征出發(fā),而是從西方戲劇的尺度來衡量,而歐美、日本學(xué)界、演藝界對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中國戲曲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卻恰恰相反,是從跳出西方戲劇的思維模式出發(fā),極其同情的理解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獨(dú)特的審美特征。這種同情的理解雖然也不可避免的包含著某種誤讀,但其對中國戲曲表演美學(xué)真精神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卻比國內(nèi)學(xué)界的解釋更接近真理。
當(dāng)然,對梅蘭芳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事實(shí)上存在著多重路向,比如國內(nèi)學(xué)界的解釋等。之所以只提出以上兩種最主要的解釋路向,是因?yàn)閲鴥?nèi)學(xué)界的解釋要么是用西方的戲劇觀念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表演美學(xué)加以全盤否定,如“五四”時(shí)期的一些文章,要么就是從非審美的角度對梅蘭芳所代表的貴族文化傾向加以批判,如魯迅對梅蘭芳的批評諷刺文章。而更多的解釋其實(shí)是沒有任何解釋,只是將梅蘭芳的言論作為不證自明的公理直接拿來就認(rèn)作“真理”。相比之下,歐美、日本學(xué)界、演藝界對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中國戲曲表演美學(xué)的解釋與梅蘭芳對自己的表演美學(xué)精神的解釋雖然錯(cuò)位,但卻能更深刻的看清解釋者本身不同的出發(fā)點(diǎn)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
愛森斯坦對梅蘭芳的景仰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初。這位在電影《戰(zhàn)艦波將金號》導(dǎo)演中因?qū)⒚商婕夹g(shù)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而使電影作為“一種新藝術(shù)誕生了”[注:盧納察爾斯基在1925年底看完《戰(zhàn)艦波將金號》后曾激動(dòng)地說:“我們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化事件的見證人。一種新藝術(shù)誕生了。從今天起,電影藝術(shù)將成為一種真正具有偉大前途的藝術(shù)。”轉(zhuǎn)引自楊?巴爾納著《愛森斯坦傳》,美國印第安納大學(xué)出版社,1973年版,第102頁。]的年輕藝術(shù)家,1930年應(yīng)邀到美國好萊塢派拉蒙公司拍片時(shí),就從查理?卓別林那里了解了梅蘭芳這位東方杰出藝術(shù)家的卓越成就。所以,當(dāng)梅蘭芳1935年早春剛起程前往蘇聯(lián)的途中,愛森斯坦就在上海《時(shí)事新報(bào)》上發(fā)表了對梅蘭芳所代表的中國戲曲藝術(shù)表現(xiàn)出極大關(guān)注的談話,并在蘇聯(lián)對外文化協(xié)會(huì)出版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一書中專門撰寫了題為《梨園仙子》的文章,高度贊揚(yáng)梅蘭芳藝術(shù)的巨大魅力。當(dāng)他親眼看了梅蘭芳的演出后,更是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不僅與梅蘭芳合作將《虹霓關(guān)》這出戲中東方氏和王伯黨對槍歌舞這一節(jié)戲,以“一個(gè)完整的藝術(shù)品”的處理方式拍攝下來,而且還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四月十四日梅蘭芳邀請?zhí)K聯(lián)文藝界人士的座談會(huì)上,全面發(fā)表了他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審美特征的看法。
在愛森斯坦看來,中國戲曲藝術(shù)與日本戲劇藝術(shù)是有著“原則性的差異”的,這就如同古希臘藝術(shù)和古羅馬藝術(shù)之間的那種深刻的原則性的差異一樣。他將中國戲曲藝術(shù)比作興盛時(shí)期的古希臘藝術(shù),而將日本藝術(shù)比作發(fā)展時(shí)期的古羅馬藝術(shù)。他認(rèn)為,在羅馬藝術(shù)中“有一種機(jī)械化和數(shù)學(xué)式的簡化的沉積層,這使它和希臘的本性和特點(diǎn)截然不同”。而中國戲劇“所具有的那種杰出的生氣和有機(jī)性,使它與其他戲劇那種機(jī)械化的、數(shù)學(xué)式的成分完全不同”。所以,愛森斯坦說這是他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最有價(jià)值的發(fā)現(xiàn)和感覺”。他甚至由此而相信,這種比日本歌舞伎更純粹的中國戲曲藝術(shù),其“影響蘇俄現(xiàn)代戲劇的潛能性很大”。
愛森斯坦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所具有的第二個(gè)鮮明和令人驚喜的特征的發(fā)現(xiàn)和感覺是它的假定性的方法。他說這一點(diǎn)與莎士比亞時(shí)期的戲劇很相似。比如“表現(xiàn)夜間的場面時(shí)舞臺(tái)上有時(shí)也不暗下來,但是,演員卻可以充分把夜晚的感覺傳達(dá)出來”。愛森斯坦說他之所以要拍攝《虹霓關(guān)》對槍歌舞這節(jié)戲,正是因?yàn)檫@節(jié)戲的假定性表現(xiàn)得特別鮮明。他認(rèn)為這種假定性正經(jīng)歷著一個(gè)特別有趣的發(fā)展階段,即“由一種戲劇原則向另一種戲劇原則的過渡,向著一種生氣勃勃的運(yùn)動(dòng),向著每一個(gè)形象的獨(dú)立自主性的過渡,就是戲劇領(lǐng)域中運(yùn)動(dòng)的綜合”。這里所說的“一種戲劇原則”即作為技藝層面的程式化表現(xiàn)方式,而它向“另一種戲劇原則”的過渡,即技藝層面的程式化解構(gòu)重新組合、化合為表現(xiàn)特定人物形象的“獨(dú)立自主性”的程式表現(xiàn)方式。這即程式技藝和個(gè)性化程式表現(xiàn)力的完美統(tǒng)一。這就是愛森斯坦所說的,“我們在他(指梅蘭芳――引者注)的表演中看到了他的舞臺(tái)動(dòng)作的每一片斷的發(fā)展過程。我們看到,他怎樣完成一系列的手法,一系列幾乎是像組成般地不可缺少的運(yùn)動(dòng)。于是我們明白,這是對一些經(jīng)過特別深思熟慮才得到的完美組合的完全固定的表達(dá)方式。為了反映重要的傳統(tǒng),制定了一系列必要的原則。可是,從一場戲到一場戲,梅蘭芳卻在用對人物性格的生動(dòng)而出色的展示來豐富和充實(shí)著這些傳統(tǒng)。因此,梅蘭芳博士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就是這種對形象和性格的令人驚異的掌握……這種生動(dòng)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感覺,正是最令人震動(dòng)的印象之一”。中國戲曲藝術(shù)是不是看重表現(xiàn)“人物性格”這是可以討論的。事實(shí)上,戲曲人物的類型化、臉譜化決定了戲曲藝術(shù)并不像西方話劇那樣特別看重表現(xiàn)“人物性格”。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愛森斯坦對梅蘭芳所代表的戲曲表演藝術(shù)的理解是并不到位的。但這并不妨礙他極其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戲曲藝術(shù)用以表現(xiàn)人物形象的豐富生動(dòng)的程式,它的“完美組合”看似“完全固定”,但它在表演藝術(shù)家“生動(dòng)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演繹下,卻完全具有確定的非確定性的美,甚至能產(chǎn)生“最令人震動(dòng)的印象”。愛森斯坦甚至認(rèn)為,這種看似“完全固定”的程式正是中國文化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一種“極端”樣態(tài),而這個(gè)“程式規(guī)范”的另一個(gè)“極端”樣態(tài)就是“變化多端”。愛森斯坦十分肯定地說:“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具有的那種極端,在它那純形象化刻畫方面,在它那些變化多端的和程式規(guī)范的象征方面,都對我們很有啟發(fā)性。”[1](P291)
愛森斯坦之所以在親歷到梅蘭芳藝術(shù)的魅力時(shí)而“緊張”起來,正是因?yàn)樗麑@種比日本歌舞伎“更為廣闊、更為深邃、也更臻于完美境地的京劇”藝術(shù)的陌生化的審美創(chuàng)造效果興奮不已。他說:“我們研究京劇,畢竟不只是贊賞一下它的完整性就算完結(jié)。我們要從中尋求一種可以豐富我們自己的經(jīng)驗(yàn)的手段。與此同時(shí),我們又處于一種迥異的立場,問題于是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恪守程式規(guī)范而且看起來同我們的思想體系不相一致的藝術(shù),我們能從中得到什么呢?如果我們能得到些東西――那又是什么呢?”愛森斯坦說:
就是構(gòu)成任何一種藝術(shù)作品核心的那些要素的總和――藝術(shù)的形象化刻畫。形象化刻畫是我們新美學(xué)中的一個(gè)主要問題。我們正在加緊學(xué)習(xí)從心理方面展現(xiàn)我們的人物性格,可是一涉及形象化刻畫,我們就還很短缺。
所謂“藝術(shù)的形象化刻畫”即上文提到的讓愛森斯坦贊嘆不已的中國戲曲藝術(shù)“極其完美的形式”,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對人物形象“令人驚異的掌握”的審美表現(xiàn)力,構(gòu)成了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yàn)藝術(shù)仍然依據(jù)的那種異常的意象的對立面。而愛森斯坦所堅(jiān)持的形象化刻畫的“新美學(xué)”,也正是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理體驗(yàn)體系相對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愛森斯坦將梅蘭芳藝術(shù)的“形象刻畫”引入他所從事的電影藝術(shù)中。他說梅蘭芳藝術(shù)的這種長處“對我們的藝術(shù)有極重要的幫助。現(xiàn)在我們的藝術(shù)幾乎完全束縛在它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之中,那就是描述。這給形象帶來很大損害。我們現(xiàn)在親眼看到,不僅在我們戲劇中,而且在我們電影中,形象文化,也就是高度詩意形式的文化,幾乎已經(jīng)完全消失了。我們可以以我國默片電影時(shí)代為證,那時(shí)純粹的形象結(jié)構(gòu),而不僅是對人的描述,可以起著巨大的作用。如果我們用過去電影中的藝術(shù)成果和今天來對照的話,那么我們就會(huì)看到,過分的描述性在損害著形式的形象性。而在梅蘭芳博士那里我們看到的正相反:那是特別豐富的形象領(lǐng)域,是得到特別有力的發(fā)展的形象領(lǐng)域。”愛森欺坦從電影特性出發(fā),反對描述性的語言,而推崇形象鏡頭自身的表現(xiàn)力,即形式因的形象創(chuàng)造,這正與梅蘭芳藝術(shù)特別突出其形式的表現(xiàn)力是一致的。所以,愛森斯坦極為清醒地反省道:“我們在形式文化方面,特別是在電影中,正明顯處于可怕的停滯狀態(tài)。我們在梅蘭芳博士的戲劇中所看到的現(xiàn)象,即令人驚異地善于發(fā)揮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一切因素,對有聲電影是特別重要,特別有迫切意義的。”
正是基于以上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看法,愛森斯坦極具卓識(shí)遠(yuǎn)見地希望中國戲曲藝術(shù)要“極力加以避免”在藝術(shù)領(lǐng)域中(也包括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現(xiàn)代化,他說:
我甚至想對我們的朋友們稍微提點(diǎn)批評。我有一個(gè)印象,在他們從列寧格勒回來以后,除了梅蘭芳博士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仍然表現(xiàn)出令人驚異的完美技巧外,他周圍的人的表演好像染上了我們的情調(diào)。我認(rèn)為,這不會(huì)給演出帶來益處。
愛森斯坦的批評讓我們直到今天都應(yīng)當(dāng)警醒。我們太容易被異種文化所吸引了,對自己的文化則缺少一種自信。梅蘭芳“周圍的人”是誰呢?一是王少亭(老生),二是劉連榮(凈),三是朱桂芳(武旦),四是吳玉玲(武戲演員,朱桂芳對把),六是姚玉芙(旦),七是楊盛春(武生)。那么,他們看了一些什么歐洲和蘇聯(lián)劇目呢?在莫斯科看過(1)大劇院的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和烏蘭諾娃演出的《天鵝舞》及歐朗斯基的芭蕾《三個(gè)胖人》;(2)斯坦尼劇院的穆索爾斯基歌劇《鮑里斯?戈東諾夫》;(3)丹欽柯劇院的威爾第歌劇《茶花女》;(4)第一藝術(shù)劇院的契訶夫話劇《櫻桃園》及另兩出話劇《恐懼》和《杜爾賓的時(shí)代》;(第二藝術(shù)劇院的話劇《鐘表匠和雞》;(6)梅耶荷德劇院的小仲馬話劇《茶花女》;(7)卡美麗劇院的話劇《埃及之夜》和《喬弗萊――喬弗拉》等。在列寧格勒看過(1)大歌劇院的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2)小歌劇院的蕭斯塔科維奇的《姆欽斯克縣的麥克佩斯夫人》;(3)話劇院的莎士比亞的《理查三世》;(4)小話劇院的《為生命祈禱者》;(兒童劇院的木偶戲等。看了這么些西洋劇,我們的演員就染上了西洋劇的“情調(diào)”。愛森斯坦一針見血地說:“如果俄國演員們喜歡這一點(diǎn)(指中國戲曲演員的西洋劇“情調(diào)”――引者注),那就更可悲”。為什么?因?yàn)樵趷凵固箍磥恚?/p>
人類的戲劇文化,完全可以保留這個(gè)戲劇現(xiàn)有的極其完美的形式,而不會(huì)影響自己的進(jìn)步。(P10-14)而這正是十四年后梅蘭芳以另外一種表述方式談戲曲改革而遭到批評的思想主旨:“移步”而不“換形”。[3][注:梅蘭芳的“反省”談話另見1949年11月30日《進(jìn)步日報(bào)》第1版和同日《天津日報(bào)》第4版。]
愛森斯坦還特別關(guān)心地提出一個(gè)問題:“今后為了保護(hù)這個(gè)傳統(tǒng)應(yīng)該做些什么?”他當(dāng)時(shí)似比較樂觀,但也有些擔(dān)心。他說:“梅蘭芳博士周圍有許多研究家和由追隨者組成的相當(dāng)完美的學(xué)派。他們會(huì)繼承他并加以發(fā)展。如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或有欠缺,那么我想,我們共同的責(zé)任就是,請求梅蘭芳博士關(guān)心一下,要使他所積聚的完美的經(jīng)驗(yàn)繼續(xù)發(fā)展下去。”但這個(gè)良好的愿望,包括梅蘭芳在內(nèi)都是難以恪守、清醒把握的。
二
丹欽柯是四月十四日梅蘭芳邀請?zhí)K聯(lián)文藝界人士的座談會(huì)主持者。他前后有兩次發(fā)言。第一次主要是贊揚(yáng):“對于我們來說,最珍貴的是看到了中國舞臺(tái)藝術(shù)最鮮明、最理想的體現(xiàn),也就是中國文化貢獻(xiàn)給全人類文化的最精美、最完美的東西。中國戲劇以一種完美的,在精確性和鮮明性方面無與倫比的形式體現(xiàn)了自己民族的藝術(shù)。我從未想到過,舞臺(tái)藝術(shù)可以運(yùn)用這樣杰出的技巧,可以把深刻的含意和精煉的表現(xiàn)手段結(jié)合在一起。”由此,丹欽柯坦率地承認(rèn)中國戲劇給了蘇聯(lián)戲劇以“深刻重要的沖擊”。然而,特別值得我們關(guān)注的是丹欽柯在座談會(huì)結(jié)束時(shí)他第二次發(fā)言所提出的問題:“關(guān)于蘇聯(lián)藝術(shù)、俄羅斯藝術(shù)能夠向中國藝術(shù)提供些什么。”之所以想到要“提供什么”,肯定是他感到中國戲曲藝術(shù)尚有不足之處。但他對“提供什么”卻持謹(jǐn)慎的態(tài)度。他說:“我們對于任何具有突出特點(diǎn)的藝術(shù)都特別謹(jǐn)慎。大家很害怕談出自己的想法來,會(huì)產(chǎn)生一些吸引力,會(huì)引人注意。可是要吸收這些想法,卻對藝術(shù)起了破壞作用”。可見丹欽柯是真正明白了中國戲曲的藝術(shù)特征,[注:1935年9月4日丹欽柯在給一位演員的信中寫道:“梅蘭芳真是一個(gè)奇跡,凡是關(guān)心藝術(shù)向前發(fā)展的戲劇界人士,都可以從他那兒在演技、節(jié)奏和創(chuàng)造象征諸方面學(xué)到東西。”參見《聶米洛維奇――丹欽柯書信集》(第2卷),莫斯科:藝術(shù)出版社,1979年版,第441頁。]所以他擔(dān)心他的意見會(huì)破壞這種純粹的藝術(shù)本身,而他所要“提供”的意見恰恰是與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本質(zhì)相抵觸的,即內(nèi)容的第一位。他仍按照西方話劇的思維方式“提供”了自己的意見:
在我允許自己向我們天才的客人提出一些建議之前,我先向自己提出一個(gè)問題。我們的藝術(shù)給這個(gè)文化帶來了什么,還將帶來什么?我想,從……普希金開始,到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為止,我國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有一個(gè)特點(diǎn),它過去和現(xiàn)在一直充實(shí)著我國藝術(shù),它迫使我們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事形式工作的――在這個(gè)詞的狹窄意義上說――藝術(shù)工作者,必須把內(nèi)容放在第一位。正是這個(gè)俄羅斯藝術(shù)的內(nèi)容,幾百年來撥動(dòng)著我國詩歌的琴弦,我們的愿望的心弦――那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美好生活的思念,為美好生活而斗爭。正是這個(g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美好生活的思念,為美好生活而進(jìn)行的斗爭,是我國藝術(shù)的最主要的動(dòng)力。我要說,我們天才的客人可以為自己的藝術(shù)感到萬分欣慰。我們非常贊賞這個(gè)藝術(shù),認(rèn)為在手法方面、色彩方面,在人類本性一切可能性的綜合方面,對我們來說都是理想的。可是盡管這是我們的理想,但在我們觀看梅蘭芳的天才的表演的時(shí)候,我們產(chǎn)生了一個(gè)想法:如果他還能推動(dòng)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的話,那就更好了。(P3-4、16-18)
丹欽柯提出的這個(gè)“問題”可討論之處很多,但這里最關(guān)鍵的是梅蘭芳對這個(gè)“建議”的態(tài)度。梅蘭芳馬上通過翻譯轉(zhuǎn)達(dá)了他的意思:他高度評價(jià)這個(gè)希望。他將鼓起勇氣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P18)顯然,這與梅蘭芳對來自西方的意見和觀念一貫所持有的“謙遜”態(tài)度是一致的。至于這個(gè)“謙遜”的接受態(tài)度是否符合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梅蘭芳是很少考慮的。這里就包含著一個(gè)我們?nèi)绾闻c西方進(jìn)行對話的心態(tài)問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談到他與梅蘭芳的一次交談:“……梅蘭芳博士,這位動(dòng)作節(jié)奏勻稱,姿態(tài)精雕細(xì)鑿的大師,在一次同我的交談中強(qiáng)調(diào)心理上的真實(shí)是表演自始至終的要素時(shí),我并不感到驚奇,反而更加堅(jiān)信藝術(shù)的普遍規(guī)律。他說,中國戲劇藝術(shù)的高峰只能通過實(shí)踐和檢驗(yàn)才能達(dá)到;接著他又闡述一項(xiàng)我們業(yè)已達(dá)到的原則,盡管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那就是演員應(yīng)該覺得自己就是他所扮演的那個(gè)女主人公;他應(yīng)該忘記自己是個(gè)演員,而且好像同他那個(gè)角色融合在一起了。”[4](P718)這顯然不是梅蘭芳的看法,而是受到西學(xué)影響又影響到梅蘭芳的齊如山的看法。但梅蘭芳就這么不加思考地接受了,骨子里有一種不與西方戲劇靠近、相似就自慚形穢的自卑。這也就難怪愛森斯坦反對梅蘭芳劇團(tuán)很快就染上了西方戲劇的“情調(diào)”。[5]
三
1919年梅蘭芳第一次到日本訪問演出。5月27日在結(jié)束演出離開日本之前,梅蘭芳發(fā)表了講話:
我國戲曲與其說是供觀看,不如說是在聽的方面更受重視。所以對我們來說,這次訪日受到了各方面的刺激。首先我覺得以往的京劇不但跟時(shí)代沒有聯(lián)系,而且在布景、服裝方面考慮得不夠。應(yīng)該從這些方面加以改良,否則京劇不能進(jìn)步。另外,日本戲劇盡管有舊劇、新派劇、喜劇的區(qū)別,但在藝術(shù)上同我們的比較起來,更注重技巧。我們則只用身段來表示喜怒哀樂。所以,看了他們精致巧妙的表情,使我們驚詫不已。但這些情況也都是由于我國對戲曲的要求有所不同,才被引導(dǎo)到今天的這一步。我回國后應(yīng)當(dāng)先注意這些方面。[6](P93)
這里涉及到兩個(gè)方面的問題,一是“布景”問題,二是“表情”問題。“表情”問題是梅蘭芳一生都非常注重的問題,并且在四大名旦評分中他的“表情”分是唯一的滿分,[注:1931年《戲劇月刊》曾發(fā)表一份《四大名旦評分表》,這是依據(jù)當(dāng)時(shí)觀眾對“四大名旦”的藝術(shù)分項(xiàng)評分匯總的,其中梅蘭芳最突出的是“表情”100分。而“扮相”90分,“嗓音”95分,“身段”95分,“唱工”90分,“新戲”95分雖都很高,但唱工卻是程硯秋100分。]這與他深受日本新派劇,或者說受到西方話劇的表演方式的影響有很大的關(guān)系。然而,恐怕連梅蘭芳也沒有想到,其實(shí)日本學(xué)界根本就不認(rèn)同梅蘭芳關(guān)于“表情”的看法。落葉庵看了報(bào)紙上的梅蘭芳的這個(gè)談話,在《品梅記》中直率地說:
報(bào)紙上發(fā)表的梅的談話,其中有支那劇只有身段而缺乏表情的發(fā)言,還稱贊了日本戲劇的表情方法。不過我覺得他說的是假話,梅以及其他各位演員的表情都很巧妙。日本戲劇的表情方法顯得那么假惺惺而且太夸張,歸根到底是比不上他們的。或者也許他們故意不用表情,但是通過身段、念白、唱詞等,在臉上也很自然地流露出情趣。[6](P93)中國戲曲顯然并不是“故意不用表情”,但是“通過身段、念白、唱詞等,在臉上也很自然地流露出情趣”卻是中的的。而“身段”尤其被看中,這從歷代的身段譜對身段的嚴(yán)格要求就可以看出。當(dāng)然,是不是“只用身段來表示喜怒哀樂”這可以討論,但中國戲曲更注重身段的審美表現(xiàn)性,而并不太看重臉上的表情性卻是非常明晰的。之所以會(huì)如此,這是由東西方戲劇的不同的表演規(guī)則所決定的。
關(guān)于“布景”的問題這關(guān)涉到如何面對文化遺產(chǎn),如何改良京劇的問題。梅蘭芳第一次到日本時(shí)正是新派劇極為盛行的時(shí)期。他雖然看了舊劇、新派劇、喜劇,但給他最大“刺激”的恐怕就是緣于西方話劇的“新派劇”。正是因?yàn)椤靶屡蓜 辟N近現(xiàn)實(shí),表達(dá)時(shí)代問題,而且特別注重逼真現(xiàn)實(shí)的布景設(shè)置,所以梅蘭芳才會(huì)如此強(qiáng)烈地意識(shí)到“以往的京劇不但跟時(shí)代沒有聯(lián)系,而且在布景、服裝方面考慮得不夠。”他首先想到的也是“應(yīng)該從這些方面加以改良,否則京劇不能進(jìn)步。”1923年冬天,梅蘭芳根據(jù)《洛神賦》,并參考汪南溟的《洛水悲》雜劇編演的《洛神》一劇就實(shí)現(xiàn)了他的改良京劇的諾言。在這出戲的最后一場,他置了山水布景。從《洛神》、《西施》到《太真外傳》等一系列劇目用布景,這也就是梅蘭芳所說的“我曾經(jīng)有一個(gè)時(shí)期熱心于試驗(yàn)如何使用布景”的時(shí)期。但這一時(shí)期梅蘭芳對布景的使用是比較盲目的,很大程度上他是受了第一次到日本觀劇的“刺激”所致。可梅蘭芳在解放后回憶這段經(jīng)歷時(shí)卻與上引的他1919年在日本的這個(gè)講話很不一致。他說:“我曾經(jīng)有一個(gè)時(shí)期熱心于試驗(yàn)如何使用布景,記得1919年第一次赴日本演出時(shí),日本報(bào)刊上有人評論過中國戲沒有布景道具,比較原始等等一類的話,但更多的權(quán)威人士,如青木正兒、內(nèi)藤虎次郎、神田鬯等等在報(bào)刊則批評前者是‘一點(diǎn)鑒賞藝術(shù)的資格也沒有’。這些權(quán)威人士最欣賞的是《玉簪記》、《琴挑》、《御碑亭》等戲。我當(dāng)時(shí)沒有被這兩派所左右,所以在承華社初期編演的戲,如《洛神》、《西施》、《太真外傳》的某些場試用了布景,例如《西施》‘佾舞’一場,有宮殿內(nèi)的布景,西施在室內(nèi)地面當(dāng)中舞蹈。《太真外傳》的‘窺浴’、‘舞盤’等都有景,都是劇情的時(shí)間地點(diǎn)固定在這個(gè)景上的,但不是整出戲始終有布景。《洛神》除了末一場以外都不能用景………”[7](P703)其實(shí),梅蘭芳恰恰是被日本一些人士的話所左右,并且是受到很大的“刺激”才來解決京劇無布景的問題的。最能說明他改良布景盲目性的是他對泰戈?duì)柼岢龅男薷摹堵迳瘛凡季耙庖姷拿摹?924年5月,印度大詩人泰戈?duì)栐L問中國時(shí)專程拜訪了梅蘭芳,5月19日他還應(yīng)邀觀看了梅蘭芳編演的《洛神》。次日,在為泰戈?duì)栶T行的的席間,泰戈?duì)枌Υ藨虻摹洞ㄉ现畷?huì)》一場的布景提了意見。他說:“這個(gè)美麗的神話劇,應(yīng)該從各方面來體現(xiàn)偉大詩人的想象力,而現(xiàn)在所用的布景顯得平淡……”梅紹武在引述了這一段話后說:“父親后來尊重泰翁的意見,重新設(shè)計(jì)了那一幕布景,果然取得可喜的效果,此后就一直沿用下來。”[注:梅蘭芳在1958年1月給蘇聯(lián)專家做《中國京劇的表演藝術(shù)》報(bào)告時(shí)說:“現(xiàn)在我還使用布景的戲,只有一出《洛神》。這出戲,離開了布景就無法演出,因?yàn)樵诰巹r(shí),就設(shè)計(jì)了布景,他與表演藝術(shù)是密切結(jié)合著的。”參見梅蘭芳著《梅蘭芳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年版,第30頁。可見,梅蘭芳對這個(gè)布景的設(shè)計(jì)是極為看重的。][1](P57)泰戈?duì)栕鳛樯钍芪鞣轿幕绊懙脑娙耍⒉欢弥袊鴳蚯囆g(shù)的特點(diǎn),他所指出的“布景顯得平淡”的意見其實(shí)恰恰說明他是按照西方戲劇的尺度來要求的。要說“平淡”,中國戲曲的素幕就更顯得平淡,但它恰恰是中國戲曲美學(xué)所要求的。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日本一些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國戲曲審美傳統(tǒng)的學(xué)者和演藝界的藝術(shù)家比梅蘭芳更加維護(hù)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純粹性。1924年10月梅蘭芳第二次訪問日本演出期間,日本《演劇新潮》雜志社邀請了一些日本的著名戲劇家、漢學(xué)家為梅蘭芳舉行座談會(huì)。其中有一段對話非常令人深思:
梅(蘭芳):……在北京有許多舊式的劇場,也有像帝國劇院那樣的新劇場。
沈(恒):梅先生大都在新劇場演出。新劇場,又新又干凈。聽梅先生說,進(jìn)新劇場,心情好。總之,梅先生頭腦很新。(沈恒,梅蘭芳訪日的藝術(shù)顧問兼日文翻譯――引者注)
久米(正雄):這次使用的帝國劇院的舞臺(tái)裝置是效法中國的舞臺(tái)建筑建造的,據(jù)說是仿照貴國的舞臺(tái),建得和貴國的舞臺(tái)樣式一樣,是這樣的嗎?
沈:那是中國舊式劇場的樣式,同現(xiàn)在的新形式就不同了。新形式并不是那個(gè)樣子。新形式劇場沒有那種柱子,舊式才有柱子。
宇野(四郎):總之,那是為了襯托出中國情趣才造成那個(gè)樣子。還因?yàn)閾?dān)任顧問的福地信世先生主張中國的舊式舞臺(tái),認(rèn)為不使用布景為好……梅先生的所謂古裝歌舞劇,大概都使用布景。這次卻沒有堅(jiān)持一定使用布景。那是……
梅:有一出戲叫《洛神》。我原本想演那出戲來著,但是上演《洛神》必須有布景。因?yàn)檫@次不能使用布景,所以無法演那出戲。
山本(久三郎):因?yàn)槊废壬鲝堖M(jìn)步,鉆研新事物,所以上次來日時(shí)上演了像《天女散花》一類嶄新的劇目,還使用了全套的新布景。可是一般認(rèn)為,雖然從中國來了這種人物,可卻沒讓他們看到純粹的中國劇。帝國劇院花了錢辦了件大蠢事。花錢辦蠢事是最愚蠢的。但是,這次我們考慮到要演真正的中國戲,就決定避免使用布景,劇目也避免新劇目,而演出舊劇目。換句話說,這次(的劇目)是鑒于對上次的批評所決定的。我對戲劇一點(diǎn)不懂,所以主要是同福地信世等先生商量,聽取了中國劇場方面的意見之后決定的。梅先生也不是來這次之后,以后就不再來,今后還想請梅先生來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想盡可能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把事情辦好。
久米(正雄):上次來的時(shí)候,是有過那種批評。當(dāng)時(shí)從中國帶來了類似帶花的厚幕,把它掛在后邊。可是當(dāng)演《天女散花》時(shí),剛巧有前面一場演出時(shí)用過的熊谷的扭打場面的布景,于是原封不動(dòng)地使用了那個(gè)海的布景。所以有人提出與其使用那個(gè)布景,倒不如使用梅先生從中國帶來的帶花厚幕。我還記著那件事。
宇野:所以使用了熊谷的那個(gè)布景,是梅先生看到之后說想使用它才用的。并不是勉強(qiáng)使用那個(gè)古董的。[1](P103-104)由這段對話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梅蘭芳和日本戲劇家在對如何保護(hù)和繼承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上有不同的態(tài)度。一是在舞臺(tái)設(shè)置上,日本戲劇家效法中國舊式劇場而建筑有柱子的舞臺(tái),為的是“襯托出中國情趣”。而代表梅蘭芳發(fā)言的沈恒卻表現(xiàn)出對中國舊式劇場設(shè)置的不屑:“新形式劇場沒有那種柱子,舊式才有柱子。”而又特別強(qiáng)調(diào)“梅先生頭腦很新”,“大都在新劇場演出”。二是在是否使用布景上,日本戲劇家主張既然是用舊式舞臺(tái),那么還是以“不使用布景為好”。而梅蘭芳卻對“這次不能使用布景”,無法演出《洛神》感到極為遺憾。三是在劇目選擇上,日本戲劇家為了讓日本觀眾看到“純粹的中國劇”,不僅避免使用布景,而且,“劇目也避免新劇目,而演出舊劇目”。可梅蘭芳卻本想演剛剛排演不久的新劇目《洛神》,甚至為不能上演而在話語中多少流露出一些不快。四是在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上日本戲劇家極為敬畏,在決定用舊式舞臺(tái)、不用布景、 演舊劇目等重大問題時(shí),不僅征求德高望重的日本戲劇家福地信世[注:福地信世,梅蘭芳在1956年訪日后所寫的《東游記》中稱為“福地信士”。吉田登志子在《梅蘭芳1919、1924年來日公演的報(bào)告》中曾詳細(xì)考證了“福地信士”其實(shí)就是福地信世。福地信世(1877-1934)是日本明治時(shí)代的戲劇界泰斗櫻癡居士的長子,1900年東京帝大理學(xué)部地質(zhì)科畢業(yè)。他是一位對戲劇頗有研究的戲劇通,也是日本新舞踴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者。他與梅蘭芳交往很早,從1917年開始,他就在北京各戲園看京劇,邊看邊畫寫生,十年間積累了幾百幅京劇素描畫,其中最出類拔萃的是1918年6月20日他在吉祥園畫的梅蘭芳《玉堂春》的水彩劇裝畫。他還到梅蘭芳家登門拜訪,除了請教專業(yè)問題之外,他還模仿過梅蘭芳的臺(tái)步,梅蘭芳甚至把當(dāng)時(shí)在《思凡》里用的云帚贈(zèng)送給了他。日本學(xué)界認(rèn)為,梅蘭芳1919年初次訪問日本與福地信世背后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參見《戲曲藝術(shù)》,1987年第1期,第80-81頁。]的意見,而且還在“聽取了中國劇場方面的意見”之后才慎重作出決定的。而梅蘭芳則在用不用布景等問題上極其隨意,甚至根本不考慮這對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有無傷害。1919年到日本演出時(shí)明明帶著提花厚幕,但在演《天女散花》時(shí)恰巧前一場日本劇目中使用過的布景掛在那,梅蘭芳竟然就“原封不動(dòng)地使用了那個(gè)海的布景”,由此還導(dǎo)致了一場日本觀眾覺得沒有看到“真正的中國戲”的誤會(huì)。宇野四郎的最后一個(gè)解釋(即“所以使用了熊谷的那個(gè)布景,是梅先生看到之后說想使用它才用的。并不是勉強(qiáng)使用那個(gè)古董的。”)已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梅蘭芳是十分主動(dòng)地覺得應(yīng)當(dāng)用這個(gè)具像的“海的布景”,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泰戈?duì)柡翢o道理的讓梅蘭芳改《川上之會(huì)》一場的布景時(shí),他竟沒有做任何思考就改了。這一方面說明梅蘭芳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因而缺乏鑒別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圍繞著他的那些有西學(xué)背景的文人所給予他的影響太深。
參考文獻(xiàn):
[1]愛森斯坦梨園仙子[J]//梅紹武我的父親梅蘭芳(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6
拉爾斯?克萊貝爾格整理,李小蒸譯藝術(shù)的強(qiáng)大動(dòng)力――1935年蘇聯(lián)藝術(shù)家討論梅蘭芳藝術(shù)記錄[J]//中華戲曲(第十四輯)[C]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3]張頌甲“移步”而不“換形”――梅蘭芳談舊劇改革[N]天津:進(jìn)步日報(bào),1949-11-3
[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論京劇和梅蘭芳表演藝術(shù)[A]中國梅蘭芳研究學(xué)會(huì)、梅蘭芳紀(jì)念館編梅蘭芳藝術(shù)評論集[C]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5]鄒元江對“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京劇精神”的反思[J]//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C]第10輯廣州: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06//鄒元江對“梅蘭芳表演體系”的質(zhì)疑[J]//中國戲曲學(xué)會(huì)、山西師范大學(xué)編中國古代戲曲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C]2006
篇4
關(guān)鍵詞:昆曲唱腔;民族聲樂;必然聯(lián)系
中圖分類號: J82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27-091-02
昆曲藝術(shù)與民族聲樂實(shí)際上是同聲同源的關(guān)系。昆曲作為我國戲曲藝術(shù)的元祖,它對民族聲樂的形成與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民族聲樂是在昆曲藝術(shù)的發(fā)展過程中,結(jié)合西方美聲藝術(shù)中的相關(guān)理念,將昆曲聲腔進(jìn)行改進(jìn)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而來。在當(dāng)今各類藝術(shù)不斷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對昆曲聲腔以及民族聲樂各自的特點(diǎn)以及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進(jìn)行探討,是促進(jìn)聲樂藝術(shù)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的必經(jīng)之路。本文將簡單介紹昆曲與民族聲樂的相關(guān)概念,并針對昆曲聲腔中的氣息運(yùn)用、字聲關(guān)系、音色特征、共鳴手法這四個(gè)方面來分析昆曲唱腔與民族聲樂中的必然聯(lián)系。
一、昆曲與民族聲樂的相關(guān)概念
昆曲是我國比較古老的劇種,起源于昆山地區(qū),在元明時(shí)期為我國古代四大聲腔藝術(shù)之一。經(jīng)過了后期的不斷發(fā)展與融合,逐步形成了格律嚴(yán)謹(jǐn)、形式完備的演唱藝術(shù)。昆曲唱腔具有念白儒雅、婉轉(zhuǎn)曲折、華麗細(xì)膩的特點(diǎn),即使在沒有舞臺(tái)表演的情況下,僅憑其唱詞聲腔就能自成一格,具有較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昆曲反映了我國戲劇藝術(shù)的最高成就。民族聲樂是從我國的戲曲、曲藝、民歌中發(fā)展而來的,本次討論的是狹義的學(xué)院派民族聲樂。這類藝術(shù)形式是在傳統(tǒng)的古典音樂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西方美聲唱法所形成的新的聲腔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其藝術(shù)精神內(nèi)核是吸取我國傳統(tǒng)的古典音樂的精華,采用西方美聲唱法的技巧進(jìn)行整合與完善,為古典聲腔藝術(shù)融入豐富性,加強(qiáng)古典聲腔藝術(shù)的層次感,依據(jù)現(xiàn)代聲樂鑒賞標(biāo)準(zhǔn)對昆曲的聲腔藝術(shù)進(jìn)行改進(jìn)與創(chuàng)新。因此,民族聲樂與昆曲聲腔藝術(shù)之間具有必然的聯(lián)系。
二、昆曲唱腔與民族聲樂中的必然聯(lián)系
民族聲樂與中國傳統(tǒng)的演唱藝術(shù)之間具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民族聲樂在聲腔的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向昆曲聲腔借鑒了許多,形成了這兩種藝術(shù)形式的共通之處,在表現(xiàn)聲腔特點(diǎn)的氣息運(yùn)用、字聲關(guān)系、音色特征、共鳴手法這四個(gè)方面,二者的聯(lián)系尤為明顯。以下進(jìn)行詳細(xì)分析。
(一)氣息處理技巧
昆曲聲腔中的氣息處理原則為“丹田氣”。認(rèn)為“氣發(fā)于丹田者,自能耐久”,在進(jìn)行演唱的時(shí)候,歌唱的人的主要?dú)庀碜杂诘ぬ锾帲哂猩舷仑炌ā⒂崎L低回的特點(diǎn),聲音呈現(xiàn)出穩(wěn)定、綿長、悠揚(yáng)的特點(diǎn)。丹田氣的應(yīng)用是通過人的意識(shí)來體會(huì)氣息在胸腹中不斷下沉的感覺,在膈肌下沉以及腹部上提的過程中,對腹腔起到了壓縮的作用,此時(shí),人通過感覺感知到氣息聚集于腹部,這實(shí)際上與西方的“腹式呼吸法”的概念相同。通過丹田氣,唱歌的人的眉心、口咽、小腹的對抗支點(diǎn)形成了一條線,發(fā)出的聲音呈現(xiàn)出集中而明亮的特點(diǎn)。這是昆曲聲腔的形成基礎(chǔ)。除此之外,氣息還需要具備“氣口”。在演唱過程中,精氣神和換氣時(shí)需要運(yùn)用到“氣口”技巧。“氣口”主要包括句讀的劃分、取氣、偷氣、歇?dú)狻Q氣、就氣等多種氣息的運(yùn)用。換氣要求找準(zhǔn)氣口,要快、要輕、要均勻,且用鼻不用口。民族聲樂的演唱中吸取了昆曲聲腔中的氣息運(yùn)用技巧,并結(jié)合西方美聲中的“胸腹式呼吸”進(jìn)行了完善。在演唱者的氣息運(yùn)用的過程中,于吸氣時(shí)將自身胸腔完全打開,深吸慢吐,使氣息令胸腹腔充盈,通過橫膈膜平穩(wěn)下降來呼氣發(fā)聲。這是民族聲樂與昆曲聲腔中氣息運(yùn)用方面同根同源的一方面。而在此基礎(chǔ)上,民族聲樂又出現(xiàn)了一絲變化。由于昆曲聲腔的審美與現(xiàn)代民族聲樂聲腔的審美具有一定的差異,昆曲強(qiáng)調(diào)聲音的細(xì)膩、靈巧,對氣息具有綿長、集中的要求,但是在氣息量的使用上要求不大。民族聲樂強(qiáng)調(diào)聲區(qū)的劃分以及音色的圓潤特征,在氣息的使用上,要求能夠支撐洪亮的音量,因此,需要較大的氣息量。從這一點(diǎn)上可以看出民族聲樂在昆曲聲腔上具有發(fā)展的聯(lián)系。
(二)曲詞處理
昆曲在演唱過程中對出字、歸韻、收聲、十三轍、五音四呼等字韻、字聲的發(fā)聲部位、著力點(diǎn)的把握上要求十分嚴(yán)格,需要相當(dāng)?shù)臏?zhǔn)確。民族聲樂繼承了這一點(diǎn),同時(shí)也在字聲關(guān)系上做出了一定的改變。字聲關(guān)系上,昆曲聲腔由于起源于江蘇昆山,故而,體現(xiàn)了當(dāng)?shù)氐姆窖运囆g(shù)特點(diǎn)。在聲調(diào)的劃分上呈現(xiàn)出較普通話更具層次性的特點(diǎn)。普通話的聲調(diào)中,包括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而昆曲中的聲調(diào)還劃分了陰上、陽上等,令聲調(diào)更加的細(xì)膩。并且在念唱中帶有吳音的特點(diǎn),尖字、團(tuán)字、上口字、入聲字等。而民族聲樂主要是依據(jù)現(xiàn)代漢語的聲調(diào)進(jìn)行演唱,較少的運(yùn)用方言,可以說是對昆曲聲腔的一方面的簡化。同時(shí),在字聲關(guān)系的處理上,民族聲樂與昆曲聲腔所表現(xiàn)出不同的處理態(tài)度。昆曲對字音的要求比較嚴(yán)格,在實(shí)踐教學(xué)過程中將咬字與吐字作為重點(diǎn),喊嗓、念白、吊嗓是昆曲聲腔訓(xùn)練的基礎(chǔ),要求每個(gè)字音都要清晰、準(zhǔn)確,整體上體現(xiàn)出字重腔輕的審美特點(diǎn)。而民族聲樂增加了對單字處理的自由性,要求字聲結(jié)合下的整體效果要具有圓潤性。從某種角度來說,民族聲樂在字聲關(guān)系的處理上以掌握昆曲的基本技藝為主,對表現(xiàn)的側(cè)重點(diǎn)進(jìn)行了轉(zhuǎn)移,使之呈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代美感。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昆曲聲腔對民族聲樂的重要影響。此外,不同于北昆,昆曲的另外一種完整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湘昆,在字詞的處理上呈現(xiàn)出以方言為主,字句節(jié)奏緊湊、聲音高亢,并融合了湖南當(dāng)?shù)氐拿窀枰约靶≌{(diào)、叫賣、吆喝之聲的特點(diǎn),獨(dú)具一格、別有風(fēng)味,在這一點(diǎn)上對民族聲樂也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表現(xiàn)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面貌以及生活等方面內(nèi)容的民族聲樂作品中,有將當(dāng)?shù)胤窖耘c普通話向結(jié)合的特點(diǎn),同時(shí)也采取了比較高亢的唱法,在節(jié)奏上也體現(xiàn)出緊湊與悠揚(yáng)相得益彰的表現(xiàn)特點(diǎn),這些都充分體現(xiàn)了民族聲樂在發(fā)展過程中對昆曲藝術(shù)精華的吸收與發(fā)展。
(三)音色表現(xiàn)
音色追求是聲腔藝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的表現(xiàn)方面。作為中國戲劇中的瑰寶,昆曲對音色的追求具有自身獨(dú)特的審美特點(diǎn)。要求發(fā)聲具有集中性,切忌發(fā)聲的散漫。民族聲樂很好的繼承了這一點(diǎn),用民族聲樂中的說法就是“氣集聲聚”。民族聲樂在對音色的標(biāo)準(zhǔn)的實(shí)現(xiàn)以及藝術(shù)處理上又具有一定的發(fā)展。由于昆曲多講述的是男女之間的唯美浪漫的愛情故事,在音色上主要要求悅耳靈動(dòng)、婉轉(zhuǎn)清亮,演員多采用假聲或者小嗓進(jìn)行演唱,演唱過程中口型微張,音色纖柔且線條流暢。民族聲樂繼承了昆曲中的真假音的混合,并結(jié)合西方美聲唱法,進(jìn)行了聲區(qū)的劃分,在演唱過程中追求高低聲區(qū)的統(tǒng)一性,在音色上追求通透、豐滿以及金屬質(zhì)感。另一方面,昆曲在進(jìn)行演唱表演的時(shí)候,針對不同的戲曲角色會(huì)具有不同的音色要求,例如,丫鬟的音色輕巧靈動(dòng)、小姐的音色細(xì)膩連綿。民族聲樂吸取了昆曲的這一特點(diǎn)并結(jié)合西方的音域理念,依據(jù)不同的角色劃分出了男女兩方面的中音、低音與高音,同時(shí)依據(jù)具體的演唱技巧,劃分出不同特點(diǎn)的高音。由此可見,昆曲對民族聲樂的影響是基礎(chǔ)的且重要的。民族聲樂是在昆曲聲腔的藝術(shù)技術(shù)上得以發(fā)展而來,兩者之間具有同源的性質(zhì)以及必然的聯(lián)系。
(四)共鳴處理
共鳴是唱腔藝術(shù)中的一個(gè)重要的方面。共鳴手法在昆曲中與演唱者的咬字方式之間具有直接的聯(lián)系。不同的共鳴位置會(huì)發(fā)出不同的共鳴效果,在唱腔藝術(shù)中,主要的共鳴位置為喉舌牙齒唇。實(shí)際上,這些不同的發(fā)音出字的部位就是五音劃分的基礎(chǔ)。在進(jìn)行昆曲演唱的過程中,需要依據(jù)適當(dāng)?shù)墓缠Q方式來調(diào)整口腔狀態(tài)。在保證元音發(fā)聲準(zhǔn)確的狀態(tài)下,擴(kuò)大共鳴效果。昆曲中的共鳴要求是將共鳴位置固定,并通過子音進(jìn)行著力展開共鳴,形成字與韻的對應(yīng),這種共鳴方式具有含蓄婉轉(zhuǎn)的美感。同時(shí),昆曲共鳴所形成的練聲方式通常為胸腔共鳴的小嗓假聲,其共鳴特點(diǎn)是音量小、音高高。現(xiàn)代民族聲樂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現(xiàn)代共鳴的美學(xué)審美特點(diǎn)的變化,對昆曲共鳴的唱腔技巧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改變。結(jié)合美聲的相關(guān)理念,將產(chǎn)生共鳴的部位進(jìn)行了更加精細(xì)的劃分,依據(jù)不同部位所產(chǎn)生的共鳴分為了上腔共鳴與下腔共鳴,并細(xì)分為頭腔共鳴、咽腔共鳴、口腔共鳴、鼻腔共鳴、腹腔共鳴、胸腔共鳴。充分體現(xiàn)了民族聲樂在昆曲唱腔藝術(shù)上的發(fā)展。
三、結(jié)語
綜上所述,民族聲樂在形成以及發(fā)展的過程中對昆曲藝術(shù)技藝具有很大程度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尤其是在唱腔方面,作為聲樂藝術(shù)的靈魂的唱腔技藝,民族聲樂在昆曲中的傳承體現(xiàn)出了相對完整性以及創(chuàng)新性的特點(diǎn)。昆曲聲腔中的氣息運(yùn)用、字聲關(guān)系、音色特征、共鳴手法這四個(gè)方面對民族聲樂的影響是巨大的,毫不夸張地說,民族聲樂的唱腔藝術(shù)是在昆曲唱腔中這四個(gè)方面逐一發(fā)展而來,以昆曲唱腔為基礎(chǔ),結(jié)合西方美聲理念,才得以形成與發(fā)展。筆者從這四個(gè)方面探討了昆曲與民族聲樂之間所具有的必然聯(lián)系。正是在昆曲唱腔的藝術(shù)優(yōu)勢的支持下,民族聲樂才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展現(xiàn)出其獨(dú)有的藝術(shù)特點(diǎn)以及完善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民族聲樂在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需要堅(jiān)持自身從昆曲唱腔藝術(shù)中所吸取的精髓,才能越來越走向國際化。
參考文獻(xiàn)
[1]程虹.戲曲唱腔與民族聲樂的比較[J].四川戲劇,2010(30).
[2]劉海燕.試論昆曲《牡丹亭?游園》閨門旦的演唱藝術(shù)[J].中國音樂學(xué),2010(31).
篇5
【關(guān)鍵詞】舞蹈藝術(shù);發(fā)展;審美特點(diǎn);欣賞
中圖分類號:J70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5-0187-01
舞蹈是人們采用音樂韻律和肢體語音來展現(xiàn)人類情感的一種藝術(shù),它是一種人類展現(xiàn)身體造型、時(shí)間藝術(shù)、空間藝術(shù)的綜合體,并將藝術(shù)美感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它的不斷發(fā)展將舞蹈審美藝術(shù)逐漸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可以說舞蹈藝術(shù)具有著顯著的藝術(shù)審美特征。
一、我國舞蹈藝術(shù)的發(fā)展概況
舞蹈藝術(shù)作為文化發(fā)展的一種載體,隨著社會(huì)文化的不斷豐富而迅速發(fā)展。舞蹈藝術(shù)是從戲曲藝術(shù)中發(fā)展而來的,并經(jīng)過不斷發(fā)展形成了一種具有獨(dú)立性的藝術(shù)。我國現(xiàn)代的舞蹈藝術(shù)作品大部分都具有很強(qiáng)的專業(yè)性。國內(nèi)舞蹈藝術(shù)不僅展現(xiàn)了藝術(shù)的多元化發(fā)展形勢,還將面臨著更廣闊的發(fā)展前景。由于我國社會(huì)文化的迅速發(fā)展,舞蹈藝術(shù)也經(jīng)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并且舞蹈作為我國文化發(fā)展的一種載體,它的展現(xiàn)形式也被不斷地豐富和創(chuàng)新。舞蹈與其它形式的藝術(shù)相比,它有著自己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它是采用肢體語言的方式為人們呈現(xiàn)各種聽覺和視覺的享受[1]。它也是一種非常復(fù)雜、豐富的藝術(shù),它具有多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例如,花樣滑冰、藝術(shù)體操等。舞者運(yùn)用自己的肢體動(dòng)作來為人們展現(xiàn)豐富的情感,是一種展現(xiàn)空間美感和身體造型的綜合性藝術(shù)。該種藝術(shù)采用舞臺(tái)、音樂以及人體語言相結(jié)合的方式,將肢體語言轉(zhuǎn)變?yōu)橐环N文化和情感,從而為觀眾帶來震懾人心的感受。對舞蹈藝術(shù)基本審美特點(diǎn)進(jìn)行了解,對于提升我們的舞蹈欣賞水平有一定的幫助,這也是我們學(xué)會(huì)鑒賞和欣賞舞蹈的基本前提。
二、舞蹈藝術(shù)的審美特點(diǎn)
(一)舞蹈是依托人體的姿態(tài)和動(dòng)作來展現(xiàn)藝術(shù)形象的。普遍將有變化的、有組織的、有韻律的、有節(jié)奏的姿態(tài)和動(dòng)作,稱為舞蹈語匯和舞蹈語言。首先,舞蹈語言具有一定的流動(dòng)性。舞蹈是運(yùn)用一連串的動(dòng)作來展現(xiàn)生活中的各種情感,所以這些形態(tài)動(dòng)作也是在流動(dòng)中完成的。其次,舞蹈語言具有一定的連續(xù)性。每個(gè)舞蹈作品都是采用具有連續(xù)性的有關(guān)的肢體動(dòng)作來塑造藝術(shù)形象的。第三,舞蹈語言是具有情感表現(xiàn)力和節(jié)奏感的。它是對生活事物不斷提煉的結(jié)果,但也只有那些具有節(jié)奏、規(guī)律的運(yùn)動(dòng)才能夠成為舞蹈化的動(dòng)作。
(二)舞蹈是以動(dòng)作抒情。從某種角度來講,舞蹈也屬于一種表情藝術(shù),它掌握了現(xiàn)實(shí)的審美特點(diǎn),展現(xiàn)了生活中的點(diǎn)滴。它將藝術(shù)美與生活中線條優(yōu)美、熱情奔放的動(dòng)作相融合,展現(xiàn)生活中的真實(shí)情感,達(dá)到拙出于事、長漱于情的效果。在舞蹈藝術(shù)的表演過程中,情感會(huì)自然而然地從各種舞姿中流露出來。
(三)舞蹈與音樂有著極為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每個(gè)舞蹈都擁有一定的音樂性。音樂的形象和舞蹈是緊密聯(lián)系的。舞蹈的靈魂是音樂,同時(shí)舞蹈又是音樂形象的具體表現(xiàn)[2]。音樂運(yùn)用樂聲來展現(xiàn)人們的情感和思想,舞蹈運(yùn)用人體的改變來展現(xiàn)情感,它們都擅長拙于敘事、長于抒情。恰到好處的音樂旋律,不只可以將舞臺(tái)氣氛烘托出來,還能夠創(chuàng)造出美好的意境,畝能夠提高舞蹈形象情感表達(dá)的效果。
三、舞蹈藝術(shù)的欣賞
舞蹈藝術(shù)欣賞指的是人在欣賞表演時(shí)形成的一種精神感受,它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理解與感受、認(rèn)識(shí)與情感高度統(tǒng)一的精神活動(dòng)。欣賞舞蹈藝術(shù)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的藝術(shù)素養(yǎng),同時(shí)能夠激發(fā)人們情感與藝術(shù)的共鳴,進(jìn)而將舞蹈藝術(shù)內(nèi)在的美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首先欣賞者應(yīng)當(dāng)對舞蹈藝術(shù)的風(fēng)格進(jìn)行初步的了解,風(fēng)格了解得越多就會(huì)獲得越多的樂趣;其次,要對舞蹈藝術(shù)的審美特點(diǎn)有明確的認(rèn)識(shí),做到有感情、有思想、有角度地欣賞舞蹈藝術(shù);第三,應(yīng)當(dāng)擁有一定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對于一個(gè)舞蹈作品的欣賞不只是在于視覺上舞姿的美麗,更要領(lǐng)悟到舞蹈中所蘊(yùn)含的內(nèi)在情感;第四,在欣賞的過程中,要集中精力將自己置身于舞蹈表演中,才能夠感受到來自舞蹈藝術(shù)的美。
舞蹈藝術(shù)將人們的情感表達(dá)和審美意識(shí)完美地融入到了舞姿當(dāng)中,運(yùn)用完美的動(dòng)作給人一種視覺上的享受,進(jìn)而激發(fā)人們產(chǎn)生的情感共鳴[3]。學(xué)會(huì)舞蹈藝術(shù)的欣賞技巧和審美特點(diǎn),能夠提升人們的內(nèi)涵,豐富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人們的整體素質(zhì),領(lǐng)略舞蹈的意境和氛圍,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欣賞者的藝術(shù)欣賞水平和藝術(shù)修養(yǎng)。
參考文獻(xiàn):
[1]徐艷.論舞蹈藝術(shù)對人的本質(zhì)生成功能――兼析舞蹈藝術(shù)在學(xué)校美育中的價(jià)值取向[J].教學(xué)與管理(理論版),2014,(10):21-23.
[2]鄒小燕.論舞蹈藝術(shù)的審美特征[D].廣西師范大學(xué),2007.
[3]饒海燕.群眾舞蹈藝術(shù)和創(chuàng)編技巧解析[J].文藝生活?文藝?yán)碚摚?014,(9):125.
篇6
任何一個(gè)民族傳統(tǒng)文化有其獨(dú)立的存在價(jià)值,因?yàn)橛兄r明的文化特征。中國戲曲在20世紀(jì)進(jìn)入了興旺繁榮時(shí)期,四大名旦的誕生,標(biāo)志著中國傳統(tǒng)戲曲藝術(shù)走入了興盛時(shí)代,臉譜是戲曲藝術(shù)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作為戲曲藝術(shù)形象塑造的主要表現(xiàn)元素,在舞臺(tái)上以夸張的表現(xiàn)形式,塑造出了許多個(gè)性鮮明的舞臺(tái)人物形象并形成中國戲曲化妝獨(dú)特的審美風(fēng)格。一般來說,臉譜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體可以從“形”和“色”兩個(gè)方面來看,從這兩點(diǎn)中,使觀眾能目視外表,窺其心胸。色彩在所有的藝術(shù)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會(huì)給視覺帶來巨大的沖擊力,色彩也是在傳統(tǒng)藝術(shù)臉譜中是主要組成部分及重要的表現(xiàn)符號,臉譜的色彩文化帶有民族性及傳統(tǒng)性,它的創(chuàng)立高于生活,同時(shí)又不失生活之源。戲曲舞臺(tái)上各種顏色的臉譜在生活中是沒有的,但它來源于生活。也就是在把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某種物象的自然形態(tài)取來加以變化,使其圖案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例如:紅臉膛、白臉膛等。臉譜的色彩特點(diǎn)具有鮮明的特點(diǎn),臉譜中的色彩運(yùn)用是多種多樣的,五彩繽紛,容易使人眼花繚亂,每張臉譜至少有三種以上的顏色來表現(xiàn),各種顏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與寓意:一般紅色會(huì)運(yùn)用到勇敢、正直、赤膽忠心的角色。在臉譜中色彩是很強(qiáng)的視覺符號,在搭配上形成了自己的獨(dú)特風(fēng)格。現(xiàn)在藝術(shù)家們的不斷探索研究,追求創(chuàng)新改革,使色彩愈來愈豐富多彩,各種不同人物性格的區(qū)分也越加鮮明,開創(chuàng)造出許許多多歷史和神話人物的臉譜,形成了―套完整的化妝譜式。其實(shí)在臉譜中色彩其實(shí)是根據(jù)人物的性格去選取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看來色彩真實(shí)的意義,也就是說通過不同的色彩可以描繪出不同層次的人物性格,形成獨(dú)立的、鮮明的個(gè)性的角色,色彩是臉譜藝術(shù)中不可缺少的一種精髓文化。
視覺表現(xiàn)元素――圖形
戲劇評論家張庚先生曾說:“臉譜是一種中國戲曲內(nèi)獨(dú)有的,在舞臺(tái)演出中使用的化妝造型藝術(shù)。從戲劇的角度來講它是性格化的;從美術(shù)的角度來看,它是圖案式的。在漫長的歲月里,戲曲臉譜是隨著戲曲的孕育成熟逐漸形成,并以譜式的方法固定下來”。戲曲臉譜是中國戲曲獨(dú)有的、有著獨(dú)特迷人魅力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臉譜中圖案非常豐富,手法夸張、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臉譜的形式都是隨戲的內(nèi)容形成而產(chǎn)生的,臉譜的外觀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為目的,使觀眾能夠看到外表就能明白人物的內(nèi)心、身份、性格、命運(yùn)等,每一張臉譜具有鮮明的思想性。造型大膽而夸張是戲曲臉譜的主要特征,這種大膽的夸張不是隨便涂抹而成,它是有一定規(guī)律性的。臉譜藝術(shù)有其固有的章法,它將繪畫中的“點(diǎn)、線、色、形”有規(guī)律的組織成變形、夸張、裝飾性極強(qiáng)的圖案造型,由此產(chǎn)生了戲曲臉譜的格式與規(guī)則,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臉譜以‘象征性’和“”夸張性”著稱,在戲曲里許多人物的臉與造型與人物特征性格接連在一起,演員面部圖形的勾法被賦予了不同的涵義。總之,臉譜的圖案非常豐富,但總的著色的方式分為:揉、勾、抹、破四種類型,揉臉,他是最古老的一種方式,色調(diào)比較凝重、威武。勾臉:色彩豐富,五彩繽紛,華麗臉上會(huì)用到金銀兩色,抹:淺色為多,一般奸詐的壞人用此方法,破臉:整張臉的圖案不對稱,左右不一樣,形容反面丑陋的角色。象征是一種符號,但不是一般的符號。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黑格爾老人說,象征符號“是一種在外表形狀上就已可暗示要表達(dá)的那種思想內(nèi)容的符號”。
臉譜藝術(shù)是一個(gè)嚴(yán)謹(jǐn)有序的過程,還包括角色與譜式之間的一整套規(guī)則關(guān)系,包括臉譜的勾畫過程等,都顯示出戲曲臉譜的程式化特征。戲曲臉譜的程式化特征,必須是服從并協(xié)調(diào)于戲曲藝術(shù)本身的整體風(fēng)格和美學(xué)特質(zhì)的。圖案化、裝飾化的戲曲臉譜程式要與戲曲本身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構(gòu)成戲曲藝術(shù)嚴(yán)謹(jǐn)和諧、節(jié)奏鮮明、氣韻生動(dòng)的藝術(shù)品格。臉譜的程式與表演等其他程式一樣,具有約定俗成的性質(zhì),它能使常看戲的觀眾明白人物的性格、情緒、心理等,讓觀眾產(chǎn)生豐富的聯(lián)想,增強(qiáng)藝術(shù)感染力。
臉譜有其相對獨(dú)立的欣賞價(jià)值及審美意義,它始終是戲曲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臉譜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和對審美特性的認(rèn)識(shí),只有在觀看戲曲表演之后才能有充分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其實(shí)每張臉譜都不是特定的,色彩、人物性格及一張完整協(xié)調(diào)的臉為一個(gè)完整的人物形象,而這個(gè)形象是通過很多元素表達(dá)包括臉、色彩、衣著、鞋飾等元素,才組成一個(gè)活靈活現(xiàn)的人物。在現(xiàn)代文化與技術(shù)的推動(dòng)下,創(chuàng)作空間有了更新的發(fā)展與突破,藝術(shù)家用新技術(shù)將人物形象重新整理與刻畫,在傳統(tǒng)中求新、求變,使傳統(tǒng)符號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間,也會(huì)在美學(xué)中開辟新領(lǐng)域。
結(jié)語
篇7
【關(guān)鍵詞】戲曲傳統(tǒng)戲 戲曲現(xiàn)代戲 戲曲舞蹈 審美特征
一、古風(fēng)雅韻:傳統(tǒng)戲中舞蹈的審美特征
(一)姿正勢美的輔助表達(dá)
戲曲中的舞蹈很少以純舞蹈形式出現(xiàn),更常見的表現(xiàn)手法是與戲曲表演的“四功”,即唱、念、做、打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統(tǒng)一的有機(jī)整體。戲曲經(jīng)常根據(jù)唱詞或道白來設(shè)計(jì)相應(yīng)的舞蹈動(dòng)作,如京劇武戲中的代表作《挑滑車》中“石榴花”一段載歌載舞,動(dòng)作幅度大、技巧難度高,舞蹈身段的表演具有極高的審美價(jià)值。劇中唱詞念到哪里,動(dòng)作就比擬到哪里,這段具有代表性的戲曲舞蹈,將驍勇善戰(zhàn)的岳家軍頭號猛將高寵在山頂觀戰(zhàn)的情形極其生動(dòng)地營造出來,讓臺(tái)下觀眾拍案叫絕。試想,如果沒有舞蹈身段的配合,戲曲藝術(shù)的精彩度就會(huì)大打折扣。
(二)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表演程式
在傳統(tǒng)戲曲中,人物行當(dāng),角色扮相,唱、念、做、打,音樂伴奏以及上、下場等,都有固定程式,這是塑造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外化人物心靈必不可少的藝術(shù)手段。戲曲的表演程式可分為塑造人物性格的程式、傳達(dá)人物情感的程式、表現(xiàn)舞蹈身段的程式。
戲曲表演中的行當(dāng)以生、旦、凈、丑來劃分,每一個(gè)行當(dāng)代表一種類型化的人物,同時(shí)具有區(qū)別于其他行當(dāng)做與打的獨(dú)特表演程式。其不僅體現(xiàn)出人物的身份、年齡、職業(yè)、性別等顯性特征,更能表現(xiàn)出人物的秉性、氣質(zhì)、品格等隱形特征。
在戲曲舞臺(tái)上,情感程式的表現(xiàn)是通過一定的形式、技巧將人物內(nèi)在的心理狀態(tài)、情感外化為鮮明的視覺形象。戲曲舞蹈有一套豐富而系統(tǒng)的表演程式為人們所熟知,當(dāng)看到演員甩發(fā)的動(dòng)作,就知道人物的情緒異常激動(dòng)或悲憤;當(dāng)看到官生閃帽翅的功夫,就知道劇中人物或欣喜若狂,或苦思冥想……
戲曲的身段程式表演是將生活中的自然形態(tài)按照藝術(shù)美的原則進(jìn)行提煉、規(guī)范,如開門、推窗、登舟、起霸、走邊……都有固定的表演程式。這些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表演程式是劇中人物非常嚴(yán)謹(jǐn)?shù)谋磉_(dá)方式和塑造舞臺(tái)形象的必要手段,也是中華民族審美習(xí)慣的高度概括。但程式絕不是古板、僵化的,優(yōu)秀的藝術(shù)家總能賦予程式一些清新的感染力,創(chuàng)造出個(gè)性化的經(jīng)典藝術(shù)。
(三)虛實(shí)相生的表現(xiàn)手法
中國戲曲是一門“寫意”的藝術(shù),是指戲曲在藝術(shù)處理上的虛擬性。傳統(tǒng)戲曲講究“戲隨人走”“景隨人移”,戲曲演員通過其穿戴的服飾、所唱的詞語、對白和一系列的動(dòng)作,將其所處的環(huán)境、所遇的事情以及特定的心理情緒呈現(xiàn)給觀眾,而觀眾會(huì)在一種既定的審美引導(dǎo)下加以想象、聯(lián)想、感悟虛擬中所標(biāo)示的豐富內(nèi)涵。
(四)借助傳統(tǒng)服飾道具的舞臺(tái)技巧
中國傳統(tǒng)戲曲中的角色人物,有著非常講究的服飾妝扮,一般都冠袍鮮明,披掛整齊。當(dāng)任何一種服飾或道具納入戲曲舞臺(tái)而成為舞臺(tái)道具時(shí),就會(huì)產(chǎn)生精彩的技術(shù),構(gòu)成富有表現(xiàn)力的舞蹈語匯。在《問樵鬧府·打棍出箱》中有一個(gè)絕技是踢鞋上冠,即范仲禹把左腳上穿的夫子履向上一踢,不用手扶,鞋子穩(wěn)穩(wěn)當(dāng)當(dāng)落在高方巾上,讓觀眾有一種出其不意的感覺,為整臺(tái)演出增色添彩。
二、與時(shí)俱進(jìn):現(xiàn)代戲中舞蹈的審美特征
(一)主題鮮明的舞段呈現(xiàn)
在戲曲現(xiàn)代戲中,舞蹈除了作為戲曲唱念時(shí)的輔助姿態(tài)與表現(xiàn)人物性格和曲辭意義的有效手段之外,還經(jīng)常以舞段的形式出現(xiàn)在劇中。其主題鮮明、動(dòng)作形式感強(qiáng)、意味深刻,并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編舞理念的諸多因素。最為重要的是,要將舞與戲融合得巧妙,既關(guān)注舞的形式,又注重戲的內(nèi)容,最終達(dá)到舞中含戲、戲中現(xiàn)舞的和諧景象。
如今的現(xiàn)代戲不能機(jī)械地運(yùn)用舊程式來表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這會(huì)讓觀眾感到審美錯(cuò)位。塑造現(xiàn)代戲人物,必須在表演程式上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騎自行車、拉洋車、趕大車、打電話等新的舞蹈化的動(dòng)作,其中“拉洋車”是現(xiàn)代京劇《駱駝祥子》中祥子出場時(shí)的程式化表演,這一新程式的創(chuàng)造受到了眾多戲曲專家、學(xué)者的一致好評,其精彩不在于演員對拉洋車學(xué)得多像,而在于通過拉洋車充分表現(xiàn)了祥子實(shí)現(xiàn)夢想后的滿足與喜悅。因此,這段程式化的表演能夠成為經(jīng)典。當(dāng)然,新程式的創(chuàng)造不能脫離傳統(tǒng)程式的審美原則,必須以傳統(tǒng)程式為根基發(fā)展為現(xiàn)代的程式表演,并且要符合劇中的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滿足當(dāng)代人的審美需求。
(二)虛擬寫意的表現(xiàn)手法
虛實(shí)相生是中國舞蹈乃至所有中國藝術(shù)的審美追求之一,也是傳統(tǒng)戲曲與現(xiàn)代戲曲所共同遵循的審美原則與表達(dá)方式,如現(xiàn)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戰(zhàn)士們的“滑雪舞”,將京劇表演程式拓展到了一個(gè)從未表現(xiàn)過的生活領(lǐng)域,舞蹈設(shè)計(jì)極具創(chuàng)意。傳統(tǒng)戲曲表演中經(jīng)常會(huì)出現(xiàn)“以鞭帶馬”“以槳帶船”“以布帶車”的虛擬表演,但在“滑雪舞”的編排中,編導(dǎo)拋棄了一切對肢體產(chǎn)生限制和束縛的道具,憑借著演員模擬滑雪時(shí)的手姿、步法、體態(tài)、韻律、狀態(tài)以及以靜顯動(dòng)、以慢見快的身體節(jié)奏處理,在有限的時(shí)空里營造出一幅在一望無垠的雪地上進(jìn)行跳躍和滑降的滑雪景觀,展現(xiàn)出小分隊(duì)?wèi)?zhàn)士們齊心備戰(zhàn)的團(tuán)結(jié)意識(shí)與作戰(zhàn)精神。
(三)運(yùn)用新器物舞出新技巧
戲曲現(xiàn)代戲的舞臺(tái)表演技巧在承襲表演技巧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諸多有意義的嘗試。為了真實(shí)展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生活,現(xiàn)代戲中演員的扮相、服飾與傳統(tǒng)戲中的人物造型有天壤之別。輕便、簡潔是現(xiàn)代戲中人物服飾的主要特點(diǎn),但如果去掉髯口、翎子、水袖之后,拿什么創(chuàng)造戲曲舞蹈的獨(dú)特技巧?這是個(gè)問題。現(xiàn)代京劇《華子良》是戲曲舞臺(tái)上成功的突破點(diǎn),特別是《耍鞋戲敵》《挑簍下山》等膾炙人口的片段,把耍鞋、耍扁擔(dān)表現(xiàn)得很到位,這是現(xiàn)代戲曲舞蹈表演中少有的亮點(diǎn)。演員運(yùn)用自己嫻熟的技巧和扎實(shí)的基本功,撥開戲曲的程式化表演,將傳統(tǒng)武生名劇《拿高登》中的耍石擔(dān)技法運(yùn)用于耍扁擔(dān)中,使作品的現(xiàn)代化躍然眼前,符合現(xiàn)代人的審美觀念。
三、傳統(tǒng)戲曲與現(xiàn)代戲曲中舞蹈的共性與特性
(一)傳統(tǒng)戲與現(xiàn)代戲中舞蹈的共性
在戲曲傳統(tǒng)戲和現(xiàn)代戲中,舞蹈的終極目標(biāo)可歸納為:描景、抒情、寫人、演故事,即突破時(shí)間、空間限制,通過虛擬性的肢體語言描繪出富有意境美的舞臺(tái)藝術(shù)世界;通過豐富而形象的角色塑造滲透出劇中人物乃至編導(dǎo)最直接的情感體驗(yàn);通過符合人物關(guān)系的準(zhǔn)確動(dòng)作語匯塑造典型的人物性格;通過舞蹈的抒情、造型和描繪等各種功能擔(dān)負(fù)起表現(xiàn)劇情、敘述故事、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任務(wù)。
(二)傳統(tǒng)戲與現(xiàn)代戲中舞蹈的特性
由此可見,戲曲傳統(tǒng)戲與現(xiàn)代戲中的舞蹈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藝術(shù)特征和審美傾向,但表現(xiàn)內(nèi)容、表現(xiàn)手段和表達(dá)方式卻不盡相同。戲曲舞蹈的肢體語匯既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體現(xiàn),又是純粹的古典藝術(shù)精神的象征。然而,現(xiàn)代戲的舞蹈繼承和發(fā)展了傳統(tǒng)戲的舞蹈原則,在立足戲曲的古典精神基礎(chǔ)上,讓這條傳統(tǒng)血脈展現(xiàn)更多的生機(jī)與活力,使傳統(tǒng)藝術(shù)也能做到與時(shí)俱進(jìn)。
四、中國戲曲舞蹈的發(fā)展前景
“傳統(tǒng)”絕不是“過去”的代名詞,其以強(qiáng)大的感召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充斥著現(xiàn)在,預(yù)示著未來。在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造、社會(huì)的發(fā)展與變革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并非相互排斥、相互抵觸。每個(gè)民族在通往現(xiàn)代化的歷程中必須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根基,以古典精神作為支撐,如果拋棄“傳統(tǒng)”,一味追求“現(xiàn)代”,戲曲舞蹈將會(huì)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離藝術(shù)的終結(jié)形態(tài)也就不遠(yuǎn)了。在堅(jiān)持以傳統(tǒng)為本位,保留戲曲舞蹈固有的虛擬、寫意的同時(shí),引入現(xiàn)代元素,進(jìn)行新的藝術(shù)探索,充分利用科技進(jìn)步為戲曲舞蹈提供的便利條件,注入時(shí)代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元素,調(diào)動(dòng)現(xiàn)代舞臺(tái)科技手段更好地為表演服務(wù),將古典美與現(xiàn)代美水融地結(jié)合起來,并借鑒當(dāng)代編舞理念實(shí)現(xiàn)戲曲舞蹈從單一到整體、局部到全面、守承到創(chuàng)新的突破,在遵循戲曲舞蹈“演故事”功能的同時(shí),堅(jiān)持實(shí)現(xiàn)戲曲舞蹈的與時(shí)俱進(jìn),使之適應(yīng)現(xiàn)代觀眾的審美需求,獲得審美的重塑,這才是戲曲舞蹈在當(dāng)展的最佳途徑。
參考文獻(xiàn):
篇8
關(guān)鍵詞:戲曲動(dòng)畫;意境;虛擬
戲曲動(dòng)畫是用動(dòng)畫的形式來演繹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一種新的動(dòng)畫樣式。從其誕生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歷了十余年的發(fā)展,有越來越多的專業(yè)制作公司和動(dòng)畫愛好者把興趣投入到戲曲動(dòng)畫的創(chuàng)作中,戲曲動(dòng)畫的風(fēng)格特征也日趨多樣化。早期的戲曲動(dòng)畫基本都是在內(nèi)容上提煉原有劇情,形象設(shè)計(jì)上盡量保留戲曲的臉譜、妝扮等裝飾符號,動(dòng)作上借鑒戲曲表演中對手、眼、身、法、步的處理特點(diǎn)并加以適度夸張。后來的戲曲動(dòng)畫則逐漸擺脫對舞臺(tái)演出情形的模仿,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對劇作意境的重新詮釋,其審美趣味也由低齡化向大眾化轉(zhuǎn)變。戲曲動(dòng)畫由此得到了更多年齡層面的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喜愛。
目前在我國的高等院校中就有與戲曲藝術(shù)相關(guān)的戲劇類課程設(shè)置,如果能將戲曲動(dòng)畫引入戲劇的課堂教學(xué),可以促成戲曲動(dòng)畫在更大范圍內(nèi)的傳播,也可以增加教學(xué)趣味。然而戲曲動(dòng)畫的采用應(yīng)當(dāng)意在鞏固學(xué)生對戲曲審美特點(diǎn)的認(rèn)識(shí),而不是取代戲曲欣賞。本文以施屹、陳海璐導(dǎo)演,上海師范大學(xué)謝晉影視藝術(shù)學(xué)院制作的動(dòng)畫短片《三岔口》為例,嘗試分析將戲曲動(dòng)畫融入到戲劇教學(xué)中的可行性和局限性。
一、可行性:動(dòng)畫與戲曲的內(nèi)在融通
《三岔口》采用了水墨動(dòng)畫的形式。“水墨動(dòng)畫的出現(xiàn)是中國動(dòng)畫界為世界動(dòng)畫作出的一大貢獻(xiàn),它突破了動(dòng)畫電影史上只有‘單線平涂’一種形式的局面,既沒有邊緣線,還要發(fā)揮濃淡渲染的效果,是動(dòng)畫藝術(shù)上非凡的創(chuàng)舉。[1](52)”水墨動(dòng)畫曾是中國動(dòng)畫“民族化”風(fēng)格的標(biāo)志性樣式,在今天隨著電腦技術(shù)的發(fā)展,這種動(dòng)畫形式的表現(xiàn)力也在不斷提高。短片《三岔口》不是對京劇折子戲演出實(shí)景的再現(xiàn),而是用高度抽象的水墨人物造型,經(jīng)過形象的演繹變化,闡釋了一個(gè)新的主題――事物的兩面性。短片的背景設(shè)計(jì)猶如宣紙,在這個(gè)背景之上,由一團(tuán)墨跡中生成一黑一白兩個(gè)小人的形象。以此為引子,造型主要以線條勾勒的任堂惠和更多以墨色渲染的劉利華的形象先后出現(xiàn)。短片通過人物形象的夸張和變形,將戲曲中精彩的打斗場面用奇特的視覺效果呈現(xiàn)出來:有時(shí)是兩個(gè)人在摸索中慢慢靠近,人物形象逐漸重疊,直至融合為一個(gè),這個(gè)疊加后的形象卻又可以一分為二,一半是劉利華,一半是任堂惠;有時(shí)是任堂惠手持燭臺(tái)尋找劉利華的蹤跡,他投在地上的影子卻越拉越長,影子變?yōu)榱藙⒗A。短片突破了戲曲的時(shí)空限制,自由地進(jìn)行場景的呈現(xiàn)。最后,相互爭斗的兩個(gè)人影模糊為紛亂的線條,線條交錯(cuò)糾纏又變?yōu)槭孜蚕嘀鹑缣珮O圖案的兩團(tuán)陰影,最后成了一個(gè)淡淡的圓,并漸漸消失。可以說在這部短片中,任堂惠與劉利華并不僅僅是以戲曲中的人物形象出現(xiàn)的,他們一黑一白,一虛一實(shí),相互對立又可以互相轉(zhuǎn)化,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虛實(shí)相生的思維方式。
《三岔口》這類水墨戲曲動(dòng)畫,更加看重傳“神”達(dá)“意”,而不拘泥于對劇情的再現(xiàn)和對表演的模仿。《三岔口》的內(nèi)在意蘊(yùn)甚至超越了原作的主題。水墨動(dòng)畫的美學(xué)理念繼承自中國傳統(tǒng)的水墨畫,注重筆墨意趣,通過點(diǎn)染勾勒、造型賦色,營造出獨(dú)特的情感意境。《三岔口》以人物造型的流動(dòng)變換代替了原作中的武打場景,通過畫面中線條的靈活交織與墨跡的浸潤滲透,使水墨元素真正地靈動(dòng)起來,創(chuàng)造出動(dòng)畫的意境美。戲曲表演本身就非常重視意境的營造,而在《三岔口》這樣的戲曲動(dòng)畫作品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含蓄蘊(yùn)藉的內(nèi)在氣質(zhì)得以充分顯現(xiàn),通過外在的動(dòng)畫形象表達(dá)微妙的心理情感,情生境中,意在言外,實(shí)現(xiàn)了水墨動(dòng)畫這種形式與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內(nèi)在融通。
像這樣具有一定審美價(jià)值的戲曲動(dòng)畫作品,符合當(dāng)今青少年對我國民族動(dòng)畫發(fā)展的心理期待。他們雖然能夠廣泛地接觸世界流行文化,但他們的審美心理與價(jià)值取向依然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如果將這類動(dòng)畫與戲曲的教學(xué)結(jié)合起來,可以幫助戲曲在現(xiàn)代化可視化的途徑中擴(kuò)大傳播范圍,幫助學(xué)生理解戲曲的內(nèi)在之美,為戲曲培養(yǎng)新生代的觀眾,更是為戲曲動(dòng)畫的創(chuàng)作貯備人才。
二、局限性:戲曲與動(dòng)畫的傳播差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用動(dòng)畫這種形式來表現(xiàn)戲曲依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戲劇教學(xué)中,是不能用來取代對戲曲的實(shí)際觀賞的。戲曲與動(dòng)畫雖然都是具有高度假定性的藝術(shù)形式,但其激發(fā)觀眾審美想象的方式不一樣。究其原因,就是舞臺(tái)藝術(shù)與動(dòng)畫藝術(shù)的傳播方式不同,與觀眾的交流方式不同,營造的審美想象空間也就不同。
戲曲的虛擬性特點(diǎn)是建立在舞臺(tái)傳播方式的基礎(chǔ)上的。在實(shí)際教學(xué)中,《三岔口》原本很適宜用來說明戲曲的這一特征。戲中的任堂惠與劉利華因?yàn)檎`會(huì)而交手,但是因?yàn)槲葜泻诎担荒芘袛鄬κ值奈恢茫谑谴蚨返倪^程時(shí)刻伴隨著摸索與試探。在這一段表演中,演員在虛化模擬中帶有適度夸張的動(dòng)作,為觀眾營造了生動(dòng)、緊張又有趣的戲劇氛圍。通過演員的精湛表演與密切配合,使得觀眾自發(fā)地在想象中構(gòu)建出伸手不見五指、一片漆黑的情景,將舞臺(tái)上正在表演的兩個(gè)人代入到那樣的情境中,這正是傳統(tǒng)戲曲虛擬表演的成功之處。在表演的過程中,觀眾的思維幻覺被調(diào)動(dòng)起來,通過舞臺(tái)這個(gè)媒介,演員與觀眾之間產(chǎn)生了直接的交流,他們的想象參與了這個(gè)創(chuàng)造的過程,由此獲得了審美的愉悅。
戲曲動(dòng)畫也在調(diào)動(dòng)觀眾的想象力。在動(dòng)畫中,形象、色彩和聲音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組合出不同風(fēng)格的視覺效果,觀眾在觀看時(shí)沉浸在非常直觀的感官感受之中,但這種交流方式是間接的。無論觀眾在觀看動(dòng)畫之時(shí)展開了怎樣的聯(lián)想,都建立在動(dòng)畫作者提供的畫面和聲音的基礎(chǔ)之上。也就是說,觀眾不能直接參與到戲劇情境的構(gòu)建過程中去。例如京劇《三岔口》的舞臺(tái)道具本來十分簡單,臺(tái)上的一張桌子,任堂惠躺在上面時(shí),它代表的是休息的床榻;劉利華把燈放在上面,它就又成了桌子。道具的意義是通過演員的表演賦予的。但如果動(dòng)畫中在這個(gè)場景里畫出了桌子,觀眾就不會(huì)把它當(dāng)成是別的東西。因此,原本舞臺(tái)表演中虛擬性的動(dòng)作和場景,被動(dòng)畫再現(xiàn)出來,就失去了與觀眾交流互動(dòng)的能力。從戲曲到戲曲動(dòng)畫,有一個(gè)從舞臺(tái)語言向影視語言的轉(zhuǎn)化過程,由于傳播介質(zhì)的不同,在這個(gè)轉(zhuǎn)化過程中,戲曲中的某些元素就會(huì)被舍棄,而這些元素恰恰是戲曲作為舞臺(tái)藝術(shù)的最本質(zhì)的特征。
另外,動(dòng)畫中人物的動(dòng)作造型是可以極盡夸張與變形之能事的,而動(dòng)畫藝術(shù)這種無限可能性的存在,使得現(xiàn)實(shí)中的戲曲演員多年苦練成就的各種絕技失去了意義。因此,在戲曲動(dòng)畫中,一代代戲曲藝人積累下來的表情、身段、舞蹈、武打等各方面的表演技巧就得不到充分展示。目前的戲曲動(dòng)畫大多是短片,對戲曲的唱詞和唱腔之美的展現(xiàn)就極為有限。例如《牡丹亭》一劇就有多個(gè)版本的動(dòng)畫短片作品[2],但昆曲唱腔的細(xì)膩婉轉(zhuǎn)、悠遠(yuǎn)流麗,所謂“功深熔琢,氣無煙火”[3](198)的特點(diǎn),以及湯顯祖這部“詩劇”的曲詞之典雅綺麗,都很難通過動(dòng)畫去了解和體會(huì)。
因此,在實(shí)際教學(xué)中,動(dòng)畫短片雖然短小精悍,富有情趣,但不能代替對戲曲舞臺(tái)演出的直接體驗(yàn),否則無從達(dá)到揭示戲曲特性的教學(xué)目的。近十年來戲曲動(dòng)畫的快速發(fā)展,說明動(dòng)畫可以成為戲曲文化的傳播方式,而戲曲中蘊(yùn)涵的民族藝術(shù)元素也應(yīng)當(dāng)成為動(dòng)畫豐富的創(chuàng)作題材來源。而怎樣將戲曲與動(dòng)畫進(jìn)行合理結(jié)合,使二者相得益彰,則需要兩個(gè)藝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進(jìn)一步的密切合作與不斷探索。
參考文獻(xiàn)
[1] 呂學(xué)武:《動(dòng)畫的“中國學(xué)派”研究:中國動(dòng)畫藝術(shù)對民族藝術(shù)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
篇9
關(guān)鍵詞:電視文藝;審美特征;豐富性;親和性;大眾性;科技性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6-0156-01
電視文藝是一種新興的文藝形式,從美學(xué)的高度與視角來研究電視文藝的審美特征,既具有重要的理性思辨價(jià)值,又具有重要的實(shí)踐參照作用。本文就此進(jìn)行探索性研究,以作引玉之磚。
具體而言,電視文藝的審美特征,可以分解為以下四大理論層面進(jìn)行分析與研究。
一、豐富性
電視文藝的第一大審美特征,是它的豐富性。
這種豐富性,既表現(xiàn)在思想內(nèi)容(題材、主題、形象、事件、情感等)方面,也表現(xiàn)在藝術(shù)形式(體裁、結(jié)構(gòu)、語言、手法、風(fēng)格等)方面。從電視文藝這一概念內(nèi)涵上而言,它“主要是指電視屏幕上播出的各式各類文藝節(jié)目,其中包括:電視劇、電視綜藝節(jié)目、電視藝術(shù)片、電視專題文藝節(jié)目,以及音樂電視(MTV)、電視文藝談話類節(jié)目、電視娛樂節(jié)目(如游戲類、益智類、乃至新近出現(xiàn)的真人秀節(jié)目)等等。同時(shí),電視文藝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直播或播映的電視文學(xué)、電視音樂、電視舞蹈、電視曲藝雜技、電視戲曲、電視戲劇、電視電影,乃至于諸多藝術(shù)電視節(jié)目如藝術(shù)體操、冰上舞蹈、時(shí)裝表演等等。
而且,每一類電視文藝節(jié)目又可以再細(xì)分為多種類別。例如電視劇,就分為單本劇、連續(xù)劇、系列劇等。
由此可見,電視文藝的豐富性,是有目共睹的事實(shí)。
二、親和性
電視文藝的第二大審美特征,是它的親和性。
電視文藝的親和性,表現(xiàn)在它使愛眾親近,感到親切、直接。電視文藝是真正實(shí)現(xiàn)與廣大受眾親情互動(dòng)、面對面交流與對接的新的文藝形式。在觀賞電視文藝節(jié)目時(shí),受眾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想象性、參與性被極大地調(diào)動(dòng)起來,對節(jié)目的內(nèi)容產(chǎn)生移情與共鳴。
許多電視文藝節(jié)目,都為廣大受眾打造出表現(xiàn)自己、展示自己的平臺(tái),成為真正的“百姓舞臺(tái)”。例如央視的“星光大道”欄目,上海電視臺(tái)的“中國達(dá)人秀”欄目等,都成為廣受歡迎與關(guān)注的電視文藝欄目,其中推出的草根明星,不勝枚舉。僅以“星光大道”為例,就有李玉剛、阿寶、玖月奇跡、鳳凰傳奇、劉大成等等。這也是有口皆碑的事實(shí)。
三、大眾性
電視文藝的第三大審美特征,是它的大眾性。
電視文藝作為大眾傳媒之一,大眾性是其根本屬性。它的快速性、便捷性、交互性、兼容性等優(yōu)長,都成為它大眾性的憑借與依托。
據(jù)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資料顯示,電視文藝的受眾數(shù),高居各類文藝節(jié)目受眾量的榜首。迄今為止,電視文藝已經(jīng)遍及我國城鄉(xiāng)各地,成為廣大群眾最喜愛的一門藝術(shù)。全國已擁有各類電視臺(tái)3000余個(gè),每個(gè)電視臺(tái)都有數(shù)十個(gè)頻道,其中不乏文藝頻道。電視文藝已成為人民群眾休閑娛樂的首選節(jié)目。尤其是電視臺(tái),更是人人喜愛的電視文藝節(jié)目。從1995年全看看播放的7000部集,到2000年全年播放12000部集,再到2011年全年播放5000余部集,再遞增之速,令人矚目。
可以說,電視文藝節(jié)目已經(jīng)走進(jìn)千家萬戶,緊連你、我、他,成為大眾心中的最愛。
四、科技性
電視文藝的第四大審美特征,是它的科技性。
電視作為現(xiàn)代科技的產(chǎn)物,電視文藝作為科技與藝術(shù)的有機(jī)結(jié)合,充分彰顯出它科技性的優(yōu)勢。很顯然,電視文藝已成為現(xiàn)代傳媒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
從人類傳媒的歷史視角都是,人類傳播媒介的發(fā)展變化速度在不斷加快:“從語言到文字,幾萬年;從文字到印刷,幾千年;從印刷到電視和廣播,400年;從第一次實(shí)驗(yàn)電視到從月球播回實(shí)況電視,50年。”尤其是電視與互聯(lián)網(wǎng)結(jié)合,更為電視文藝插上了現(xiàn)代化高科技的翅膀,在藝術(shù)的天空中飛得更高、更遠(yuǎn)、更久。
參考文獻(xiàn):
篇10
【關(guān)鍵詞】民族聲樂;審美特征;審美取向
中國是一個(gè)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中國人民在勞動(dòng)和生活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成為一朵奇葩,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輝。人們在生產(chǎn)勞動(dòng)之后,創(chuàng)造了一種音樂形式,這種音樂形式是源自民族自身的特色,具有深刻的民族特點(diǎn),經(jīng)過不斷地進(jìn)化和積累,漸漸形成了獨(dú)具民族風(fēng)味的中國聲樂藝術(shù)。這是中國勞動(dòng)人民的結(jié)晶,是長期勞動(dòng)實(shí)踐創(chuàng)造出來的民族藝術(shù)。這種藝術(shù)以其獨(dú)特的審美特點(diǎn),在我國燦爛的文化長河中,散發(fā)著獨(dú)特的絲絲幽香。下面談?wù)剬χ袊晿匪囆g(shù)審美取向的思考。
一、我國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概念
我國的聲樂藝術(shù),由于民族文化自身的特征,具有十分廣泛的內(nèi)涵,民族聲樂包括傳統(tǒng)的戲曲演唱、曲藝說唱、民歌演唱等幾方面。在藝術(shù)形式上,涵蓋民族唱法、新歌劇唱法、西洋歌劇民族化唱法等形式。狹義上的聲樂藝術(sh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民族唱法,這種藝術(shù)形式是在民族風(fēng)格較強(qiáng)的作品中體現(xiàn)出來的。民族唱法是對我國民間民歌的進(jìn)一步升華,民族唱法是對民歌唱法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在原生態(tài)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規(guī)范和科學(xué)化地進(jìn)行民歌演唱,使其更加具有民族性,更具時(shí)代性。民族唱法的聲樂藝術(shù),是在廣泛借鑒西洋唱法的同時(shí),與民族的聲樂藝術(shù)有機(jī)融合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演唱民族唱法的歌曲,歌唱者要真假聲合起來演唱,需要歌唱者具有很高的呼吸本領(lǐng)支持,在音色上強(qiáng)調(diào)流暢,要求演唱者字正腔圓,并能夠在演唱中運(yùn)用共鳴,充分融入演唱者的感情,達(dá)到以情感人的目的。所以說,中國民族聲樂藝術(shù),是一門植根于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國大地的中國藝術(shù),是一種以聲情并茂的演唱形式為載體的民族音樂形式。
二、中國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審美取向
中國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審美從本質(zhì)上講是音樂審美,這個(gè)審美是一種與人的聲音相關(guān)的審美。聲樂的審美是一種以聲音為表現(xiàn)形式的歌曲,當(dāng)然聲樂是離不開器樂的。歌曲演唱中所涉及的旋律、和聲、織體、配器等方面同樣是藝術(shù)表現(xiàn)不可缺少的形式,所以說,民族聲樂作品和其他聲樂作品一樣,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shù)形式,判斷一首歌曲的藝術(shù)價(jià)值,不僅僅是歌唱,還有其他各方面涉及到的相關(guān)因素。一首民族聲樂作品不僅僅是歌唱者的聲音,曲調(diào)、歌詞、器樂等都和聲音共同構(gòu)成聲樂藝術(shù)的全部。離開任何一方面的因素,都是會(huì)割裂聲樂的整體美。而且還會(huì)喪失聲樂作品所具有的獨(dú)立存在的藝術(shù)屬性。由于受到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影響,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審美風(fēng)格。但是也有一些音樂工作者和演唱者試圖將國外的一些觀念和技巧應(yīng)用在民族聲樂中,但是由于文化的差異,審美的差異,導(dǎo)致融合出現(xiàn)矛盾。所以對西洋聲樂只能是借他山之石,否則難以收到預(yù)期效果。聲樂的審美是從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判別的,這也是人們對聲樂美的理解。
(一)關(guān)于聲音的審美
聲音如果是一種科學(xué)的藝術(shù)發(fā)聲,那么一定是一門藝術(shù)。聲樂首先是以聲音為主的藝術(shù),通過聲音的美感而形成藝術(shù)的內(nèi)涵。歌唱家把自己對作品的理解融合到自己的演唱中,把歌曲所要表達(dá)的思想、情感都用歌聲來體現(xiàn),這種聲音就具有了藝術(shù)的美感。歌唱者如果把情感融入得更好,那么歌唱作品就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其藝術(shù)價(jià)值就更高。反之,藝術(shù)價(jià)值就不夠鮮明。
(二)民族聲樂中情感的審美
聲樂藝術(shù)是一種欣賞的藝術(shù),是一種讓人用心靈去體會(huì)的藝術(shù)形式。因此在聲樂作品中,重要的審美因素,應(yīng)該是情感審美,美感和情感是相互半生的,成正相關(guān)。沒有情感的作品就沒有藝術(shù)美可言。情感和美感是相互促進(jìn)和相互影響的,聲樂藝術(shù)的最佳審美境界應(yīng)該是聲情并茂。如果歌唱者不能把歌曲中所蘊(yùn)含的情感表達(dá)出來,或者不能把自己對作品理解的情感表達(dá)出來,那么就沒有藝術(shù)的美感體現(xiàn)。所以想感動(dòng)別人必須先感動(dòng)自己,歌唱者首先要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融入到歌曲中,通過自己的表現(xiàn),傳達(dá)出一種情感來,使別人也因?yàn)槁牭礁杪暥簧钌罡袆?dòng)。歌唱者本身要把自己的感受以美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使歌唱具有強(qiáng)烈的美的形式,生發(fā)出無窮的感染力。歌唱者把自己的愛、憎用歌聲和表演體現(xiàn)出來,使人們在觀賞的過程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三)歌唱形象的審美
我們都知道,歌唱藝術(shù)具有自身的特點(diǎn),是通過人物的形象來表現(xiàn)的,是一種以人物形象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的歌唱藝術(shù)。歌唱藝術(shù)具有理智性,而且還富于情感。人物通過歌唱把作品中賦予的情感色彩以一種美好的形象表現(xiàn)出來。歌唱藝術(shù)如果把情和理能夠緊密結(jié)合起來,那才是美的形象。演唱者是聲樂表演的主要環(huán)節(jié),不管歌唱的內(nèi)容是什么,主題都是體現(xiàn)人物的思想感情,歌唱家在演唱中是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全力塑造藝術(shù)形象,但是這種形象的塑造不用語言、不用文字,而是用歌聲和形象,用藝術(shù)家的肢體語言,把歌曲中所蘊(yùn)含的情感因素表現(xiàn)出來,用聲音和形象塑造藝術(shù)形象。所以聲樂的審美,要從形象上去判別。
中國傳統(tǒng)審美中,講究的是平和、人和,天人合一。應(yīng)用在音樂中,特別是民族聲樂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民族文化,長久的積淀,凸顯著強(qiáng)烈的中華民族的特點(diǎn)。中國人對藝術(shù)的審美深深地影響著聲樂藝術(shù)的審美,歌唱中的回歸,聲音的修飾和塑造,傳情達(dá)意。音樂在人的心靈中所產(chǎn)生的震撼,就是一種審美的體現(xiàn)。
三、民族聲樂的審美特征
中國民族聲樂是一種根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上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從內(nèi)涵到外延,都繼承了我國傳統(tǒng)音樂的審美精髓,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記和積淀。民族聲樂的審美特征具有很多的因素,人們在評價(jià)和欣賞一首聲樂作品的時(shí)候,首先從依字行腔方面、字正腔圓方面進(jìn)行審美,把這兩個(gè)因素作為審定演唱的標(biāo)準(zhǔn)。一首優(yōu)秀的音樂講究的是一唱三嘆,追求的是一種情韻美,要求珠圓玉潤的感覺,將曲中情婉轉(zhuǎn)吟出,深厚綿遠(yuǎn),讓聽眾在這其中享受那種心靈的震撼和情感的提升。唱的感人首先要把美好的歌詞唱清楚,歌唱者要吐字清晰,將歌詞內(nèi)容連接唱出來,唱出潤腔,這是中國民族聲樂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民族聲樂具有自身獨(dú)特的個(gè)性,那種五聲調(diào)式,使聲樂演唱非常富有歌唱性,民族風(fēng)味濃郁,而且民族特色的音樂旋律具有單純、簡潔、明快的特點(diǎn),尤其適合中國觀眾的審美口味。我國民族聲樂的藝術(shù)形式,具有橫向織體特點(diǎn),使得演唱起來抑揚(yáng)頓挫,極富樂感和美感。通過聲腔的流動(dòng)和氣口的運(yùn)用等方法,表現(xiàn)歌曲中的思想感情。中國人是一個(gè)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優(yōu)秀民族,具有豐富的文化,表情達(dá)意講究的是委婉含蓄,曲折迂回,民族聲樂也正是迎合了觀眾的這一心理特點(diǎn)。奠定了中國民族聲樂的風(fēng)格特色,并且民族聲樂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景象,為我國的藝術(shù)寶庫增添了一朵奇葩。
民族聲樂的形式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流派和風(fēng)格,陜北民歌、山東梆子、江南小調(diào)等藝術(shù)形式,而且這些民族藝術(shù)的元素都在各種聲樂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都成為民族聲樂審美的重要內(nèi)容。另外,我國民族聲樂的審美,符合國人的審美取向,符合民眾的欣賞口味。我國的民族聲樂注重對歌曲情感的表達(dá),注重樂曲韻味的表達(dá),注重樂曲對情感的表達(dá),重視觀眾的感官,這是與西方文化區(qū)別的主要一個(gè)因素。情感的表現(xiàn)是樂曲演唱中最為重要的一面,表達(dá)情意是民族聲樂的主要特征。這與西方文化重視理智和知識(shí)的特點(diǎn)截然相反。
中國聲樂藝術(shù)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歷時(shí)過程,在這個(gè)發(fā)展過程中,民族聲樂融合了很多種現(xiàn)代元素,而且在不斷的兼并和融合中,形成了民族聲樂自己特有的風(fēng)格和審美特征。在演變中,民族聲樂藝術(shù)采用了多種發(fā)聲技巧和氣息方法,使歌唱者對音樂的領(lǐng)悟和表達(dá)實(shí)現(xiàn)一個(gè)最佳的融合。自然、圓潤、明亮,是民族聲樂的最大特征,歌唱者要真實(shí)且創(chuàng)造性地用聲音和形象去表達(dá)自己對歌曲的理解,形成一種藝術(shù)美,讓聽眾在歌唱中享受那種或空曠、或遼遠(yuǎn)、或悠揚(yáng)的聲音藝術(shù)。人物的聲音、樂曲的聲音、歌詞的意境、演員的形象、配器的協(xié)調(diào),都是民族聲樂審美的體現(xiàn),帶給觀眾美好的感受和無限的遐想。
四、中國聲樂審美的價(jià)值取向
聲樂,顧名思義是聲音的藝術(shù),因此在民族聲樂審美價(jià)值取向中,聲音的審美是一個(gè)重要因素,也是歌唱過程中,藝術(shù)家的重要追求目標(biāo)。民族聲樂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本民族的藝術(shù),所以民族聲樂具有特殊的和突出的民族性,也是民族聲樂的主要特征。歌唱者將自身的聲樂條件和民族語言的音韻特色進(jìn)行了融合,通過音樂和聲音塑造鮮活感人的藝術(shù)形象。所以民族聲樂的審美,應(yīng)該是歌者的嗓音條件優(yōu)越、歌唱技巧科學(xué)、呼吸和發(fā)聲方法得當(dāng)、具有混合共鳴的良好條件、清晰準(zhǔn)確的吐字等因素,同時(shí)還需要具備一定的音樂素養(yǎng)。
(一)聲音審美的解析
中國民族聲樂是我國民族藝術(shù)的結(jié)晶,聲樂藝術(shù)蘊(yùn)含了我國的歷史文化、審美情趣,并且成為民族聲樂藝術(shù)發(fā)展的沃土,民族聲樂的表現(xiàn)形式是演唱,以聲音的形式進(jìn)行音樂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在民族聲樂藝術(shù)中,融合著民族情感、民族語言、民族文化、民族審美等因素,通過歌唱傳承和弘揚(yáng)了民族藝術(shù),而且這種藝術(shù)形式,也是增進(jìn)人們聯(lián)系和情感融合的中介和載體。聲樂中的聲,包括聲音、語言、行腔,而且還要歌者的形象和情感,所謂聲情并茂是也。民族聲樂和西洋聲樂發(fā)生方法不一樣,民族聲樂發(fā)生舌位靠前,元音共振中心是口腔的前硬腭部,口腔上壁是硬腭,前方是牙齒,牙齒反射聲波較強(qiáng),共振重點(diǎn)靠近口外,因此民族聲樂的歌唱,聲音明亮和開朗,清脆集中。在民族聲樂的審美中,人們習(xí)慣用那些大氣磅礴的語言形容聲樂的魅力:余音繞梁、繞梁三日、黃鐘大呂、宛轉(zhuǎn)悠揚(yáng)、響徹云霄等等,可見,聲樂的審美,重點(diǎn)是聲音,真正被歌者所推崇的是甜、脆、園、亮、水的歌唱境界,對歌者的演唱藝術(shù)、發(fā)聲技巧、音樂素養(yǎng)都有很高的要求,對于音色的定位,是在我國多民族、多文化基礎(chǔ)上積淀起來的,所以民族特色鮮明,民族聲樂的藝術(shù)價(jià)值極高,已經(jīng)超越了民族聲樂藝術(shù)本身所具有的范疇。
(二)唱歌的氣息審美
氣息是歌唱的動(dòng)力和支持力,聲樂藝術(shù)要的是較高的呼吸控制能力,沒有呼吸控制的聲音就沒有藝術(shù)可言,歌者會(huì)出現(xiàn)音色緊張、肌肉用力的非正常現(xiàn)象。提高聲樂的藝術(shù)感染力和歌唱的聲樂藝術(shù)氛圍,需要歌唱控制好呼吸,運(yùn)用正確的呼吸方法,就能夠較好地表達(dá)音樂作品的情感。聲樂演唱中的呼吸方式,一般確定為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胸腹呼吸三種氣息控制方式。
采用胸式呼吸方法進(jìn)行演唱,具有不利于共鳴腔體打開的弊端,這種呼吸方式不利于歌詞完整意義的表達(dá),因此在演唱中表現(xiàn)的缺乏音樂的韻味和美感;所謂腹式呼吸,這種呼吸方式有利于假聲頭聲的高位置,氣息在腰部以下活動(dòng),比較典型的是戲曲中的女角唱腔,普遍采用這種方法;熊腹式呼吸,氣息活動(dòng)范圍在下胸部和上腹部,運(yùn)用氣息歌唱時(shí),借助人體橫膈膜擴(kuò)張的力量,這種呼吸方式,是廣為認(rèn)可的廣泛應(yīng)用的。
(三)曲調(diào)的音韻美
音韻美是聽覺的感知,在民族聲樂中,韻律、押韻形成了人們聽覺美感。我們的語言具有四個(gè)聲調(diào),而且所有韻母都可以延長,這一特點(diǎn),為民族聲樂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使得歌詞內(nèi)容特別適合演唱。音樂的節(jié)律和節(jié)奏也是民族聲樂的一項(xiàng)審美內(nèi)容,節(jié)奏,是歌詞詩歌化的標(biāo)志,句式要求整齊、鮮明、統(tǒng)一,這就構(gòu)成了音樂的節(jié)奏感,韻律安排后的歌詞就和普通的念白不一樣了,具有了音韻美,讓觀眾聽起來,抑揚(yáng)頓挫,極富美感。
(三)情感審美
情感是民族聲樂或說其他聲樂的審美核心,情是歌唱藝術(shù)的靈魂。歌唱是一種情感的表達(dá),情感可以感染人。用聲音的藝術(shù),荷載情感的因素,教育和鼓舞聽眾,是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價(jià)值所在。歌唱藝術(shù)的目的是交流,歌者和聽眾的交流,人與人之間抒感、激感、交流情感,用情感將藝術(shù)體現(xiàn)出來,用情感將人與人之間連接起來。因此,民族聲樂的審美,應(yīng)該以情感作為重要的取向。
在人們的消費(fèi)意識(shí)中,聲樂藝術(shù)不是靜止的,是隨著人們追求美的變化而變化的。人們的消費(fèi)意識(shí) 就是審美化和風(fēng)格化的特征,比如對于民族聲樂的審美取向。審美的標(biāo)準(zhǔn)是藝術(shù)牽引的,反過來,人們對聲樂的審美也影響著聲樂藝術(shù)的發(fā)展。發(fā)揚(yáng)我國民族聲樂對文化的傳承和弘揚(yáng)作用,是研究聲樂審美的重要目標(biāo)。只有不斷地追求和完善,與時(shí)俱進(jìn),才能適應(yīng)消費(fèi)者對藝術(shù)的審美需求。
參考文獻(xiàn):
[1]李亞男.淺析民族聲樂藝術(shù)的覺醒[J].成才之路,2007(20).
熱門標(biāo)簽
戲曲文化論文 戲曲音樂 戲曲 戲曲藝術(shù)教育 戲曲藝術(shù) 戲曲劇種 戲曲腳色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