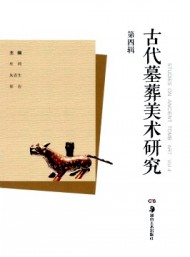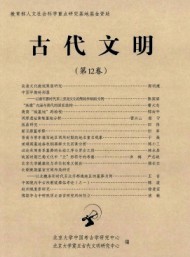古代文化常識大全范文
時(shí)間:2023-08-29 17:17:46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代文化常識大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guān)鍵詞:伏羲氏;古代;傳說;八卦;文化;價(jià)值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0-0145-02
在人類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傳說貢獻(xiàn)最大的是被后代尊稱為“三皇”的伏羲氏、神農(nóng)氏和女媧氏。而伏羲傳說的故事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奇妙的情節(jié)和神奇的色彩,著重刻畫了伏羲文化其固有的創(chuàng)造性和實(shí)踐性,展現(xiàn)出其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和認(rèn)識世界的科學(xué)精神,從而使人們從中受到陶冶和教益。傳說伏羲氏教人結(jié)網(wǎng)、捕魚打獵,還教人把漁獵得來的魚蝦肉放在陶器里煮著吃,把活著的野獸畜養(yǎng)起來。最為值得一提的是,伏羲氏還創(chuàng)制了伏羲八卦。我們聽說過許多的神話傳說,但細(xì)想一下也不是大批量的,而且這些難得的神話傳說是經(jīng)過多少年才錘煉而成并廣為流傳的。一些古代的神話傳說之所以可以流傳至今,是因?yàn)槠涔适聝?nèi)容本身吸收了時(shí)代的限制性和物質(zhì)的局限性。中國歷史上的經(jīng)典神話傳說之一———《伏羲氏的傳說》便是如此。
一、關(guān)于伏羲傳說
有關(guān)伏羲傳說的故事有很多。相傳開天辟地之后,天下依舊十分荒涼。人們都愚昧無知。玉皇大帝便命圣母帶著仙犬下凡,管理人間。居于華胥那個(gè)地方(今指陜西藍(lán)田)。有一年,雷公神發(fā)怒,凡間河水泛濫,使人們遭遇了巨大的災(zāi)難。圣母于是化身變成一位美麗的姑娘,當(dāng)時(shí)稱華胥姑娘,前往雷澤國(今指甘肅境內(nèi))說服雷公,勸他不要隨意發(fā)怒,禍害人間。一路上,圣母歷盡了千辛萬苦,當(dāng)她來到雷澤國附近時(shí),突然發(fā)現(xiàn)地面上有一巨人的腳印,由此心動。誰知這一凡心被天上的彩虹感動,便飛下來纏繞住了圣母。恰巧的是,雷公正好在此,于是便領(lǐng)著圣母進(jìn)了華池,圣母因?yàn)榕c彩虹相交懷孕,并在成紀(jì)生下了伏羲,而其實(shí)為大風(fēng)國雷神之子。后人為了紀(jì)念華胥姑娘踩了巨人腳印而生下伏羲,至今豫東猶遺,俗稱“擔(dān)經(jīng)挑”,即“巫舞”的習(xí)俗。伏羲自稱“風(fēng)”姓,“風(fēng)”便成了華夏民族的第一個(gè)姓字。后來雷公聽從了華胥姑娘的勸說,自此改邪歸正,不再隨意發(fā)怒,危害人間。從此,天下便安樂太平、五谷豐登。
幾千年來,人們在創(chuàng)造了物質(zhì)財(cái)富的同時(shí),也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藝術(shù)。在文藝的百花園中,民間神話傳說以其源于生活、群眾創(chuàng)作、口頭傳播的特征而經(jīng)久不衰。正如郭沫若所說:“如果回想一下中國文學(xué)的歷史,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遺產(chǎn)中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就是民間文藝或是經(jīng)過加工的民間文藝作品”。一般民間口頭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神話傳說,肯定人生的意義,整個(gè)故事情節(jié)是為了說明人通過積極、艱苦的奮斗,可以取得幸福,所謂“不知嚴(yán)霜寒,焉知太陽暖”,只有歷經(jīng)憂患的人才懂得歡樂的價(jià)值。
1.史說伏羲
據(jù)《中國姓氏大全》載文道:“伏羲氏、女媧皆風(fēng)姓”。又據(jù)史料推測,女媧是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領(lǐng),而伏羲則是父系氏族部落的首領(lǐng)。神話傳說中所謂伏羲與女媧的結(jié)合,歸根結(jié)底是兩個(gè)氏族部落的結(jié)合。神話傳說二人曾以兄妹相稱,事實(shí)上,應(yīng)該是二個(gè)氏族部落地位平等結(jié)合的反映。
“三皇”—伏羲氏、神農(nóng)氏、女媧氏,三者反映的是氏族公社時(shí)代,女媧氏是女的,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首領(lǐng),應(yīng)當(dāng)比較早,伏羲氏、神農(nóng)氏是男的,是父系氏族公社的首領(lǐng),應(yīng)當(dāng)比較晚。為什么反而把女媧氏放在后頭呢?原來這些傳說大都經(jīng)過后人整理,把次序顛倒了。還有,在傳說中女媧氏是造人的,把她放在伏羲氏、神農(nóng)氏后頭又怎么講得通呢?神話傳說本來不是歷史科學(xué),所以難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伏羲傳說所提供的歷史知識,有些是可能的,也有些是荒誕的。一般說來,離我們越遠(yuǎn)的可信程度越少;離我們比較近的就可能比較接近于真實(shí),就該神話傳說本身很有教育意義的同時(shí),也反映了一部分我國原始社會的歷史。
2.伏羲傳說的典型性
生活在天地之間,我們?nèi)祟悤?jīng)常問自己天地是怎樣起源的?人類本身又是從哪兒來的?這些問題今天都已經(jīng)有了正確的答案。天文學(xué)家告訴我們,地球是星云凝結(jié)成的;考古學(xué)家和人類學(xué)家告訴我們,人類是由古猿進(jìn)化而來……這些答案在今天已經(jīng)成了人們的普通常識。然而幾千年以前的古代,要是有人提出這些問題,答案往往是一個(gè)又一個(gè)的神話傳說。
伏羲傳說反映了遠(yuǎn)古時(shí)代生產(chǎn)和生活發(fā)展的進(jìn)程,我們知道,人類解決居住、食物等等問題,是同自然界做斗爭逐步積累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果。這里面包含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奮斗、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從懂得很少到懂得較多,使生活從很不完善改進(jìn)得較為完善,最后才取得成功。我們把伏羲氏看成象征性的人物,他象征了氏族社會時(shí)期努力解決生活問題的群眾。
說過:“典型是一種政治力量,樹典型等于插旗子,其秘訣就是把需要加以提供的精神、加以推崇的價(jià)值觀、加以實(shí)現(xiàn)的原則、加以推廣的經(jīng)驗(yàn)具體化,在一個(gè)或幾個(gè)看得見摸得著具體人物或事件上,使之成為一面鮮明的旗幟,指引大眾前進(jìn)的榜樣、標(biāo)兵。因此,凡需要提倡一種什么精神,就需要找到一個(gè)或幾個(gè)相應(yīng)的典型來體現(xiàn)這種精神。”
二、伏羲八卦與伏羲文化的價(jià)值
篇2
“我們生活在節(jié)奏越來越快的世界里,無暇理性地思考生命的真諦。讀書會使我們停下來,享受一種深度的安靜,調(diào)養(yǎng)疲憊的心靈。我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書業(yè),希望留給世人一個(gè)生生不息的書業(yè)品牌。”
在唐碼書業(yè)(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唐碼)的網(wǎng)站上,我們看到唐碼創(chuàng)始人曲波留下的這段語錄。從簡單樸實(shí)的話語里,我們看到一位出版人的責(zé)任與雄心。8年了,唐碼以其獨(dú)特的經(jīng)營模式,在中國的出版史上,寫下了屬于自己的一頁。
中國符號:只做葫蘆不做瓢
認(rèn)識唐碼,要先從唐碼的LOGO說起。唐碼的LOGO其實(shí)是典型的中國符號:造型酷似一部古代“書卷”,又似一部打開的現(xiàn)代圖書,凸顯了唐碼的行業(yè)特征;隱含于東方神秘圖騰之中的,是鑲嵌著的字母“T”和“M”――TANGMARK(唐碼)之縮寫,體現(xiàn)了這個(gè)企業(yè)民族性與國際性的和諧融通。
那么,帶著濃重中國符號特點(diǎn)的唐碼,在做著一件什么樣的事情呢?很簡單,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超市圖書。
目前,唐碼是國內(nèi)最大的超市圖書專業(yè)提供商之一。唐碼自創(chuàng)立之初,就把目光鎖定圖書產(chǎn)業(yè),堅(jiān)持以“只做葫蘆不做瓢”為目標(biāo),用最原始的方式,即策劃、出版、運(yùn)營、銷售等在內(nèi)的所有環(huán)節(jié)由公司進(jìn)行一體化運(yùn)作,后來逐步做到了控制超市圖書產(chǎn)業(yè)鏈的整體。
截至目前,唐碼下設(shè)編輯、設(shè)計(jì)、制作、營銷、印務(wù)、財(cái)務(wù)、人力資源七部門,總部現(xiàn)有員工80余人,主辦公區(qū)居于北京極簡主義典范建筑――左岸工社,下?lián)硇氯A書店中關(guān)村店萬米賣場,北鄰北京大學(xué),辦公面積600余平米。“同讀者一起分享和感悟生命賦予我們的歡愉;心有所愿,行有所為,為社會帶來可以觸摸的價(jià)值,讓世界記住我們的存在。” 成立8年來,帶著這種價(jià)值觀,唐碼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開發(fā)了數(shù)千種圖書產(chǎn)品,涉及文史、生活、兒童、勵志四大出版領(lǐng)域,屢次進(jìn)入各地圖書銷售排行榜,并多次向韓國及香港、臺灣地區(qū)輸出版權(quán)。另外,唐碼還策劃了不少擁有自主創(chuàng)新專利權(quán)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如特種賀卡、紀(jì)念冊等,充實(shí)、豐富了商超系統(tǒng)內(nèi)的產(chǎn)品形態(tài)。
唐碼用事實(shí)證明,“專注而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就有很大的成功機(jī)會”。
經(jīng)營模式的轉(zhuǎn)折,從一個(gè)超市開始
曲波早期與朋友合伙創(chuàng)業(yè),在圖書行業(yè)打拼了10余年之后,2002年,曲波決定成立自己的圖書公司,取名“唐碼”。唐碼依靠傳統(tǒng)的二渠道為起點(diǎn),開始了探索之路。
由于曲波有著多年的圖書行業(yè)從業(yè)經(jīng)驗(yàn),這家年輕的公司在壓力巨大的主二渠道生存下來并不難。但是,曲波的目標(biāo)不僅僅是公司能活下來,而且要活得好,活得有質(zhì)量,活得有價(jià)值,最終做出自己的品牌,就像他說的那樣:“我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書業(yè),希望留給世人一個(gè)生生不息的書業(yè)品牌。”
根據(jù)自己多年的從業(yè)經(jīng)驗(yàn)和新公司起步階段的探索,曲波發(fā)現(xiàn):整個(gè)出版行業(yè)主體商業(yè)運(yùn)作能力非常弱,產(chǎn)業(yè)化規(guī)模也不強(qiáng)。幾乎所有的出版機(jī)構(gòu)都在爭搶國有、民營這兩個(gè)主要發(fā)行渠道,而擁擠的渠道往往會出現(xiàn)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如賬期長、產(chǎn)品生命周期短等。因此,做一個(gè)更好的銷售平臺成為很多發(fā)行人的愿望,唐碼也不例外。那么,唐碼怎樣做才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呢?
2003年,曲波跟一位朋友聊天,偶然間聽朋友透露了一個(gè)當(dāng)時(shí)并不引人注意的消息:大連沃爾瑪超市的一家店,有一本“相貌平平”的書平均每天的銷量都在200本以上。曲波訂好機(jī)票,直飛大連。敏銳的商業(yè)直覺讓他似乎發(fā)現(xiàn)了這個(gè)消息的不尋常。他帶著兩瓶水在這家超市觀察了整整一天,最后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在大概1平方米的柜臺上,一天竟然賣出了280多冊圖書。這讓他既驚訝又興奮,一個(gè)新型銷售平臺的輪廓漸漸呈現(xiàn)在腦海中。因?yàn)樯虉觥⒊星辣旧砭陀邢鄬Τ墒斓纳虡I(yè)基礎(chǔ),運(yùn)營模式、經(jīng)營理念早已經(jīng)完成了市場化進(jìn)程,所以在商超銷售圖書,實(shí)現(xiàn)“差異化生存”,似乎大有可為。
“大伙都做的事,頂多是喝粥的事。要想吃肉,就得有所不同。”回到公司后,曲波便開始策劃轉(zhuǎn)型,目標(biāo)很明確:開拓“商超渠道”。
2004年,唐碼嘗試性地進(jìn)入商超渠道。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運(yùn)營,曲波發(fā)現(xiàn)商超渠道有三大好處:一是不拖欠賬款,二是利潤穩(wěn)定、持久,三是隨機(jī)消費(fèi)增加。這些好處使唐碼更加堅(jiān)定了全面構(gòu)建商超渠道的信心。2005年,唐碼書業(yè)正式啟動全國商超平臺構(gòu)建計(jì)劃。第一步是“圈地”,全面進(jìn)入全國一線城市各大連鎖賣場,與賣場簽訂合同,自主經(jīng)營圖書柜臺。第二步是“圈人”,各大區(qū)域經(jīng)理管理賣場,區(qū)域經(jīng)理直屬唐碼管理。各區(qū)域是按客流量大小來配備人力的。曲波介紹,銷量好的賣場平均一天的銷售額是1萬元,這樣的賣場可能需要三四個(gè)人同時(shí)維護(hù);而有的城市網(wǎng)點(diǎn),一個(gè)人可以同時(shí)維護(hù)幾家賣場。2006年,唐碼創(chuàng)立并實(shí)施了公司直營、風(fēng)險(xiǎn)抵押承包經(jīng)營、渠道授權(quán)加盟等多種形式并存的復(fù)合經(jīng)營模式,渠道規(guī)模迅速擴(kuò)張。2007年,“唐碼模式”引起業(yè)界廣泛關(guān)注。2009年,唐碼商超平臺規(guī)范化運(yùn)營體系日臻成熟,連續(xù)五年同比增長超過三位數(shù)的經(jīng)營業(yè)績,讓唐碼具備了在更深、更廣層面上拓展渠道空間、整合出版資源的能力。到如今,唐碼直控大型連鎖超市如沃爾瑪、家樂福、樂購等為核心的直控和經(jīng)銷終端已達(dá)2000個(gè),唐碼的圖書產(chǎn)品日益受到讀者的喜愛。
曲波詼諧地說道:“傳播書的人是俗人,是血液中流淌著高貴品質(zhì)的俗者。把書變得容易消費(fèi)需要大智慧。”
唐碼策劃:個(gè)性化出版與公版資源的運(yùn)用
把書變得容易消費(fèi),不僅需要一個(gè)好的銷售渠道,還需要對圖書的市場競爭力有一個(gè)準(zhǔn)確的把握。在曲波看來,要獲得成功最核心的就是產(chǎn)品策劃和成本控制。唐碼的圖書策劃經(jīng)驗(yàn),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是個(gè)性化出版,一個(gè)是公版資源的運(yùn)用。而成本控制最優(yōu)化,也都體現(xiàn)在這其中。
所謂個(gè)性化出版,就是根據(jù)市場的需求,通過專業(yè)化資源整合,策劃出既適應(yīng)市場需要又獨(dú)具唐碼特色的圖書產(chǎn)品。其實(shí),這中間充滿難度。比如唐碼出品的Qbook版口袋書,目前已經(jīng)上市了Qbook文化經(jīng)典、Qbook勵志書、Qbook菜譜等三個(gè)門類幾百個(gè)品種。Qbook版圖書個(gè)性鮮明,不僅開本特殊,便于攜帶、把玩,外面還封裝了特別書盒,精致可愛;更讓人驚奇的,是Qbook圖書在翻閱時(shí)還能散發(fā)出特殊的檀香味,真正是一卷在手,書香滿懷。就目前普遍的印刷技術(shù)來說,很少有其他出版商能夠策劃出這樣的圖書。首先,獨(dú)特的開本難以復(fù)制,大部分印刷廠的機(jī)器是不能直接切出這個(gè)開本的;其次,有些印刷廠的機(jī)器也許能切出這個(gè)開本,但是卻無法避免紙張的浪費(fèi);再次,看似簡單的書盒,也沒有現(xiàn)成的加工設(shè)備,幾乎只能靠手工粘合。此外,讓圖書翻閱時(shí)散發(fā)特殊香味,也同樣沒有現(xiàn)成方案。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解決,生產(chǎn)成本就會失去控制,很可能書還沒上市就面臨虧損。對于這些難題,唐碼又是怎么克服的呢?曲波給出的答案是:組建專業(yè)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加大創(chuàng)新成本投入,摸著石頭過河。唐碼的專業(yè)印務(wù)人員不僅要配合出版社協(xié)調(diào)紙廠、印廠、包裝廠間的工作,優(yōu)化各項(xiàng)工作流程,還要及時(shí)了解跟蹤當(dāng)前最先進(jìn)的印制工藝,為個(gè)性化生產(chǎn)提供技術(shù)支持。為了提高紙張利用率及印刷質(zhì)量,曲波曾親自到歐美等國家對相關(guān)設(shè)備進(jìn)行考察研究,回國后便和合作良好的印廠一起研究設(shè)備引進(jìn)或改良。當(dāng)然,唐碼的個(gè)性化出版并不只體現(xiàn)在小開本圖書策劃上,也有大開本的,如《大全集》系列叢書,其獨(dú)特性主要體現(xiàn)在書籍厚重、文字量大、內(nèi)容豐富,每本書針對各自所涉獵的領(lǐng)域進(jìn)行了最全面的信息搜集、匯總,力求成為該領(lǐng)域內(nèi)最權(quán)威、最精確、最實(shí)用的版本。還有正常開本的“個(gè)性化圖書”,比如《線裝經(jīng)典》系列叢書,其獨(dú)特性主要體現(xiàn)裝幀方式上,古樸雅致的縱紋紙封面,密實(shí)精致的銅色線繩,讓人看了就有一種想收藏的愿望。
所謂公版資源,就是根據(jù)國際版權(quán)公約和國內(nèi)有關(guān)版權(quán)方面的規(guī)定,某些已不再需要支付版稅的內(nèi)容資源,如我國的四大名著、外國的一些名家名作等。這些內(nèi)容資源多是人類千百年積淀下來的經(jīng)典作品,文化傳播價(jià)值很高。對公版資源最大化利用,一方面降低了產(chǎn)品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縮短了生產(chǎn)周期。比如唐碼出品的《家庭書架》系列叢書,古今中外經(jīng)典文化文學(xué)作品均有涉獵,出版后影響廣泛,很快出現(xiàn)了跟風(fēng)之作。這些使用公版資源策劃的圖書,通過唐碼的精心設(shè)計(jì),不但降低了讀者的消費(fèi)難度,同時(shí)也增強(qiáng)了讀者的閱讀欲望,提升了文化知識的傳播效率。
經(jīng)營有道,唐碼就在前進(jìn)的道路上
在公司的經(jīng)營方面,曲波總結(jié)出了一個(gè)獨(dú)具特色的“五道”。正是憑著這經(jīng)營五道,唐碼在民營書業(yè)中站穩(wěn)了腳跟。
人道――人性先于個(gè)性;潛力大于能力。所有資源要素中,合適的人最稀缺。誠信需要成本,卻最該支付。活人沒有圣人,志同才能道合。知事難,行事難,知行合一最難。
職道――思維品質(zhì)、執(zhí)行力,一個(gè)都不能少。從事一份職業(yè),而不只是一項(xiàng)工作。首先對自己有要求,然后才是對別人。結(jié)束不等于結(jié)果。想到頭兒,做到底。學(xué)習(xí)永遠(yuǎn)是現(xiàn)在進(jìn)行時(shí)。在合適的時(shí)間、合適的地點(diǎn)做合適的事。做事用腦,不惟用手。清楚溝通與八卦的區(qū)別,追求有品質(zhì)的交流。短板決定團(tuán)隊(duì)力量,長板決定個(gè)人力量。
商道――地上本無路,走得人多了,便有了路;地上本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沒了路。有路無路,全在思路。尊重規(guī)律,做規(guī)則制訂者。做大家都在做的,只能喝粥,想吃肉就要不同。有所為,必有所不為。先驅(qū)與先烈只差一小步。永遠(yuǎn)與看不見的手手拉手。穩(wěn)健才能持久,專注才能專業(yè)。貳比壹大是常識,但能正確判斷哪個(gè)是貳哪個(gè)是壹卻是難事情。
書道――把書變得容易消費(fèi)需要大智慧。商品是書的第一性。被消費(fèi)的難易程度甚至比書本身更重要。偶爾無中生有,經(jīng)常有中生無,創(chuàng)新的舊事物比創(chuàng)造的新事物更易成功。定價(jià)不僅僅是數(shù)字,更是能力。
渠道――有渠水自來。渠道具有商品屬性,渠道消費(fèi)需要成本。沒有渠道的商品只是產(chǎn)品。渠道價(jià)值取決于為商品提供服務(wù)的能力和品質(zhì)。整合渠道資源的能力體現(xiàn)企業(yè)核心競爭力。渠道是滿足需求的途徑,更是孕育需求的土壤。渠能載舟亦能覆舟。
2010年,又是一個(gè)新起點(diǎn)。唐碼不僅在渠道方面向二線城市全力進(jìn)發(fā),在出版資源整合方面也向的出版人拋出了橄欖枝。在合作方面,曲波說,他希望能盡量爭取所在細(xì)分領(lǐng)域的話語權(quán),引導(dǎo)市場,擴(kuò)大合作。“大陸目前的發(fā)展階段,與臺灣三十年前極其相似,未來若能得以和三十年前臺灣暢銷書的出版單位合作交流,是唐碼一大幸事。”
篇3
關(guān)鍵詞 天人觀;命;天道;人事
人的命運(yùn)是我們思考的最棘手最復(fù)雜的問題之一。“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做什么?我們往何處去?”這些疑問眾所周知。在每種文化中,人們在思索中發(fā)現(xiàn),他們的一生不過是彈指一揮,他們只是其所屬整體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追問這樣的命運(yùn)的意義,而對人的命運(yùn)的思索不能不從超驗(yàn)的角度出發(fā)。
本文以對《易經(jīng)》、《中庸》等中國經(jīng)典文本的思考為出發(fā)點(diǎn)。這些文本是儒學(xué)在中國、韓國復(fù)興的源泉,也賦予了李栗谷大量的靈感。確實(shí),理學(xué)家會經(jīng)常回歸到某些基礎(chǔ)性的章節(jié)。
傳統(tǒng)認(rèn)為,理學(xué)把人的本質(zhì)看作理。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曾經(jīng)有過很多的辯論,有的強(qiáng)調(diào)它的善,有的則指出其惡的傾向。然而,中國關(guān)于這方面的思考很快就把人性和天命的概念聯(lián)系起來。因此,挖掘天命問題也就是挖掘人性問題。
根據(jù)我們的研究方法,我們力圖證明,把人性問題和天命聯(lián)系起來,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它,是很有啟發(fā)性的。對天的研究自孔子以來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而李栗谷則是如此表述的:“以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言之,則謂之性,其實(shí)一也。”(《圣學(xué)輯要》)所以,對人的正確理解離不開天與天命。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先繞個(gè)小彎子,來看看保羅·利科《意志哲學(xué)》中的部分章節(jié)。這些文字介紹了生活、命運(yùn)以及在有限的生命里獲得自由的難度。因此,“命”里不僅有命運(yùn),而且還有意志,意志與天、與人都有關(guān)系,在現(xiàn)代社會里必須對此進(jìn)行新的闡釋。
我們以中國經(jīng)典為基礎(chǔ),重新審視了李栗谷部分重要文章,如《四子立言不同疑二首》、《圣學(xué)輯要》、《易數(shù)策》等,以便總結(jié)他關(guān)于天人關(guān)系中人之命運(yùn)的獨(dú)特觀點(diǎn)。李栗谷不僅因?qū)?jīng)典十分深刻的思考而出名,更因他在抓住其獨(dú)特寓意的同時(shí),還在不同的經(jīng)典之間建立聯(lián)系,并與宇宙相聯(lián)系,因?yàn)樗M麑ΜF(xiàn)實(shí)的真正理解更加深入,而不希望被任何一種觀點(diǎn)所束縛。
李栗谷闡明了天人關(guān)系中人類命運(yùn)的幾個(gè)重要方面。在這一點(diǎn)上,他與孔子非常相似。孔子雖然審慎,卻還是表現(xiàn)出了與天的密切關(guān)系。李栗谷以天期待圣人為眾人的利益?zhèn)鬟f信息為中心,討論了天人之間的神秘交流。
與希臘文化中的命運(yùn)及基督教的天意相聯(lián)系來思考中國文化中的命運(yùn)和天意問題是十分有意義的。希臘人,尤其是荷馬的《史詩》,賦予了命運(yùn)一種悲劇意義,這又與基督教的冥想混合在一起。但神意也通過愛和慈悲來啟示和引導(dǎo)人的意志,把愛與慈悲同中國文化的天意相比較,應(yīng)該會帶來很多啟示。
一 中國經(jīng)典中的天與人的命運(yùn)問題
在開始介紹李栗谷對人的命運(yùn)的探索之前,本文將先對部分經(jīng)典如《易經(jīng)》中的重要章節(jié)進(jìn)行重新審視。張岱年介紹了王充、張載、王夫之等數(shù)位思想家對命運(yùn)的思索,指出“在古代,命指的是天意。隨著神的含義不斷減弱,到了孟子時(shí)期,命指的是一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東西”。然而,如果我們重新研究某些文章,我們的理解就會有細(xì)微變化。
現(xiàn)在,隨著現(xiàn)代化,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也集中到了個(gè)體,即完全橫向意義上的人。因此,隨之而來的是人性問題被某些思想加以否定,如薩特,他認(rèn)為,人只能由其自身塑造。其他哲學(xué)家則抹煞一切高級層次,提出人即上帝的觀點(diǎn)。然而,這些觀點(diǎn)并不能用來詳盡分析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這一思想并未受到質(zhì)疑。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類似的章節(jié)引發(fā)了大量的評論。但我們必須接受它們,因?yàn)樗鼈兪腔T谶@里,人性表現(xiàn)為天所賜予、分配給每個(gè)人的能力。這里的分配并不是上級的指令,而是賦予每個(gè)人某種才能,順應(yīng)這種才能行事就是人道、體道。
其他談?wù)撎斓恼鹿?jié)還有《禮記》:“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易經(jīng)》同時(shí)還提到了乾的賦予和坤的接收。關(guān)于“乾”的注解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關(guān)于坤的注解有:“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成亨。”
類似的章節(jié)對改變?nèi)鍖W(xué)形象十分重要,因?yàn)槿鍖W(xué)把天意視為不可置疑的宿命,或者強(qiáng)調(diào)堅(jiān)強(qiáng)的意志。此外,在這里還有著與基督教相關(guān)的基礎(chǔ):基督教講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意志并不是一種要求或客觀的律法,而是對每個(gè)存在的個(gè)體產(chǎn)生仁慈。
因此,在《易經(jīng)》的哲學(xué)部分,有一段話不由讓人想到孟子。正是這段話促進(jìn)了理學(xué)的發(fā)展:“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物的本源上,道與天互為補(bǔ)充。
道在天賦的繼承和物的終極中得以體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道“顯諸仁,藏諸用”。這必然會引起很多關(guān)于命運(yùn)的思考。由此,我們可以認(rèn)識到,人性與道德顯現(xiàn)有關(guān)。人的根本必須由人自己來發(fā)掘。
我們通常單獨(dú)分析一些基本概念,如天、人性、理等等。然而,我們發(fā)現(xiàn),一旦把這些概念相互聯(lián)系起來,它們就變得十分清晰了。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力圖從天人關(guān)系的角度來思考人性和命運(yùn)問題。我們在天人關(guān)系上投入的精力越多,我們可以從中挖掘的意義就越多。在對人性和天命的理解中,天與道遙相呼應(yīng)。因此,會有“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樣的說法。由此,關(guān)于人性的認(rèn)知和關(guān)于道、天的認(rèn)知相互聯(lián)系起來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這段著名的話就是其見證。
主動的一面與《易經(jīng)》中被動的承受結(jié)合起來:坤“率性”、“乃順承天”的特點(diǎn)在主觀意志傾向中是十分困難的。
陳淳(1159~1223)在其理學(xué)著作中以“命”開篇,把“性”放在“心”之前,這一點(diǎn)十分耐人尋味。比如,他說:“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
陳淳重新在乾、坤的特點(diǎn)(元、亨、利、貞)和人性的特點(diǎn)(仁、禮、義、智)之間建立對應(yīng)系:“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賦予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此道之流行賦予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
我們可以上文的粗略闡述為基礎(chǔ),來理解下面這句引發(fā)理學(xué)家們很多思考的話:“和順于道德而禮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爭論的焦點(diǎn)通常在“性即理”上。但我們卻很少與上文提到的“和順于道德”和理解人的命運(yùn)的終極目的聯(lián)系起來。我們再次看到了形容坤的“順”字,只有順應(yīng)道、德、理,才能進(jìn)入人性與命運(yùn)的深處。
《中庸》里的一段話揭示了人對于人性必須起到的積極作用:“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由此,人性的發(fā)展與天建立了聯(lián)系。
在經(jīng)典研究中,我們往往會與重要啟示擦肩而過。在上文中,“誠”是人性發(fā)展及與天地協(xié)調(diào)的關(guān)鍵。與孟子作一比較就會顯得十分明朗,可以明確自然、命運(yùn)與天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繼續(xù)上面提到的引文:“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過“立命”這個(gè)詞,我們看到了天人之間的互動。人只有通過等待、忍受,改善本性,才能創(chuàng)造獲得天命的條件。
理雅各(James Legge)在評論《孟子·盡心上》時(shí),在對“盡其心,知其性”的理解上表現(xiàn)了與朱熹不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朱熹的解釋不夠明確。在他看來,整段話都強(qiáng)調(diào)了天的重要性,而天又與上帝很接近。因此,他贊成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孟子原文上,而不是注解。
孟子同時(shí)談到了知性與養(yǎng)性、知天與事天,然而我們往往會把人性與天,或者抽象的知識與事天的意愿和行動分割開來。另外,孟子思想的重點(diǎn)在于人的內(nèi)在發(fā)展。這一發(fā)展使人能夠承擔(dān)天命,服從天的神秘意志。我們不能不想到孟子自我犧牲的鮮活例子,它已成為很多亞洲人的典范:“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性和命運(yùn)的了解與形式與可能很神秘的極端經(jīng)歷混合在一起了。
《孟子·盡心上》第二段關(guān)于命的思考反映了孔子對命的重視程度。“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這里又提到了“順”字。命遠(yuǎn)非宿命,而是需要主動的認(rèn)識和行動,需要了解天和天意,而這一點(diǎn)又以思想的成熟為基礎(chǔ)。孔子為此樹立了榜樣。人既是其命運(yùn)的先決條件,而對其所不能改變的東西卻又不得不屈服。
如果我們把《孟子》、《中庸》、《論語》、《易經(jīng)》放在一起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在天、人性、命等方面各有側(cè)重。這一點(diǎn)非常具有啟發(fā)性。《孟子》談?wù)撝浴B(yǎng)性,而《中庸》和《易經(jīng)》則講盡性。其目的都在于強(qiáng)調(diào)一種決定性和升華性的行動,如《孟子》中的“事天”,《中庸》里的“與天地參”。因此,命可以理解為一項(xiàng)神圣的使命,有待于人在具體生存環(huán)境中發(fā)現(xiàn)。
我們在這里順帶簡要地講一下西方哲學(xué)。保羅·利科的思想,尤其是關(guān)于“贊成與必然”的思考,為從個(gè)性角度思考人性設(shè)立了大框架。通過“親身經(jīng)歷的必然——個(gè)性”,利科提出了把本性與自由聯(lián)系起來的問題:“常識所無法理解的是,自由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種本性。性格是自由本身的個(gè)體風(fēng)格。自由既不能選擇也不能改變這種風(fēng)格。”
西方關(guān)于命運(yùn)的看法:“我的性格是附著于我的本性,它是如此地貼近我,以至于我無法與之對抗。”“性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命運(yùn)……我的性格造就了我的特性,我承受我這個(gè)個(gè)體,然而,我不過是我自己塑造的一切罷了,除了使用它之外,我不知道我的力量以何為止境。……我想,我性格中不可改變的部分不過是我的自由的存在方式,但我卻又無法正確地表述這一想法……我有自己的選擇方式,但我選擇自我的方式卻不是我能選擇的。命運(yùn)是與我的自由密不可分的、個(gè)人的無意識的表現(xiàn)方式,這一點(diǎn)超出了常識和哲學(xué)家最微妙的極限……我只能首先深信我要負(fù)起全部責(zé)任。我的主動性是無止境的。然后,我才能根據(jù)一種已經(jīng)規(guī)定好的不可更改的方式運(yùn)用我的自由……”
正如利科所指出,難點(diǎn)在于把人所接收到的自我與他所做的,無限的可能與既定的條件調(diào)和起來。人并不僅僅是其自身塑造的,同時(shí)也是一種被動接收。中國古代哲學(xué)對此有所察覺,而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在與存在和道德的源泉斷絕聯(lián)系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的獨(dú)立性上,因而也許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人的限度。
關(guān)于人被動的一面,利科某些漂亮的文字與中國古代經(jīng)典遙相呼應(yīng):“生命支持著我。出生把我?guī)У搅诉@個(gè)世上,死亡又會把我?guī)ё撸驗(yàn)椴皇俏野才派巧才盼遥陨窕粯又С种遥粑窈@艘粯影盐彝衅稹保弧按嬖趯τ诜制缧缘睦斫舛允且环N矛盾,對于更為隱蔽的統(tǒng)一性的意識而言則是一種奧秘:它既是有意識的,又是強(qiáng)制性的,它是生命活動的源頭。”以及:“我不僅承受了開始,而且承受了一種本性,即成長的規(guī)律,構(gòu)造的原理,一種無意識的機(jī)制以及一種個(gè)性。”
對利科而言,對自我的深層理解就是從抗拒走向接受,接受在賦予我們的本性的范圍內(nèi)體驗(yàn)自由。我們可以看到,這里觸到了利科在與加布里埃·馬塞爾(Gabriel Marcel)的交往中所接觸到的智慧。這種智慧與《易經(jīng)》作者的創(chuàng)作源泉并無很大差別。《易經(jīng)》和李栗谷的這種智慧正是本文所希望采取的角度。
利科把對人性的思考重心置于概括了完美人性的三個(gè)方面上:個(gè)性、幸福和尊重。從超驗(yàn)的角度思考,世界是一個(gè)物的綜合體;從實(shí)際的角度思考,就可以區(qū)分出人、其個(gè)性的局限性、其幸福的無限性和人的敬畏本性的調(diào)和性。
我們逐步進(jìn)入性格的局限性。性格是我們“整體動機(jī)上一個(gè)有限的出口,……既定了人所有可能性中我能享有的實(shí)際自由度”。人希望實(shí)現(xiàn)的業(yè)績就像“一片已確定了方向的動機(jī)場,性格是動機(jī)場方向的起點(diǎn),幸福是這個(gè)方向上無限遠(yuǎn)的盡頭”。因此,性格的局限性和幸福的無限性不成比例。理性要求整體性,而幸福的感覺告訴我,我正朝我的目標(biāo)前進(jìn)。
性格與幸福的綜合在人身上完成,但這里的人指的是其理想狀態(tài),是一個(gè)可以稱之為人性的目標(biāo)。人在敬的道德情感中完成綜合。利科在研究康德思想時(shí)指出,人性的構(gòu)成保證了心有它的位置,有能力接受純粹倫理的益處。但他認(rèn)為,康德過分強(qiáng)調(diào)了人墮落的一面,建議超越道德二元論,從人最初的純潔中挖掘情感的基礎(chǔ)。人內(nèi)心的敬表明,人能夠識別某種神秘的、需要思索的本性。
對人性的思索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與天有關(guān)的超驗(yàn)性和人在努力承擔(dān)其命運(yùn)時(shí)深層次的一面。幸福在西方人性論中變得如此重要的同時(shí),對人性和行為的修正,即可以避免一切悔恨的生活方式,卻是自古以來最受中國人關(guān)注的。因此,韓國人極度強(qiáng)調(diào)的敬也就帶上了宗教色彩,它可以表現(xiàn)為敬畏或關(guān)注,在對他人的關(guān)注中忘卻自我來接受和改變。我們在面對各種事件時(shí)就不會抗拒,而會進(jìn)入其奧妙,采取一種能使我們達(dá)到快樂的行動方式。
進(jìn)入這一層次的思考,馮友蘭《新原人》的第七章對我們十分有啟發(fā)。在講到“天地境界”時(shí),馮友蘭指出,要完全理解人和人生,就必須超越自然、功利和道德境界,進(jìn)入對天的覺解。他對中國古代傳統(tǒng)中的天的介紹十分感人。“知天然后可以事天、樂天,最后至于同天,此所謂天者,即宇宙或大全之意。”這是達(dá)到天地境界的最后一步。“同天的境界是不可思議底。但人之得之必由于最深底覺解,人必有最深底覺解,然后可有最高底境界。同天底境界,本是所謂神秘主義底。”
馮友蘭用優(yōu)美的筆調(diào)提到了儒家樂的一面,儒家的樂有助于對命運(yùn)的理解。“樂天者之樂,正是此種之樂。明道說:‘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說:‘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fēng)弄月而歸,有吾與典也之意。’此等吟風(fēng)弄月之樂,正是所謂孔顏樂處。”我們將超越李栗谷的痛苦來尋找對這種樂的理解。
二 李栗谷的天、命觀
我們下面來探討李栗谷的研究。他的研究不僅以對中文典籍的分析為基礎(chǔ),而且還包含了深刻的親身體驗(yàn)。我們將把他對天命的研究方式與他對天、變化和涉及智慧、精神、具體生活、詩等獨(dú)特觀點(diǎn)聯(lián)系起來討論。
對經(jīng)典的詮釋
我們評論很多智者和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留下的文字的不同之處,但這些文字同時(shí)也有共同的思路,因?yàn)樗鼈兌荚噲D從與實(shí)在的關(guān)系出發(fā)來理解人。這就是孔子思想吸引李栗谷的地方。文字就是道的痕跡:“言本于道,而未嘗不異焉。道見于言,而亦未嘗不同焉。道之同者,原于天而前后所以一本也。”
言扎根于道,而道的本質(zhì)來源于天。因此,文字是本質(zhì)體驗(yàn)的一種方式。四書體現(xiàn)了道實(shí)體的不同方面。李栗谷在比較了這四者后寫道:“《大學(xué)》,明道之書也……欲使學(xué)者自明其天之明命,以及乎天下,而其旨則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論語》,入道之書也……欲使學(xué)者全其本心之德,以立其根本,而其旨則倦倦于仁之一字而已……《孟子》,衛(wèi)道之書也……因人性之本然,遏人于欲將萌,則其旨在于存天理而已……《中庸》,傳道之書也,究性命之蘊(yùn)奧,致中和之極功,費(fèi)而至于配天,隱而至于無聲臭,則其旨豈在于誠之外哉。”因此,每個(gè)圣賢都表達(dá)了發(fā)掘人性的獨(dú)特的、與他人互補(bǔ)的方式,把這一過程引向一個(gè)更高的目標(biāo),即與道或天溝通。
四書以道為核心:明道、人道、衛(wèi)道、傳道。《大學(xué)》的目的在于自己發(fā)現(xiàn)天之明命,并把它推廣到天下人;《論語》旨在完成本心之德,并立其根本;《孟子》的目的在于通過克制欲念來保存天理,而《中庸》旨在通過深究人性與天命,建立中庸與和諧來與天配合。
每本書都涉及天命,并要求人在其中找到他的角色。李栗谷談到了明命。我們在下文中還可以看到表現(xiàn)他對命運(yùn)高度評價(jià)的其他文字。我們可以簡單概括每本書的精華,《大學(xué)》是敬,《論語》是仁,《孟子》是存天理,《中庸》是誠,而不同的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達(dá)了每個(gè)要點(diǎn)。
個(gè)人經(jīng)歷
不探索內(nèi)心最深處怎能發(fā)現(xiàn)道、天和天命?所以,李栗谷在重讀四書時(shí)指出了了解內(nèi)心的重要性。孔子意識到,天下失道,人心迷惘,因此必須超越自我,努力接近仁。孟子也同樣關(guān)注心,大量錯(cuò)誤的觀點(diǎn)使心處于危險(xiǎn)之中,所以,他把思索集中在善心上。子思則努力達(dá)到人性的本質(zhì),提出了聯(lián)系人性與天的誠,而曾子則為了更接近宇宙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德上。
李栗谷在其思考過程中寫道:性則天也,而誠者天之道也,則中庸之論誠,不得不爾也。因此,對他而言,如果一個(gè)人能夠好好地修煉并保護(hù)其本性,那么天與天命就不再遙遠(yuǎn),而要做到這一點(diǎn),反映天之本性的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庸》在贊美孔子的誠時(shí)說:“溥溥如天。”
盡管《中庸》十分強(qiáng)調(diào)誠,因?yàn)樗P(guān)注人性與天命的問題,但正如李栗谷分析的那樣,誠把四書緊緊地聯(lián)成一個(gè)整體。如果誠是天道,我們?nèi)绾文懿恢匾曀?因此,《中庸》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論誠:“不誠無物。”最誠的人有決心度過一切人為和自然造成的境遇。因此,我們可以重新理解孟子的話:“莫非命也。”通過觀察誠,我們可以找到各自的道路:“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在存在的奧秘中,也許沒有什么比意志更有決定意義的了。利科認(rèn)為,意志“是人最基本的實(shí)質(zhì),是人最深層的東西,同時(shí)具有天性和人性兩方面”。因此,未來的一切都在此時(shí)此刻成為定局。我要么行動,要么不行動,或者套用利科的話說,我或者說好或者說不,而這一時(shí)刻可能會帶來歡樂或悔恨。因此,遠(yuǎn)東傳統(tǒng)中的四書引導(dǎo)人們達(dá)到真心愛善、為善的境界。
《易經(jīng)》一直啟發(fā)著遠(yuǎn)東的思想家。“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為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wù);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為了更接近命運(yùn)的神秘之處,可能要從深度、從源頭、從神的角度來分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jì)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樂乎,故能愛。”
人的責(zé)任在于把自己視為宇宙中最關(guān)鍵的部分,不要犯錯(cuò)誤,這樣,人就會逐步融入到天命的運(yùn)動中,就可以“樂天知命”。這一運(yùn)動還與向善、體仁有關(guān)。仁與支撐萬物的道的本性善一致。如果歷史上有人認(rèn)為天命很可怕或者難以捉摸,這是智慧減弱的緣故。
我們來看一下孔子和顏回的“樂”,周敦頤和程顥對此非常敏感。初看,“樂”在李栗谷思想中并不明顯,他對世界流露出一種悲傷。李栗谷的詩是對處于危險(xiǎn)中的天然本性的一種向往:“天真汩私偽……色為伐性斧。”
顏回雖然身處窮困,沒有官職,卻不為自己的出路而憂心,反而關(guān)心他人的發(fā)達(dá)。李栗谷對這種“樂”還是十分敬佩的。這不是個(gè)體的樂,而是與天下人利益相關(guān)。顏回敢于實(shí)踐孔子的教誨,保持天性,表現(xiàn)了他對求知的熱愛。李栗谷對此十分欽佩。
李栗谷對孔子思想的思考
孔子的弟子們不明白為什么孔子在人性和天道方面沒有更多的言論。李栗谷在其中一部著作中解釋說,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孔子關(guān)于教育的想法,但會聽的人就能覺察出孔子所要傳授的東西:“夫子之教循循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yuǎn)者,則宜夫子之罕言,而學(xué)者之有所不聞也。至于孟子,則承道微之余,任明教之責(zé),擴(kuò)前圣之所未發(fā),而垂訓(xùn)于后世,故顯其微,而闡其幽,以天之妙用,性之本原,揭示學(xué)者,欲使因其言而造其理耳。……圣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其發(fā)于文章之顯,動作威儀之節(jié),成性明德知天命之訓(xùn)者,莫非示以至理,而人自不察。至孟子,而始著其微旨焉。……夫子之道合乎天,而孟子發(fā)揚(yáng)以言語者也,此夫子之所有欲無言,而孟子所以未免于好辯者歟。”
天人關(guān)系及對命的理解
李栗谷指出:“夫子之道合于天。”他明白,古代的圣賢是在與天的密切關(guān)系中得以看清宇宙之理的。所以,他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道統(tǒng)攸始。”如果說孔子對于天與命運(yùn)相關(guān)的重要問題顯得非常審慎,但他的一生卻顯示出了他與天的密切關(guān)系,而且,在他生命的關(guān)鍵時(shí)刻,明確、有力地表達(dá)了他的看法。在讀李栗谷的文章時(shí),我們可以感到一種類似的與天的強(qiáng)烈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也許經(jīng)過在金剛山多年的修煉變得更加成熟。
李栗谷的思想發(fā)展了一種對統(tǒng)一意/心、意/氣、氣/體的追求。這在他的“理氣之妙”的觀念中可以看到。李栗谷希望避免一切二元論。我們感到他在與天的關(guān)系中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下面這段話就是很好的例證:“嗚呼!天人一也,更無分別。惟其天地?zé)o私,而人有私。故人不得與天地同其大焉。”在他的書中,李栗谷多次談到了天人之間的自然感應(yīng):“自然之應(yīng),而天人交與之妙也。”
和孟子一樣,李栗谷進(jìn)一步申發(fā)了孔子對天的思考。和孔子一樣,他在閱讀《易經(jīng)》的過程中意識到,要想在一生中不犯錯(cuò)誤不后悔,就必須理解人性,而且必須從與宇宙的實(shí)在關(guān)系中去理解,而不是抽象地把握。每個(gè)人都有不同的本性和命運(yùn)。這就是他的價(jià)值、尊嚴(yán)和意義。但是,只有從最親近的人開始與千千萬萬其他命運(yùn)充分接觸,才能達(dá)到成功,才能有所作為,而理解的關(guān)鍵在于天人關(guān)系:“莫之為者,天地有所為者,人也。知天之未始不為人,知人之未始不為天,則始可謂知命矣。”
李栗谷在追求至誠的同時(shí),對與天合一的重要性進(jìn)行了思考。他解釋說,孔子即使在重病時(shí)也拒絕別人為他祈禱,因?yàn)樗雷约喉樚煲舛小Ke了周公的例子:周公為了救君主祈禱,因?yàn)樗靼琢顺剿陨淼奶煲猓础疤熘畬?shí)命”。
李栗谷專門撰文來證明天與人、天道與人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韓國對包括祈禱在內(nèi)的靈性、自然與人神圣的一面理解上的特征。這在李退溪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順德者吉,逆德者兇。天人感應(yīng)之理,斯可知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在也。逆于人而順乎天者,未之有也。順于人而逆乎天者,亦未之有也。然而間或有人事似順,而天不助順者,亦有人事似逆,而天反佑逆者,其故何哉?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镃基,不如待時(shí)。失其時(shí)勢者,似順而必?cái)。闷鋾r(shí)勢者,似逆而有成。”
因此,對李栗谷而言,天人關(guān)系并沒有那么簡單。德與順可以使人更接近天,但還有讓人難以應(yīng)付的現(xiàn)實(shí)。和孟子一樣,李栗谷十分重視對情境的理解。這顯示出了一種超常的睿智。在此也包含了孔子關(guān)于知天命的回答的其中一方面。因?yàn)槲覀冎溃鬃釉庥鲞^很多次拒絕、反對和不屑。當(dāng)他喜愛的弟子去世時(shí),他還高呼“天喪我”。但孟子還是贊美孔子是“圣之時(shí)者”。我們在前文已經(jīng)看到,《易經(jīng)》認(rèn)為,樂天與知命、安土有關(guān)。李栗谷一生坎坷,也常常思索“時(shí)”的問題。
李栗谷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話:“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在”。這很像孟子。孟子重視歸心、回歸自我和滿足于誠。所以,天命不像道那樣遙遠(yuǎn)、抽象、不可名狀,它與人很接近,滲透于日常生活和人內(nèi)心最深處。天與那些超越純粹責(zé)任而愛德的人十分密切。正如老子所說:“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
李栗谷對《易經(jīng)》的研究
李栗谷在《易數(shù)策》中表達(dá)了他對命的一些獨(dú)特想法。和《天道策》一樣,這本書也描述了天的寬宏大量,表達(dá)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的原因。
人所應(yīng)循之道是通過圣人來傳遞的:“天地必待圣人,然后乃以是數(shù)示人;圣人必待文瑞,然后乃以是理著于世。天不得不生圣人,亦不得不生文瑞,此則自然之應(yīng),而天人交與之妙也。”
天對圣人的期望和圣人實(shí)現(xiàn)這一期望來回應(yīng)天,是中國古代思想中常見的主題。這并不是要圣人站在其他人之上,而是在天所期望的某一特定時(shí)刻為眾人的利益說話和行動。為此,需要天和受命之人的長期準(zhǔn)備。子貢的話眾所周知:大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縱天之將圣,又多能也。”
李栗谷認(rèn)為:“河圖未出之前,八卦之形已具于伏羲方寸中矣。”理一而在于天。伏羲造八卦,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由于人的無知,文王、周公和孔子不得不加《傳》來啟示人們。三圣一心,釋伏羲之卦,把卦象留給了古代,如日中的太陽光芒萬丈。
書中的一段話使我們了解到李栗谷對《易經(jīng)》的敏銳洞察力。李栗谷用他常用的研究方式,讓我們超越不同的創(chuàng)作層次和不同歷史條件下的這種評論,感受到與天相通的圣人最深切的關(guān)懷。這就是圣人們能夠一心的原因。“求之于心術(shù)之動,得之于精神之運(yùn),非圣人焉能知《易》之微意乎?大《易》之義,實(shí)理而已。真實(shí)之理,不容休息,則上天安得不生三圣,三圣安得不衍大《易》哉?……大哉《易》也,以之順性命之理,以之痛幽明之故,以之盡事物之情,其體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
李栗谷以一段對太極的思考作為《易數(shù)策》的開篇:“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李栗谷就這樣耐心地把現(xiàn)實(shí)復(fù)雜、神秘的不同角度從深層次上聯(lián)接起來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人及其命運(yùn),李栗谷從未忽略整體性的意義。他為《易經(jīng)》中如此豐富的人與道的交流而激動不已:“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對理和心的闡釋的主線和聯(lián)接起復(fù)雜的方方面面的,就是李栗谷在上文通過實(shí)理所再次提到的。實(shí)理與實(shí)心呼應(yīng),而實(shí)心就是誠。
《易經(jīng)》全書講的都是變化。變化,一方面要求通過現(xiàn)實(shí)最神秘的地方,如生死之理,來洞察它的本質(zhì),另一方面可以應(yīng)用于人、情境和現(xiàn)實(shí)事物。敏銳的目光穿越時(shí)間和距離,行動合理而富成效。沒有與純粹的誠融為一體的明晰精神,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李栗谷對古代關(guān)于誠的傳統(tǒng)進(jìn)行了深刻的思索。周敦頤認(rèn)為:“誠者,圣人之本。”“嗚呼!誠之為體,至微而至妙;誠之為用,至顯而至廣。體乎萬物,而為物之終始。故元亨利貞,天之誠也;仁義禮智,性之誠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誠如神。”因此,對李栗谷而言,成圣決定了能否與天建立和諧關(guān)系,能否通過明晰的認(rèn)識和實(shí)現(xiàn)生命的實(shí)質(zhì)來與天溝通。洞察敏銳,行動恰到好處,我們由此可以明白誠在李栗谷思想中認(rèn)識論的一面:“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我們的快樂不僅因?yàn)槔斫饬擞钪嫔铄涞囊饽睿且驗(yàn)槟軌騾⑴c其中。然而,只有達(dá)到至誠才能做到這一點(diǎn)。這就是為什么在修身方面,《中庸》把誠意看得如此之重。這是實(shí)現(xiàn)認(rèn)識和完成行動的關(guān)鍵:“如志無誠則不立,理無誠則不格,氣質(zhì)無誠則不能變化。”
三 命運(yùn)在東、西方的交匯:幾點(diǎn)看法
人類的命運(yùn)是一個(gè)普遍的問題。遠(yuǎn)東文化對天人關(guān)系的看法和基督教智者的觀點(diǎn)并非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嘗試就這一點(diǎn)談?wù)剮讉€(gè)看法。目的并不是簡單的比較或比附,而是在兩種探索和表達(dá)方式間找到共鳴。
在研究西方形上學(xué)時(shí),利科從上帝與人的關(guān)系出發(fā)研究意志問題。上帝既藏又顯,既遙不可及又親近如朋友。上帝引起自我的死亡,又培育著意志。我通過詩的靈感這樣的幻想,通過神賜的緩慢成熟,通過相遇尤其是友誼,獲取生命。在關(guān)于人類意志的作用方面,利科想要揭示的是,“生命是神恩和努力的統(tǒng)一體。既要接受給予的一切,同時(shí)又要嚴(yán)格控制自己。”他這樣說:“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選擇。”
利科認(rèn)為,上帝與人的關(guān)系沒有清楚的邏輯,我們只能承認(rèn)自由和恩典之間的矛盾。人在自身的選擇中發(fā)現(xiàn)上帝的威力。“人的自由與上帝的無所不能相通,但我們不能達(dá)到其中任何一種境界。”選擇的奧秘只能從行動的層次上來理解。
這里提到了“神恩”這個(gè)經(jīng)常讓人反感的詞。然而,“神恩”可以是理解命運(yùn)的關(guān)鍵之一,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ll)這樣受過希臘精密思想訓(xùn)練的哲學(xué)家也使用這個(gè)概念。“靈魂的一切自然的運(yùn)動受物質(zhì)萬有引力一類的規(guī)則制約,惟有神恩例外。……兩種力量主宰著宇宙:光和重力。……創(chuàng)世是重力的下降動作所為,是神恩的上升動作和第二品級天使神恩的下降動作所為。神恩,這是下降動作的法則。”
居斯塔夫·蒂蓬(Gustave Thibon)使我們認(rèn)識到薇依關(guān)于神恩的見解的高深:“一種規(guī)則只能以無限小的形式融入比它小的規(guī)則中去。”這一觀點(diǎn)補(bǔ)充并深化了帕斯卡三種品類不同秩序的理論。神恩好比面團(tuán)中的酵母。“神恩不能改變主導(dǎo)這個(gè)世界的必然與偶然之間的盲目游戲,就如滲入的水滴不能改變地質(zhì)層的結(jié)構(gòu),滲入靈魂的神恩也是如此,它在靜默中期待我們接受恢復(fù)神性。”
在薇依筆下,上帝是最脆弱最樸實(shí)的。我們掏空自我,接近上帝。神恩需要空間才能進(jìn)入我們,意志付出的努力不過是迎接神恩的條件,就如播種前要翻地一樣。我們必須順從神恩,善才能迸發(fā)出來。這一切都伴隨著凈化與痛苦。薇依認(rèn)為,我們不理解神恩,是因?yàn)槲覀儾辉敢馊淌芡纯啵辉胳`魂受到傷害。反之,如果我們接受現(xiàn)實(shí)在我們身上啃嚙出空隙,我們就能接待神恩。
在這一視角下,意志的工作為生命更高級、更真實(shí)的層次作準(zhǔn)備。神恩在這層次上發(fā)揮作用,也就是說上帝與人、天與人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共同行動。當(dāng)我們意識到,我們想要的對我們自己和他人并不總是最好的時(shí)候,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也是修女特蕾莎的邏輯。中國法學(xué)家和思想家吳經(jīng)熊就毫不猶豫地把老子和特蕾莎作比較。特蕾莎把小途徑和與大行為結(jié)合起來。在最艱難考驗(yàn)中,完全聽天由命,達(dá)到“一切皆神恩”的境界。貝納諾(Bernanos)在其作品中也表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特蕾莎的選擇,在放棄個(gè)人意志以成全上帝意志的同時(shí),表現(xiàn)出了最強(qiáng)烈的意志。
我們也許會認(rèn)為,儒學(xué)的方法和基督教的角度十分不同,一個(gè)建立在人的能力的基礎(chǔ)上,另一個(gè)則以天啟為基礎(chǔ)。然而,在這個(gè)復(fù)雜世界中摸索前進(jìn)時(shí),儒家和基督教的重要人物都表現(xiàn)出了一種相似的謙卑順從態(tài)度。并不存在接近天或上帝的捷徑。薇依說:“上帝只有隱形才能創(chuàng)造,否則就只有他自己。”帕斯卡說:“上帝是多么希望隱藏他自己!”而《易經(jīng)》則認(rèn)為道既藏又顯。此,天對孔子和李栗谷而言,和帕斯卡的上帝一樣隱秘。一般認(rèn)為,儒學(xué)一方面重視人的意志,一方面卻又對天意表現(xiàn)出某種宿命論。然而,正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對道和天的順從并不意味著盲目服從,而是從內(nèi)心接受一種對現(xiàn)實(shí)和人類局限性的深刻理解,否則我們怎么能達(dá)到樂天和知天命的境界?
基督教作家所稱的神恩說明,他們發(fā)現(xiàn),人在自己身上遇到比他自己更深切更親密的存在,它尊重人的意志,照耀它并給予它力量。盡管條件艱辛,人有力量開辟一條道路。他知道,這不只是他個(gè)人的力量。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一觀點(diǎn)與孔子和孟子所說的差別并不大,雖然天人關(guān)系并沒有像基督教中那樣明確地表達(dá)出來。
四 結(jié)論
韓國理學(xué)家李栗谷值得重視,因?yàn)樗粌H繼承了中國經(jīng)典的根本,而且在建立韓國理學(xué)上,比他的前輩李退溪表現(xiàn)出了更大的創(chuàng)造性。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做進(jìn)一步研究。
本文旨在從天人關(guān)系的角度介紹李栗谷對人類命運(yùn)問題的探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李栗谷以圣人與天的經(jīng)歷為基礎(chǔ),苦苦思索,力圖把傳統(tǒng)的重要經(jīng)典聯(lián)成一個(gè)整體。非常重要的《遠(yuǎn)東智慧詩選》就顯示了這一點(diǎn)。
李栗谷的研究不僅充滿了對他引用的道統(tǒng)的敬仰,而且在關(guān)于思想進(jìn)步和解決當(dāng)時(shí)社會問題的個(gè)人思考上表現(xiàn)出了很大的勇氣,這就是他的觀點(diǎn)的價(jià)值所在。和孔子一樣,他并不是僅僅介紹想法,或熱衷于升官晉職,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改變世界、實(shí)現(xiàn)誠的事業(yè)中去。李栗谷在其思想最重要的地方明確地談到了天,表現(xiàn)出了特殊的價(jià)值。
然而,伴隨著現(xiàn)代化,人類命運(yùn)與天的關(guān)系很大程度上變得難以理解。在李栗谷和孔子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與天、人的密切關(guān)系,它開啟了對天意和人類命運(yùn)神秘的探索之路的思索。“夫子之道始于天。”“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自然之應(yīng)而天與人交與之妙也。”“皇天無親。”
李栗谷對孔子思想進(jìn)行了深入思考:“天知我。”“五十而知天命”表現(xiàn)出了一種與天的密切關(guān)系。人都渴望能夠抓住其命運(yùn)的關(guān)鍵。李栗谷不到50歲就力圖洞察自己和國家的命運(yùn)。“知天之未始不為人,知人之未始不為天,在始可謂知命矣。”“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在。”“天地必待圣人。然后乃以是數(shù)示之人。”“大哉《易》也,以之順性命之理。”
但天意仍然難以察覺,因?yàn)樨?fù)面的力量干擾著我們。在認(rèn)識和行動上,盲目和誤導(dǎo)妨礙人的努力,或把它引向錯(cuò)誤。李栗谷對此十分敏感。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都與這些負(fù)面理論做過斗爭。
為了理解局勢和意志的驅(qū)動力量,必須調(diào)動一切可能,力求達(dá)到最深層次。李栗谷用實(shí)心與天的實(shí)理配合達(dá)到真正的實(shí)現(xiàn)來表達(dá)這一觀點(diǎn)。李栗谷的方法是盡自己所能,天又在此基礎(chǔ)上與人共同行動。
在《易經(jīng)》中,圣人從現(xiàn)實(shí)的混沌中挖掘出實(shí)理,解開縱橫交錯(cuò)的復(fù)雜性,所以君子以圣人為榜樣,與天結(jié)交,了解天意。圣人與基督教的圣徒一樣,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
熱門標(biāo)簽
古代建筑論文 古代文學(xué)論文 古代科學(xué)技術(shù) 古代數(shù)學(xué) 古代科技 古代世界史 古代法律文化 古代法律 古代敘事文學(xué) 古代美學(xué)思想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