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模式下法律制度探索
時間:2022-09-28 03:59:50
導語:德治模式下法律制度探索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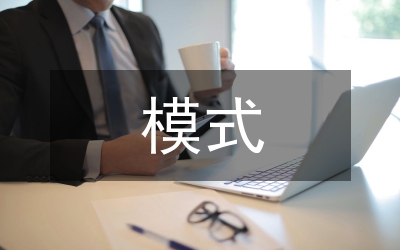
本文作者:司漢武賈莉工作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一、中國傳統德治模式形成的人性假設
制度是在社會或群體生活中逐漸形成的,調節、規范其中各行為主體之間互動關系和互動行為的社會規則或規范。作為廣義的組織或群體行為規則,從人結成社會的那一刻起,制度就與社會、與人如影隨形地共存著。[1]傳統社會的道德、風俗習慣和禮儀,現代社會的法律制度、組織章程和紀律,不過是制度不同形態或同一形態不同演化階段的表現。對于共同組織和社會,制度確保其秩序穩定和整體目標之實現;對于個體或個人,制度則提供在不違背共同利益和集體目標前提下個人行動的領域、限度和方式。制度雖然是群體行為與活動的結果,但卻不純粹是自發的東西,制度尤其是組織制度總有人為設計的痕跡。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設建立的制度往往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社會治理效果。西方的理性人假設把每個人都看作理性的個體,他們精于判斷和計算,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使人們有利于理解經濟規律,設計出符合理性人的經濟制度;社會人假設認為人是社會存在,具有社會性的需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組織的歸屬感比經濟報酬更能激勵人的行為,從而為管理實踐開辟了新的方向。道德人假設認為人們在追求物質需要的同時,也能夠承擔對組織的道德義務和責任,并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進行自我治理。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強調每個人都具有向善、成善的能力,并能接受道德教化的塑造。受這種道德人假設的影響,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德治思想。這種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兩個基本環節,一是人皆可為堯舜,被統治者具有向善的能力和欲望,可以實現自我管理。二是治國者的道德素質成為德治的關鍵,關系到治國的興衰成敗,這個關鍵環節又可概括為賢者治國。何為賢者,司馬光認為“德行高人謂之賢”,朱熹認為“賢,有德者”,所以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特別注重君臣的自身道德修養。在具體的治國方略上,強調一定要處理好君臣民的關系,君是通過臣來實施對民治理的,而民又為國之根基,民心向背關系到政權穩固和長治久安,所以歷代思想家和統治者都主張以民為本,形成民本文化的德治核心內容。
二、德治模式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建構的影響
(一)權力本位
盧梭認為,人生來自由,具有自然權利,處于沒有國家或政府的自然狀態。為了解決自然狀態的困難和不方便,人們通過協商,形成共識,達成默契:每個人都讓渡一部分自然權利,把大家讓渡的這部分權利交給一個后來稱之為國家或政府的組織,交給政府的權利就成為權力。[2]因此,權力來源于人民;政府權力的正當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認同及人民主權的賦予。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的,政府是社會制度和法律規范義務的主要承擔者。正如迪爾凱姆認為的那樣,傳統社會是機械團結的社會,集體意識是傳統社會實現整合的精神基礎。在機械團結社會,集體意識籠罩了全部個人意識,駕馭著大部分個人,左右他們的日常生活,表現出強大的社會強制力。古代的中國社會就是統治者通過強化民眾的集體意識,愚化、奴化民眾社會心理實現其統治的。這個社會沒有法律或統治者的權力不受約束,只尊重神圣的傳統習慣;統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主子”,其行政班子成員不是“官員”,而是“仆從”,決定行政班子與主子關系的不是事務上的職務職責,而是仆從的忠誠;服從是建立在對主子的忠誠上,而不是建立在法規上。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對統治者來說不僅缺乏約束,而且賦予統治者個人充分的獨斷自由。因此,統治者的權力在實際運作中無限膨脹,從而使他的臣民對他的服從失去了具體的限度,造成官員越權瀆職、貪污腐敗泛濫成災。
(二)理性缺失
中國傳統德治模式強調從當權者自身的德性修養出發實現德治,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充分保障并實現統治者的權力,領導者的言行是作為社會的準則和行為規范仿效的,從來都沒有被統治者的權利。即使他們勉強承認作為被統治者的百姓有自由,那也是在無知基礎上的自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明顯的例證,它與道家所強調的“不以明民,而將愚之”殊途同歸。既然是愚民,自然也就不會以智慧解決問題,實現民主和自治,只有靠當權者用高尚的道德來役使。這樣,在傳統德治思想影響下產生的社會管理和治理方式,就是完全依靠對某些魅力型人物的極端迷信而維持的。統治者周圍有一大群支持者和擁躉,他們聽從長官的命令和指揮,國家的權力至高無上。這樣的管理模式上行下效,官員做出的決定和決策完全依據以往的經驗,缺乏必要的監督和保障機制。被統治者只能被動地接受和完成,他們沒有表達的渠道,也沒有表達的權利,民眾的行為一旦違反領導者的意志,既要受道德輿論的譴責,也要受國家權力的強制懲罰。與之相反,官員的地位和權威不容置疑。在這樣的體制和制度下,既無成型的權力約束機制和制度,即使有制度,官員的行政行為往往跨越權限、超越程序,而不必承擔必要的責任。對權力的枉縱和寬容,則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差序制度加以論證。在中國存在和沿襲了逾2000年的封建等級制度就是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建立和形成的。這種制度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卻缺乏必要的彈性,一旦朝廷和政府的越權行為超越了民眾的容忍限度,就必然導致制度衰亡和天下大亂,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法律制度的人格化甚至人情化傳統德治模式不能把對社會的有效治理與人們的基本社會權利保障相聯系,卻與對英雄和偉人的道德水平相對應,從而造就了制度面前的雙重標準:即“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制度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管理的人格化、人情化,而非制度化和理性化,維護社會的制度力量相對松散,沒有強制性的法律做后盾。形成的是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差序格局下的禮俗社會,是一種包含著不民主的橫暴權力結構。這種治理模式在中國傳統社會盛行的結果就是沒有規矩、腐敗橫行,造成丑惡現象的大肆泛濫,最終對社會秩序和制度造成致命的沖擊,同時也沖擊政權的合法性。迪爾凱姆認為有機團結社會的客觀標志是復原性法律。這種法律其目的不是立足于懲罰,也不是強烈的集體意識的表現,其功能是把分化的個人組織起來,促進社會和諧運行,維護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3](P234)儒家的傳統德治模式對管理者或統治者的理想化期待,使中國社會在民主化、法制化進程中大量殘留著機械團結的人治社會的痕跡。
(二)法律工具主義和對程序正義的忽視法律要被信仰,必須以正義為先。天理、王法觀念構成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其邏輯前提是王權不容置疑地合乎道義,統治階級是先天正義的。這不僅是法律工具主義的道德前提,而且同時也是以性本善為基礎的道德中心主義的邏輯結論。這種意識體現在中國傳統法律制度中,就是表現為公民權利的缺乏和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受儒學倫理和封建集權政治的影響,在傳統中國,國家權力始終處于強勢的支配地位。在公民與國家關系、權力與責任關系中形成了不對等關系,這些不對等關系意識最終都可歸結為權力中心或官本位。表現在法律制度中,便是國家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不僅忽視而且排斥對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保護。[4]
(三)法治的表面化和口號化中國傳統社會依靠對某些有威望的卡里斯馬型人物的過度信任造就了泛道德化的社會土壤,通過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形成了固有的統治模式,國家與公民之間缺乏溝通的社會渠道,社會民眾既是順民也是愚民,除了安于現狀服從國家統治之外,基本沒有健全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也缺乏必要的社會知識和理性的法律精神,而在權力階層的意識中,則充斥著法律工具主義、政治實用主義和法治表面化傾向。受這種思想影響,至今仍有一些官員表現出明顯的官本位意識;大量社會民眾仍然缺乏制約權力和維護自身權利的信念,導致法治秩序難以化為中國的社會現實,甚至出現依法治國中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和治民不治官的“三治三不治”現象。
- 上一篇:工商局發展提升督查方案
- 下一篇:中國地役權法律機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