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利益: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時間:2022-06-12 09:41:00
導語:機會利益:一個新的理論視角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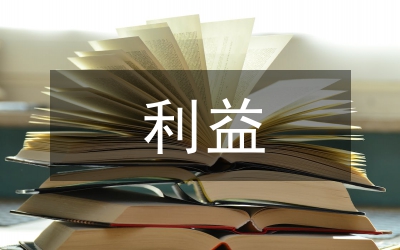
不對稱信息是現實經濟活動的基本特征,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獲取相對信息優勢的競爭。為了對以不對稱信息現象為基本特征的現實經濟活動進行深入分析,筆者把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利用相對信息優勢所提供的機會而獲得的經濟凈收益叫做機會利益。筆者認為機會利益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現實基礎,堅信機會利益理論能夠為現實經濟活動提供一種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思路。本文試圖從前提、性質、淵源、特征、影響和激勵約束機制等角度,為機會利益理論提供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
一、機會利益的前提與性質
在現實中,各經濟主體在社會分工、歷史背景、文化素質、通訊條件等方面必然存在著一定差異,因此他們收集、處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也就必然不同,彼此之間必然存在不對稱的信息分布。在不對稱信息的條件下,那些具有相對信息優勢的經濟主體,就可能作出更加準確的決策、獲得更大的利益。如果說人類在幾個世紀以前主要依靠勞動和土地來獲取經濟利益,在工業革命后主要依靠資本來獲取經濟利益,那么在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就必須主要依靠信息優勢來獲取經濟利益。在現代經濟中,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獲取相對信息優勢的競爭,這就必然會驅使各個市場主體去搜尋信息、創造信息優勢并利用信息優勢來獲取機會利益。由于各個經濟主體可得到的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不同、在交易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各個經濟主體往往能夠在不同的方面創造相對信息優勢、獲得機會利益。可見,不對稱信息是機會利益存在的基本前提。
信息優勢者之所以能夠獲得機會利益,是因為信息是有經濟價值的,信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主體對決策環境的無知程度,能夠消除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因不確定性所導致的風險成本,增加決策主體的收益。正因為信息具有經濟價值,市場主體才有動力收集市場信息,直至搜尋信息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但是,信息優勢者可獲得的機會利益與掌握同一信息的市場主體數量成反比。也就是說,掌握同一信息的市場主體的數量越多,信息優勢者可獲得的機會利益就越低;反之,則反是。當所有市場主體都獲得了某條信息從而該信息成為市場的共同信息時,則市場主體處于對稱信息狀態,沒有任何市場主體在該條信息上占據優勢,從而也就不可能由此獲得機會利益。
經濟主體要獲取機會利益,首先必須創造相對于他人的信息優勢,其次必須能夠及時地準確地利用信息優勢所帶來的經濟機會。
機會利益概念是中性的,它既可能是損人利己的結果、也可能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結果。威廉姆森曾把機會主義定義為“經濟活動人會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他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他會有目的地、有策略地利用信息(包括有時說謊、隱瞞、欺騙)。”(注: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講座專輯》,見《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87年第50期,第15頁。)的確,人類在某些場合會不擇手段地利用各種機會來獲取經濟利益。但是,人類所選擇的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并不一定都是卑劣的、損人利己的。比如,經濟主體通過技術革新與發明等方式而擁有有關新產品、新技術、新材料、新市場等方面的信息優勢且及時地利用這種信息優勢而獲得經濟利益,不但沒有損害他人利益,反而給社會帶來了好處。機會利益的本質是,不失時機地發現機會、并不擇手段地利用機會來獲取利益。因此,機會利益的性質如何,取決于經濟主體發現了什么機會、怎么樣來利用機會。
機會利益根源于人類的經濟活動。人類獲取經濟利益既可以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入手,通過提高征服自然與改造自然的能力、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實現;也可以通過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來實現。人們最終會采取何種方式來獲取機會利益,取決于他們擁有的相對信息優勢的類型,取決于在特定的情景中何種方式能夠給他們帶來最大的綜合利益和機會利益。如果機會利益僅僅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那便是一種零和博弈或負常和博弈,是利益再分配的結果。我們把這種來源于利益再分配的機會利益,叫做分配性機會利益。如果機會利益同時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配置關系,那就可能是一種變和博弈,其綜合影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互作用的人們的對策。我們把那種伴隨著社會財富增加而獲得的機會利益,叫做生產性機會利益。
機會利益不同于信息的經濟價值。信息的經濟價值是指在其它經濟主體的行為不變的情況下某經濟主體獲得信息后按該信息采取最優行為時所得到的經濟利益與獲得該信息前采取最優行為時得到的經濟利益之差。機會利益和信息的經濟價值兩者的關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兩者的實體都是追加信息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增量,即知識差帶來的預期收益增量。但是,信息的經濟價值,是同一個經濟主體在不同的時點上擁有不同的信息量,從而產生知識差所導致的預期收益增量;而機會利益是不同經濟主體在同一時點上擁有不同的信息量,從而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主體之間產生知識差所導致的預期收益增量。第二,信息的經濟價值僅取決于經濟主體自身的主觀評價,機會利益則不僅取決于經濟主體自身的評價,還取決于相互影響的其它經濟主體的決策。只有當競爭者B的信息量沒有任何變化時,A獲得的信息的經濟價值才可能與給它帶來的機會利益相等。A如果不能及時地利用相對信息優勢,它獲得的機會利益也就可能小于信息的經濟價值。第三,信息優勢轉化為機會利益還需要其它生產要素的配合使用,需要有利用相對信息優勢的能力。比如,甲先生事先獲知近期中央銀行將調低存貸款利率,而且甲先生正確地預期到近期債券和股票價格必然要上漲。但是,甲先生沒有資本能夠投資于債市和股市,他就只能望洋興嘆、坐失良機。
機會利益也不同于機會成本。機會利益是相對于其它經濟主體而言的,而機會成本是相對于自己的不同投資機會而言的。機會成本是資源所有者把資源用于某種投資機會的潛在成本。當某經濟主體獲得機會利益時,它可能本來面臨著更好的獲利機會,但由于“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因而它獲得的機會利益就小于機會成本。相反,假定某經濟主體處于信息劣勢且在一段時期內無法改善處境,但如果其現在的投資已經最大化了它的投資機會,那么該經濟主體的凈收益總額仍將大于機會成本。
二、機會利益的理論淵源
盡管機會利益一詞鮮為人用,但是有關機會利益的一些理論思想則早已出現。馬克思、熊彼特和奈特,是機會利益理論的先驅。
馬克思盡管沒有使用過機會利益的概念,但曾精彩地分析過在信用領域投機者是如何利用信息優勢來獲取機會利益的。馬克思指出:“用未售的商品作擔保得到貸款越是容易,這樣的貸款就越是增加,僅僅為了獲得貸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遠方市場去的嘗試,也就越是增加。”(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8頁。)也就是說,在職能資本家能夠運用未出售的商品作為擔保來獲得貸款時,職能資本家就會有很強的動力獲取貸款從事高風險事業,而且越是產品滯銷、資金緊缺、資信程度差的企業,越是有動力用這種方式來融資。因為在實行有限責任制的情況下,企業冒險失敗的損失(破產)是有限的,而冒險成功的收益是巨大的,從而增加了職能資本家利用信用擴張來獲取機會利益的動力。
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企業家創新模型,指出為了獲取可能帶來的超額利潤,企業家不斷地冒險進行創新活動,尋求相對的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
弗蘭克·奈特在其1921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認為,企業總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從事經營活動,而信息或知識可以降低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因而信息是具有經濟價值的。而且,市場競爭愈激烈、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愈大,企業就愈有動力去收集和生產更多的信息,以求保持競爭優勢。
阿羅、喬治·J·施蒂格勒、格羅斯曼和施蒂格利茲等對機會利益理論的形成作出過重要貢獻。阿羅(1973年)暗示了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取得相對信息優勢可以獲得某種利益、該利益具有不確定性、并且可能是生產性的也可能是分配性的等重要思想。喬治·J·施蒂格勒(1964年)論述了廠商怎樣為長期利益而合作、又怎樣利用信息優勢來獲取短期利益。格羅斯曼和施蒂格利茲(1980年)認為,在市場不穩定的條件下,信息優勢者將比信息劣勢者占有更大的市場優勢,但信息優勢者所掌握的信息的經濟價值,與掌握同樣信息的市場參與者人數成反比。這也就是說,機會利益的大小取決于相對信息優勢的程度,而且機會利益與信息的公開程度成反比。
雖然“機會利益”一詞是筆者首次使用的,但是肯尼思·阿羅在1971年首先使用了與機會利益相似的“odds”一詞。阿羅寫道:“下面我們將假定唯一可采用的行動是對自然狀態的發生打賭。……設X[,i]為自然i發生時打賭的機會收益(odds),這就是說,如果狀態i發生,對狀態i打賭的個人每美元的收益為X[,i],否則,收益為零”(注:肯尼思·阿羅:《信息經濟學》,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odds”原意是指打賭獲勝后的收入,譯者劉永強將其譯成“機會收益”也是很恰當的,但其內含與機會利益概念不盡相同。相同之處是均指在不確定性情況下根據自己的信息優勢作出正確決策所獲得的利益;不同之處是機會利益多數場合是一種變和利益,即相互作用的雙方所獲得的利益總和隨雙方的決策不同而不同;而“odds”是零和的或常和的,即打賭雙方的總收益是給定的,雙方利益是互相沖突的。法勃利索·馬丁西尼(FabrizoMattensini,1993)運用了“opportunityreturn”即機會收益一詞,意指在有風險的投資項目中可獲得的凈收益。其含義盡管與我們的機會利益(opportunityinterest)概念已比較接近,但仍比機會利益相對要寬泛一些,后者主要指因擁有信息優勢而獲得的收益。opportunityreturn與odds更類似,多指在風險投資中賭對了而獲得的收益。
三、機會利益的特征與影響
機會利益具有三個基本特征:
第一,機會利益具有不確定性。獲取機會利益的不確定性,首先導源于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決策環境的不確定性,又可區分為客觀不確定性和主觀不確定性。客觀不確定性是因為影響經濟決策后果的許多客觀因素均不是個人能夠把握的;主觀不確定性是決策過程中因個人因素所導致的,這種不確定性導源于個人預測與客觀存在的差異。機會利益是獲取信息后與獲取信息前的綜合利益之差,而獲得信息前后的預期利益的計算取決于對某些狀態出現的概率判斷。這樣,現實中客觀概率與主觀概率的差異,使得以客觀概率計算的機會利益就不一定與以主觀概率計算的機會利益相等,導致機會利益的實現存在著不確定性。其次,導源于相關經濟主體行為的不確定性。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經濟主體并不一定知道對方擁有的信息量以及可能會采取什么對策。于是,獲取了某種追加信息的經濟主體,也許知道自己擁有相對信息優勢,但不知道相對優勢到底有多大,由此造成獲取機會利益的行為具有不確定性。比如,某企業通過技術創新而擁有某種生產性信息優勢,但該信息優勢到底能帶來多大的機會利益存在著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來自于企業自身的生產能力和保密工作,也來自于競爭者能在多快的時間內通過“反向工程”破譯該技術,從而生產出類似的產品。
第二,機會利益具有時效性。信息具有較強的傳播性和擴散性。大多數私人信息在一定時期后要成為公共信息。私人信息一旦被相關的經濟主體獲知,在其它條件不變時,原來的不對稱信息狀態就會轉變為對稱信息狀態,原來的信息優勢者就會失去信息優勢,從而無力獲取機會利益。可見,機會利益的獲取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機會利益永遠屬于善于捕捉機會的經濟主體。
第三,機會利益具有主觀性。首先,在信息的獲得、處理、評價、利用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主觀性。任何事物在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總是會發送出一些信號或信息,這些客觀存在的信號與事物的本質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接收到這些信息的經濟主體,通常會根據自己的特定目的和實際能力來處理、加工、評估、利用所得到的客觀信息,以求排除經營環境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每個特定的決策環境中,經濟主體能否從混沌一片中整理出一系列備選的決策方案、并準確地預測每個方案可能產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主體的技能、價值觀、對決策目標的了解程度、所具備的相關背景知識、所收集資料的完備程度等因素。其中,決策者是否具有“破譯”客觀信息的能力起決定性作用。實際上,不同經濟主體“破譯”客觀信息的能力存在很大差異。經濟主體“破譯”客觀信息的能力越強,越能去偽存真,在給定的客觀信息中獲得盡可能大的主觀信息。相反,“破譯”客觀信息的能力越差,越有可能熟視無睹、“有眼不識泰山”,忽視了零亂分布的、被掩蓋的重要信息。比如,面對相同的宏觀形勢、市場環境、科技創新新動向,不同的經濟主體會看出不同的“苗頭”,獲得不同的主觀信息。那些信息處理能力比較強的經濟主體,就可以獲得不同程度的信息優勢,相應地贏得機會利益;相反,那些信息處理能力較差的經濟主體,則可能遭受機會損失。其次,經濟主體能否準確地意識到自己的相對信息優勢、能否對競爭者的可能反應作出準確的預測、是否具有果敢的決策風格,都將影響經濟主體的實際決策,從而影響著他實際上可獲得的機會利益。但上述因素往往因不同經濟主體而異,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于是,擁有同樣信息優勢的不同經濟主體往往會采取不同的使用信息優勢的方式,從而獲得不同的機會利益。
機會利益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主要通過三個機制來實現:
第一,追尋機會利益引起的信息需求的競爭,導致了信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引起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經濟主體為了獲取機會利益而尋求相對信息優勢的競爭,不但導致經濟主體對生產性信息和非生產性信息的巨大需求,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產品花色品種的激增、信息流動速度的加快,使經濟主體對所需求的信息的質量要求和傳遞速度要求也大幅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各經濟主體完全靠自己的信息部門來提供所需要的各種信息已變得低效率也無必要。于是,各經濟主體在把自身精力集中于獲取一些關鍵性信息的同時,把大部分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信息需求轉向市場,從而直接激發了對信息服務業的需求。原先屬于企業內部管理的許多信息工作也逐漸地獨立出來,成為提供信息產品或服務的新型產業。信息服務產業在近二三十年發展很快,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日益深遠。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巨大“魔力”面前,為了獲取機會利益、免遭機會損失,工商企業均不得不相繼接受信息化改造。傳統產業的信息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勞動力結構的智能化,使工業經濟走向信息經濟,廣義信息已成為主要生產要素。
第二,獲取機會利益具有直接的資源配置效應。一方面,獲取機會利益的努力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追求生產性機會利益的努力,促進了技術創新,優化了生產要素組合;節約了企業對能源、原料、人力和資金的使用和消耗,提高了各類商品的智力含量、信息含量;導致了新產品、新材料;新能源層出不窮,提高了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提高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比如,石英原來僅僅是生產玻璃的原料,但技術創新把石英變成了信息裝置(硅片)和能源轉換裝置(阻擋層光電池)。另一方面,獲取機會利益的努力,導致了非生產性地利用信息優勢的增加,部分地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由于非生產性機會利益不是以增加社會財富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是通過變換切蛋糕的方法來增加自己的利益,導致了各經濟主體為了不使自己分到的蛋糕變小而付出種種努力。這種努力的代價是社會財富的凈消耗。
第三,追尋機會利益行為和反機會利益行為導致制度變遷,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當某經濟主體發現某種潛在的經濟利益盡管在現有制度安排下無法獲得、但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可以獲得時,它就會產生改變現有制度安排、把這種信息優勢變為現實的機會利益的動機,從而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追求機會利益的行為,將會導致合法的創新活動和灰色的創新活動。合法創新者在其創新活動過程中可能會發現,對現有制度安排的某些方面進行調整或變革,可以明顯地有利于保護創新者的利益、抑制相關經濟主體的“搭便車”行為。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屬于微觀方面的,那么創新者會率先進行這種制度創新來獲取生產性機會利益;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屬于宏觀方面的,制度創新需要集體行動,那么創新者就會成為制度創新的發動者、主要行動集團的成員。面對灰色創新活動,有些人可能會發現對現有制度安排作某些變革,就可以明顯地約束灰色創新活動。如果這種制度變遷屬于微觀方面的(比如交易制度變革),那么他就會率先進行這種變遷從而減小灰色創新給他造成的機會損失;如果這種制度變遷屬于宏觀方面的,那么他就會成為抑制灰色創新活動的制度變遷的發動者。某種制度創新帶來的預期凈收益越大,對該制度的需求就越強烈。
盡管追尋機會利益導致了制度創新的需求,但是制度變遷的真正發生還需要有制度供給的配合。制度變遷的供給,取決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馬克思認為,當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時,舊制度也不會自動消亡,新制度的供給只能通過暴力革命來取得。如果就宏觀的、根本性的制度變革而言,馬克思的觀點至今仍然正確。奧爾森也曾指出,在和平環境中,隨著歷史的推演,特定利益集團的勢力會越來越大,從而變革舊制度、創立新制度會越來越困難。最終,只能借助外界的強大沖擊力或暴力來進行制度創新。但是,馬克思對漸進的制度變遷過程分析不夠。事實上,在可預見的將來,社會經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同一制度內的體制創新將持續不斷地發生。因此,如果把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理論與新制度學派的制度創新理論結合起來,就可以比較全面地解釋從微觀到宏觀的各種大小的制度變革。
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經濟主體以不同的方式追尋生產性或分配性機會利益,會導致不同性質的制度變遷,從而對資源配置效率產生不同的影響。
四、機會利益的約束與激勵機制
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應當約束分配性機會利益、鼓勵獲取生產性機會利益。
社會經濟活動是在特定法律規章制度的約束下進行的。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人們有可能通過違反這些規章制度來獲取分配性機會利益。我們用下列的違規模型為例來加以分析。假定違規者的違規水平用Q來表示,違規收益用W來表示,違規收益是違規水平Q的增函數,但違規的邊際收益遞減。再假定違規者是風險中立的,因而其效用函數等于收入函數。同時,假定違規行為被查處的概率為P,平均每件違規事件被查處后受到的懲罰用F表示,F稱為懲罰強度;違規者從事違規活動的機會成本為U(Q)。這樣,違規者從事違規活動可獲得的機會利益為:
EW=W(Q)-PFQ-U(Q)(1)
違規者使其機會利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W''''(Q)=PF+U''''(Q)(2)
(2)式表明,違規者將使其違規的邊際收益等于違規的邊際成本;監管部門可以通過變動查處概率P和懲罰強度F來控制違規水平。如果監管部門提高查處概率P與懲罰強度F,就會提高違規行為的邊際成本,從而使有些違規行為變得得不償失,使違規行為減少。反之,則反是。
假定違規事件造成的社會總損失由以下三部分構成:
第一,違規事件造成的社會凈損失D(Q)。D(Q)等于違規造成的社會損失H(Q)與違規者的違規收益W(Q)之差。因W''''''''(Q)<0和H''''''''(Q)>0,故邊際社會凈損失D''''''''(Q)是遞增的。
第二,違規事件的查處成本C。C由違規事件被查處的概率P、違規水平Q和每件違規事件的平均查處成本λ決定,即:C=λPQ,且
附圖{圖}
第三,懲罰違規事件的成本。我們假定懲罰違規事件時社會承擔的懲罰成本(F[,s])是違規者所受的預期懲罰成本(PFQ)的函數。為了方便起見,假定這個函數是線性的,即F[,s]=aPFQ。a為懲罰的社會成本系數。當采用不同的懲罰形式時,a的取值變化很大。
于是,我們可以得到社會總損失函數:
L=H(Q)-W(Q)+λPQ+aPFQ(3)
管理部門使違規的社會總損失最小化的一階條件為:
W''''(Q)=H''''(Q)+λP+aPF(4)
(4)式表明,當監管部門使違規者違規的邊際收益W''''(Q)等于違規的邊際社會成本[H''''(Q)+λP+aPF]時,能使社會總損失最小化,相應的違規水平Q[*]''''是社會最優的。當違規者違規的邊際收益小于違規的邊際社會成本時,監管部門將努力減少違規水平,因為違規造成了社會凈損失。隨著違規水平Q的降低,違規的邊際收益W''''(Q)將上升,因為W''''(Q)是遞減的;Q減少還將使違規的邊際社會損失H''''(Q)降低,因為H''''(Q)是遞增的。因此,Q減少最終將使違規的邊際收益與違規的邊際社會成本趨于一致。反之,則反是。
但是,由(4)式決定的社會最優的違規水平Q[*]'''',并不一定等于由(2)式決定的違規者個人最優的違規水平Q[*]。如果Q[*]>Q[*]'''',就表明社會上的違規水平大于監管部門認可的違規水平,監管部門將通過提高查處概率P或懲罰強度F,提高違規的邊際私人成本和違規的邊際社會成本,從而降低違規者個人最優的違規數量Q[*]和社會最優的違規水平Q[*]''''。由于Q[*]與Q[*]''''的下降速率不可能完全相同,通過適當變動P與F的組合,肯定能夠找到使Q[*]''''=Q[*]的P與F組合,從而使得違規者個人最優的違規水平等于社會最優的違規水平。也就是說,要使個人最優的違規水平Q[*]與社會最優的違規水平Q[*]''''相等,必須同時滿足(2)和(4)式。通過求解(2)、(4)式組成的方程組,可解得最優的違規水平Q[*](Q[*]=Q[*]'''')和最優的PF值(查處概率與懲罰力度的最優組合)。事實上,對于任何社會與個人聯合最優的違規水平Q[*],都存在著最優查處概率P[*]與最優懲罰強度F[*]的許多組合。把P[*]、F[*]、Q[*]代入(1)式,還可求出在社會總損失最小化時違規者獲得的機會利益。
充分理解違規模型,對設計制約分配性機會利益的機制很有啟發意義:
第一,追求機會利益是人類的本性。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果某種行為能夠獲得機會利益,經濟主體就會有相應的行為產生;如果某種行為不能帶來機會利益,人們也不會有此徒勞無益之舉。
第二,通過違規而獲得的分配性機會利益往往具有很大的外部不經濟性,故對違規行為應予以懲罰。違規水平與查處概率P和懲罰強度F成反方向變動。P與F越大,經濟主體違規的邊際成本就越大,違規的機會利益就越低,違規水平就越低。
第三,查處概率和懲罰強度并非越大越好。因為查處和懲罰違規事件是需要成本的。查處的力度越大,付出的查處成本λPQ和懲罰成本aPFQ就越大。當懲罰的力度達到某一臨界值時,繼續查處違規行為所增加的社會成本將大于因減少違規事件所減小的社會邊際損害,從而使查處和懲罰違規行為變得得不償失。因此,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存在一定數量的違規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查處違規行為的平均成本λ和懲罰違規行為的單位成本a,明顯地影響著社會所允許的違規數量。λ或a越大,查處和懲罰違規事件的邊際社會成本就越大,查處和懲罰違規行為所導致的社會總損失減小額就越小,從而社會可容忍的違規數量就越多。反之,則反是。
第五,在不同的情況下,提高P或F對減小違規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當懲罰的社會成本很低時,應盡可能地提高懲罰強度,以更加有效地降低違規數量。當查處成本λ較低時,加大查處概率可以較好地降低違規數量。
類似地,我們可以用創新模型來分析生產性機會利益的獎勵機制。限于篇幅,我們不再推導創新模型。但是,創新模型得出的一些結論仍可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第一,經濟當事人從事創新活動,主要是為了從創新中獲得最大機會利益。如果不能獲得機會利益,人們從事創新活動的動力將明顯不足。第二,創新活動普遍具有很大的外部經濟效應,創新的邊際私人收益往往小于邊際私人成本,因此創新的供給明顯不足,對創新成果應予獎勵。通過提高創新受到保護的概率P與創新的獎勵強度I,可以增加創新者的邊際私人收益,從而增加創新的動力和創新的供給。第三,獎勵創新活動需要付出認證成本和獎勵的社會成本,因此對創新活動的獎勵并非越高越好,存在著最優的獎勵強度與發現概率。獎勵的力度越大,認證成本與獎勵的社會成本就越大。當獎勵力度超過最優的P[*]和I[*]組合時,獎勵創新活動將導致社會總福利下降。第五,創新成果的平均認證成本λ和獎勵創新的社會成本系數a影響著創新的最優規模。λ和a越大,認證和獎勵創新活動的社會成本就越高,創新的最優數量就越低。反之,λ和a越低,認證和獎勵創新的邊際社會成本就越低,創新的社會凈收益就越大。因此,應簡化認證創新的程序、降低其平均成本λ,努力設計出成本更低的獎勵制度。